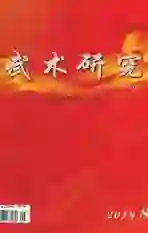竞技武术套路规则发展的研究综述与思考
2018-09-11魏贵男邢萌萌
魏贵男 邢萌萌
摘要:查阅研究竞技武术套路规则相关文章,分析学者研究重点,发现竞技武术规则变化、竞技武术规则与武术套路、运动员、裁判之间关系等研究是学者主要关注方向。而有关规则变化对传统武术项目、武术文化、武术入奥带来的影响则普遍缺乏关注。针对研究现状分析认为,导致研究者研究面狭窄原因包括竞技体育制度不完善和武术研究者缺乏发散性思维。
关键词:竞技武术 套路 规则 体制 文化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839(2018)8—0040—05
1 《规则》的特证
在研究《规则》的文献中,具体可分为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对某一版本《规则》进行具体研究,针对其有待完善的地方,提出可行性建议。另一种是通过比较研究,分析规则的优缺点。本研究搜集的文献以对比研究为主,分为两大种类。年份较早的文献,多是仅对新规则和前一版规则的变动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并提出作者见解,年份较新的文献多会在对之前各版本《规则》做对比之后,探讨新版本的特征并提出建议。
1.1 对具体版本《规则》中评分模式的研究
在对规则做具体研究的文献中,以研究规则的评分模式文献偏多。研究1991版规则的学者,有人认为现有规则评分模式不够合理,对规则整体改善提出如下建议:创建可以提高运动员竞争意识的体制,在现有加分规定的基础上增加创新分,放宽对“限制动作”“自选套路的内容”的限制;采用完整评分方法,统一各项目评分和扣分的标准与分值;改革裁判员、运动员上场执行工作和比赛办法并作为制度纳入规则,提前抽签,保证公平性;健全管理监督机制,明确仲裁的职权范围,设立监督组。[1]也有学者仅针对“难度动作(指定动作)”提出更具体建议:“难度动作及其评分应向艺术体操等难美性项目学习,规定难度动作的加分以及难度的分值,评分标准中错误的类型和扣分可设立一般错误的扣分和专项的扣分,设置起评分和应扣分,并采用基础分的算法。设立控制组并精简裁判人员机构。”[2]持这一看法的文章在本次研究中还有1998年邱丕相的《对武术套路竞赛裁判法可操作性与合理性的探讨》、2000年韩雪教授的《武术与技能类难美性项目竞赛规则的分析比较》、2001在王路遥等人的《竞技武术套路裁判法的优化构想》等文章。研究1996版规则,学者发现新规则对比1991版规则进行了很大完善,但是裁判员执裁时并没有跟规则同步,因缺乏对裁判评分范围具体落实,致使规则在执行中难以操作,给裁判工作带来困难。因此建议“在分块打分的基础上,设立上、下肢裁判组,演练水平评分裁判组以及专门对精神面貌进行评价的裁判各两名一组。”[3]针对分组打分也有学者建议改为演练水平评分和错误动作扣分两部分。[4]经多位学者实验,研究发现“分块打分过程中裁判员为避免出错,打保险分,出现多场均同一分数。”[5]针对规则规定总裁判长、裁判长有权决定运动员最后得分这一情况,温佐惠、关铁云、邱丕相、张选惠等学者认为裁判长对运动员最后得分的调整缺乏说服力。另外,虽然规则对多项内容进行了规定,但仅依靠裁判在几分钟内对每项内容进行判罚,实际操作中缺乏准确性,学者认为部分内容需要进行精简,建议“将指定动作和创新难度统一归为难度动作,并进行如A、B、C、D分级,不统一规定具体的难度动作,提高竞赛的可比性,并设置起评分专家组或裁判组。”[6]建议“指定动作和创新难度统合为难度动作进行评分”的学者有韩雪、李传国、温佐惠等人。鉴于认为竞技武术规则应学习难美性项目,多位学者建议应在规则中放宽对可以强化武术艺术表现性的辅助器具的限制,如服装、音乐等。研究2002版规则,从规则的可操作性角度考虑,有学者建议“采用精细评分法——重新对动作评分进行分类,如A类:手型、手法和各种器械方法;B类:步法、步型和身型、身法;C类:腿法、平衡;D类:跳跃和一般难度动作;E类:演练技巧和编排;F类:指定动作和创新难度动作,每一评分类别中安排两名裁判,并安排裁判长执裁F类,为0.2分。”[7]孙建等人在《武术套路新规则(试行)实施下对裁判员执法水平的评定研究》中认为,新规则虽然裁判员评分的客观性提高了,但仍然不够完善,建议评分过程进一步量化,运用高科技产品提高成绩客观性,并通过建立指标体系对裁判员业务能力进行评定。[8]
1.2 对比研究各版本《规则》
通过对历年版本的研究,来分析竞赛规则的除上述部分文章外,还包括2006年李楠等人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发表的《析武术套路竞赛规则演进的趋势》、2011年方方发表的《武术套路竞赛规则的回眸与思考》以及硕士论文《<武术套路竞赛规则>的变化与发展趋势》《竞技武术规则嬗变》等文章。[9]虽然各学者在文中对规则阶段的划分方法和文章侧重研究的领域不同,但多是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1)难度分类的变化;(2)分值分配的变化(3)评价体系的变化;(4)评判方式的变化以及规则的可操作性、规范性、规则演进趋势等方面进行分析。[9]也可以表述为从动作质量、演练水平、动作难度三个方面的变化进行研究。
2 研究《规则》实施带来的影响
2.1 规则变化对套路武术发展带来的影响
研究者在“规则变化对套路带来影响”这一板块中,多从规则变化对套路风格、技术特点两方面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有多位研究者(如温佐惠、李传国、赵秋菊、陈东等)认为规则对限定动作(难度动作)规定过多,造成难度动作不仅多出现在套路的前半段,且动作连接不连贯,不符合艺术的编排要求;规则缺乏鼓励创新的导向,各代表队对难度动作处理方法相似,比赛套路多有雷同。[10]另一方面,整个套路编排只注重难度动作转体的度数和稳定性,忽视动作质量和演练水平,但难度动作普遍失误率高,使得动作质量下降,影响了套路的观赏性。[11]温博在《从十运会看武术套路竞赛规则的演变对武术技术发展的影响》对比历年规则,认为“裁判分工和评分量化的细化,使得规则的客观性、可操作性提高,技击性的淡化及动作难度增加,使得竞争更激烈。在难度影响得分的情况下,高质量的难度动作仍是主导方向,未来将更加突出技术创新和个人技术风格。”[12]针对竞技武术规则趋同难美性项目,在给武术套路带来更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有学者认为指定动作影响了武术套路节奏;评分的量化使得执裁过程中裁判员将过多注意力放在指定动作的评分中;过分追求“高、难。[13]2011年陈远馨在《新规则引领竞技武术套路发展缺失分析》中通过对1959-至今规则的分析,认为“武术套路发展忽略了“手法、眼法、身法、步法”及“注重内外兼修崇尚武德”等武术本质,导致套路武术成为‘中国式体操。”[14]张茂林等在《武术套路竞赛规则的演变及其对武术发展的影响》中通过对规则的分析,同样认为应增强武术的本质属性。除上述文章外,研究此类话题的文章还包括《2002年武术竞赛规则对竞技武术套路竞赛的导线作用》《试论武术竞赛规则的变化对技术发展的影响》以及《武术套路競赛规则改变对竞技武术发展的影响》等文章。
研究“规则对武术套路发展趋势的影响”这一板块的学者(包括姜泽玉、温博等人)多认为高、难、美、新是未来竞技武术发展的主方向。对比1996版和2002版规则,学者认为“套路武术发展从指定难度动作向开放性难度动作转变,更加注重动作的创新性,在教练员、运动员都把训练重点放在难度动作这一普遍趋势下,动作质量和演练水平在未来武术套路中依然重要。”[15]王继娜在《从规则演变看竞技武术套路技术的发展》中在赞同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套路武术竞赛规则逐渐向国际化、奥运化、代码化发展,“高、难、美、新”是套路技术的发展趋势。”[16]李信厚在《新竞赛规则对现代竞技武术套路运动发展的影响》中分析认为规则对套路发展起指导方向的作用,规则导向下的套路要突出难度、编排简练,注重动作演练的艺术表现力;配合音乐和服饰增强竞技武术套路表演效果。[17]在普遍重视难度动作的情况下,有不少学者认为武术套路的技击性和观赏性同样重要。武术套路将向着动作规格更加严格,编制合理,武术特点突出,技术表现更鲜明,动作难度更大,更具有观赏性方向发展。[18]
2.2 规则变化对运动员带来的影响
学者在研究“规则变化对运动员带来的影响”,多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研究,一方面是规则对运动员身体和竞赛成绩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对运动员、教练员在创编套路提出更高要求。规则对运动员身体带来的影响有:(1)研究规则对运动员受伤率以及最后名次的影响;(2)研究规则对运动运身体素质提出的要求,包括增强一般素质练习和专项素质练习。规则对运动员在套路动作编排上提出如下要求:(1)重视基本功的训练;(2)套路编排要合理,避免难度堆积(3)在重点攻克难度动作的同时,兼顾演练水平和动作质量;(4)增强创新能力,编排适合自身特点的动作。
研究者通过实验发现,“指定动作的设定,不仅加大了运动员的受伤率,同时对指定动作的扣分严重影响到运动员的个人名次。”[19]这样的文章还有《竞技武术套路运动员新老规则前后运动损伤的调查》《新旧规则前后竞技武术套路运动损伤调查研究》等。《对武术套路竞赛中指定动作的扣分與相关因素的研究》《关于武术套路竞赛新规则评分方法的研究》和《九运会武术套路指定动作现状研究》等文章也阐述了指定动作的扣分,与运动员的最后得分相关程度高。陈琳认为“难度动作在比赛中的关键因素,为套路武术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对运动员专项素质要求更高。重视难度忽略基本功,使得各武术队缺乏自己的风格。规则对运动员的心理素质提出更高要求,建议运动员动作安排循序渐进,重视准备工作;重视动作内在意识,使动作具有武术的内在美和形体美。”[20]《武术竞赛套路新旧规则的比较分析及训练对策》中通过对规则的分析,认为新规则要求武术运动员训练时要一般素质和专项素质相结合,在编排套路时充分发挥运动员的个人技术特点。选材时优选外形美、气质佳,柔韧性和协调性好的运动员。训练时设立训练目标,以全运会及全国武术锦标赛为训练重点,抓重点项目,加大创新难度的训练。[21]陈东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教练员运动员在编排套路时,动作结构要完整,布局合理,不能只重视难度动作的创编,要在继承与创新的基础上,突出项目自身的特点,调整难度动作出现的时间。”[22]席饼嗣认为新规则为运动员提供了更大的自主发挥空间,因此,在套路动作编排时要具有多样性和创新性。配乐项目与套路内容要一致,提高艺术表现力,提高动作编排的创新能力,形成独特风格。[23]2003年以后,“普遍重视难度,忽视演练水平和动作质量,造成运动员演练水平分明显下降,使得难度动作已不再是决定成绩和排名的关键因素,而演练水平和动作质量与总分的相关性高。作者认为,难度动作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兼顾演练水平和动作质量很重要。”[24]提出这些观点的文章还有2007年马管管发表的《武术套路竞赛规则变化对武术训练和比赛的影响》、2012年魏垂发表的《武术套路竞赛新规则对武术训练技术发展的影响》以及《竞赛规则视野下竞技武术套路运动员表现力的研究》和《新规则下中国优秀武术套路运动员技术发展的现状分析》等文章。
2.3 规则变化对裁判员执裁的影响
研究“规则对裁判员的影响”的学者主要研究规则变化对裁判工作的客观性、可操作性以及对裁判员自身能力带来的影响。如《从新旧规则比较比较探析武术套路裁判员执裁能力》(1996版和2003版)中认为“精细分工对裁判员业务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客观评分值的增加是对裁判员心理素质的挑战;规则量化有利于裁判员的技术判断;硬性条件对裁判执裁能力起到制约。裁判员需加强业务学习、掌握新规则的评分特点,加强硬件设施。”研究规则对裁判员的影响的文章还有2003年林小美发表的《影响武术套路裁判员执裁能力的因素分析》、2006年孙健等人在《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发表的《武术竞赛新规则(试行)实施下对裁判员执法水平的评定研究》等文章。
2.4 规则与其他
研究规则与其他方面的包括规则与教学、规则与音乐、美学,规则与多媒体和规则对各小项的影响。这些方面的研究文章各仅有三四篇,如2005年刘涛发表的《从新规则的实施谈武术套路教学优化设计》、2006年周丽娟发表的《对新规则下武术套路配乐演练的探究》、2011年韩英甲发表的《武术套路新规则在长拳项目比赛中的实施效果研究》以及郑磊石的硕士论文《新规则下竞技武术套路南拳项目的发展研究》等文章。
3 竞技武术规则特征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竞技武术规则研究具有以下特征:
(1)发表年限在2002年以前的文章,学者在文中提到的关于规则的一些建议,在以后的规则中都有了相应的改进,如建议学习难美性项目设定起评分、对难度进行分类等。
(2)针对《规则》研究,以2002年为分割点,在此之前出版的文章多认为规则对难度动作的加分、扣分项关注过少,套路运动观赏性不强。2002年以后,学者在研究中则更多的认为在鼓励难度创新的基础上,应增加对演练水平和动作质量的重视,在保证观赏性的情况下适当突出武术技击属性。
(3)以研究《规则》为侧重点的文献居多,包括对规则的裁判分组、评分方法的变化研究、规则中难度动作相关事项的研究等。竞技武术规则变化对套路发展的影响也是学者研究的重点。这其中包含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应促进武术向高、难、美、新方向发展。另一部分学者(少数人)认为,过度重视难度,忽略动作质量和演练水平,使得竞技武术的技击本质淡化,成为“中国式体操”。竞技武术规则对运动员、裁判员的影响也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以研究规则变化对运动员(高水平)成绩的影响、规则变化对运动员的一般素质、专项素质及创新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为研究重点。这一部分研究中虽然提及规则变化导致运动员受伤率增加,但几乎忽视规则变化对武术参与人数的影响。
(4)虽然近30年来研究竞技武术规则的文章很多,但是研究方向以及研究内容雷同性很高,即使有一两位学者提出不同见解,也只是将关注点放在如何进一步改善规则,缺乏对武术文化与竞技武术规则之间的关联、竞技武术规则与奥林匹克运动等的研究。包括研究竞技武术规则对传统武术影响的学者也很少,仅有两三篇文章。传统武术是中国武术不可切割的一部分,武術文化一直是武术研究者最关注的话题之一,武术成为奥运会项目也是竞技武术的奋斗目标。但在规则研究中,研究者普遍忽略这些有价值和意义的研究方向,造成研究成果处于一家之言状态。
4 结论与反思
通过对各文献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论的梳理,可以看到,研究者在研究中多将自己置身于社会结构之外,有关政治秩序本身闭口不谈,武术管理制度只是被设定为一套颇为规定、与己无关的框架。要分析造成研究者如此研究趋势的原因,从研究者所处历史结构以及社会结构进行分析必不可少。纵观竞技武术规则发展历史,最早一版的竞技武术规则诞生于“大跃进”和“反右倾”时期,之后的规则也都是在高度集中的体育行政管理体制下形成。实行“举国体制”的目标是为了我国运动员能够在奥运会上为国争光。因此,现代竞技体育从一开始便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其蕴含了更多的国家经济利益和政治价值,这一制度实行最初,因竞技武术不是奥运项目,武术甚至被国家从全运会中摒弃。诞生于这一社会背景下的现代竞技武术规则,其出发点一开始便是发挥武术的政治色彩。当1998年全面提出改革“举国体制”,其他项目纷纷将视野转向市场时,竞技武术依然仅依靠国家行政管理,并未实行简政放权。因这一研究不可避免的涉及到政治问题,从规则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看到,研究中以研究规则对竞技武术发展趋势的良好促进作用为主,即使学者看到规则的不完善,研究也仅集中在竞技武术比赛、训练和选材上,提出的建议也仅试图通过单纯的模仿来迎合奥林匹克运动对规则的要求,以增强套路运动艺术表现性。这一过程研究并不涉及对竞技武术规则本质以及奥林匹克运动本质的研究,更从不触碰有关政治体制管理相关话题。
从上述资料中可看到,一方面,高度的行政管理体制使得研究者不敢发表不同言论,即使一些学者提到有关规则制定对武术产生负面影响的观点也缺乏官方认可,更多的情况是研究者注意到某些负面现象,但缺乏发表言论的渠道。例如,在90年代左右的武术期刊《武林》中,有多位学者呼吁重视传统武术,但因规则涉及政治因素,并未有学者从这一角度提出言论。另一方面,虽然国家鼓励民间武术社团发展,但政策并未体现出对市场作用的认可和信任,使得竞技武术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脱节,武术发展异化。因政策并未谈及传统文化、传统武术,致使规则研究者对这一议题集体忽视。
除研究者将自己置身社会大环境以外,研究者所处的社会立场也影响到研究者的研究视角。从人口结构上看,竞技武术对应的人口并不多,在竞技武术发展高峰期时,全国一线运动员不超过500人,相对于整个武术从业人员来说,这仅占据很少的比例。而这少部分人,却主导了中国武术的发展方向,笔者认为原因与对武术发展起到重要传播作用的规则执行者以及武术教育者自身脱不开关系。在以全运会和奥运会为目标的“举国体制”管理下,中国武术协会在很长时间担任行政主管部门,对武术事项具有独断权。因武术所处的特殊位置,不需要服务于奥运会,国家赋予中国武协在履行保证全运会获得一定数量的金牌外,也需要承担起发展民间武术的责任,但这一部分和“举国体制”发展目的并无关联,即使国家投资了大量财力物力,在声势浩大的武术遗产发掘整理之后,武协依然仅以竞技武术为重点。从竞技武术规则研究现状以及各大院校教学板块中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所占比例可以看到,在全国集中资源于竞技武术时,占据武术发展主流的民间武术处于“真空”状态。制度管理层的态度对教育发展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导致在武术发展的关键时期,以师范类院校和体育专业院校所执行的学院派竞技武术系统中,教育者没能在整个竞技武术发展过程中积极吸纳传统武术的人才进入到竞技武术系统,造成整个武术研究体系仅从竞技武术发展的立场出发,仅针对竞技武术需要来研究制定和修改规则。同时国家体委武术研究体系、体育教育体系中仅针对武术发展中“武”的部分进行大力推广,缺乏对“术”的学习和钻研,进一步导致竞技武术发展与传统武术文化彻底脱节。而这一脱节,造成从规则的制定,到参与者,到最后所展现的效果之间出现彻底隔离。从上述资料看到,规则执行者的行为影响到学院派体系下的教育者,而研究竞技武术规则的学者多处于这一学院教派之下。因此,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势必要服务于科层管理,在价值选择时忽视探讨问题的本质,导致研究结论及研究视角出现高频率雷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武术规则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需立足于自身所处的时代背景,运用比较-历史分析法,结合多学科知识,深入分析所研究议题。在价值选择时直面政治以及道德问题,以分析问题本质为立足点,需要积极发挥市场作用,增加民间武术社团对武术事项的管理权限。鼓励武术专业学者对规则的制定提出不同意见,使武术发展呈现“百花齐放”的姿态,促进武术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各个院校的武术教育者以及竞技武术规则的制定者,在武术发展中应积极吸收民间武术人才,融合传统武术文化,进一步加强武术规则与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研究,促进中国武术早日实现全面国际化、市场化发展。
参考文献:
[1]单锡文.现实武术竞赛规则的若干修改建议[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1995(1):69-71.
[2]张选惠.王静.马艳丽.关于武术套路比赛评分方法的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5(2):20-25.
[3]邱晨.武术套路竞赛规则可操作性的探讨[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1⑶:66-67.
[4]姜娟,关铁云,越秋菊,张秋.竞技武术天路竞赛规则改革的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1⑶:39-40.
[5]关铁云,关博,张绍英.对九运会前后武术套路竞赛规则的改革设想[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2(2):27-30.
[6]温佐惠.对竞技武术套路规则实施效果的探析[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1(1):91-93.
[7]周兰萍.对竞技武术套路评分新模式的研究与探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3⑶
[8]孙建,沈建英.武术套路新规则(试行)实施下对裁判员执法水平的评定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6(13):415-417.
[9]李楠,王明建.析武术套路竞赛规则演进的趋势[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6⑶:82-84.
[10]李传国,王成.关于武术套路技术内容单调、雷同倾向之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1(6):85-88.
[11]温佐惠.竞技武术套路竞赛规则的发展变化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4(1):64-67.
[12]温博.从十运会看武术套路竞赛规则的演变对武术技术发展的影响[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8(5):66-69.
[13]姜娟,关铁云,赵秋菊,张秋·竞技武术天路竞赛规则改革的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1⑶:39-40.
[14]陳远馨.新规则引领竞技武术套路发展缺失分析[J].内江科技,2011(7):154.
[15]史儒林.从规则变化分析竞技武术套路发展趋势[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2).
[16]王继娜.从规则演变看竞技武术套路技术的发展[J].体育科学,2007(4):50-52.
[17]李信厚.新竞赛规则对现代竞技武术套路运动发展的影响[J].体育世界,2008⑴:78-79.
[18]范石汉.戴赤彬.从《武术套路竞赛规则》的变化看武术套路的发展趋势[J].湖北体育科学,2004(1):81-82.
[19]温佐惠.对竞技武术套路规则实施效果的探析[J].成都体育学院.2001(1):91-93.
[20]陈琳.武术套路新规则对经济套路训练的影响[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8):58-61.
[21]聂建国.武术竞赛套路新旧规则的比较分析及训练对策[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2⑵:48-51.
[22]陈东.对武术套路新规则实施后若干问题的思考[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5(8):113-115.
[23]席饼嗣.规则演变对竞技武术套路编排新思路的影响研究[J].搏击,2009(12):43-45.
[24]杨新.2002年武术竞赛规则对竞技武术套路竞赛的导向作用[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5(1):7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