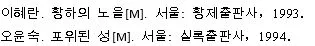《围城》海外旅行70年*
2018-09-10余承法
余承法
(湖南师范大学,长沙 410081)
提 要:基于WorldCat, Google Scholar, Amazon和CiNii等网络资源,通过文献阅读和史料爬梳,回顾《围城》70年的海外旅行旅程,考察9种外文版本的出版发行情况,总结它们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馆藏的规律,探究对多元文化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深刻启迪。这是我们对《围城》中文单行本出版70周年的最好纪念,将对海内外“钱学”研究、文学研究、跨文化研究、版本学研究、出版发行研究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1 引言
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是一部记录人生旅行、描摹人情世态、暗示人生困境、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围城”的小说,其外文译本之多、图书馆收藏数量之众、传播力度之大、影响范围之广、研究成果之多,是中外现当代出版史上浓重墨彩的篇章,在中外文学交流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本文借助WorldCat, Google Scholar, Amazon和CiNii数据库回顾《围城》70年的海外旅行历程,总结它在全球范围内译介、传播和馆藏的一般规律,是对《围城》中文单行本发表70周年的最好纪念,将为海内外“钱学”研究挖掘史料,为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外译提供有益启迪。
2 《围城》的外文译本
《围城》问世之初即受到广泛关注,法国来华传教士秉善仁等人(Schyns et al. 1948:182)在《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中肯定钱钟书创作中的幽默艺术,但站在宗教立场否定小说的价值。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称赞《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趣味横生、最用心经营的一部小说,也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小说”,在中国所有的战时战后小说中“最能捕捉到旅行中的喜剧和苦难”(Hsia 1961:432-460)。这一评介从此揭开《围城》在海外译介和传播的序幕,先后出现英语、俄语、法语、日语、德语、波兰语、捷克语、西班牙语、韩语、越南语和荷兰语等十余个外文译本,经历过多次域外旅行。
2.1 英译本
继夏志清之后,珍妮·凯利(J. Kelly)1974年在香港《译丛》(Renditions)杂志上发表《围城》第一章的英译,美国出现两篇研究《围城》的博士论文:胡定邦(Hu 1977)的《钱钟书三部文学作品的语言学—文学研究》和胡志德(Huters 1977)的《传统的革新:钱钟书与中国现代文学》。1979年,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围城》的第一个外译本FortressBesieged,以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的《围城》版为底本,凯利译出初稿,美国华裔学者茅国权(N.K.Mao)完善,收入美籍华人学者罗郁正、刘绍铭和李欧梵等主编的“中国文学的英译”(ChineseLiteratureinTranslation)丛书。《译者序》指出:虽然钱钟书受到夏志清的高度评价,但“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因此希望《围城》英译本能够引起读者对钱钟书及其作品更大的兴趣(Chi’en 1979:xi)。《译者导言》除简介作者生平和著作外,着重将《围城》作为一个完整艺术品进行讨论,认为这既是一部带有幽默风格的喜剧,又是一部讽刺爱情婚姻、评论和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学者小说,其最高艺术成就是对主人公方鸿渐的成功塑造(同上:xiii-xxix)。
英译本被美国图书协会评为1980-1981年“杰出学术著作”,3年内至少有8篇书评发表于《图书馆杂志》《纽约图书评论》《国家评论》《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观察家》《今日世界文学》《亚洲研究杂志》和《中国文学:散文、论文和书评》等英美主流期刊杂志。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在题为《永恒的玉石》的书评中指出,《围城》“是一部才华横溢、技艺精湛、趣味横生的小说,文笔高雅,结局带有浓浓的悲观色彩”,“富有活力、结构严谨的英译本将会立刻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某些看法”(Spence 1980:20)。胡定邦认为,文学翻译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翻译钱钟书这位文学大师的作品更是如此,《围城》英译本令人肃然起敬,但在文化负载词、句法语义和原著风味等方面存在不足,只有钱钟书本人才能胜任翻译(Hu 1978:427-443)。
1989年,英译本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重印,在中华大地开启“出口转内销”的历程: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被授权出版;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1995年发行该版本的有声图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汉英对照本,增加杨绛撰写的中文前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出版英译本,收录杨绛作、凌原译的《记钱钟书与<围城>》汉英对照本。2004年,美国纽约新方向出版公司推出经杨绛授权、两位译者同意的修订本,收入“新方向经典系列” (Qian 2004)。该修订本除将钱钟书姓名的威妥玛拼音Ch’ien Chung-shu改为汉语拼音Qian Zhongshu外,书中人名、地名的拼写和其他内容都未做变动。史景迁在《前言》中指出,《围城》是一部构思非常奇巧的喜剧性传奇小说,充满创造力、机智和正直,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杰作,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部值得称道的作品”(Spence 2004:vii-x)。英国企鹅出版社2004年再度出版,收入“企鹅现代经典”,旗下的艾伦·莱恩出版社2005年再版,企鹅出版社2006年再次印刷。美国亚马逊官方网站评论《围城》是“中国20世纪最优秀的一部小说,是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是仿拟西方文学传统与哲学、描写民国时期中产阶级的一部杰作”。至少7篇关于该修订本的英文书评发表于《图书馆杂志》《对抗》《观察家》《泰晤士报文学副刊》《金融时报》《纽约图书评论》和《独立报》等期刊上。
2.2 日译本
日本汉学家荒井健1956年开始接触《围城》,多次尝试翻译未果。1975年前后,他听到钱钟书去世的传言,怀着悼念的深情翻译《围城》前四章,连载于飙风杂志(1977-1981年)。他与学生中岛长文(翻译第5至7章)、中岛碧夫妇(翻译第8至9章)合译的結婚狂詩曲(囲城)上、下册由岩波书店1988年出版,列入专收外国文学名著的“岩波文库赤系列”,2002年再版(銭鐘書 1988/2002)。日译本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本为底本,略去“重印前记”,并参考英译本。钱钟书(1981:97-98)应邀作序,回忆他与荒井健的文学因缘,相信原著“会在日语里脱去凡胎、换成仙体”。荒井健在“跋”中写道:该小说在日本最初以“被包围的城堡”为题名出现,日语中找不到“围城”的准确译法,只好选取作品的一个主题——“结婚”,因此将书名改译为“结婚狂诗曲”,并将直译的“围城”附在其后(荒井健 1996:155-159)。荒井健还指出,《围城》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好作品”,针对有人批评书名的改译,他觉得问心无愧,因为钱钟书本人并不在意(同上 1988)。中岛长文以跟钱钟书通信的形式写成《<围城>论》,提出一些不同于我国学者的独到见解,如:“围城”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会注考证》(钱钟书指出)或蔡文姬的《悲愤诗》(这一猜测未得到钱钟书回应);夏目簌石的《我是猫》与《围城》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都市幽默方面;《围城》明显继承西欧小说的血统,在现代中国小说中是罕见的,也表明西欧文学很好地移植到中国文学的土壤(中岛长文 1990:189-209)。《围城》日译本为日本157家图书馆收藏,帮助日本读者意识到现当代中国竟有这样了不起的小说,至少有5篇日语文章研究《围城》。
2.3 俄译本
莫斯科文学出版社在1980年出版前苏联汉学家、翻译家符·索罗金(Владислав Федорович Сорокин)的《围城》俄译本Осажденная Крепость,以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版本为底本,收入“中国文学文库”(Цянь 1980)。前苏联杰出的中国文学翻译家和研究专家艾德林(Лев Залманович Олдрин)在题为《作家和学者钱钟书的〈围城〉》的序中着重分析小说的社会意义,指出该小说吸收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小说的精华。俄译本的内容简介指出,小说以幽默笔法描写1930年代末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前景悲观失望、忧郁苦闷、动摇不定的性格,表现出作者的社会批评精神和人道主义倾向。俄译本首印5万册很快售罄,1989年再版时印刷10万册。符·索罗金(1996:160-177)根据原著修订本作过部分改动,将书名改为Осажденнaя Крепость: рoмaн; расскaзы(Цянь 1989),收入《上帝的梦》《灵感》《纪念》3部短篇小说和杨绛的《干校六记》,用《<围城>俄文版再版前言》取代艾德琳的序言,回顾钱钟书和《围城》相互交织的命运以及中西方对《围城》的主要评价,解释未收录《猫》却收录《干校六记》的原因,提及杨绛的文学创作以及钱钟书的创作、学术和社会活动,最后指出:钱钟书小说创作时间虽然不长,却引起遥远国度读者的极大兴趣,足以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围城》俄译本对苏俄传播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重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力量发行《围城》新版本。
2.4 法译本
巴黎克里斯蒂安·布格瓦出版社1987年出版西尔维·塞尔望-许来伯(Sylvie Servan-Schreiber)和华人记者王鲁(Wang Lou)合译的《围城》法译本LaForteresseAssiégée,收入“东亚丛书系列”,1997年再版(Qian 1987/1997)。跟英译本一样,法译本也是中外译者通力合作的成功范例,但王鲁的名字一度被忽略,连钱钟书在《围城》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一版第四次印刷本的“重印本前记”中也只提到西尔维的名字。法国汉学家毕仰高在序中评价钱钟书是“中国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知名专家”(Bianco 1987/1997:I-VII),分析《围城》的创作艺术和法译本的翻译技巧。美国学者贝缇娜·纳普(Knapp 1988:332)在法译本的书评中指出,“钱钟书不具体描述日本对中国的掠夺与破坏,而是借助人物角色来叙述战事,以一种全新方式来处理战争话题”,华人学者马森认为,《围城》是与传统偏见不同、反映人类厄运的一部长篇小说,法译本难免存在少许瑕疵,但非常忠实原著,“是一部杰出译作”(Ma 1988:305-306),它的出版为钱钟书这位中国重要作家和学者的声誉增添“一顶皇冠”。
2.5 德译本
1978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汉学家会议上,钱钟书流利的英语演讲为德国著名汉学家莫宜佳(Monika Motsch,曾译为莫妮克,莫芝宜佳)打开通向中国文化的大门,成为她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她决心跟德籍华裔学者史仁仲(Jerome Shih)合译《围城》,并跟钱钟书保持书信往来,到北京向他求教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他们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印刷本为底本,将书名改译为DieUmzingelteFestung:EinChinesischerGesellschaftsroman,1988年由法兰克福岛屿出版社出版(Qian 1988),2008年慕尼黑施尔默—格拉夫出版社再版时将书名定为DieUmzingelteFestung:Roman(Qian 2008)。莫宜佳为译本作注并撰写后记,从西方文学传统的角度将《围城》定位为“社会小说”,指出它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中西文学合璧的小说:钱钟书借用法国哲学家蒙田的一句名言,既暗射中国的抗日战争,又讽刺那些自私的人——中国人、西方人以及全人类,因此发现中西文化的不少共同点。钱钟书欣然为德译本撰写前言,称赞她对中国现代文学在德国传播做出突出贡献(钱钟书 1982:108)。《围城》德译本迅速跻身于畅销书之列,曾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获最佳翻译奖,《明镜周刊》《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等主流媒体纷纷发表书评,有人甚至认为钱钟书完全有资格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高度评价到:“就其独一无二的构思和深度而言,《围城》堪称中国现代小说艺术最为讲究的、在此意义上也是无可逾越的标志”(顾彬 2008:209)。 龚刚认为,《围城》德译本“对于德国汉学界及德国文学界重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发挥重要作用”(龚刚 2010)。2016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围城》汉德双语版,中文本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本为底本,德文本即为莫宜佳和史仁仲的译本(钱钟书 2016),这是中国文学作品外译中“出口转内销”的另一成功案例。
2.6 西译本
1992年,巴塞罗那阿纳格拉玛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围城》西班牙语译本Lafortalezaasediada,收入“叙事全景丛书”(Qian 1992)。译者是西班牙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塔西娅娜·菲萨克(Ta-ciana Fisac),1986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访华时,她担任随行翻译,多年从事中国文学、文化和中西关系的教学与研究。据钱钟书透露,该译本“译笔其实寻常,聊胜于无而已”(陆文虎 2007)。西译本于1996、2009和2011年多次印刷,不像英、法、德译本那样有很大影响,西语世界目前分别只有一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研究该译本。
2.7 韩译本

2.8 其他外文译本
3 《围城》外文译本在世界各地图书馆收藏情况的统计与分析
“一个国家、地区的图书馆系统拥有某本书的数量,代表这本书在这个国家、地区影响力的大小,这种影响力包含思想价值、学术水平及作者知名度、出版机构品牌等各种因素的认定。”(何明星 2016)70年间《围城》的不同中文版在世界各地图书馆收藏的数量依次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200家)>书林出版有限公司版本(58家)>华语出版社版本(51家)>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版本(47家)>台湾辅新书局版本(46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本=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版本(33家)>香港基本书局版本(31家)>厦门音像出版社版本(26家)>香港文教社版本(21家)>台湾大地出版社版本(18家)。根据《围城》外译本在世界各地图书馆的收藏情况统计可知:
(1) 按收藏《围城》外译本的图书馆数量依次为:英译本(873家)>日译本(159家)>荷译本(52家)>法译本(49家)>德译本(42家)>越译本(22家)>西译本(18家)>俄译本(2家)>韩译本(0家)。
(2) 美国是《围城》外译本的馆藏大户(636家),通常译本为出版社所在国的图书馆收藏最多,其次是以译语作为(半)官方语言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但俄语、越南语、韩语译本例外,因为WorldCat和CiNii中没有这3个国家图书馆系统的收藏信息。
(3)英译本先后在美国、中国、英国的5家出版社出版过6个版本,被收藏的图书馆数量最多(873家),传播范围最广(包括全球6大洲23个国家和地区),影响力最大,再次印证英语图书的强势地位。“中国文学作品在美国及其他英语国家的英译本也同样在英国传播开来”(王洪涛2016:146-151),《围城》即是典型一例。
(4)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汉英对照本(2003)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英译本(2003)早于纽约新方向出版公司(2004)和企鹅出版集团(2004)的版本,因而在欧美等地也有收藏,属于出口转内销之后的再出口,而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英译本(1989)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同年出版,在北美图书馆几乎没有收藏信息。
4 《围城》“走出去”70年的传播规律和深刻启迪
4.1 《围城》“走出去”70年的传播规律
《围城》堪称“曾经的流行、如今的经典”,它的真正流行始于夏志清的高度评价以及其他美国学者的译介与研究,凯利和茅国权的英译本在中国是一部典型的出口转内销的文学经典。借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传播学奠基人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2003:35-36,65-66)的5W传播模式:who(什么人——传播主体)、says what(说什么——传播客体)、in what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传播渠道)、to whom(对谁说——传播对象)、with what effect(达到什么效果——传播效果),总结出《围城》外译本在海外译介和传播的5个共同规律:
(1) 传播主体:译者无一例外都有译语所在国的学者,或是知名汉学家、“钱学”专家,或是文学家、翻译家,或独译或主译,华人华侨学者参与英、法、德3个译本的合译,体现出外国学者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享有的优势、采取的主动和发挥的主导,表明《围城》是外国人的主动引进而非中国人的主动输出。
(2) 传播客体:所有译本都是全译本,除李惠兰的韩译本转译自英译本、日译本参考英译本之外,其他外译本都直接译自汉语,都有序言或前言,德、日译本邀请钱钟书作序,英译本再版、俄译本初版、法译本由著名汉学家作序,书末附有译者注,英译本再版、德译本、吴允淑韩译本还有译者后记,通过简介作者生平、概述主要内容、评价艺术价值来吸引读者的兴趣,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译本在译语所在国的接受和传播。
(3) 传播渠道:这些外译本或在出版前已有相关评介,或在出版后有书评发表于主流期刊杂志,英语报纸还有对钱钟书和《围城》的相关报道。《围城》被拍成电视剧上映后,美国加州南海有限公司1990年发行家庭影院版,在海外华人界掀起“《围城》热”。除了传统纸版,1979年英译本也有电子版收藏于美国谷歌公司总部和HathiTrust 数字图书馆。
(4) 传播对象:基于WorldCat和CiNii的统计和分析发现,外译本都有再版或多次印刷,韩译本和越译本都有两个,英译本先后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在世界各地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社区图书馆都有收藏,可见读者群体不限于专家学者,也有普通读者。
(5) 传播效果:《围城》的中文本、外译本、相关书评、媒体报道以及相关研究论著助推这部小说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并获得高度评价。英译本的版次、发行量、收藏的图书馆数量、传播力和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版本,中文本(被421家图书馆收藏)以及德、法、西等语种的译本也取得一定传播效果,外译本的海外旅行反过来促成《围城》作为一部文学经典在中华大地的传播。
4.2 《围城》海外旅行70年的深刻启迪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个热议话题是:谁是主译者,是我国译出还是他国译入。结合莫言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刘慈欣科幻小说获得第73届雨果奖的成功案例,《围城》70年的海外旅行给中国文学“走出去”带来5点深刻启迪。
(1)前提:必须首先考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需要,只有明确输入国的现实需要,才能挑选适合外译的中国知名作家的经典作品,厘定相应的翻译原则,培养翻译人才,在输入国寻找合作伙伴,即如梁启超百余年前的呼吁:“择当译之本”“定公译之例”“养能译之才”(梁启超 1984:11)。
(2)出发点:必须以服务于翻译产品的需求方为出发点,考虑译语受众的语言习惯、文化传统、审美情趣和接受心理等因素,并根据译语读者的特定需求决定采取全译还是变译。
(3)保障:(主)译者必须是以译语为母语者,同时精通中国语言文化,或者是长期生活、工作在译语国家的双语双文化的华人华侨学者,中外译者合作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外译的理想译介模式。
(4)核心:译作必须既能传达原作风味,又满足译语受众需求、符合译语的审美接受。“化境”是中国文学作品全译的最高理想和最高标准,变译是解决中国文学作品的语际文化供求矛盾的有效策略。
(5)关键:必须实现中外文学界、翻译界、编辑界、出版发行界、传播界、图书馆界等领域的通力合作,确保作品的“评介——翻译——出版发行——市场策划——媒体宣传——读者反馈”的一条龙传播渠道畅通无阻。唯有如此,中国文学才能被积极“引进去”、主动“走出去”、成功“走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