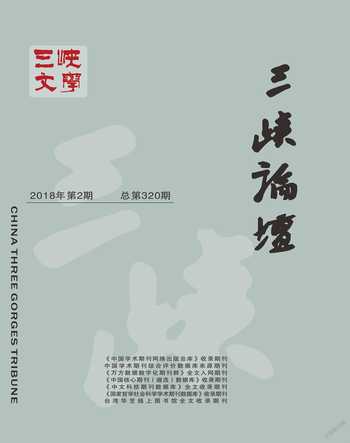论《使女的故事》对《圣经》生存观的思考
2018-09-10钟圆肖四新
钟圆 肖四新
摘 要: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中,以戏仿和重构的方式反对《圣经》生存观的权威设定,以人物的意识流突显《圣经》生存观的隐喻思维,同时还注重阐释《圣经》生存观中本已包含的和谐观念,由此体现了对《圣经》生存观的和谐真义的追求。而这些思考,既体现了《圣经》生存观的内容意义,也彰显了加拿大民族的生存品质,还反映了反乌托邦小说的思想内涵,最终为经典的流传、现代人类的生存提供了有益的向度。
关键词: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生存观;反乌托邦小说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8)02-0091-05
《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1985,其后简称《使女》)因其对基督教的反思和挑战,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个“麻烦”[1]251。小说讲述了一名女性在原教旨主义的统治下被迫沦为名曰“使女”的生育工具,继而如何顽强生存的故事。因此小说引用了大量的《圣经》原文,不仅对它们进行了反讽的处理,也对它们进行了非传统的阐释。
这种反思和挑战实际并不简单。首先是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从小是在加拿大的大自然中长大的,很早便产生了对宗教的思考,发出“天堂既然是好的,为什么杀人却不好”[2]100的疑问。后来这种质疑愈发理性,因为阿特伍德不仅在求学期间旁听过本国学者诺斯罗普·弗莱的圣经课程,而且自己也获得博士学位,具有了专业批判的能力。但最重要的是,阿特伍德始终关注女性、民族和人类的生存问题,以反乌托邦的方式进行思考,而《圣经》对这些内容同样关注,却具有乌托邦的性质。因此,小说对《圣经》生存观的思考也就具有了多重的内涵与意义。
一、反对《圣经》生存观的权威设定
《圣经》可谓权威之书,自《创世纪》开始,《圣经》就在反复强调上帝的权威。可以说犹太民族的世界观与上帝的权威息息相关,他们的人生观也围绕着上帝的权威而展开。
对于一个人来说,“真正的生命就在于与神之间的交通”[3]3:22-24,要想与神“交通”,人就必须努力弥合人与神之间的鸿沟。人能够做到的就是培养对神的“信”,而要有“信”,就必须“顺从”行事。所以《圣经》生存观的第一要义就在于“顺从”,为的是在终极的意义上,人能凭信仰而获得拯救。
但由于人性使然,人很难完全委身信仰,所以人就必须寻找自身世界的生存方式。无论是神学视角下的“与神同工”[3]还是社会学视角下的“劳动是人的基本活动”,都注定让劳动成为生存观中的重要一环。而在《创世记》中,亚当和夏娃被罚劳作和分娩,更是通过上帝的裁判,定下了人类“各司其职”的生存观念。
另外《圣经》还记载了更为具体的生存故事,体现了当人遇到艰难险阻之时,人的生存就与智慧息息相关的道理,比如,亚伯拉罕、雅各等人能三番五次地化险为夷,就离不开他们自身的圆滑和忍耐。而这说明《圣经》的生存观实际上隐含了对人的情智行为的注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情智若表现得太过取巧,也会招来上帝的惩罚。
《使女的故事》就从这三个方面,以戏仿的方式反映了《圣经》生存观的权威设定。小说以美国的生态社会危机为背景,讲述了当时原教旨主义者们企图建立极权统治、以宗教拯救的方式来改善国家状况的故事。他们模仿经典,强调《圣经》权威,认为人们只有信奉《圣经》的价值观念才能生存。然而他们所谓的“顺从”,指的是完全遵守《圣经》的字面义,比如让使女必须依照拉结的“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的话语,躺在主教夫人两膝之间与主教性交,以此来达到生育的目的。而他们虽然规范了“各司其职”的劳动秩序,却是纯粹按“工作”和“生育”来安排人们的生活,以至于男性只有劳动而无娶妻生子的权利,女性则按照有无生育能力进行分配,有的被送到政府高层“大主教”的家里,成为美其名曰“使女”的生育机器,有的则被送往隔离营或俱乐部,成为清扫核垃圾的奴隶或供官员享乐的妓女。最后,他们还表现出了绝情弃智的倾向,竭力把民众调教成顺民愚民,一心毁灭人的智性和尊严。比如,使女们不许再用自己的本名,而要用“奥弗”(OF)和大主教的姓氏衔接组成的新名字,把自己变成大主教的从属物。到这里,小说表达了对《圣经》生存观的权威叙事的担忧,并通过戏仿,做了一次微妙的解构和反抗,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反权威”的特征。
而小说继续通过女主人公奥弗雷德的生存过程,重构出了一系列“反权威”的生存观。在心理活动与现实事件大篇幅交织的叙事中,奥弗雷德可谓采用了类似人格分裂的生存策略。
首先,奥弗雷德向外界展示了“超我”的一面。可以说,她把基列国的社会规范、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加以内化,而不惜自我麻痹,弃绝理性,甘当行尸走肉:“我走到街角等着……恭顺站立等待的人同样也在侍奉上帝。丽迪亚嬷嬷说。她要我们将此铭记在心。她还说,你们并非个个都能善始善终,开花结果……有的人就是根儿浅……我站在街角,权当自己是棵树。”[4]19-20
其次,奥弗雷德又表现出了充分的“自我”意识。这体现在她注重提高自我的情智能力,使得自己在与外界的交往中显得游刃有余。比如,奥弗雷德在闻到出炉面包的香味时,虽然涌起了母性的感觉,但又立即谨慎克制起来:“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味道,必须将其拒之门外”[4]49。而在危险面前,奥弗雷德变得冷静沉着,不仅“装出不以为然的样子”[4]144,还敢揣摩弗雷德大主教的心理:“必定有什么是他有求于我的,有需要便有弱点。”[4]142至于面对前途未卜的命运,奥弗雷德则更是坚强忍耐。她一方面保持着乐观的态度,期待丈夫卢克的到来:“他知道我在这儿……对此,我唯有相信。”[4]109另一方面,她也努力维护心智的健全,尽可能积极地生活:“健全的精神是宝贵的财富;我将它储存起来,就像過去人们储存钱财。”[4]113
最后,奥弗雷德还沉醉于“本我”的冲动欲望之中。她借助大自然的力量滋养自己:“至少一张椅子、一束阳光与几朵花还是有的。我毕竟还活着,存在着,呼吸着。”[4]8她还任由性幻想在饥渴的内心游走:“那古铜色的皮肤,在阳光下润泽发亮……我叹息着深深吸了口气。”[4]19在某些时刻,她甚至使情绪强烈释放:“笑声在我的喉咙口如沸腾的熔岩咕咕作响,我爬进柜子……全身抖动着,上下起伏,像地震来临,又像火山爆发……炸得满橱柜通红一片,欢乐与新生协调同步,哦,笑别人世。”[4]152
到这里《圣经》生存观的传统结构体系已经明显发生了变化。首先,在《圣经》中,“超我”的原则被视作权威,而在《使女》中,这却只是异化人的工具;其次,《圣经》对人的情智能力不以为然,但在《使女》中,情智能力却成了极其重要的生存法则;此外,《圣经》否定本我的欲望冲动,以扫的故事便体现出这一点,而《使女》却突显了人物的本能欲望在生存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使之成为了生存观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可以说《使女的故事》颠覆了《圣经》有关生存观的传统权威设定,深入发掘了生存观的全面景观,整合出了一套更为完善、平等的《圣经》生存观。而这种内涵在小说的反乌托邦语境中对应着一种反对人性压抑、提倡多元共存[5]110-114的生存理念,于是小说对《圣经》生存观的思考便体现出了更加鲜明的人文关怀。
二、突显《圣经》生存观的隐喻思维
通过对“权威”生存观的戏仿和重构,小说还原了《圣经》生存观中被遮蔽的部分。而通过奥弗雷德的意识流,小说则突显了《圣经》隐喻的思维方式,纠正了基列只从字面上来理解《圣经》生存观的做法。语言是人类的生存方式,而语言思维的不同更是能将人类引入不同的生存境地。因此小说突显《圣经》生存观的隐喻思维,不仅是因为它有助于理解生存观的基本义,也是因为它有望能深化拓展生存观的内涵与表达。
首先还是关于基本义的理解问题,我们最初可以看到基列统治者的原教旨式的理解。小说在许多地方都着力表现这种理解的荒诞性,而其之所以荒诞,就在于只讲求纯粹的逻辑,连最基本的想象力都丧失殆尽。而这种情况,不仅会造成一切事项都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和遵行,还会造成某种生命力的衰亡。所以在小说中,以这种思维方式来理解《圣经》,不仅没有起到改善生存处境的作用,还使原有的情况更为恶化。大主教们按照拉结生子的典故依葫芦画瓢,不仅没有解决原有的生育问题,反而带来了更为荒谬尴尬的家庭关系和孤独封闭的精神困境。
与此相反,奥弗雷德的理解更灵活变通,反而获得了生命与精神。这可体现在奥弗雷德经常不按字面的仪式祷告,而是任由意识回忆和现实事件在脑海中交叠,产生幻觉。只有在幻觉中,她才向上帝真诚祈祷,并从中得到真正的解脱。这种生存方式在弗莱那儿得到了概括说明:“只有当我们在实际存在的事物中看见想象的因素,而在对未来事物的想象中看见真实的因素时,严肃的人生才会开始。”[6]76而这种“人的意识和物理现象的统一性”[6]36,正是“隐喻”。从这里可看出,奥弗雷德以意识流的方式进行生存,不仅体现了她对隐喻思维的坚持,也更突显了隐喻思维的特质,而这不仅使生存观的内涵得到了强化,也使生存观的表达得到了更新。
这种情况在奥弗雷德对名字的怀恋上已有所体现。具体来说,既然隐喻具有“词语和事物共有的能的意义”[6]28,那么隐喻思维就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能够统一人的精神和肉体,从而在外界不断施加压力的情况下,还能让人感到生命的坚实完整,保持坚定的生存信念。因此奥弗雷德对名字有所怀恋,不仅是因为名字是一个人的本质的隐喻,也是因为名字所包含的隐喻思维与生存之间有着这样重要的联系。尤其在失去了本名的情况下,奥弗雷德只有凭借隐喻思维,才能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坚守自己的本质。所以她这样说道:“于是,我把这个名字珍藏起来……这个名字被一股香气缭绕,它像一道护身符,某种从遥不可及的远古时代遗传至今的符咒,将这个名字牢牢护卫。”[4]88不妨说“香气”一定程度上指的就是隐喻思维,而在“香气”的环绕和护卫下,“名字”所代表的生存信念也就得到了巩固和强化。
而这种情况还体现在奥弗雷德对“爱”的思考上。因为隐喻还可以说是“众多的神,或多个人与自然统一的化身”[6]26,所以隐喻思维也就具有一种泛神论的特质,容易让人随时随地找到精神的安慰,哪怕是从细小的事物中也能寻得。与此相应,奥弗雷德对基督教的“爱”做出了以小见大的解读。她一开始就说了一个关于爱的谜语,仿佛要让读者由近及远地感受和想象:“这里曾经有过性、寂寞及对某种无以名状之物的企盼……那是对随时可能发生,但又始终虚无缥缈、遥不可及的事物的企盼。”[4]3后来她坦诚公布了谜底:“谁也不会因为缺少性而活不下去,缺少爱才会置人于死地。”[4]107最后在弗雷德大主教谈到“爱”的时候,奥弗雷德也就正好澄清了她所謂的“爱”的概念:“不,是恋爱……上帝就是爱,人曾这么说,可我们将其颠倒过来。爱,就像天堂,总是近在咫尺。越是难以爱上身边那个具体的男人,我们对抽象绝对的‘爱就越发坚信不疑……”[4]235-236
奥弗雷德对爱的理解看似狭隘,但实际上她利用隐喻思维,更新了生存观的表达。通过这种做法,她才能找到个人的精神安慰,而又与宗教的大爱保持着联系。由此一来,隐喻思维先是表达了人性的渴望,满足了人的生命需要,而后又表达了人类对崇高的向往,满足了人的智性追求。也正因为这样,隐喻思维就超越了原教旨主义那种固执的理性思维和僵化的刻板视角,使生存观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正如弗莱所说:“使这些材料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力不可能是坚持教义或逻辑的刻板的力,这样的力在文化的重压下会被摧毁,而是由建立在隐喻基础上的、想象的统一形成的更富有弹性的力。”[6]279这句话说明了《圣经》只有凭借隐喻思维,才能把“材料”统一起来,明白而生动地传达生存观的意义,也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出更为普适的生存真谛,始终保持教义的活力。
相应地,小说突显《圣经》生存观的隐喻思维,不仅是因为隐喻思维有助于理解《圣经》生存观的基本义,也是因为隐喻思维能够强化或更新人们对《圣经》生存观的认识与表达,从而能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圣经》生存观的意义。
而从反乌托邦的角度来说,突显隐喻思维,对《圣经》生存观的发展还具有更深的引导意义。隐喻思维实际上拒绝了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理解世界[7]12,对绝对理性作出了自觉的反抗,表达了一种重要的生存意向。进一步来说,从小说中可看到,无论是非理性对理性霸权的否定,还是感性对绝对理性的修正,都指向了一条更为和谐的生存之路。
三、追求《圣经》生存观的和谐真义
无论是恢复《圣经》生存观中被忽视的部分,还是运用隐喻思维来处理《圣经》生存观与人类生存现实的关系,都可以看出,小说想使《圣经》生存观变得更具有和谐性。具体来说就是,小说试图对《圣经》进行意识形态的祛魅,使生存观更为完整化和全面化,并让《圣经》生存观与不断发展的现实相调和,让传统的生存观变得更加包容和开放。
小说的这种追求,还体现在阐释《圣经》生存观中本已包含的和谐观念。例如,对“宽恕”的讨论,就明显体现了这一思想。奥弗雷德用相当迂回的方式谈论“宽恕”,并在这种迂回中显示出寻求某种平衡的努力:“倘若将来有朝一日,你成了男人,并有幸出人头地,切记千万别受诱惑,产生作为女人理当宽恕男人的想法……不过请记住,宽恕本身也是一种权利。祈求宽恕是一种权利,给予或是不予宽恕更是一种权利,或许是最大的权利……也许这一切全都与驾驭无关。也许这并不真是有关谁可以拥有谁、谁可以对谁做什么而不必受追究,甚至置其于死地也同样可以逍遥法外的问题。也许这也不是有关谁可以坐着,而谁又必须跪着或站着或躺着张开双腿的问题。也许这一切只是谁可以对谁做什么并得到宽恕的问题。两者性质决不相同。”[4]140
这是对她与好友莫伊拉的某次争论的进一步思考,论争焦点主要是在于两性和谐。奥弗雷德认为不能用女权代替男权,也就是“不能只是简单让男人走开……不能只是对他们置之不理”[4]179。作为二号人物,莫伊拉则将这种和谐进一步深化到女性的同性友谊,对待奥弗雷德与有家室的卢克谈恋爱的问题,她明确指出这“是在侵占另一个女人的地盘……女人之间的权利对比是相同的”[4]178-179。当时奥弗雷德对这种观点并不以为然。但可以看出,她对这段往事的回忆和叙述,开始具有反思的性质,是她在经历了使女之间“飞短流长”,但又“互相交流治病良方,争先恐后地诉说自己遭受的各种病痛”[4]10之后的有感而发:女性与女性之间,应该和谐交流,而非相互压迫。
值得一提的是,这类阐释不仅体现在正面人物的思考中,也通过基列的统治思想表現出来。比如基列国的初衷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这些都是针对环境污染、社会犯罪、泛滥的自由主义和人类健康危机而提出的。而基列国想要返回伊甸园社会,更是在追求《圣经》中所记载的终极和谐。另外,基列国的立场中有一些抨击女权的合法观点,也辩证地体现了和谐的思想。可以说基列政权表达“和谐”的方式,正如阿特伍德在《别名格雷斯》的结尾所呈现的百衲被的图案那样:“生命之树”被群蛇所缠扰,即“罪恶是生活的一部分,但生命之树常在”[8]P137。而作者让基列的统治体现出这种罪恶之蛇与生命理想相互交缠的内涵,也含蓄地表现出了《圣经》中“善恶共存”所蕴含的和谐意识。
可以说,阿特伍德的这种追求,既包含了对《圣经》原始生存观的加工,也包含了对《圣经》精华价值的撷取,所以它并不是简单的倡议,而是在有意识地追求《圣经》生存观的“和谐”真义。而这种追求越具有自主意识,也就越具有复杂性。它首先是为了女性和人类的生存着想,但实际上更与加拿大的民族生存问题有关。进一步来说,它不仅是寻找加拿大民族出路的愿望寄托,也是具有加拿大民族特征的处理方式。
在阿特伍德的写作中,曾出现过这样的例子。比如,荒野是代表加拿大民族特征的文学意象。而围绕这个意象,阿特伍德发展出“潜入地下”的主题,让笔下的女主人公在身体上或意识上潜入地底,以此摆脱地面上的既有秩序,回归到原始的自我意识中,让圆融的自然力量对受伤的女性进行净化,使女性重新寻回内心的和谐状态。
而在《使女》中,奥弗雷德的故事也有着类似的情况。首先,阿特伍德时常提到,女主人公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往往就象征着加拿大在大国环境中的夹缝生存[8]21,她们“不断地失去自我,又不断地寻找自我,象征了加拿大寻求身份的种种努力”[8]40。反观《使女的故事》,很容易看到奥弗雷德也具有这样的寻找民族出路的象征性。
其次,奥弗雷德的性格还暗示了民族特征。这体现在,奥弗雷德一向胆小怕事、温和驯顺,认为母亲的女权斗争“毫无意义”,也不敢像莫伊拉一样大胆反抗。而她的这种温和懦弱,却具有某种实际性。比如在受精时,奥弗雷德这样想道:“希望它能奏效。那样我就能好起来,这一切也随之消失。”[4]99而面对大主教的宠爱和关心,她不过看到了冷漠的夫妻关系和虚伪的风流情性,只想用它来保全性命,而没有任何恃宠而骄的心态。
可以说,奥弗雷德的温和的性格,就如同加拿大简单的山地平原和稀少的人口组成的“扁平的地图”,符合加拿大人“比较平和且缺少个性”[9]66的特点。而她身上那种务实的冷漠气质,正是加拿大民族面对恶劣环境和大国压力时的谨慎品质。正如有人说的:“加拿大始终被生存的焦虑感所包围。加拿大的故事不是创造奇迹而是描绘可怕的北方暴风雪、沉船、溺水等,幸存者没有胜利凯旋的自豪感只有侥幸生存下来的事实,除了庆幸没有丢掉性命外一无所获。”[10]100
质言之,奥弗雷德就是加拿大民族精神的象征。她围绕《圣经》发展出来的一系列生存观念和行为策略,表现出了加拿大民族努力摆脱边缘化、追求自然和谐的生存斗争。由此可见,阿特伍德追求《圣经》生存观的和谐性,实是彰显了加拿大民族的生存品质,也为加拿大的生存问题提供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启示出路。
最后,对“和谐”真义的追求也离不开小说本身的反乌托邦特色。除了前面所提到的价值取向(生存意向)以外,反乌托邦的“和谐”还与其精神品质有关。这种精神品质不是基列式的保守主义[7]12,即为了排除现代乌托邦的“科学、自由、进步”所带来的问题,就选择逃回到原始自然社会中去。恰恰相反,它是以奥弗雷德的思想内容为代表的,其中既包含了对现代社会的生存信条的批判思考,也包含了对基列的人间天国的凝重审视。这一精神总的来说,就是要走出有关“自由”、“平等”和“人”的迷思[4]27,以辩证的思考和警惕的态度,保障人类社会能够健康和谐地生存和发展。
总而言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通过反对生存观的权威设定、突显生存观的隐喻思维,不仅完善了生存观原有的意义,还力图进一步拓展生存观的意义。她最终不断地追求《圣经》生存观的和谐真义,则为女性的边缘生存、加拿大的民族生存、人类的社会发展以及《圣经》的当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出路。而无论是思考、启示还是出路,都在反乌托邦小说的价值观念中得到了深化。可以说人最需要掌握的应该是一种承认多元共存、拒绝二元思维、强调辩证谨慎的认清“人”自身的生存方式。
注 释:
[1] 傅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译林出版社,2003年。
[2]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好骨头》,包慧怡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3] 新世界书房有限公司编著:《精读本圣经》,新世界书房有限公司,2013年。(该版圣经在第2章15节指出,神是通过“事工”创造了天地、人类。因此,对于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劳动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只有“与神同工”的時候,才能发现乐园真正的意义,并从中体会真正的喜乐和幸福。)
[4]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陈小慰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论文中凡有引用小说原文,都只注明页码。关于“迷思”的问题,在小说中有一定的体现。比如在小说第27页,奥弗雷德提到了丽迪亚嬷嬷所说的“自由有两种……一种是随心所欲,另一种是无忧无虑。在无政府的动乱时代,人们随心所欲、任意妄为。如今你们则得以免受危险,再不用担心受怕。可别小看这种自由”,由此暗示了人们不是崇尚消极自由就是崇拜积极自由的问题。而前文所提到的奥弗雷德与莫伊拉争论的部分,可以说是对女权主义、父权暴力进行了否定,并对“平等”进行了重新的定义。而这些最终都是对“人”的反思。)
[5] 谭言红:《论北美反乌托邦小说的自然价值观》,《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关于反乌托邦小说反对人性压抑、提倡多元共存的理念,可参见此文。)
[6] [加]诺斯罗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郝振益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7] 谢江平:《反面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南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8] 袁霞:《生态批评视野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学林出版社,2010年。(袁霞在第21页说到:“70年代初,阿特伍德在诗集《苏珊娜·穆迪的日记》、小说《浮现》和论著《幸存》中都谈及了加拿大独特的民族传统问题及其对加拿大身份问题的关注。她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加拿大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境遇类似于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遭遇。”)
[9] 张雯:《另一世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文学招魂》,《外国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10] 张传霞:《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存”主题和“经典重构”策略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责任编辑:杨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