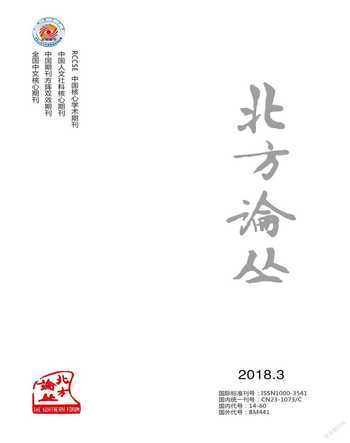儒道会通与现代理想人格的建立
2018-09-10姜婉婷
姜婉婷
[摘要]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是中国文化在轴心时代开创的两个重要文化基点。,在中国文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两种文化构成了士人进退出处、塑造自我人格的重要参照。从人格塑造的导向来看,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倡导自然人格,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则崇尚社会人格。对现代社会而言,二者仍是构建理想人格不可或缺的文化参照系。
[关键词]轴心时代;儒道会通;自然人格;社会人格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3541( 2018) 03 - 0062 - 03
春秋战国是雅思贝尔斯所说的中国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1](p.8),轴心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2] (p.396),轴心时代基本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审美范式和思维范式,多方面影响了民族群体性格和个体自我人格的形成。对后世而言,儒家学派与道家学派的影响最为深远,而其代表人物孔子与庄子,则各以其仁爱理想和逍遥境界,成为人们“高山仰止”的文化高峰。换言之,儒道互补,庄孔对举,乃是中国古代士人人格追求的最高境界。就社会理想而言,儒道思想体系截然对立,但是在人格修养的层面上,二者却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它们实质上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个“我”字,“我”既是德、礼外烁的对象,也是天、道言说的主体,德礼孕育人的社会人格,天道滋养人的自然人格,社会人格与自然人格的结合,才是真正完美的理想人格。
一、天地与我并生——庄子的自然人格
庄子是自然人格的追求者,其人格理想中有一种天地境界存在。
庄子追求物我合一,《齐物论》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3](p.79);庄子以真人、至人为楷模,《大宗师》谓:“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熟,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3](p.226)其《逍遥游》则言:“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3](p.17)
追求物我合一,追求至人境界,是要以“吾丧我”为前提的。所谓“丧我”,是指个人要超越于世俗的价值观之上,它既包括人们念兹在兹的功、名、利、禄,也包括常人不能摆脱的生死之惑。
庄子《逍遥游》谓: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实际上,无己、无功、无名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它们都有“舍我”“忘我”的意味。修道的人只有把名、功、己都遗忘了,才能与道合一,遨游于“无穷”之域,获得自由。《应帝王》云:“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3](p.294)由此可见,“游心”是指心灵的自由,顺任事物的自然而悠游自适。逍遥之游主要是游心,讲究精神虚静。庄子在《大宗师》中所说的“朝彻”,就这样一种境界。
对死亡的超越以及对心理焦虑的消释,同样是庄子“舍我” “忘我”的思想诠释。庄子认为,宇宙间充满了气,人与万物都是由气演变出来的,气凝聚,则成为万物,万物死亡消散又复归于气,气又重新演化为其他的形体和生命。《知北游》言:“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3] (p.733)庄子充分意识到时空的无限性:“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3] (p.800)人生与之相比,充满着脆弱感和虚幻感:“人生天地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3](p.1000)但他并没有过多地渲染死亡的恐惧,而是对死亡有一种超越的理解,甚至歌咏死亡、赞美死亡。《至乐》篇是超越死亡的言说,文中骷髅对梦境中的庄子说:“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3](p.619)庄子借骷髅之口,渲染死亡之乐的初衷,固然是对现实生存环境不满的曲折反映,但如果抛开这一批判现实的目的,其豁达的死亡观无疑具有一种超越性的精神指向。问题在于,生死是每一个人都无法逃避的自然规律,与其生活在恐惧死亡的阴影中,倒不如从容平和地对待生死,从而更积极地投入现实生活。
对庄子而言,“丧我”是一种突破个人小我局限,向天地大我回归的必然之路。其《天地》篇云:“忘乎物,忘乎天,其名日忘己。忘己之人,是之渭入于天。”[3](p.428)这种思想体系引导着人们冲破自身束缚、摆脱困境,从而使自己的精神得到超越和提升,进而达到一种人生修养的更高层次。
二、仁以为己任——孔子的社会人格
《淮南子·要略》认为,先秦诸子之学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4](p.360)。对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学派而言,这一论点尤其成立,在某种意义上,儒家人物往往具有极其强烈的社会人格。
众所周知,孔子是一位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西周末年,礼崩乐坏,百姓处于水深火热的“乱世”中,孔子提出“仁”来作为济世良方,目的是希望实现天下太平、社会和谐的宏伟目标。他主张在政治上实行仁政,与人相处要施行仁爱,个人修身要具备仁德。
所谓“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孟子日:仁也者,人也。”[5](p.365)张舜徽先生说:“仁从人从二,即二人以上群居之关系也。人在天地间,为最能群居之动物,故古人直以仁解人。仁之本义,盖但为亲比之意。”[6](P.1906)这即是说,“仁”乃是一个群体性和社会性概念。在孔子那里,在不同的场合,孔子对“仁”的概念的阐述是不同的:
樊迟问仁。子日:爱人。(《论语·颜渊》)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日: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日: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达人。(《论语·雍也》)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为仁由己,由人乎哉?(《论语·颜渊》)
孔子认为,“仁”是“爱人”,是各种美德的总称,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是孝悌伦理,是人发自本心的能力,其论述虽然如此不同,但却始终有一个共同的价值指向——群体和谐与社会和谐,换言之,孔子是“仁以为己任”的,其君子人格表现出强烈的道德担当和社会担当。
在孔子的“仁”学体系中,仁与礼相须为用。“礼之用,和为贵”[7](p.46),“礼”是仁的重要表现形式,它调和人际关系,规范人的行为,旨在实现人们相处的和谐。孔子十分重视礼的作用,他认为:“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7](p.1168)他强调: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恭近于礼,远耻辱也”[7] (p.49)。因此,要真正成为一个仁者并非易事,他应该“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7](p.539),应该“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7](p.926)。这是一种始于道德自律,达于道德自觉的修炼过程。
孔子的“仁”“礼”思想,看似是要解决社会问题,但实质上直指“人”的问题,主张从教化“人”人手,引领人们实践“仁”与“礼”,进而建成大同世界。
三、儒道会通——社会人格与自然人格的互补
儒道两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和庄子由于认知视角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的不同而创立了不同的学说。孔子以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为指向,强调进取有为,注重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提升,旨在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庄子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指向,主张无为而无不为,造就超凡的逍遥情怀,注重顺其自然的自觉和物我合一。儒、道学说之所以能够经历数千年,绵亘不断,共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两大思想渊源,足以说明二者具有一定的共生性和互补性。
在现代社会中,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爱慕虚荣等人性弱点被充分暴露出来,人们在精神上开始出现迷茫和痛苦,精神家园迷失。此刻,需要儒、道文化来滋养心灵的绿茵,需要儒、道精神扫荡内心的尘埃。儒、道文化既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是华夏重要的精神遗产,对此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抽象继承的方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现代理想人格的建立。在对儒道思想的继承中,需要注意如下三点:
一是在贞固自我的过程中秉承儒、道的思想自觉。庄、孑L都觉悟到内在世界贞固的重要性,二者实际都在追求“内圣”。孔子讲“为仁由己”,重视主体德性的能力;庄子讲“内不化”“心不死”的自我。孔子提倡“内省”,曾云:“观过,斯知仁矣!”[7](p.241)庄子也重视主体内在精神之自觉,曾云:“其于人也,乐物之通而保己焉。”[3] (p.878)
二是在规范自我的过程中达成儒、道的思想境界。儒家主张通过个体的“内省” “内修”“克己”“尽心”而达到“仁”,将自己融化在“礼”“德”中,从而完成其理想人格的塑造;道家主张抛弃外物,不受外物所累,但又以“道”以及“自然”之法则规范主体自由,以“去欲”作为通向主体自由的通道,把自己融化在“道”与“自然”中,从而使“无我” “忘我”与道融合,完成理想人格的塑造。
三是在穷达之境中体悟儒、道的达观思想。“穷”与“达”二境虽然是人生际遇使然,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泰然处之。儒家在面对贫富、贵贱、苦乐、生死之时能够表现得很豁达。 《述而》云:“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7](p.465)《学而》云:“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7](p.58)道家强调,通过内养精神求得克制生命、权力、物质利益等三个方面欲望的平衡。《刻意》云:“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天行,此养神之道也。”[3] (p.544)身处“穷”境,不忘以儒道思想修“心”,不忘以道家精神保持顺应天道的超然心态,穷且志坚;身处“达”境,同样不忘以儒道思想修“行”,利而不害、为而不争,不急功近利。
面对儒道学说相伴而生、共同孕育中华文化的文化事实,我们应该摒弃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二元对立思维,重视儒学与道学内外兼修,奉行“独善”与“兼济”的融通。以儒家思想指引人的人世进取,以道家思想慰藉人的內在世界,儒道互补,儒道会通,这是一条被历史证明的实现理想人格的文化之路。
[参考文献]
[1][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
[5]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6]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7]程树德撰.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