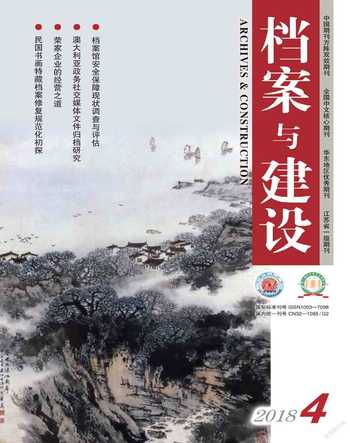口述档案与社会记忆构建关系再思考
2018-09-10韩良
韩良
[摘要]论文首先从当前数字化转向带来新的“真实性”问题出发,探讨口述档案与社会记忆构建的逻辑起点与归宿;其次就口述档案对于社会记忆构建的重要作用以及社会记忆构建对口述档案研究的促进作用进行了探究;最后提出口述档案在社会记忆构建过程中作为多学科参与、融合的桥梁,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历史真实性口述档案社会记忆数字化
[分类号]G270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al Archives and Social Memor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Han Lia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
Abstract: The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destin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oral archives and social memor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new "authenticity" problem brought about by the current digitization; Secondly, it explor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oral archiv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emory and the promoting rol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emory to the study of oral archives. Finally, it points out that oral archives are involved as multi-disciplinary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memory construction. The bridge of fus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Keywords: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Oral File; Social Memory; Digitalize
口述档案,也可以称为“口述历史”或者“口述资料”,是一种通过口头讲述传承并进行记录的新的历史记录形式。口述历史工作起步较早,1948,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第一个“口述历史研究室”,之后又成立了多个口述历史研究机构。美国对于口述历史的研究包括理论研究及实践操作,并形成了相应的规范和标准。在口述历史的记录保存方面也取得了诸多成果,标志着这一时期口述档案史学的形成。美国对于口述历史的研究,推动了口述档案的发展。19世纪80年代,新加坡也开始了口述档案的研究,建立了专门的机构,按照不同的主题搜集、制作口述历史资料,用以弥补传统档案的不足。口述档案概念的提出,最早是1980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九届国际档案大会,当时的肯尼亚国家档案局局长MKagombe在会上所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口述档案”的概念。我国学者对于“口述档案”概念的接触最早是在1984年国际档案理事会出版的《档案术语词典》,其中将口述档案概念定义为“为研究利用而对个人进行有计划的采访的结果,通常为录音或录音的逐字记录形式”。
近年来,国内档案学界学者开始关注档案与社会记忆构建的关系。随着“世界记忆工程”的启动,我国也开展了相关的“城市记忆工程”和“乡村记忆工程”。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档案的记忆属性开始受到关注与挖掘,档案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记录,对于社会记忆的构建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口述档案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记录形式,对于弥补、丰富传统档案和社会记忆有着独特、不可或缺的作用。
1口述档案与社会记忆构建對话的逻辑起点——历史真实性
1.1口述档案、档案与社会记忆
近年来,随着档案记忆观的兴起以及后现代理论对于传统档案理论的影响,档案的记忆属性开始得到广泛的关注。后现代理论的批判精神和解构主义,倡导人类和世界存在的多元化,反权威、去中心,解读权力因素对于社会历史的影响,发掘以往权力遮蔽下的边缘声音。后现代主义自产生以来,在多个学科进行了快速的发展融合。随着后现代主义与传统档案学理论结合,档案工作者开始尽可能从更多元的角度来认识理解档案。著名档案学家特里·库克归纳了四个档案学范式思想。库克认为,档案的观念经历四个范式的转移:证据、记忆、认同、社会/社区。库克的后现代档案思想,从更多元的角度看待档案,关注档案形成的背景及权力关系,其中的“记忆”范式,便是强调将档案作为历史文化记忆。档案不再只是传统的知识与信息的载体,也承载着社会历史的记忆。档案是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历史记录,具有无可比拟的原始记录性,这一本质特征使得档案成为社会记忆构建不可或缺的因素,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也需积极投身于社会记忆的构建。
口述档案不同于传统档案,二者在形成方面有着巨大的不同。传统的档案是社会实践活动中的直接记录,具有很强的参考、凭证作用,原始性是其本质;而口述档案的形成,则是基于对以往历史事件的经历者、参与者所做的访谈,而后加工整理而成的。对于口述档案的属性,诸多学者存在争议,认为口述档案并不能称作档案。基于后现代理论的批判思想,笔者认为对于口述档案的看法可以更宽容一些,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演进,档案的载体和形式也会发生改变,每一次大的革新必然影响到传统档案理论,作为档案工作者,我们应从更多元的角度看待口述档案。虽然口述档案在真实性、可靠性方面并不具备传统档案的优势,但是口述档案有着其独特的形式,丰富的情感表达和久远的历史渊源。如我国蒙古族口口相传的《格萨尔王》、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荷马史诗》,这都是较早期的口述历史,虽不是直接形成的社会记录,但是却在传承民族精神,丰富民族感情、加强民族认同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档案记忆观视角来看,口述档案是另一种角度的社会记忆,它的存在和发展可以丰富传统档案的记忆属性,也是社会记忆构建不可或缺的部分。
1.2数字化转向带来新的“真实性”问题
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为档案及档案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革新,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的出现也对传统的档案理论产生了巨大冲击。尤其进入Web2.0及“互联网+”时代以来,档案数字化已成趋势,对于口述档案及社会记忆的构建也带来了新的途径。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将传统载体的口述档案进行数字化保存与利用,能够更好地让公众参与到口述档案的研究发展和利用中来。近年来,关于数字化的社会记忆构建也进入人们的视野,“数字记忆”作为记忆的新形式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一些全新的社会记忆实践,如我国的“数字敦煌”、国外的“威尼斯时光机”,极富创造力,让社会记忆更加鲜活。数字化转向给口述档案的研究发展和社会记忆构建带来了新的生命力,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共同挑战。
数字化时代,依托于新的信息技术,数据化档案数据剧增,随着“数字记忆”的构建,不仅依靠传统的档案资源,新型的数字化档案也将参与到记忆的构建。一方面,网络化的档案数据具有虚拟性、瞬时性、碎片化的特点,这就导致数字化档案数据以及数字记忆的构建也开始面临“真实性”问题的考验。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公众开始积极参与到档案及社会记忆构建中来,个人的知识背景和情感倾向不同,也可能导致数字化档案及社会记忆的失真。
1.3历史真实性:口述档案与社会记忆构建对话的逻辑起点
口述档案由于其形成方式,一直以来面临学者对于其“真实性”的疑问,而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数字化快速发展,数字信息和公众参与的不稳定性导致社会记忆的构建面临同样的“真实性”考验。随着档案记忆理论范式的转换和档案记忆观的兴起,学者开始认识到档案的记忆属性,档案作为社会记忆的中介,产生形成于一定的社会时代背景之下,“真实”或是“虚假”,本身就是当时社会背景和权力关系的正视,口述档案亦是如此。口述档案不同于正统档案,正统的档案往往包含了统治阶级的意志,蕴含的是精英群体、中心群体的“记忆”,口述档案则包含边缘群体的故事,反映的正是另一种的“真实记忆”。事实上,无论是口述档案还是社会记忆构建,二者本质上都是对于过去社会历史的竭力“重现”,是对过去“真实”的追求与情感的重构,这一点上二者具有共同的归宿。数字化转向背景下,让公众参与到口述档案实践研究和社会记忆构建中,也是二者对于“历史真实”的不断追求,透过技术手段,“历史真实性”的本源已成为二者关系重新思考的逻辑起点。
2口述档案是社会记忆构建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2.1口述档案对于社会记忆的补充、矫正
传统档案所承载的是官方的记忆,我国的档案自古以来就具有较强的资政性,档案多为统治阶级服务,基于传统档案所构建的社会记忆是主流群体的记忆,是不够完整的社会记忆。而口述档案正视边缘群体、正视被以往权力关系遮蔽的边缘人群的记忆,是社会记憶的重要补充。
“后真实”语境下,语言学转向,对于传统档案本身的真实性也存有了质疑。语言本身是不透明的,是承载记忆的一个“媒介”,传统档案本身是否完全客观、真实,便难以确定。而口述档案从不同主体、不同角度来“记忆”,可以与传统档案互为印证补充,更好、更真实地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矫正社会记忆构建。
2.2形式独特,使社会记忆更鲜活
口述档案是通过对事件亲历人进行实地访谈,制作保存而形成的文字材料或是声像材料。口述档案是当事人或知情者通过口头讲述来记录,这样的形成方式容易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讲述者的年龄、知识水平、情感倾向、时间久远程度、当时的社会背景等,导致口述档案一方面包含了当时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也包含了讲述者的主观意志。一定程度上,讲述者的主观意志会影响口述档案的真实客观性,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口述档案这种“主客一体”的独特形式,使得口述档案具备独特的魅力,既包含过去的客观事实,又融合了主观情感;既是对过去的回忆,同时也夹杂了当下现实的社会背景;既是社会的记忆,同时也是个人的记忆。口述档案为社会记忆构建融入了更多新元素,让社会记忆构建更鲜活,更富生命力。
2.3促进社会记忆建构转向,增强民族认同感、归属感
当今社会是一个开放多元,以人为本的社会,社会记忆的构建也应更加多元。口述档案记载了边缘人群的声音,承载着非主流群体的记忆。构建社会记忆,应打破传统以官方主流为主体的模式,转而以民为主,构建大众记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口述档案记录着人民的点滴生活,包含着底层人们的情感与记忆,这样的社会记忆构建才更完善,更生动,更有感染力,能更好地激发民族认同感、归属感。
3社会记忆构建为口述档案研究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3.1记忆工程推动口述档案研究发展
一方面,口述档案对于社会记忆构建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是社会记忆构建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社会记忆构建也推动了口述档案的快速发展。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世界记忆工程”,关注人类文献遗产,旨在通过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从而保护世界记忆。近年来,我国也开始了“城市记忆工程”和以传统村落档案为主的“乡村记忆工程”。社会记忆的构建不能缺少口述档案的补充完善,一方面“记忆工程”的开展,导致对于口述档案的需求加大,使得口述档案迅速走进人们视野,得到了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记忆工程”的研究实践成果也为我国口述档案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支持,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口述档案研究重理论、轻实践的现状得以扭转,并为日后开展口述档案实践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记忆工程”的开展,让学界注意到了口述档案在社会记忆构建中无法替代的作用,让学界得以再次认识与思考口述档案,能够给予口述档案一个更为公正、宽容的定位,极大地促进了口述档案走进档案大家庭的步伐,为口述档案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平台。
3.2数字记忆的发展建设为口述档案提供了新途径
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原生和此生的数字档案信息不断增加,数字记忆也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有学者已经提出建立“中国记忆”数字档案资源库的构想。以非遗为代表的数字记忆建设已经开展了广泛的实践。如运用3D技术的“虚拟紫禁城”项目;运用AR、VR技术的“数字圆明园”“敦煌莫高窟”;建立《格萨尔王》影音数据库等。这些实践及技术的运用,也为口述档案在数字时代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口述档案虽然由亲历者讲述,但是却可以运用新的信息技术进行多层次的开发利用,不局限于传统的文字记录和声像记录。借鉴数字记忆建设,对口述档案进行更为艺术化的呈现,更好地传播给社会大众,让过去的故事以更鲜活的方式存活。
4口述档案为社会记忆构建与多学科融合提供了桥梁
基于后现代主义,档案范式逐渐转移,为档案学者、工作中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看待档案。随着近年来档案记忆观、档案文化观、大档案观的出现,档案的属性愈来愈多元,学科融合现象也愈加显著。社会记忆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工程,档案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档案馆保存着社会记忆,但绝对不是唯一的记忆参与者。要想真正做好社会记忆构建,多学科融合是必然趋势,而口述档案的出现为社会记忆与多学科融合搭建了桥梁。口述档案本身就具有非常丰富的属性,多元的属性决定了“口述档案”并不是局限于档案学领域。图情学科、历史学科、文化学科等诸多联系密切的学科纷纷开展关于“口述档案”的研究。这就使得这些学科在参与社会记忆构建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融合点。口述历史档案的研究更是一场多学科参与的档案运动。
5结语
总的来说,口述档案与社会记忆从记忆观的角度是有一定相似性的,口述档案就是社会记忆的载体,对社会记忆的构建、完善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二者都存在“真实性”问题的质疑,但是二者本源都是對于以往社会历史事实的不断追寻,以期能够重现历史事实、重构历史情感,这是二者关系重新思考的逻辑起点和归宿。另一方面,社会记忆的构建也对口述档案的研究起着“反作用力”,它让口述档案再次活跃于学界视野,为口述档案“正名”,同时为口述档案实践研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极大地促进了口述档案的研究发展。
口述档案与社会记忆构建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研究的必要性,基于这样一个合作共生的视角,学界应以更为宽容的态度看待口述档案,既不盲目吹捧,也无须“一棒子打死”。借由社会记忆构建这一机会,尝试通过口述档案来促进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推动我国社会记忆建设。
参考文献
[1]刘磊.档案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再思考——基于“数字化转向”的视角[J].档案学通讯,2017(5):34-38.
[2]黄霄羽.魂系历史主义——西方档案学支柱理论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47-55.
[3]闫静,徐拥军.后现代档案思想对我国档案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启示——基于特里·库克档案思想的剖析[J].档案学研究,2017(5):4-10.
[4]曲春梅,王静,王宁.近年来我国档案与记忆研究综述[J].档案学研究,2017(1):17-22.
[5]周亚,许鑫.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述评[J].图书情报工作,2017(2):6-15.
[6]王玉龙.不同的记录不同的过去:口述历史档案的兴起及其理论影响[J].档案学研究,2016(5):40-44.
[7]子志月.近三十年来我国口述档案研究综述[J].档案学通讯,2013(1):12-15.
[8]黄明辉.口述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新释[J].兰台世界,2016(23):6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