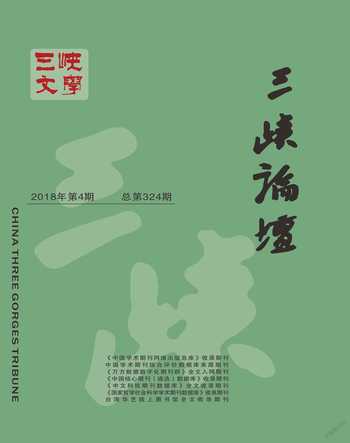莫言八九十年代的小说还原历史的叙事策略
2018-09-10曹金合
曹金合
摘 要:十七年文学中追求历史的本质并以“真实”作为衡量小说的社会价值的重要尺度的红色经典,就会以先入为主的认知方式储存于莫言对史诗性的理解和感悟之中,作为一种衡量文学思想和艺术标高的参照系潜移默化地影响他文学创作的时空布局、情节选择、结构安排、人物塑造等内在的肌理方面。这在洪水创业神话、革命英雄传奇、百年历史的谱系寻踪中都有比较鲜明的表现。
关键词:莫言;八九十年代;小说;史诗性;反史诗性;还原历史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8)04-0084-06
莫言在还原历史的过程中体现的史诗性追求和建构企图肯定与十七年文学中的“红色经典”有密切的关系,莫言在与评论家王尧的对话中曾提到《红日》开篇的悲观描绘背离了自己既定的历史观产生的不适感,以及随着阅历的丰富和创作经验的成熟对当时偏离约定俗成的审美习惯的由衷赞赏:“《红日》一开始写悲观,失败,我觉得很不舒服。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后,才知道当初那些让我看了不舒服的地方,恰是最有文学意义的描写。”[1]11在少年儿童的类似白板式的认知过程中,这种以再现宏大的历史和战争场面、注重英雄形象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突出重围的传奇壮举的描摹、追求历史的本质并以“真实”作为衡量小说的社会价值的重要尺度的红色经典,就会以先入为主的认知方式储存于莫言对史诗性的理解和感悟之中,作为一种衡量文学思想和艺术标高的参照系潜移默化地影响他文学创作的时空布局、情节选择、结构安排、人物塑造等内在的肌理方面。所以,莫言在还原历史的本真面目的时候,是有一种史诗性的因素作为他异于当代文坛的创新驱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当然,这种模糊 “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相对比较肤浅的文学创作观念在莫言的心目中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在八九十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大行其道的时候,莫言在八十年代中期的《红高粱家族》中追求的站在民间的立场还原历史的“真实”,到了十年之后的史诗性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就转变为尊重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艺术虚构的“真实”。在九十年代《我的〈丰乳肥臀〉》的创作谈中,他认为:“小说家并不负责再现历史也不可能再现历史,所谓的历史事件只不过是小说家把历史寓言化和预言化的材料。”[2]33这样,在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转型的史诗性框架中出现的带有主观化意识的反史诗性的情节结构也成为莫言小说的一大特色。这在洪水创业神话、革命英雄传奇、百年历史的谱系寻踪中都有比较鲜明的表现。
一、洪水和创业神话的建构与解构
在人类生命的起源和文明的源头上,不同的民族、种族和地域的创世纪神话中总是记录了与洪水和创业密切相关的文字传说,可以说,洪水的原型和创业的原型就作为文化基因和遗传密码在不同民族的潜意识心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无论是西方《圣经》中的创世纪还是中国的女娲补天、抟土造人、大禹治水都意味着人类童年时代的史诗性追求。正像黑格尔说的,“正式的史诗既然第一次以诗的形式表现一个民族的朴素的意识,它在本质上就应属于这样一个中间时代:一方面一个民族已从浑沌状态中醒觉过来,精神已有力量去创造自己的世界,而且感到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种世界里;但是另一方面,凡是到后来成为固定的宗教教条或政治道德的法律都还只是些很灵活的或流动的思想信仰。”[3]137作为深受齐文化“怪力乱神”影响的莫言真诚地相信万物有灵的民俗传说的同时,西方的文学思潮特别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激活了他童年时期被饥饿和洪水所缠绕的记忆。莫言曾深情地回忆:“童年留給我的印象最深刻的事就是洪水和饥饿。那条河里每年夏、秋总是洪水滔滔,浪涛澎湃,水声喧哗,从河中升起。坐在我家炕头上,就能看到河中高过屋脊的洪水。”[4]57因此,儿童时的刻骨铭心的记忆、祖辈创业的传说和域外文艺观念的启发共同影响了在军艺学习的莫言,他在小说《秋水》中表现的就是祖先在洪荒年代与洪水和灾难作不屈抗争的创业神话。作为“高密东北乡”的史前史的地域风貌就很具有开天辟地的史诗性色彩,从塑造的人物形象来看,我爷爷、黑衣人、白衣姑娘、紫衣女人的行为方式、处世态度和神态表现都具有传奇的色彩,是史诗性英雄人物惯常的塑造模式,但在具体的细节和情节上,个人的偶尔不被人觉察的行为和神态表现又呈现出反史诗性的格调,比如我爷爷在力比多力量的驱使下杀死三个人所体现的英雄壮举与事后“梦里常忆起那几颗血淋淋的人头”的提心吊胆,面对滔天的洪水和妻子难产的生活困境产生的绝望心理就与史诗性的英雄人物不畏艰难、越挫越勇、勇往直前的行为表现有比较大的差别。正是这种史诗性和反史诗性的辩证因素有机地统一在对我爷爷的形象塑造的过程中,才使得他老人家成为活生生的“这一个”和过目难忘的圆型人物。从总体来说,尽管是短篇小说的文体格局限制了史诗性追求的宏阔的时空跨度和规模,但表现的主题、渲染的氛围、塑造的人物、凸显的精神都皴染上了史诗性的色调。
莫言对古老的创世纪的神话传说情有独钟,短篇小说《马驹横穿沼泽》作为《食草家族》中的第六梦,在异类通婚、羽化成仙、洪水再殖、兄妹乱伦的神话原型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史诗性的元素。在代代相传的身份不明的黑色男人对小杂种讲述的小男孩和小马驹横穿沼泽的故事中也包含了远离文明的洪荒神话的因子,当很早很早以前(时代愈久远愈带有神话和史诗色彩)的迁徙途中只剩下一匹小母马和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为了满足创世纪的生殖繁衍的神话要求,作为异类的小母马必须羽化成仙变为千娇百媚的姑娘才能赢得男孩的爱怜,完成生儿育女、开辟鸿蒙的史诗性任务。所以在流传的史诗性故事中,小母马在小男孩爽快地答应“结成夫妻之后,你永远不能提一个马字”的誓约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叫“草香”的温婉可人的姑娘。他们结为夫妻受尽千辛万苦横穿沼泽到达的地方的环境条件,以及生儿育女的生活方式都具有创业原型的史诗性质素,但当男孩在子女乱伦的条件下违背当初的誓言骂道“打死你们这两个母马养的畜生”时,马驹在山崩地裂的巨响中“被那浪涛翻滚般的烟雾卷跑了”。儿女的死去、马驹的逃走、男孩“由一个膘肥体壮的大汉变成了一具又黑又瘦的活死尸”又在演绎着一个毁灭的神话。在“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创世轮回中凸显的是创业神话的建构和解构的永恒主题。
对于女人与母马之间的象征、暗示和隐喻关系,在《周易》的坤卦卦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中得到了比较鲜明地体现。是女性—马(妈)—母亲—大地之间异质同构的本能养育和创业(世)功能激发了莫言创作史诗性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的灵感,也将莫言八九十年代的史诗性建构和解构的抒写主题有机地贯穿了起来。在现实生活中的亲生母亲死去之后,用了83天的时间写就的煌煌巨著《丰乳肥臀》,反映了莫言对母亲——大地的孕育再生的同构功能早就了然于胸,从父系氏族社会推翻母权制之后进行的一系列的杀伐和争斗,到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记载的帝王将相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为功名和事业发动的不义战争在说明着“乾”的破坏作用,而在漫长的文明进化过程中地势“坤”和母亲的厚德载物起到了创世、创业和建构的功能,这是通晓历史和文明发展的莫言无意识中将母亲与大地联系在一起,并为她们大唱赞歌的最为重要的原因。莫言在1995年写的《〈丰乳肥臀〉解》中提到:“丰乳与肥臀是大地上乃至宇宙中最美丽、最神圣、最庄严、当然也是最朴素的物质形态,她产生于大地,又象征着大地。” [5]124对于母亲的养育之恩,莫言也把它还原到最原始、最纯洁、最本真的功能和意义上:“母亲之恩,大莫大过于养育之恩。养用什么养?育用什么育?用乳、用臀。”因此,把小说命名为《丰乳肥臀》就具有和滋养万物的大地同构的创业神话的史诗性意义。母亲含辛茹苦抚育九个孩子的过程中,最震撼人心的莫过于翻江倒海呕吐粮食的情节,此时的母亲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博大的胸襟就具有了大地母神的象征意蕴,她超越政治、阶级、民族、种族的偏见,对子女一视同仁的平等心态和宽容态度也是富有建设性的阴性母神共有的特征。在百年的家族历史的风流变化中,母亲就是一个典型的创业原型,是母亲用自己坚韧的臂膀和达观的态度为整整两代人提供了避风的港灣。母亲的超出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底线的行为不能按照“百年屈辱,百年荒唐”[6]70的卫道士般的价值标准进行批判和决断,从总体上来看,母亲是真正遵循了“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原则和信条才具有了史诗性的神话色彩。可以说,母亲“在物质、肉体和精神上所遭受的蹂躏,深刻揭示出中国女性卑微的家庭、社会地位和悲惨的命运”[7]166,莫言以永恒的人性代替主流意识形态所规约的阶级性的审美思维让母亲成为《丰乳肥臀》最动人的艺术形象。
二、革命英雄传奇的史诗性变奏
在黑格尔看来:“战争情况中的冲突提供最适宜的史诗情境,因为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这个原则适用于绝大多数史诗。”[3]137莫言作为一个军旅作家虽然没有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但相对熟悉的军旅生活、实弹演习和对战友的体察也使得他把革命英雄传奇作为自己创作的主旋律。此时,尽管莫言也发表了一些反映革命英雄的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经历的小说,但真正对革命的史诗性题材有自己比较独特的看法,并付诸实施写出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的《红高粱》,实在是出于偶然的年轻气盛将自己逼上梁山的无奈之举。在1984年冬季的一次军事文学创作座谈会上,面对着有人提出的一些军队老作家经历过战争却没有精力创作、年青一代有精力创作却没有亲身体验战争的尴尬现状,莫言在发言中对这种对军事文学的发展抱有悲观态度的观点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小说家写战争,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 也可以写战争。”[8]47这样,莫言在历史主义思潮下所形成的革命英雄传奇的史诗性观念与红色经典的史诗性之间就有了比较大的对立和差距,1986年发表的《红高粱》《狗道》《奇死》《高粱酒》《高粱殡》就是对革命英雄传奇的重新书写,史诗性的变奏在历史的本源、英雄的塑造、时代的精神、真相的还原、艺术的虚构等方面都得到了鲜明的表现。从历史的本源来说,“它用民间化的历史场景、‘野史化的家族叙事,实现了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原有的权威叙事规则的一个‘颠覆,在历史被淹没的边缘地带、在红高粱大地中找到了被遮蔽的民间历史,这也是对历史本源的一个匡复的努力。”[9]37它对红色经典的主流意识形态所遮蔽和过滤的边缘化的历史真相,真正做到站在民间立场上的还原,无疑是对历史本源的异质的复杂构成和多元存在形态的修正和匡复。共产党、国民党、土匪、民众组成的力的平行四边形的撕扯和纠结构成了对红色经典反映的历史本源的反叛和变奏。在英雄形象的塑造上,设置土匪余占鳌而不是抗日的胶高大队队长江小脚作主角,更多的是出于回归本源意义上的史诗性英雄人物的塑造上。莫言对既是保家卫国的抗日英雄又是杀人越货的土匪王八蛋的余占鳌进行浓墨重彩的刻画和描摹,就接续了史诗性英雄人物塑造的优良传统。从时代精神的视角来看,《红高粱》张扬的敢说、敢想、敢爱、敢恨、敢做的个性解放的自由精神契合了八十年代个性觉醒的要求,自由的创造精神和担当意识也就浸染了史诗性的色调。而真相的还原与艺术虚构的辩证统一,从史诗性的口头传说到整理成文字记录的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体现。这首先就是一种历史立场和评价观念的转变,因为“我们心目中的历史,我们所了解的历史、或者说历史的民间状态是与‘红色经典中所描写的历史差别非常大的。我们不是站在红色经典的基础上粉饰历史,而是力图恢复历史的真实。”[1]10所以在《红高粱》中从历史上实有的“孙家口伏击战”和“公婆庙惨案”转变为由我爷爷余占鳌带领土匪部队去伏击日本鬼子的汽车队,历史的本事诗学呈现出不离本源意义的事件的更高的真实。正是莫言用“耳朵阅读”的民间口述史影响了他的历史观、英雄观和价值观,用桀骜不驯的偏离正统观念的“酒色财气”表现的史诗性的英雄气概颠覆了红色经典中的英雄崇拜心理。正如作者所说“在民间口述的历史中,没有阶级观念,也没有阶级斗争,但充满了英雄崇拜和命运感……而讲述者在讲述这些坏人的故事时,总是使用着赞赏的语气,脸上总是洋溢着心驰神往的神情。”[10]21-27
莫言沿着这种带有民间色彩和主体意识的历史观念对革命英雄传奇的抒写就呈现出别样的风貌,无论是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的革命英雄的形象刻画和表现的民间的历史价值观念都贯穿于他的同类题材创作的始终,只不过在表现程度和个性色彩上呈现出一些变奏的差异。这种对史诗性的推崇和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视带来的艺术观念上的变奏与中华文化传统开创的史传模式有密切的关系,正如评论家季红真所说“他对于史诗的推崇,更多地来自对于司马迁所开创的史传文学伟大传统的景仰。这一切都使他区别于二十世纪域外的经典作家,以民间的记忆恢复历史的宏大与诡谲。”[11]91《史记》并没有按照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念对失败的英雄项羽进行妖魔化的抒写,而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对西楚霸王 “力拔山兮气盖世”式的洒脱豪放、天真纯洁、胸无城府的行为方式赞叹不已,莫言也通过改编话剧《霸王别姬》进一步领悟了其中的人性的精髓,所以他的革命传奇题材的小说在尽量还原历史的真相的同时,更多地是用历史参与者的本源意义上的生命价值的思考来激活僵硬冰冷的历史理性。在《凌乱战争印象》中的游击队姜司令对盗卖军火的一母同胞亲兄弟大义灭亲,在按照军法和理性原则处置亲情的时候,也设置了站在人性的角度上,对姜司令为死去的兄弟的亲情眷顾而伤心痛苦的情节,在军纪严明执法如山、英勇善战不顾生死的英雄的刚烈果断的传奇行为中,也描绘了他与三老妈柔情缱绻、儿女情长的一面。《革命浪漫主义》对英雄形象的塑造和主题的表现更多地倾向于“食、色”等形而下的需求层面,“时势造英雄”的价值观和命运观也使得他对英雄的表现渲染了黑色幽默的色调。“我们本来是跟着炮弹往越军的地窨子里扔手榴弹的,我本来是背着火焰喷射器往越军的猫耳洞里喷射火焰的,可是,我的命运不济,我一跤跌倒我就知道坐在地雷上了。”愿望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得“我”本来能成为战斗英雄的感人壮举与迫使自己的屁股坐在越军埋设的一颗小香瓜那么大的地雷上不敢有一丝松懈的滑稽行为所解构。在炸掉屁股成为残废军人住进疗养院之后,“我”非常渴望与在此工作的护士结婚生子。出生入死的红军老战士按照严酷的革命现实主义讲述的故事凸显的是“食”在危及个人生命的情况下人性中自私的一面,这些战士在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时候表现出的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确实是无愧革命英雄的称号,但在行军途中只要有一口青稞面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让任何一个人拿出决定自己命运的口粮都是比较困难的。
也许是战争的偶然因素改变一个军人的命运的机遇对莫言有太深的感触,他也是在军旅生涯中偶然的机遇改变人生命运的受益者,所以他对“壮志未酬身先死”的身体和技术素质过硬的英雄总是从人性方面予以表现。《战友重逢》中的钱英豪“大行不顾细谨”,在生活细节上对军队比较僵化的管理模式和太注重形式的评价标准是比较反感的,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夕,对连长指导员的柔性政策所发的牢骚就将一个满身正气、不怕牺牲、“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英雄人物的豪爽英姿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就是这样一个被授予一级投弹能手的荣誉称号,无论是射击、投弹、拼刺刀还是爆破、土工作业都在守备团拔尖、在军区挂号的英雄,为了掩护身边的战友,“却一枪未发就成了敌人枪下的冤屈的孤魂”。小说通过与生前的好友赵金阴阳两隔的往事回忆,对传奇式的英雄的不幸命运更多地给予了理解和同情。这种感同身受到英雄多舛的命运并给予宽慰的悲悯情怀在90年代末期的小说《儿子的敌人》中发生了变奏,如果说在此前的革命题材小说中也出现了对土匪式的英雄的赞叹和赏识,那是在民族/国家的宏大话语中凸显的抗日御侮的国族意识起到了情感铺垫的保护色的作用。而在这部比较精致的短篇小说中出现的被我方击毙的敌人,在你死我活的严酷的战争条件下,设置的把敌人的尸体错当做烈士的抬回来让烈士的母亲辨认的情节,实际上就把革命英雄传奇的变奏推向了极致。这突出地表现在烈士的母亲孙大娘在认出不是自己的儿子,而在幻觉中听到“一个细弱的像蚊子嗡嗡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之后,按照人性的本能认下了这个儿子的敌人作为自己的儿子。莫言采用了“这种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不相融的言语形式叙述和塑造人物,显示了震撼读者灵魂的威力。”[12]52 这是莫言真正站在超阶级的人性立场上,对边缘性的英雄人物按照“人”的样子进行刻画和描摹的典范之作,也是莫言的自由思想在九十年代的英雄形象的探索中最鲜明的表征。
三、百年历史的史诗性创生与颠覆
如果把莫言在八九十年代创作的小说看作是一个对历史的镜像反映的大文本的话,那么这部大文本集中表现的是中华民族百年历史的沧桑变迁。莫言从民间的边缘视角审视和把握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社会的风云变幻是带有史诗性企图的,这首先与莫言的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立场和自由思想有密切的关系:“莫言小说的自由思想也体现为超越意识形态制约的历史观。” [13]79也就是说,在莫言对教科书书写的官方的历史不再采取红色经典的图解和演绎的方法论证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唯一性,而是在地域文化的集大成者——高密东北乡的文学王国中重新建构方志式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的时候,史诗性的创生与颠覆的叙写策略就形成了不同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的历史风貌。
从八九十年代莫言小说史诗性创生和颠覆的内在连续性方面来看,他对百年历史的反映采用的是以人物的行为表现为纲、历史事件的发展变化为维的纪传体式的方法。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反映统摄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中,尽量淡化历史和时代背景。但通过对莫言小说反映的时间和事件的谱系寻踪不难发现,百年历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比较鲜明的反映。特别是对贯穿百年纷纭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生活的描摹,无意中凸显了莫言要为历史的发展做书记官的史诗性欲求。正是因为莫言不同于巴尔扎克式的逼真的、鲜活的反映历史本质的企图和雄心壮志,所以他对历史事件的处理总是采取模糊或淡化的方式。正如《透明的红萝卜》对文革的反映一样,“有意识地淡化政治背景,模糊地处理一些历史的东西,让人知道是那个年代就够了。”[14]81在历史背景的淡化背后站立的是一个能够反映历史另一番面貌的有血有肉的人,在这篇小说中对文革期间的农村欢乐与痛苦并存、理想与现实联姻、贫穷(物质)与富有(精神)携手的多色调的历史生态的还原,是莫言在文革时期的乡村生活的记忆对拨乱反正时期意识形态的宣传和血泪斑斑的伤痕文学的反叛,也是莫言采取唯物主义的辩证色彩对文革时期的乡村进行民间抒写的时候追求的史诗性的“真”。 但当莫言刻意地追求生活艺术的朦胧美、含蓄美和神秘美的时候所展示的主观化的夸长和变形显然又是对史诗性的“真”的背离。对他来说,史诗性的复调和驳杂色彩的形成与他对既定的文学规范的反叛和历史生活中作为主体的人的重视有很密切的关系。莫言的深刻性就体现在这个地方,“他试图超越历史直接窥查人的本性,历史在他这里只提供了一种外在的刺激,他更关心人心和人性的种种反应。” [15]217这样,在莫言八九十年代创作的大文本的史诗性框架下,物是人非难以真正恢复原貌的历史就成为人性的试验场和展示人物主体性的参与意识的舞台。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由于莫言太关注人性在历史的封闭区间的发展变化,史诗的碎片化和模糊化又在创生与颠覆的力量纠结中呈现出变动不居的风貌。
在百年历史的沧海桑田的发展变化中,莫言的小说用天马行空般的自由思想将世界各地的山川风物、人文景观都搬迁到高密东北乡,生花妙笔的点化和渲染自然浸润了主体的感觉化的色彩。对历史的从点到面、点面结合的反映和表现搭建了文学故乡的史诗性结构的背景,在历史的前台活动的是一些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排斥的边缘人物,他们行为的狂放不羁、性格的叛逆与执着、富有野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都为历史的发展抹下了多彩的一笔。所以,把莫言的小说作为一个大文本来观察,对之所反映的历史时代按照序列的方式排列起来,就构成了一部比较完整的乡土中国的百年变迁史。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地方史的方志体叙事策略所造成的史诗性的漫漶和扩散又使它具有了隐喻的色彩。正如有的学者所评论的:“他对高密东北乡全景式的文学书写建构出长河似的历史序列,形成一部文学的地方史。”[16]160
由此可见,莫言在还原历史的过程中,按照传统的价值观念理解的历史成为表达他的主观化认识愿景的能指,历史的所指成为“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媒介。他的夫子自道就将他展示主观意义上的历史真相的企图暴露无遗:“我认为小说家笔下的历史而不是教科书中的历史,但我认为这样的历史才更加逼近历史真实。因为我站在了超越阶级的高度,用同情和悲悯的眼光来关注历史进程中的人和人的命运。”[17]64所以,他的小说中呈现的史诗性和反史诗性的辩证统一的特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注 释:
[1] 莫言、王尧:《从<高粱>到<檀香刑>》,《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2] 莫言:《我的<丰乳肥臀>》,《用耳朵阅读》,作家出版社,2012年。
[3] [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商务印书馆,1981年。
[4] 莫言:《超越故乡》,《名作欣赏》,2013年第1期。
[5] 莫言:《<丰乳肥臀>解》,《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1期。
[6] 唐韧:《百年屈辱,百年荒唐──<丰乳肥臀>的文学史价值质疑》,《文艺争鸣》,1996年第3期。
[7] 吕周聚:《中国左翼文学中的美国因素》,《文学评论》,2016年第6期。
[8] 莫言:《关于<红高粱>的写作情况》,《南方文坛》, 2006年第5期。
[9] 张清华:《莫言與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以<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为例》,《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10] 莫言:《用耳朵阅读》,《天涯》,2002年第2期。
[11] 季红真:《神话结构的自由置换——试论莫言长篇小说的文体创新》,《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
[12] 庄森:《莫言小说的自由思想》,《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2期。
[13] 张军:《莫言:反讽艺术家——读<丰乳肥臀>》,《文艺争鸣》,1996年第3期。
[14] 贺立华、杨守森编:《莫言研究资料》,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
[15] 夏志厚:《红色的变异》,《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16] 宋学清、张丽军:《论莫言“高密东北乡”的方志体叙事策略》,《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6期。
[17] 莫言:《小说的气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
责任编辑:王作新
文字校对:孙 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