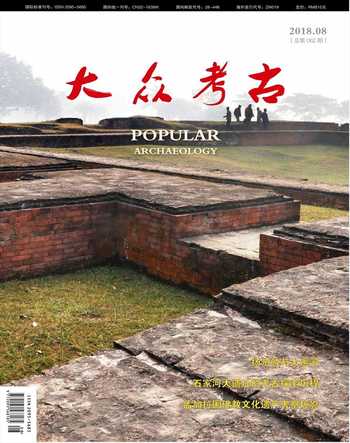甗形盉——江淮、皖南的青铜器瑰宝
2018-09-10余飞白国柱
余飞 白国柱

半个多世纪以来,江淮、皖南地区陆续出土过一种造型特别的青铜器——甗形盉。这种盉,整体上呈甗的形状,但个体较小,有箅子,有短流,有柄。从目前资料来看,这种青铜质地的盉出现的时间比较集中,大致处于西周晚期至战国早期这个时间段内。当地在铜盉出现以前,便已经有了类似形态的陶盉,且经历了数百年的演变。尽管这种铜器非常典型且极富特色,我们在文献典籍中却找不到相关记载,也不见该类青铜器的自铭,这导致学者对这种铜器的称谓不尽一致,牟永抗先生称该类器物为甗盉,李国梁先生则称之为甗形盉。考虑到该类器物的形态、大小以及功用,本文采用李说。
目前的主要发现
目前所见的甗形铜盉,出土地点主要集中在巢湖以西平原区、皖南的濒江地带,大别山以南的皖西南沿江区也有分布,以舒城—肥西一带、铜陵—繁昌一带分布最为密集。
也有少量甗形盉见于安徽以外地区,如河南光山、河南信阳、湖北汉川、湖南衡南、浙江绍兴各出土1件。
大小、分类和演变
甗形铜盉的个体大多不大,口径在11—18厘米之间,多集中于13—14厘米;高度在16—22厘米之间,多集中于17—19厘米。
根据口部形态的差异分为两类,第一类为钵口,第二类为盘(盆)口。第一类铜盉大约是西周晚期出现的,并一直延续到春秋末。第二类铜盉出现的时间稍晚些,应在春秋早期,它是在钵口盉发展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
第一类甗形铜盉
西周晚期为口径偏大的敛口钵形,腹部普遍收较急形成浅腹,腹壁几乎斜直弧曲小,近口沿处收成敛口状,如肥西小八里铜盉。至春秋早中期,腹收趋于缓和,腹壁的弧曲变大,如桐城天城中学铜盉。到了春秋中晚期,腹收更缓,弧曲继续变大,呈扁鼓腹状,腹壁中部似有变直倾向,如铜陵金口岭铜盉。至春秋末期,本地已不见钵口铜盉,仅在浙江绍兴坡塘306号大墓发现1件,该盉腹缓收,上腹壁弧曲极小,呈微微的斜直腹状。
第二类甗形铜盉
该类铜盉形态呈折腹的盘(盆)形,腹部内曲,折棱随时代的不同有所变化。春秋早期,腹收较急但腹深并不小,折棱位于近口沿处,折棱以上腹壁内曲,敛口,唯一实例见于河南信阳樊君夔夫人墓,安徽暂未发现。进入春秋中期,腹部仍然较深,折棱下移至腹部略偏下的位置,折棱上、下腹壁均内曲,敞口,如铜陵钟鸣铜盉。至春秋中晚期,折棱略下移,敞口变大,如舒城河口铜盉。再至春秋晚期,腹部相对变浅,折棱位置继续下移,折棱上、下腹壁均内曲,大敞口,如舒城春秋塘铜盉。
以上是两类铜盉发展的大致趋势,总体来说二者差异较大,但也可发现其共同发展规律。时代自早至晚,均经历了腹部凸显特征逐渐下移、腹深相对渐小的变化。

除此之外,按柄部形态的不同,又可分分装柄与聯体柄。分装柄自早至晚均有发现,柄的末端为仅显示轮廓的鸟首;联体柄似出现于春秋中期之后,柄的末端为龙首。柄的长度,早期短柄者居多,柄末端多不高于口部;之后长柄者渐多,柄末端也渐高于口部。
渊源
目前所见的甗形铜盉可能并无早于西周晚期者,但却有时代更早的甗形陶盉。纵观巢湖西侧、皖南地区的相关资料,我们发现与陶盉有关的考古材料较为丰富,可以推知甗形铜盉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这些地区,许多遗址出土了两周时期的甗形陶盉,如霍邱堰台、六安庙台、六安堰墩、霍山戴家院、庐江大神墩、铜陵师姑墩等,个别遗址也有明确的器物发展序列。通过分析可知,两地至迟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便已出现了同类陶盉,并持续发展到春秋晚期战国初期,而在此之后便无觅踪迹。
那么,有没有早于西周的该类陶盉呢?答案是肯定的。但略为遗憾的是,无论是巢湖以西的平原区还是与之相邻的皖南沿江地带,商时期的考古材料比较贫乏,更谈不上陶盉的发现了。将视角投往巢湖的西南侧,是皖西南沿江地区。该地区有几处遗址出土了商时期的甗形陶盉,如潜山薛家岗和安庆沈店神墩。结合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的分析可知,这些器物的年代在早商偏晚至晚商偏早阶段。尤其是薛家岗遗址,存在商不同阶段的该类陶盉。该地区缺乏西周时期的甗形陶盉,唯一一件是在枞阳汤家墩发现的。跨过皖西南再往西,在接近长江中游、下游交汇处的江汉地区也发现了类似陶盉,如阳新大路铺、大冶蟹子地等遗址,但所见的同类器物年代似在晚商阶段。
在经过以上梳理以后,我们基本可以明确甗形陶盉的渊源和演进顺序。初步判断,这种形态的甗形陶盉最早出现于皖西南地区,然后逐步发展影响到江汉、巢湖西及皖南地区。
国别与族属
甗形铜盉多和鼎同出于贵族墓葬,偶见单独出土者。这些甗形铜盉的出土地点,多见于群舒故地,不见于中原,是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礼器。那么,这种铜器是否属群舒特有呢?
群舒并非单指一个国家,有舒鸠、舒蓼、舒庸、舒龙、舒鲍、舒龚等,另有宗、桐为其属国,分布在巢湖以西平原及皖西南地区。它的北向、西北方向,有六、巢、蓼、州来、英、黄等诸国。这些方国,属地变化频繁,如巢本在巢湖北,后迁至巢湖南或西南;蓼本在英之北,后附于舒,可能迁至巢湖西。这些方国中,巢、桐为子姓,后附于群舒;黄为嬴姓;其他则为偃姓。河南信阳黄君夔夫人墓、光山黄君孟夫人孟姬墓均出土有甗形铜盉,另外,光山黄季佗墓也出土了甗形陶盉。这些墓葬的年代均属春秋早期偏晚,确切时间是在楚灭黄之前(公元前648年)。考虑到黄与群舒有亲缘关系且地域相接,那么在黄国故地出现该类甗形铜盉则是可以理解的了。由偃姓衍生出来的族属多分布于江、汉,多为小国,其中两个为“贰”和“轸”。何光岳先生曾考证,“贰”在湖北随州之南;“轸”初在湖北应城附近,为楚所亡后迁于岳阳附近。湖北汉川、湖南衡南所见的甗形铜盉,很可能便是和这两个偃姓国家有关。绍兴坡塘所见的甗形铜盉的时代,已到了春秋末期,甚至可能晚至战国初。《左传》记载:“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其时为定公二年(公元前508年)。同是在此年,“桐叛楚”。群舒诸国在此之前便已陆续亡国,有一部分鸠人过江南下逃往吴地,至今芜湖一带仍有“鸠兹港”。靠近长江边的柳春园出土的甗形铜盉或许与之有关联。镇江北山顶春秋晚期墓出土的自铭为“甚六”的铜器,经考证为群舒遗物,很可能便是与群舒各国在灭国后族群的迁徙有关。绍兴坡塘甗形铜盉,更像是群舒铜器的挽歌,从此便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了。
铜陵、繁昌、南陵沿江地带也出土了较多的甗形铜盉。过去研究多认为,巢湖西的平原区及皖西南沿江地带应为群舒故地,而这些地区的出土情况证明其可能属实。徐中舒先生考证,现无为县姚沟镇一带为史载的“庸浦”,其地属舒庸。可能确如徐先生所言,滨江的“庸浦”确为舒庸属地。那么,与此相距仅二十公里之遥的江南之地的铜陵及相邻地带,可能在历史上也曾属群舒。
甗形铜盉并非群舒族群的特有器物。早在群舒族群到达江淮以前,甗形陶盉便有了数百年的发展。而偃姓的群舒是从徐方分生而来,均属东夷集团之后,而徐擅于冶炼青铜之物。而群舒族群集中南迁淮河流域的时间为西周晚期。可能便是这些族群,带来了先进的冶炼技术。在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因素并水乳交融之后,从而促使了甗形铜盉的产生。春秋时期各国之间势力错综复杂,黄、英、六、蓼、州来等诸国陆续为楚所灭,其后群舒暂附于楚。之后至群舒国灭之前约有百年左右的时间,甗形铜盉得以继续发展、大放异彩,成为群舒族群最有代表性的青铜礼器。
(作者余飞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白国柱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