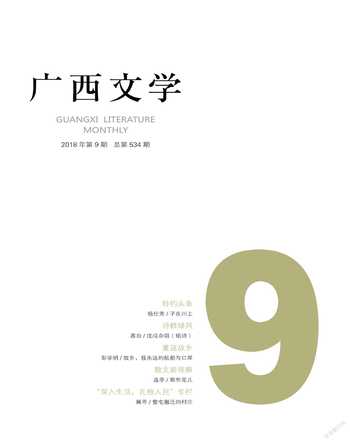悖谬与抒情
2018-09-10张清华
张清华 1963 年10 月生,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出版《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天堂的哀歌》《文学的减法》《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等著作十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理论与评论文章四百余篇;涉猎诗歌、散文写作,分别出版散文随笔集和诗集。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 年度批评家奖、第二届当代中国批评家奖等;曾讲学德国海德堡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遇见》应该是田湘的第四本诗集。
十年前我通过作家东西认识了田湘,之后共读过他的三本诗集。最早的那本《边城》是我认识他之前出的,似乎还带了初学的一点点痕迹,印象不是很深了。我觉得田湘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他说话声音大,笑声特别地爽朗,爱喝茶,喜沉香,喜与朋友唱酬,人又特别谦虚,总爱一本正经地向别人请教诗歌写作的问题。总之是一个认真而又有趣的人。
我个人的田湘阅读史,主要是由他后来的三本诗集构成的。第一本叫《虚掩的门》,第二本是《放不下》,第三本是《遇见》。我记得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有一段话,大意是“古今成大事者,必经历三种境界”:第一种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即有所期待、企望。这让我想起《虚掩的门》,那时他情感和经验的门一直兀自开着,期待有人造访,有作为“不速之客”的不期而遇,有某种情感撞击的力量来接近他。说白了,他是用一种情怀,一直守望,来期待某种境遇的降临,期待这个世界走近他。而这种状态,在我看来恰好与王国维先生说的“第一重境界”类似——首先得有所思,哪怕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且“强说愁”毕竟与“万古愁”也是相通的,也是一个必要的过渡。
第二重境界,便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了,它是一个僵持的时期,经历煎熬与消磨,甚至会因为这些煎熬而“生病”,所谓“放不下”。若是能够放下自然也就心宽体胖了,但是此兄天性固执,一根筋,甚至偏执症。可是古今所有成功的人,无不是因为这种偏执症,唯有固执和坚持,人方能够苦思冥想,有所探求,唯其矢志不渝,方才“衣带渐宽”。这一重境界可能就是漫长的过程,是比较折磨人的一个时期。对田湘兄的诗歌而言,也是一个历经痛苦蜕变的时期。他早期的那些比较纯美和感伤的意绪,在这个阶段也逐渐被更深入的经验探求,被某些潜滋暗长的哲学意识所僭越。
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所谓的成功,当然也就是第三种境界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意外的发现,不期而遇,当然也就是“遇见”了。在王国维看来,真理的出现或者顿悟的情境,并不是穿越裂帛、惊天动地、海枯石烂、石破天惊之类的境地,而是一种踏雪无痕、飞鸿雪泥式的巧遇,不经意的发现,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踏破铁鞋”是第二重境界,随之而来的遇见,却是始料未及的返璞归真和洗尽铅华之时。《遇见》这部集子,在我看来,渐渐有此种气象了。
这样说来,田湘在最近的十年时间里,由“旧病复发”重拾诗歌,到历经探求和守望,最后愈发纯熟、成其正果,也刚好是我作为读者一起经历和见证的。从最初大学时代狂热的文学青年,文学社的社长——东西和凡一平都曾是他的随从,到中间很多年投身俗务,凫水于衣食粱谋,再到中年以后的旧事重拾,这个过程就像王国维所说的三重境界,到这部《遇见》,他的诗渐入佳境,越写越好了,越写越松弛了,越写越不经意间触及许多最敏感最核心的东西了,这是一个充满变化和成长的写作道路,也是一个充满喜悦和体悟的阅读历程。我相信诗歌就是某种直抵核心的东西,拥抱它,当然有时也有可能是一种轻轻的抚摸或是擦肩而过。诗歌的境界和可能性是无限的,田湘越来越明白这一点。他的《雪人》这样的作品,可谓读之让人怦然心动,让人久久无法忘怀,就是因为他用细节和形象,刻画出了时光与生命中的冷酷与大爱,也进而表达出命运的悲伤与无常。可谓以轻代重,四两拨千斤,用了平常的话语,并不奢华的修辞,便达到了直击心灵的程度。
再一个强烈的感受,是关于抒情的问题。田湘是一个真正的抒情诗人,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有着抒情诗人的本色,我以为是非常不容易的。诗歌写作千差万别,但在我看来只有三种情况,一是用脑子写,二是用心去写,第三种是用身体去写。用脑子写的人,他很可能突出了诗歌的思想与智性,诗歌里面那些复杂的、悖谬的、各种各样经验的处理,他会把诗写得很缠绕和复杂,写得非常丰富和有深度。有的人是用身体去“写作”的,这方面有成功的例子,也不乏粗俗和粗鄙之作,如弗洛伊德所说,“文学是力比多的升华”,身体写作是把没有升华的力比多直接端出来了。对田湘而言,这两种写作基本上都与他无缘,我觉得他总体上是一个“用心”写作的人,他并不追求诗歌中特别复杂的东西,但他是一位非常坦诚、非常执着、非常真诚地表达感情的诗人,在诗歌中他乐意塑造一个很容易“受伤”的抒情者形象——但我想多数情况下他是“装”的,“装”是诗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像我个人有时候也写,我写之前总是要先“装”一会儿,我先将角色置换为一个诗人,然后自己开始变得脆弱且容易受伤——我指的是要让自己处于一种角色感之中,关于语言和经验的状态,处在一种高度敏感且微妙的状态,方能有灵感和冲动。所谓“神灵附体”的感觉,无非也就是这种神经质的敏感状态。
田湘的诗中有很多地方让人怦然心动,他喜欢写容易受伤的自己,或者镜像,写得最感人的受伤者即是沉香,《沉香》这首诗之所以感动了很多人,大家都说写得好,其实他不是写沉香,而是设想人的境遇,也是写他自己。因为沉香的生成过程,确实是一个事件、一个灾难,压抑与沉埋,错过与死灭。沉香就是“没有遇见”,很多年不被赏识,最终因为某个机缘而得见天日,得觅知音。顺便说一句,他的《沉香》比《黄花梨》写得好,因为黄花梨没有受过沉香那么多灾难。这便是生活和诗歌的辩证法了。
田湘喜欢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灵感,发现诗情,然后从中提炼出有意思、有情感色彩并保有原生的生命体验的,且饱蘸了生活的汁水的那些部分,提炼出其中精华并把它点染成诗句。他喜欢炼字炼句式的写作,所以他的作品不是那种一团一团的块状的东西,不以意境为主——尽管像《雪人》那样的作品也很有意境。他常常是以某种辩证的哲理或者生命的悖论的体察作为诗意的旨归。但如果仅仅视其为“哲理诗”不足以肯定他的特点和价值,因为他近些年的作品,好就好在既有哲理,但同时又常常有一个非常适度的感性形象来作为载体,又很好地保留了他抒情的本色,这就使他在原有的特色之上,变得更加丰富和成熟。
田湘也是一个“较劲”的诗人,像逆时针,“在加速的时代寻找缓慢的爱”,这是他一首很不错的诗歌的名字。他喜欢逆着来,我觉得这也是诗歌的本源,他自己的一个本色。田湘多数感动我的诗基本上可以看作是“自画像”,充满了自我欣赏、自我剖析、自我想象与自我虐待的复杂冲动。他的《遇见》便是一首自画像式的诗,我建议大家关注一下。他是一个喜欢思索悖谬的人,一会是太阳的冰凉,一会是月亮的灼热,充滿了多重的悖谬,他也善于在生活生命的悖谬中去找诗情。
还有一点,我比较欣赏田湘的诗写得越来越轻逸,或者说越来越松弛,但是境界却比原来更高了,有了很多机智、很多反讽、很多跳脱的东西。他那首叫《况且况且》的诗,“况且况且”其实是火车行驶的声音,这样的东西都能够入诗,确实是达到了信手拈来的地步。这也回应了我刚才所引的王国维先生的三重境界。我希望田湘今后能够一直保有这样一颗诗心,非常日常地、生活化地,非常潜意识化、也非常直觉化地进入诗意之中,这种状态对于写作本身而言,正意味着进入一种自由之境。
一个纯净敦厚、一根筋、执着的人,一个未经污染或者很少心有旁骛的人,一个经历了多年世俗的浸淫却仍保有一颗纯洁纯粹的心的人,这种境地是殊为难得的。我希望田湘能永远保有这种本色。希望他的诗能写得更好——今后不止“用心写”,更希望看到他“用脑子写”甚至偶尔也“用身体写”,写得更跳脱松弛,更诙谐反讽,更复杂一些。这是我的希望,也是预感,因为我从多年的阅读中,仿佛已看到了这些前景。
责任编辑 冯艳冰
特邀编辑 陆辉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