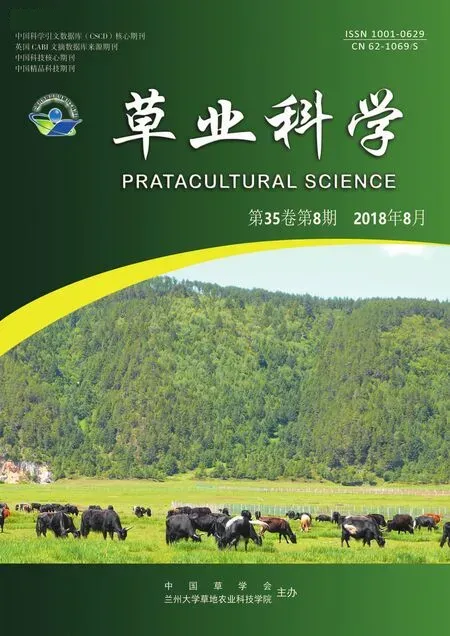中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碳排放的对比分析
2018-09-06李重阳
高 晶,唐 增,李重阳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兰州大学农业农村部草牧业创新重点实验室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食物消费是人类最基本的消费行为与需求,是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在进行食物消费过程中因食物的生产、加工、运输等多个环节中都有能源和物质的消耗,进而引起温室气体的排放[1]。目前,有关食物消费带动相关能源的消耗对全球气候变化及碳循环的影响已有诸多报道[2-3]。研究显示,与食物消费相关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已达到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9%~29%[4],其中消费动物性食物引起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已占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8%[5]。早在1976年,Leach等[6]首先就食物消费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之后荷兰[7]、美国[8]等陆续开展了食物消费与温室气体排放、食物能源消耗方面的研究[9]。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食物消费对环境的影响,家庭碳代谢法、投入产出法等不同的计算方法也随之运用于测算居民食物消费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乡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和模式发生了变化,食物消费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差异也在不断变化[9]。为进一步研究城乡居民食物消费产生的碳排放的差异,本研究通过搜集大量相关数据,从食品消费的根源入手,运用综合食物碳排放系数和生命周期法,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对我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引起的碳排放量进行更为全面的测算,在众多学者的研究[10]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探讨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碳排放的特征及差异,进而为食物生产相关部门制定减排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与数据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引用2000-201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畜牧业年鉴》、《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查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资料》的数据。选取其中的人均食物消费量、各类畜禽肉类产量、消费量及零售价格、城乡居民户均规模、每百户家庭拥有冰箱数、交通运输和仓储产生的能源消耗量和总产值等指标进行深入分析。
1.2 数据处理
1.2.1直接碳排放 食物消费直接碳排放量(Wc)等于食物消费量(Qi)与综合碳折算系数(Ri)的乘积[9]。其中,综合碳折算系数是借助罗婷文等[11]的直接碳排放系数和动物性食物的料肉转化比例计算得到的。动物性食物的料肉转化比例分别为猪肉2.86 kg,牛羊肉3.4 kg,禽肉及蛋类2.3 kg,奶类1.11 kg,水产品1.8 kg[9],经处理,各类食物的综合碳折算系数分别为粮食1.199、鲜菜0.099、水果0.183、植物油4.250、猪肉4.360、牛肉5.009、羊肉5.009、禽类3.689、蛋类3.311、奶类1.562、水产品2.684。
1.2.2间接碳排放 居民食物消费产生的间接碳排放量是采用生命周期法将各类食物的生命周期流程划分为生产、运输仓储和加工消费几个环节分别进行测算[12]。
(1)生产阶段:生产阶段碳排放包括两部分,一是植物性食物(包括饲料用粮)生产过程中,农药、化肥施用产生的排放W1。该部分的计算是利用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得出的碳折算系数[13],以及我国各类农药化肥比例计算得到农药和化肥的碳折算系数(分别为18.007、2.501 kg CO2·kg-1)[10],结合我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农药化肥足迹进行计算[14];二是牲畜胃肠道发酵及粪便排放产生的碳排放(W2),包括甲烷(CH4)及氧化亚氮(N2O)的排放。具体计算参见王益文和胡浩[12]的方法。各类畜禽对应的CH4和N2O的排放系数如表1所列。
(2)运输仓储阶段:运输阶段产生的碳排放,主要包括运输工具能源消耗产生的排放和仓储产生的碳排放。计算公式为E2=Li×X×(CT/VT)×2.493。
式中:Li为各类食物的物流成本占食物价格的比例(植物性食物为45%,动物性食物为65%[17]);X为各类食物的消费支出(万元);CT为交通运输业的能源消耗(万t 标准煤);VT为能源运输业的总产值(万元);2.493为标准煤的碳折算系数[12]。

表1 各类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系数Table 1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coefficient of various livestock and poultry
(3)加工消费阶段:加工消费环节的碳排放主要包含食物的储藏及食物加工消费(食物初加工和烹饪)产生的碳排放。食物消费的过程中涉及初加工的主要是农副产品,在本研究中,食物的初加工过程只考虑粮食与植物油的初加工。设定粮食的初加工采用中型碾米机,功率为41 kW,主要参数是4.5 t·h-1,对植物油进行初级加工使用的机械参数为0.21 t·h-1,功率为7.5 kW,电力碳折算系数为0.85 kg·kWh-1。烹饪产生的碳排放量(E3)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3=Estorage+Ecook;
Estorage=Efridge×Yi×N/100n×2.493;
Ecook1=0.4×2.09×Ti×M×2.493;
Ecook2=100×Pi×2.493。
式中:Estorage为食物贮藏产生的碳排放(kg);Ecook是对食物进行初加工和烹饪产生的碳排放量(kg);Efridge为家用冰箱年均耗标准煤的量(万t);Yi为各类食物消费在总食物消费中所占的比例;N为每百户居民所拥有的电冰箱数(台);n为家庭户均规模;Ecook1表示城镇居民烹饪产生的碳排放量(kg);2.09为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kg·m-3),0.4为燃烧效率(m3·h-1);Ti为煮食各类食物所需时间(h);M为人均畜禽消费量(kg);Ecook2表示农村居民烹饪产生的碳排放量(kg);Pi为各类食物占总烹饪食物的比例[12]。煮熟各类食物所需的时间分别为粮食70 min·kg-1,蔬菜4 min·kg-1,畜肉类80 min·kg-1,禽肉20 min·kg-1,蛋类50 min·kg-1,水产品20 min·kg-1[18]。
1.2.3不同因素对碳排放量的影响 食物消费碳排放量受GDP指数(A1)、可支配收入(A2)、食物消费支出(A3)、恩格尔系数(A4)和食物消费价格指数(A5)等因素的影响,为分析以上5个因素对食物消费碳排放量的影响,本研究利用LMDI分解模型分别计算这5个因素对人均食物碳排放量的贡献[19]。计算方法:
ΔA=ΔA1+ΔA2+ΔA3+ΔA4+ΔA5;
式中:E0和Et为0-t时期食物消费碳排放量(kg);ΔA为食物消费碳排放量的变化;ΔAi为0-t时期内各因素变化对人均食物消费排放量的贡献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居民食物消费结构
随着居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图1)。近15年来,我国城镇居民食物消费中其他植物性食物及动物性食物的消费比例变化幅度较小。其中,2000-2007年其他植物性食物所占比例基本保持不变,2008年有所增加并达到最大值59%,之后出现缓慢下降的趋势,至2014年下降到45%;动物性食物所占比例略有增加,由2000年的18%变为2014年的21%;粮食消费所占的比重在2008年之前呈下降趋势,2008年之后逐年增加,2014年较2000年增加了27%。在此期间我国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变化较为明显,动物性食物所占比例由2000年的7%逐年增加到了2014年的14%;其他植物性食物所占的比重虽变化不大,但仍稳中有增;粮食的消费量则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2000年居民粮食消费量所占比例为61%,超过总食物消费量的一半,至2014年已下降到49%。
2.2 食物直接碳排放量
城镇居民粮食消费产生的直接碳排放量明显低于农村居民,但二者之间的差距在逐年缩小(图2)。2000年城乡居民粮食消费产生的直接碳排放量的比例为1∶3,至2014年城乡居民粮食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差距变小,比例仅为1∶1.4,且仍有继续缩小的趋势。除粮食消费外,城镇居民其他食物消费产生的直接碳排放量均明显高于农村。
城镇居民各类食物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均呈上升趋势,但人均粮食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在2000-2012年期间并未发生大幅度变化,基本保持在95 kg左右,自2012年后,随着粮食消费量的增加,碳排放相应增加,2014年达到140.4 kg,较2000年增长了42.4%。2014年城镇居民消费其他植物性食物和动物性食物产生的碳排放量较2000年分别增长了14.6%、24.2%。在此期间,农村居民食物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整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趋势,与粮食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粮食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由2000年的299.84 kg快速下降到2012年的196.84 kg,降幅为34%,之后出现缓慢回升的趋势,其他植物性食物和动物性食物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增长速度较快,分别由2000年的37.22、101.75 kg,增长到2014年的52.03、167.97 kg。
2.3 食物消费间接碳排放
从生命周期各阶段来看,城乡居民食物消费间接碳排放量均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各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城乡居民食物消费在生产阶段的碳排放量的增长较为缓慢,在整个生命周期碳排放过程中所占比例也最小(图3)。城镇居民在该阶段碳排放量由2000年的183.06 kg增长到2014年的223.64 kg,增长了22%。农村居民对肉类消费的增长幅度大于城镇居民,因此,截至2014年,农村居民食物消费产生的碳排放较2000年增长了27%,涨幅略大于城镇居民。运输及仓储阶段是城乡居民碳排放量增长最为迅速的一个阶段,尤其是2008年后出现显著上升,2014年城镇居民在该阶段的碳排放量达到443.51 kg,是2000年的2倍之多,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产生的碳排放量也由2000年的186.95 kg增长到2014年的307.64 kg。城乡总体对比发现,城镇居民在运输阶段食物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基本是农村居民的1.4倍。2000-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在加工消费阶段的碳排放量要高于生产和运输阶段产生碳排放量;2008年之后,在该阶段产生的碳排放虽显著高于生产阶段,但开始低于运输阶段产生的碳排放,城镇居民在该阶段产生的碳排放由2000年的303.23 kg,增长到2014年的399.41 kg,增长了27%;相比城镇居民而言,我国农村居民在该阶段的增长幅度较小,从2000年到2014年增长了15.51 kg。

图1 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对比Fig. 1 Comparison of food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图2 城乡居民消费不同食物种类的年均直接碳排放量Fig. 2 Annual direct carbon emissions by category from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图3 城乡居民生命周期内食物消费产生的碳排放Fig. 3 Carbon emissions from food consumption in the life cycle stage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2.4 食物消费碳排放总量
2012年前城乡居民人均食物消费量的变化趋势截然相反,2012年后开始同步增加,城乡居民食物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虽总体呈增长趋势,但城乡之间的增长幅度仍存在较大差异(图4)。我国城镇居民人均食物消费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较小,2000-2014年人均食物消费量上涨9%,对应的食物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却同比由1 070.07 kg迅速增长到1 531.51 kg,涨幅达43.1%,食物消费碳排放的增长速度达到了食物消费数量增长速度的4.8倍;2000-2012年,在粮食消费量逐年下降的影响下,我国农村居民人均食物消费总量也呈快速下降趋势,2012年后有所增长;但农村居民在2000-2014年食物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仍呈逐年上升趋势,虽然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不及城镇,但在此期间仍由1 023.26 kg增长到1 179.09 kg,增长了15.2%。通过对比发现,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食物消费在数量上的差距不断减小,由2000年的1∶1.27减小到2014年的1.04∶1,而食物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的差距却在不断拉大,2000年城乡碳排放的差距为1.05∶1,到2014年变为1.3∶1,且仍有继续变大的趋势。

图4 2000-2014年城乡居民食物消费及碳排放总量对比Fig. 4 Comparison of food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from 2000 to 2014
2.5 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LMDI分解模型分别计算出各因素对人均食物碳排放量的贡献值(表2)可以看出,人均GDP、可支配收入、食物消费支出以及食物消费价格指数对食物消费碳排放量起到促进作用,且以上4个因素对城镇居民的影响要明显大于农村居民的影响,在2001-2014年,对城镇居民食物消费碳排放的贡献值达到农村的1.3倍。在起促进作用的几个因素中人均GDP的影响最为明显,在相同年间对城镇和农村的贡献值分别达到10.81、9.46 t;相比而言,食物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最小,仅为1.01、0.82 t;恩格尔系数的变化降低了人均食物消费碳的排放量,但影响并不大。通过对比发现,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对城镇的影响低于农村,在这14年间,恩格尔系数降低使城镇食物消费碳排放减少0.95 t,农村则达到了1.48 t。

表2 不同因素对城乡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碳排放的影响Table 2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factors on carbon consumption in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
ΔA1、ΔA2、ΔA3、ΔA4、ΔA5分别表示为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食物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和食物消费价格指数对碳排放量的贡献,ΔA为食物消费碳排放量的变化。负值表示对碳排放量是减少的作用,正值示对表示对碳排放量是增加的作用。
In the table, ΔA1, ΔA2, ΔA3, ΔA4, and ΔA5are considered as the contribution of per capita GDP,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per capita foo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the Engel coefficient, and food consumption price index to carbon emissions. ΔA represents the change in carbon emission from food consumption. Negative values indicate reduction in carbon emissions, and positive values indicate increase in carbon emissions.
3 讨论
本研究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分析我国城乡居民的食物消费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发现我国城镇居民在饮食习惯和消费结构方面仍与农村居民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城镇居民的食物消费对碳排放的影响更为明显,由于城镇居民消费的动物性食物较多,且动物性食物对应的碳排放系数高于植物性食物,因此,城镇居民的食物消费模式较农村居民而言更不利于降低食物消费产生的碳排放[20]。
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的直接碳排放量在2010年前由于农村居民的粮食消费量远高于城镇居民,导致直接碳排放量也高于城镇居民,2010年后城乡居民食物消费量的差距不断缩小,尤其是粮食消费量差距缩小,动物性食物消费逐年增加[21],使得城镇居民食物消费的直接碳排放量开始高于农村居民。
在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的生命周期内,食物消费各阶段的碳排放量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农药化肥的使用是生产阶段影响CO2排放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农药化肥的使用不仅仅影响碳排放,对环境也有不利影响。如何通过调整农业结构,包括种植业结构,减少农药化肥使用对于降低碳排放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学者大力提倡的草地农业则是未来我国农业调整的重要方向之一。通过发展草地农业,用优质饲草代替饲料粮种植,不但可以满足生产动物性产品对饲料的需求,还可以提高土壤肥力,从而大幅度减少化肥用量,降低碳排放量;此外,草地农业的种植模式还可丰富农地的生物多样性,提高作物抗病能力,减少病虫害,减少农药的使用,会进一步降低碳排放[22-23]。研究表明,与粮食作物相比,投入相同的农药、化肥可以生产出更高产量的优质牧草,经济回报率也更高[24]。
有相关数据显示,我国交通运输能源消耗较大,仅在2000年到2010年期间我国交通运输业的能源消耗就由1亿t标准煤增长为2.61 亿t[18],有学者认为,在人类消费活动过程中,交通运输产业已成为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碳排放增长速度最快的领域之一[25]。本研究发现,运输及仓储阶段是生命周期内碳排放增长最为迅速的一个阶段,这可能是由于城乡之间的消费习惯和人均收入的差异导致的。农村居民食用的大部分食物可自给自足,食物消费以当地食物为主;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高,对反季节性食品及各类生鲜产品更为喜爱,所以消费外地食物的频率要远高于农村居民,使得能源消耗增加导致运输阶段城镇碳排放量显著高于农村[10]。该结果与Pradenas等[25]的研究基本一致。鉴于此,在加强低碳食物消费、节能减排的宣传和教育的同时,要积极引导城镇居民尽量消费当地的季节性食物。与此同时,我国还应努力提高食物消费相关行业特别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例如可通过开发新能源、采用环保型交通工具和提高运输效率等方式来降低食物消费带来的碳排放。
本研究发现,城乡居民食物消费在加工消费环节的碳排放量的增长幅度并不大。虽然我国居民对动物性食物的消费逐年增加,导致烹饪肉类食物因耗费大量能源产生更多的碳排放,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低碳能源的开发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致使我国居民的能源消费结构不断改善,烹饪食物所用的能源也更加趋向环保[26],尤其是在我国农村地区,炊事环节所用的秸秆、柴火等非商品性能源逐步向较为低碳便捷的商品性能源转变。因此,能源利用的转型可能是未来减少碳排放的重要措施。
此外,随着居民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食物浪费现象日益严重。丁珊[27]就曾对我国有代表性的9个省(区)的家庭食物浪费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了量化,结果表明,我国居民人均食物浪费量为16 kg·a-1,最高的人均食物浪费量可达38.6 kg·a-1,假设每年将9个省(区)所浪费的食物进行填埋并完全发酵,则相当于释放了2.7×106t的CO2。同时,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也指出,全球每年粮食的浪费量高达13亿t,损失或浪费掉的粮食占到总生产量的1/3,生产这些粮食的过程中向环境排放了33亿t温室气体。减少食物浪费可以为降低碳排放做出巨大贡献。国家应通过出台相关政策或加强宣传教育的方式减少食物浪费,从而减少食物浪费带来的碳排放[27]。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食物消费碳排放的研究越来越多,但由于没有统一的食物碳排放计算方法,且对食物消费碳排放的概念界定有所不同,导致计算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本研究计算所得的结果高于尹英琦[28]、智静和高吉喜[9]的研究结果,一方面是因为在计算食物消费直接碳排放时本研究考虑了饲料粮的碳排放,采用综合碳排放系数计算,另一方面是在间接碳排放的测算过程中,计算方法不同,且智静和高吉喜[9]并未考虑畜禽类肠道发酵和粪便排放产生的碳排放,导致结果偏低。本研究的测算结果低于王晓和齐晔[5]的研究结果,主要原因是本研究并未考虑农田作业及水稻(Oryzasativa)种植产生的碳排放。在测算过程中,由于部分数据较难获取,导致计算结果不太准确,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通过查阅相关统计年鉴和实验等方法收集更全面详实的数据,补充本研究中忽略部分食物消费的碳排放,尽可能使估算结果更准确。
4 结论
通过综合碳折算系数法和生命周期理论,本研究对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的碳排放差异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改变对碳排放量起促进作用。食物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呈逐年增长趋势,城镇居民食物消费产生的碳排放显著高于农村,且城乡碳排放的差距有继续增大的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食物消费模式不利于降低食物消费的碳排放量。
2)居民食物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显著高于食物消费数量的增长速度,其中城镇居民的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达到食物消费量的4.8倍。
3)2010年之前城镇居民食物消费产生的直接碳排放量低于农村,说明粮食消费对直接碳排放起主要作用;2000-2014年间食物消费产生的间接碳排放量城镇居民显著高于农村,表明消费同重量的动物性产品所产生的碳排放量高于植物性食物。
4)食物消费碳排放与我国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和社会的能源利用效率密切相关,提高与食物消费相关的能源利用效率可显著降低间接碳的排放量。
5)人均GDP、可支配收入、食物消费支出对居民食物消费碳排放的影响较大,食物消费价格指数和恩格尔系数对碳排放量影响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