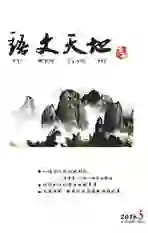一场令人玩味的对话
2018-09-03刘光泉
刘光泉
高中语文教材所选《论语》中有一段记载孔子与其四位弟子的对话场景: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
有意思的是,这一段孔子让弟子们言志的对话里,在问弟子们的人生志向之前,孔子先给弟子们做了一番减压和开导工作。他说,在年长的老师面前,你们说话不要有什么顾忌,更不要当着老师的面不说,却在背后发牢骚,说没人了解你们的志向,生发出怀才不遇的感慨。孔子说这些话的目的自然是要让弟子们在自己面前能畅所欲言,说真心话。问题是,在这里,孔子为什么突然问起弟子们的人生理想来?且又不直接问,开门见山地叫弟子们谈将来有什么打算,却要先做这一番思想疏导工作呢?其关键就在于有弟子们居则曰“不吾知也”的慨叹。由此可知,在夫子问话之前,弟子们在背地里就已发出了这样的慨叹。想必让孔子知道了,于是就找个场合询问一番。看来,平时弟子们还是有些敬畏自己的老师的,在老师面前说话多少有些顾虑,虽然他们心中早有人生规划,但不肯轻易地在老师面前说出来。可能是怕言语不当,或招来老师或同学的批评,甚至嘲笑,因而只好在背地里发牢骚,说出无人了解自己的话来。弟子们的牢骚话传到了孔子的耳朵里,孔子也感觉到了弟子们在自己面前说话的拘谨心态,因而才有了这种委婉的问话。可见,尽管孔子与弟子们的关系是亲密的,但还没有到“无间”的程度,师生之间仍然上下有别,长幼有序。当然这也符合孔子对礼的一贯要求。
更有意思的是接下来四位弟子与孔子的对话方式,折射出了各个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
这四位弟子与孔子的对话方式可分为两种情景:子路一人是主动勇跃发言的,另三位是老师点名后才发言的,尤其是最后一个发言的曾皙,是在孔子询问了两次后才把话说完。我们看到这四位弟子发言的过程是由主动到被动,而且是越来越被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发言越来越消极的情形?显然这与孔子在子路发言后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有关。孔子对子路发言不满的“哂之”,导致了后面几个人的心态起了变化,有了想法,变得谨慎了起来。
文中用“率尔”来表明子路的发言是轻率的,但我认为不妥。子路的发言并不是不经思考的轻率之举。前文已表明,弟子们心中早已有了人生规划,只是没有在老师面前表达而已,而且还苦于无人了解,此时老师主动问及,子路焉能不积极踊跃?何来“率尔”之举!
子路主动坦率自信的发言招致了老师不满的“哂之”,这让后面还没有发言的三位弟子产生了警觉。此时他们一定在心里琢磨:老夫子为什么会对子路的发言不满呢,是子路说话的方式不对呢,还是他发言的内容有问题。经过思考,根据平时在老师面前说话的经验,最后他们一定会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不能像子路那样冒然主动发言,更不能像子路那样自信满满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于是出现了冷场的局面。后面三位都不吭声了,此时耳边只听到曾皙弹奏出来的悠扬的琴瑟声。这时孔子似乎也觉察到了这点,“我不点名,他们是不会发言的”。于是只好点了。由于有了前面子路的教训,冉有的回答尽管也是谈治国的大事,但就谦虚低调了许多。
冉有回答后,孔子再没有“哂之”,而是黯然不语。这起码表明孔子对冉有的回答基本是肯定的。有了前面冉有回答的经验,让后面还没回答的人心中有了底,知道该采用何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照例,公西华是要等到老师点名后才发言的,既然老夫子喜欢谦虚谦让的回答,那么我就应该表现得比冉有更加低调,这样定会赢得老师的赞赏。因而公西华的回答更加谦虚了,而且还多了一份含蓄委婉。
最有意思的当是最后一个人—曾皙的回答了。按理四个人中已有三人回答,剩下的就是他了,該不需要老师点名了吧。但你不得不佩服曾皙真能沉得住气。此时曾皙心里可能在想,咱们今天要的就是谦虚低调,就是剩下我一个人,我也是不会主动起来发言的,你不叫我,我就不说。于是孔子只好点曾皙的名了。曾皙停止了奏瑟,起身行礼回答,从举止的细节中表现出了自己的谦虚有礼。但曾皙的回答方式和前几个人又不一样。前三个人尽管在态度语气上有所不同,但都是一次性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完,而曾皙只说了一句自己的志向与前三个人不一样的话,就停住了话头不说了,这含蓄低调得让孔子心里也过意不去了,害得老夫子又单独对曾皙做一次宽心开导工作,让他打消顾虑大胆发言。“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这语气似乎是在哀求和催促对方讲话。曾皙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此时曾皙早已成竹在胸,知道了怎样的回答能使老师感到最为满意。
通过前面的观察,曾皙发现,子路是输在了太积极主动、太过实在上,没体现出谦谦君子的风度;而冉有吸取了子路的教训,说话就收敛了许多,表现出了谦虚的态度,使老师基本上感到满意,不再“哂之”;公西华受冉有回答的启发,表现得更加虚心低调,也得到老师的肯定。但冉有公西华二人的回答只是得到肯定而已,并没有赢得老夫子的赞赏。这表明,他们二人的回答只是得到老师理性上的认可,但还没从情感上打动老师。聪明的曾皙明察夫子目前的处境和心境,于是说出了引发老夫子“喟然叹曰”的一番话来。我们不知道曾皙是否真的说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但他的确说出了孔子在现实中屡遭碰壁后的心境。知孔老夫子者,曾皙也。
从对话一开始,师生心里面就在彼此猜测、掂量着。双方都在针对对方的心思把握着说话的分寸,看似平静的对话,其实进行着一场心理暗战。
夫子一哂,使本应单纯轻松的问志对话改变了初衷,变成了沉重的老师对学生“礼”的素养考查,致使弟子们不敢畅所欲言,尽情倾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发言消极等待,心里揣磨,说话斟酌;看似谦让有礼,实则小心谨慎。这真是:盛礼之下,活人也累。
作者单位:陕西省汉台中学 (72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