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墨随心,刘学伦和他的中国人物画
2018-09-01林元亨
林元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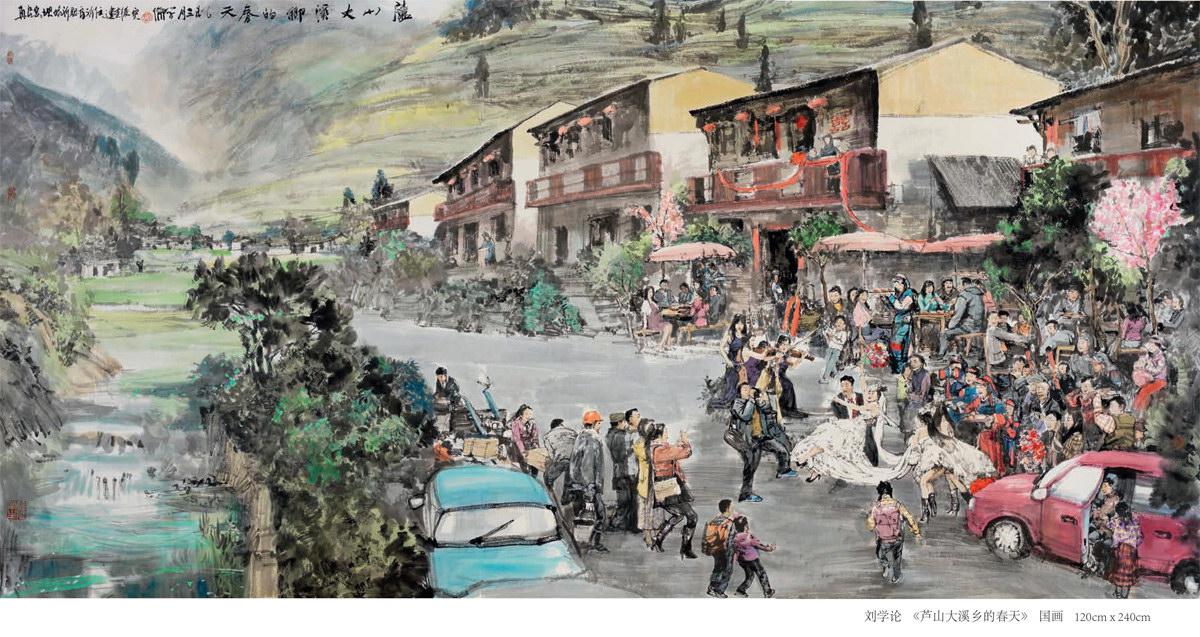

2011年3月,“巴蜀画派”首次整体集结亮相,在“第一批巴蜀画派影响力代表人物”名单中,刘学伦位列其中。对于这样的殊荣,刘学伦认为这是对自己多年勤奋绘画的肯定,同时,也是一个激励与鞭策。事实上,在绘画这条长路上,这个在50岁“好像能称自己是一名画家了”的人,他从来就没有懈怠过。
在“推广巴蜀画派研讨会”上,刘学伦说,多出好作品是根本。他认为,在打造巴蜀画派的大背景下,四川的本土艺术家应该抓住这样一个机会,要有全局观念,多出质量高的作品,因为毕竟优秀的作品才能够成就巴蜀画派的高度。而且应该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不应该昙花一现,这是一个持之以恒的事。而对于社会大众,刘学伦说:“我想社会应该对画家提出要求,画家也是人不是神,不要把画家宠坏了,那些瞎炒的事尽量少做一些,运作一定要务实。”
这是一个儒雅而安静的人,正如朋友甄先尧这样记述和他的第一次相识:“某日,朋友聚会,大家海阔天空,高谈宏论。一位儒雅的中年男子却静静地坐在旁边,在速写簿上写着画着什么,神情格外专注,他在为我们画漫画肖像。画毕,大家传看,一致认为是传神之作。”
很多时候,画家刘学伦都是这样静静地在画速写。没有谁能够打扰这个男人丰富的内心,更没有谁会想到,面前的这个人曾经是对越自卫反击战场上的一位经历过战火与生死的士兵。“这种绘画本身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当时草草几笔似乎并不能记录下什么,但经过时问的打磨后,一种‘真实被留下来了。”也许,这也正是刘学伦痴迷速写、苦练基本功的原因,他说:“我不喜欢那些矫情的照片,我认为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写生是有相当优势的。在写生的过程中,捕捉到的那种微妙的存在,才是艺术家需要追求的最珍贵的东西。”
“你的作品有生命吗?你能不能赋予它生命?你怎样赋予它生命?这些似乎只能越来越会让人迷惘的命题常常困扰着我,或者说让我不得安宁……”學伦先生把创作中国人物画的“朝圣”当作一次“飞蛾扑火”的“苦旅”,他在中国人物画艺术这条高远、厚重、超逸的心性之路上,反复思考着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话题,那就是世纪之交的画坛,中国画的变革已呈现出多元多层次的状态,是依旧延续元明清以来的笔墨形式,走重复的路?是借鉴20世纪以来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借古开今,从传统中学传统的经验?还是不断承继中国画的民族特性,开拓中国画的多元格局,找到一条有浓郁东方韵味的绘画语境,让作品真正具有“生命”?画家是这样痛苦地思索着,也是这样执著地探求着,他把自己创作的坐标最终定在了“重神忘形”之上。(马安信《立象以尽意重神以忘形》)刘学伦说,“以前做加法,现在做减法”,“五十而知天命”的他开始做简笔,“打进去要出得来”。他认为,笔触是看得见的,不是完全混在一起的,现场感区别于那些画照片的画,真正的画要有灵动的感觉。“创作是生命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置身在黄山美丽的风景中时总会情不自禁地咏唱起李白、杜甫的诗歌,是我们活在祖先的精神中,还是他们的生命在我们这儿延续,很难说清。伟大的艺术家正是用他们的创作时时温暖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切实地感受到生命存在的意义。这——也就是我在创作时经常想到的。”
《上层》:我看过你的简历,从知青、军人到考上美术系、留学日本,这些经历都相当不平凡。当时,为什么要选择去考美术学院的?
刘学伦:从小就喜欢画画,我曾经写有一篇文章《与画有关的日子》,回忆过我小时候和唐雯、黄振国等同学一起学画的一些经历。王羲之在《兰亭序》里讲过,“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大千世界,自有各种性情、各种品类,才构成人的世界。我从小就有阴影——与生俱来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驱使我们去自己的天地里寻找属于自己的东西。孤独感使我喜欢去画画。
当然,其问,也颇多周折,酸甜苦辣,一言难尽。现在,我一边教学一边创作,殊途同归,自己感觉这就是我们应该的生活,属于我们画画的美好日子。50多岁了,我们都在感叹,一起学画画的人很多都放下了画笔,而我们却觉得才刚刚开始,每一天都是好像铺在我们面前要你去画的一张新的画。
《上层》:后来,为什么又要选择出国留学呢?
刘学伦:我是1979年考上了美院又没有去,后来才意识到这很可惜。这样才发誓要到日本去拿一个文凭。后来我确实交的“学费”很多,代价太大。那时很苦,但在大阪艺大只差十多学分,因为护照的原因,也没拿到毕业证,但是现在的大阪艺大人才一览表上仍挂着我的名字,那次出国,打开了我的眼界。那时候目的不是很明确,但对我来说,是有一个契机,让我了解了国外是怎样看待中国。在国外,确定了我对中国画的认识,了解了它的精粹。那时候,我才开始画国画。我曾经和朋友在日本找工作,找到一个写毛笔字的工作,原来是写灵牌。虽然没有去做这个工作,但却给我们很大的震撼。一个异国他乡的人走完了一生,最后一次装点用的是毛笔字。你看日本、韩国、越南,他们灵牌上用的是纯粹的毛笔。
毛笔是一个神奇的东西,我们的先人们就是用毛笔开创了属于汉字的文明,艺术的职责需要我们在电脑时代的今天更加珍惜这份传统,继续用它去探索更多表现的可能性。我觉得说到中国画,第一还是毛笔,有了毛笔才有气韵,气韵生动,然后才有新意。
《上层》:你在绘本、插图、国画、油画都有涉猎,且有不俗的表现,这些也给你的基本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你觉得哪一块是你的主攻方向?
刘学伦:还是中国人物画。人非要上了一定岁数,有了一定经历,有一定的眼界过后,才会理解中国绘画的真正底蕴在哪儿,笔墨精粹在哪儿。我正在写一本书《吾墨随心》,其实仅仅是一个追求,你要想笔下流出的墨和自己的心一起涌动,肯定是一种理想的永无止境的追求——通过这个过程,这个追求,这种实践,来展示自己对中国画的理解。这个应该说是我今后确定的非常明确的一个目标。
《上层》:中国画很强调传承和师承,但现在很多国画家都把这种师承和传承当成一种时尚和价码的标签,对于传承和师承,你是怎样理解的?能谈谈你的师承吗?
刘学伦:我说两个我最佩服的人。第一个是黄胄,他速写最多,我也一样,他也当过兵,我也一样。但我不能和他比,我一直在向他学。他在世时,被攻击也较多,很多人说他是用毛笔画的速写。但现在谁还敢说他呢。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应该向像他一样,有大胆的去探索的勇气。探索是一种自觉意识,他能领悟到中国绘画的责任心,这个是一个中国画家应该具有的责任意识、时代意识。第二个是戴卫,他对现代中国画的贡献,是要求强调线的质量。现在,中国画继续得到发展,有了很多门类,但是,如果丢掉了中国画本身对线的质量要求,中国画就无法继承,中国文字本身就是一幅幅画,这些文字与世界上其他文字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独特的线条。但是这一点又不能作为束缚中国画发展的一个理由,我个人认为,比如说我,既要追求线的质量,同时又要追求它的立体感,这一点,我很明确。
《上层》:这个立体,如果说从技艺上来论的话,有师承上吗?
刘学伦:有哇,肯定有,我们去看一下郑板桥的竹子,我们去看一下徐渭的青藤与水墨葡萄……那些线条,都是立体的。我在画《金沙祭》时突然领悟到用毛笔勾出的线是有立体感觉的,重要的是看你着意去追求。
《上层》:你很强调速写,原中国美协副主席、著名画家尼玛泽仁就认为,你的艺术特色是追求写实和写意的结合,突出笔墨精神又墨不碍色,色墨合用,画面的现场感和生动感得到充分传达。
刘学伦:我其实强调的是画画的现场感。你仔细看很多速写稿,你才会发觉写实如果和写意结合能达到多么了不起的程度。
我认为速写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是观察生活的能力,你通过速写来培养自己达到观察生活的能力,来为表现生活做积累。比如说《清明上河图》,画上有一个细节,是一个大门口,躺着一个家丁,后来经过专家考证,才发现当时就是这样的,作者观察入微,以这个在大门口躺着的家丁来表现“太平盛世”的主题。
速写和照片是不一样的,要精细入微地观察生活,要看生活中问到底是怎样的。尊重现实,从真实中来,当代缺少这些东西。
我现在还是坚持画速写,只不过都经常是用毛笔来画了,用熟了以后才知道它是最快的速写工具,要细要粗都可以,所以能快,但是它又是最难掌握的工具,需要长期的练习才能达到随心所欲的境地。
《上层》:尼玛泽仁说你的作品在结合西画严谨造型的同时表现中国画的笔墨精神,在形神兼备、气韵贯通两个方面下工夫,自成一格。这个作品也在你的重要作品《金沙祭》(长13米,高2.4米,183个人物)中表现无疑。为什么要画这个看似不讨好的作品?
刘学伦:金沙出土了很多文物,但没有文字记载,作为一个本土画家,以发生在自己熟悉的生长地的故事为创作题材应该是顺理成章的,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去传承蜀文化最璀璨的部分之一——金沙。以水墨人物画再现三四千年以前的一次发生在金沙的祭祀活动,用宏大的场面、众多的人物构成一个壮阔的、史诗性的远古历史画面,这本身就是一次探索,一次探险,一次对自己的挑战。
当然,开始我画这个《金沙祭》并不明确,当我真正开始画的时候,我才明白自己,要表现生命,对生命本身的一种歌颂。那么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精力去表现那些人的盲从,是想表现我们人类世界性的一种无知、盲从的心理。其实,我真正想表现的恰恰是相反的,就是不能无知和盲从,每个人都应有尊严。
《上层》:现在,很多画家都不再强调作为一个画家、艺术家的“责任感”,而只关心市场,对于这一点,你是怎么看的?
刘学伦:晚年的时候,有人问恩格斯,你这一辈子,真正让你花去时间精力最多的去做的一件事情,与其做斗争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恩格斯毫不犹豫地回答,庸俗。其实我们都很庸俗,包括艺术家,只是在我们创作的时候,纯粹一点更好一点,可能纯粹一点对自己的作品有好处。有两种作品让人看了不舒服,一种是矫情,太造作;一种是痞子,装作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其实也是造作。
《上层》:中国画的振兴与当下面临的挑战,你有怎样的看法?
刘学伦:有的东西该进博物馆就进博物馆,我还是赞同余秋雨的这句话。因为,不是说我们非要去振兴,它就能够茁壮成长,不一定。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好多年轻人,其实已经在非常关注中国精神、中国笔墨,加进毛笔这些传统的文化根脉中来。这一点,其实,我是很有信心的。
这是两层意思,第一層,你想,你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全盘西化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肯定要面临挑战,甚至要丧失一些我们宝贵的东西;第二层,同时,在新的时代,我们不是没有希望,我们的传统文化,正被注入新鲜的血液,这种血缘式的文化谱系、艺术谱系不会断的。
《上层》: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艺术创作、艺术市场和艺术机构,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并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但艺术审美的普及,依然任重道远,而艺术的普世精神与人文关怀,还需要我们去彰显与担当,作为一个画家与教授,你有怎样的思考?
刘学伦:我认为当今中国画有一个很大的失策,就是平庸的东西太多,民众能够真正欣赏到的高水平的画作的机会很少。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喊一些口号,而是确实要做一些实事,比如说基础文明建设,就应该有对传统中真正优秀的东西欣赏的导向。这些方面,我觉得确实需要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比如说,从小学生起,就应该进博物馆,去看一些真正好的画,就像当年小平同志说中国足球要从娃娃抓起一样。
中国画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它是实在的,比如说笔墨精神,比如说它的一些特色,这些东西是需要我们去普及的,从传统到现代、当代,代表性的,博物馆都应该有,让我们带着娃娃去看,去接近。这一点日本就做得非常好,我们国家应该在这一块上积极跟上,这是精神文明很重要的一点。这一点跟上了,很多人就不愿意去耍那些低级的玩意儿。我们现在庸俗的比比皆是,并且不觉得以此为丑,而且还以此为美,这个是我们当下很典型的问题。
《上层》:对于自己的艺术创作,你是怎样看待的?
刘学伦:作为画家个体,创作本身才显意义,像山林里的老农民一样常年守住自己那几分田,又得像踏向人烟罕至的探险家一样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似乎这也是老生常谈了,我认为作为当代的艺术家还应具备属于时代的情怀,义不容辞地追求一种属于自己所在时代的浪漫生活,这种浪漫首先是属于精神层面的,是贯穿或融合在生活中的想象世界的部分,它是超越平常生活的,它是能够反映一个普通生命有着崇高理想追求的印迹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