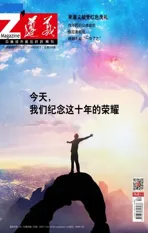落炉:隔着的山水那边
2018-08-29文丨陈章泉
文丨 陈章泉
“隔着的山水那边”,想写落炉的时候,这句诗涌向笔端。
当然有众多的想象如烽烟升起——
汇川区山盆镇的一个小山村,与千年前的汉代放置一块来谈论,似乎有些挨不着边,但据山盆来的资料说,“汉代,落炉便有了人迹活动”,仅此一句,资料没有展开,许是一种推断,但我信了,以地形地势看,这里四面环山,山高谷深,形同炉井。居高视下,流水蜿蜒,彷如八卦。举目仰望,落炉人,要么装一天灿烂星月于胸,要么做井底之蛙自傲。其实到了落炉,谁也不会怀疑,这里的每一个石旮旯都可能长着故事,这里的每一片陡峭山崖或许都悬挂着传说。
最平常的山水,在这里,也堪称大景象,山高,白云便慵倦在山顶休闲,日月便摆设在山梁当镜。一湾清流起源平正,从仡佬山民奉为生命之源的黑脚岩破土穿洞而来,汇一路的传说掌故流经落炉盆底,峡谷幽深,河道曲折,妙趣天成太极图中的子午线。这是落炉。
四平方公里的小小村落,有大桥有古庙有集市有丰饶的物产,依山傍水生活着近四千人的一个群体,历史盘根错节故事扣人心弦,有诗有歌有最本色的农耕文化。这是落炉。
贵州人口密度最大的村落,1988年,遵义市唯一直通客车的村落,唐代便有人在这里定居,曾是古播至泸州的重要驿站,从陆卢、乐炉到落炉,巴掌大的一块地数百年间几易其名,由村到乡到大队又到村,偏安一隅与世无争数十年间却又几多风云。这是落炉。
还记得去落炉的那天天气异常的好,高天朗朗辽阔无垠。那天是元旦以来最好的一个天气,掐指一算,这一天距我生命中第一次听到落炉这个名字已经30年。
在我的记忆中,30年前,“落炉”这两个字是与一种非常雅致的花名“茉莉”连在一起的,每每听到落炉,那盏清香仿佛就在手边。后来喝到了茉莉花茶,更对落炉有了不少的美的遐想。
临近正午,太阳像一个炉盖,烧得通红。估算了一下时间,紧,于是两辆车一前一后毅然驶向前往落炉的盘山公路。
谁把阳光比作金色的野兽,不出色都奇巧。关严了车窗,冷空气在身前身后咝咝咝的响,大伙还是喊热。
七弯八拐,甩开一个山头,又爬向一道山岭,车技再好也只能缓行,驾车的杨师叫着够呛,一截平展的泊油路后,车轮碾向乡村常见的泥石路。
车过一乡场,熟知情况的同事说,这里就是山盆的打鼓。大山的褶皱里,乡场拳头般大,街上人稀稀拉拉,眨眼便直穿了过去,印象深的是路边还有现代的挖机在忙碌,明晃晃的阳光里,挖机鲜艳的色彩特别抢眼,便纳闷,这里还建气派的民房,有钱何不到山盆镇上去使,车上没有当地的人,疑问还是咽了回去。忽又想起小学时教过我书的一位语文老师,老家就在山盆的打鼓,当时听这地名就觉远山远水,近四十年,那时的打鼓,我想是可以用荒凉来描绘的,回想那老师确实也土,木讷,讲课也流露几分古板,山里人,用老实巴交来形容不过分,不知眼下是否健在。
这样想着想着,车便下到一个山嘴,杨师一把刹车,车稳稳停在了黑色越野的后面。摇下车窗,热浪扑了一脸。估计目的地已经不远,我们便兴冲冲纷纷把脚踩到了落炉的山脊上。
在路边的一座钢筋水泥雕塑下一碑,碑上两字“落炉”,心想这该是落炉地标性的建筑了。忽然便想起看过的资料来,有一段好像说到这么一桩事—— 村东的岩顶上有一人工开凿的岩口,20世纪八十年代,贵州省交通厅以工代赈支持炸药帮助当地修建通村公路时,村民用小扩炮的方式开挖了一个炮洞,山口在14吨炸药中一炮轰开,后面便成了唯一进村的公路大门,人们称它石门口。不需多问,看来这里就是了。
接下来的行程可想而知,弯曲在落炉东边辽阔舒展的山坡,泛白的公路像谁由着性子甩出的一记响鞭,汽车便在这抖颤的鞭影上向下滑,抢先喊出惊讶的是我们的节目主持人,他说我们好像到了云南。大伙就说你说说看怎么个就像到了云南。小伙子说,首先是山大,然后你们瞧瞧山坡上的那些影子。一句话提醒了大家,我是在不同的时节去过云南的,果然,雪白云朵好看的影子在眼前的山坡上移动,仿佛神灵在大地布下的图案,这在云南司空见惯,难怪小伙子惊诧。
现在,我们已经真正掉进了落炉的视野中。
之所以这样来叙述,是因为在偌大一个落炉的面前,我们,实在是太渺小。周遭是满眼绿森森的包谷林,似可听见热风中唰啦啦的声音。来之前便听镇里的干部介绍:落炉人均不足三分耕地,眼下居住了数千人,活得很是滋润。人多地少,这是客观的现实,高高的山岭,低低的河谷,不难想见落炉人的坚韧倔强。在这里生成,的确是需要一些智慧的。落炉人生存的秘决就是因地制宜,不断调整产业结构,种植茉莉花、玉兰花、水果、蔬菜等经济作物,狠抓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发展教育,兴集镇、繁商贸,同时,剩余劳力转移外出“淘金”,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里已经走出了500多名事业有成的落炉人。

汇川区落炉村新貌(胡志刚/摄)
一台挖机正在作业,笨重的履带悬在几十米开外一个拐弯处的坎子上咔咔咔响,大伙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跟在黑色越野的后面,都屏住呼吸停了下来等候通过。
正好可以放眼落炉。
其实,可以从这里能够看到的不过是落炉依山而建的房屋的屋顶,那些檐角与色彩都很打眼,很是漂亮。
居高视下,尤为夺人眼球的,是谷底一处寺庙,四合院方方正正,高天丽日,寺庙却安静,宛如沙盘上一个精致的物件。这大约就是资料上提到的金龙寺,寺庙建在落炉村脚底伸向观音寺河岸跷起的一个山堡上,三面环水,景致非凡。那里流传着半幅颇有名的联语,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为应对另一座寺庙的上联“楼上楼,楼下楼,楼上楼下三重楼,重重紫微高照”,源于独特的造型,该寺对上了丝丝入扣的“塔前塔,塔后塔,塔前塔后两座塔,座座佛光显圣”的下联。对联是汉语言中的特殊现象,或许,同一个村落,几处庙宇,联与联照应,严丝合缝,这样凑巧的事在全国怕都罕见。后来得到的答复是,如我所猜。
这样想着的时候车便不易察觉中到了街口,车子穿过当街,便再次看到了柏油的路面、斑马线、古香古色的店面、路灯。想,这便是藏在深山里的落炉?车再往前,右拐,下一段陡坡路,路边精心制作的栏杆文化韵味十足,匠心独运。往下,便是落炉的广场。
两个车上的人便前前后后走下来,阳光刺眼,天空依然蓝得透明,广场朝南的两边各建了造型典雅的风雨凉亭,正前方石林顶上一歇山亭。
站在观景台,那感觉真的天宽地阔起来,顺着指点,方知道峡谷深处淌响的便是桐梓河与观音寺河的流水,两条河都发源于大娄山仙人山山脉,这里处在播州、桐梓、仁怀三县(区、市)的交界处。左边是仁怀市的地盘,右手向前一点,桐梓县的村落近在眼前。背后自然就是落炉村。俯瞰谷底,浩荡的河流翡翠般绿得发亮,有江轮游弋在水面,如果有机会坐船上走一遭,落炉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经过了一下午的紧张作业,终于结束了当天的工作。然而还是留下遗憾,在车窗升起来的那一瞬,我脑子里蹦出一帕拉的想法:本来,我想我应该去落炉公路大桥上散散步,从仁怀的角度看看那片扎根在山坡上的民居;我想我应该深入到峡谷之中,去感受那一脉灵气是怎样养育了甘于宁静却又不甘于无为的落炉人;我想我应该走进李子树下,去遥想雪白梨花点染的山岭是怎样影响着落炉的早春;我想我应该去踏访一回那几座寺庙,去领略佛教文化在这里的道德流布袅袅香火;我想我应该落坐落炉人的家中,去认真聆听他们的讲古说今谈天论地……也许,我还想……
此次道别,也不知几时再见,但我承诺,一定会再去落炉,因为,我与落炉,已经一见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