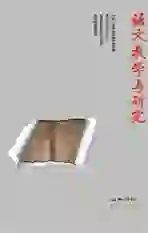文学教育在于启发和培养人的自觉
2018-08-24陈思和胡读书
陈思和 胡读书
陈思和,1954年生,祖籍广东番禺。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教学名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等职。代表作:《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新文学整体观续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主编)《巴金论稿》(合著)《陈思和自选集》《思和文存》(三卷本),以及《陈思和文集》(七卷本)等,学术著作被翻译成英、法、日、韩等多种语言。
一、学习一定要有主体性
胡读书(复旦大学2017级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胡):陈老师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采访,我们今天主要聊一下中学教育以及文学教育的问题。据说您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进入中学的,那个时候的中学是怎样的?您的学习状态怎样?
陈思和(以下简称陈):我于1967年进入中学,那时候的中学和现在的很不一样。当时正是“文革”时期,高考已经取消了。学校的秩序混乱,老师上课大都草草了事。老师不怎么认真教,学生更不认真学。我在中学时代主要是靠自学,虽然当时中学的教育体制对我没有什么正面的影响,但是我的自学很大程度上多亏了几位老师的辅导。比如我自学英语的时候,我的英语老师主动借了我一本英语语法自学教材。我的英语基础知识都是那时候靠她的指导完成自学的。还有我的数学老师,当时的数学课是最不受欢迎的,但那时候我特别喜欢数学,在课后经常找她请教。当她发现我是真的喜欢数学之后,老师借了我一本“文革”前出版的自学代数第二册。后来我在上海旧书店把这套书一本一本的找全了,大约是十几册中学数理化的自学丛书。学完这套书基本可以达到高中毕业的水平,恢复高考后,自学这套书对于我后来考入复旦大学有很关键的作用。学语文倒是没有什么自学的概念,就是到处找书读,也读过五十年代高中的《文学》课本(四册)。所以我高考的时候是很占便宜的,当时从宣布恢复高考到正式考试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我的学习成绩很快就拉上去了。我当年完全是一种自觉的学习状态,学习有一定的主体性。
胡:您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您对高考的看法是怎样的?
陈:我对高考的认识是有过变化的。首先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这个体制的最早的一批受益者。我是1977年11月底参加高考,到第二年春天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在这里遇到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接触到巴金先生的著作,我的人生从此开始转变。所以当时我是极力赞美高考的,它的的确确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
但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开始对高考渐渐地有了一种批判的态度。我是从“文革”过来的,学习对我來说是一种求之不得的事情,在那个时代根本就不存在应试的问题。那个时候,学习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只愁没有知识,没有正常的教学,所以当我们得知恢复高考的时候,大家都欢欣鼓舞,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复习功课中去了。我是69届初中生,两年半的中学里几乎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基本靠自学。至于为什么会自学,其实就是因为我喜欢知识,喜欢求知;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除了自学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消遣,也没有其他让我产生更大的兴趣的事情去做。当然也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在里面,就是我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都不是一个喜欢随大流的人。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对流行的东西大都还是拒绝的。当时的主流就是上山下乡啊,红卫兵运动啊,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好像也有一点特别想和时代保持距离的意思,那么只有沉迷于学习当中。但是九十年代开始我发现,中学教学与我当初学习时渴望求知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学生基本上是跟着老师的标准答案走。当年我认识一个外省的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她给我举过一个例子,说当时考一道填空题,标准答案是“奋勇前进”,你如果填的是“努力前进”,那就要判学生答错了。你说怎么可以这样教学生呢?所以我觉得应试教育最大问题就是它给了你一个现成的标准答案,这样会让学生完全丧失主体选择的可能。没有主体性、没有选择性的学习,我是很反感的。这也与我自己的学习经历有关,我的中学阶段就没有这些严格的教学体制来约束我,我的自学都是靠自己的兴趣来支撑的。其实考试也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标准,这种标准答案式的应试教育也反映了当年官僚化、技术化、世俗化的特征,不需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和社会活力。
所以针对九十年代以来的这个现象,我的观点就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最最重要的就是主体的选择。我之所以高考成绩好,后来在中文系的学习成绩也一直很好的原因,就是我的学习方法从来都不是去死记硬背的。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一般都会联系实际去谈我自己的想法,中文系的老师一般都会比较鼓励这样的学生。反过来说,如果现在的中学语文学习多数变成背课文、背语法,我是不支持的。我当时大学班上有一个同学,他能把《文学概论》整页整页背出来,但是这样的背是没用的,最后答题还是谈不到点子上,还是没有好分数。
另外还有一点,随着世俗对应试教育越来越重视,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就会一切围绕着高考转,而跟高考无关的事情,家长对孩子的限制就会越来越多,其中就包括孩子应该读的课外阅读啊,与考试无关的课外活动啊,这些都会受到限制。这也是我非常反感的。所以我当时编了一套“火凤凰青少年文库”,就是故意把阅读面搞得很宽,目的就是想让大家扩大一点知识面。当然我也失败了,因为大家还是围绕着考试转,也没有人愿意看。当时我跟很多中学的特级教师交流过,其实人人都知道,包括当时上海市的语文教研学科的负责人,他们都知道(应该多阅读),但是所有人在高考应试的大潮当中,都抗拒不了。
胡:高考自从1977年体制化,固定下来之后,确实让很多学生为了过这个独木桥挤破了头,所以近年来有很多地方在试点各种各样的多元化教育,但收效可能不如最初设计时的那样好,一般会认为如果高考的体制没有变化,那么其他的改革都是换汤不换药的。可是我们常常还是会说,高考仍然是目前相对公平的选拔方式。
陈:对,我也这样想。所以大约到了新世纪以后,我的想法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我看到现在社会腐败的风气远远比高考的应试教育问题更严重。所以这种时候,我就觉得任何一种缝隙,都会让这个体制崩塌,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现在高考制度存在各种各样的缝隙,只要有一条缝隙出现,马上就会有社会上一大批人涌上来,挤进来,最后把缝隙越撑越大,造成新的不公平。在这种情况下,我倒反过来觉得,虽然高考这种考试机制是摧残人性的,但是与其造成更大的不公平,那还不如坚持让大家都比较公平地参加高考了。
胡:您之前与李辉先生在《新世纪谁还忧伤》的访谈中也谈到了中学应试的教育。您认为过于死板的应试教育是一种违反人性和知识本质的考试制度,它会埋下两粒种子——当然也是比较尖锐的抨击这一社会现象的说法——它会激发学生对知识和禁欲的仇恨,还有就是埋藏很深的自卑,这两粒种子会在学生进入大学之后从不同的方面爆长出来,所以您当时提倡的方法是支持教育的多样化,具体体现在多元化的选拔机制。
陈:对,不过当时这个提倡不是针对中学,而是针对大学的。我当时是认为大学应该分出各种各样的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标准,不应该是一个统一的招生方式或者分数线——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比如复旦大学的要求和师范院校的要求就应该有差异,现在的一切统一的高考制度就很难拉开各个院校的差异度。我认为,师范院校通过制定他们专业性的标准,可以让他们在需要的生源范畴中选择他们认为最好的学生,而不是仅仅从分数标准上来做选择。现在的选拔对学生来说就缺少了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但现在好像也改变了很多,包括填志愿的方式。学生还是可以(通过志愿的选择)把自己的特长展示出来。但严格的说,我不认为高考考出好成绩的就是优秀学生,这不是一个硬性标准。
二、文学教育就是美的教育
胡:现在很多教育质量较高的地方,往往会在语文课本之外提供一些课外阅读的教材或者“经典书单”,而这些“提供”却引起一些争论,因为书目的选择,就意味着有的书在里面,而有的书就不在书单当中了。
陈:对,(划定必读书单)这也是我反感的事情。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对于读者来说,具体读哪一本书不重要,或者说,没有哪一本书是非读不可的,某一本书重要不重要只是对你本人来说的,是关乎每一个读者自己的。可能这本书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但是对别人来说读来可能不会有相同的感受。因为一旦设定了必读书目,反过来就一定有哪些书是不必读的。我认为,只要对你来说是开卷有益的,只要这本书能够增长你的知识和心灵的智慧,这样的书都是可以读的。阅读人文经典的目的不在于你读过了这本书,而是在于通过阅读唤醒内心做人的自觉。所以,我反对这种规定别人一定要读多少本书,一定要读什么书的行为。我认为阅读应该随心随性,有时候还要看缘分;但是读书本身是件快乐的事情,应该多读书,多多益善,而且应该打破禁区。
胡:之前您在与刘志荣教授对谈的《文学会使校园变得更美好》里面提到文学教育对于学生学习的重要性,也讲到了文学教育最重要的是唤醒人内心的自觉。
陈:文学教育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中学里,我当时主编“火凤凰青少年文库”也就是这个意思。人文教育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教育,受教育者不同的生命体验,也会导致不一样的自觉。这就是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人文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在于启发和培养人的自觉,它与知识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机制,知识教育应该在学校里完成,而人文教育(文学教育)则可以通过自我感悟、名师指点、经典阅读、人生体验等多方面的途径来获得。当然,如果在我们学校里设有完整的人文教育机制,则受益者就会更多更广泛,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也更有保障。我之前和刘志荣谈的主要是大学里面的文学教育。之所以要在大学里提倡文学教育,其原因是现在中学里不提倡文学教育了。其实中学里的文学教育更重要。
实际上我们的孩子并不缺少文学教育。学龄前的孩子,一打开电视就是动画片啊科教片啊,或者手机电脑上教儿歌、常识等,这样的东西一点都不缺。缺少的是在孩子們应该接受教育的时候应该尊重他们的兴趣和主动性,从学龄前到小学,特别是到中学。这又回到应试教育的问题。现在,人们太急功近利,文学教育被忽略了。缺失了文学教育就缺失了美的教育。文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体现美。如果没有美对人的心灵的普及和教育,一个人就会变得很枯燥,他的情商也不会高。现在我们常常讲情商,情商的教育其实就是美的教育,文学的教育。
文学教育是整体的人文教育的一部分,而人文教育与知识教育是不一样的教育类型。知识教育对学生来说是从无到有的教育,即受教育者原先不具备某方面的科学知识,他不通过学习是永远不会掌握的,如数理化知识、人文学科中的某些知识体系,所以需要进入专门的教育机构(如学校)接受这方面的教育,他通过接受教育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然而人文教育是涉及到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说通俗些就是人性的教育。人性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人文的要素于每个人都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人文教育不是从无到有的教育,不是把外在的知识通过教育灌输到人的头脑中去,而是一种含有启蒙性的,通过教育来激发受教育者内在的人性因素,使之觉悟到人之所以为人的自觉性。
我们也可以说文学教育是人文教育的最初阶段,这个阶段是最贴近生命的原初形态的,也是最富有感性的力量的。学生在中学时代或者刚进入大学的时候,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没有达到可以从哲学层面思考人生的高度的时候,他可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从文学的层面感受到生命的各种体验和对人生的各种认识,具备了丰富的感情世界。一个生命意识强烈的人、人文体验深刻的人、具有非凡想象力的人,未必就接受过完整的知识体系的教育,但是他对人文方面的感受能力可能超过那些高学历低情商、感情枯燥、面目可憎、乏善可陈的人。因此,人文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它是通过启发受教育者自己意识到某种与自己生命内涵相连的东西,使其获得对自己的深刻认知,从而获得做人的尊严和自觉来完成的。
三、关于文学教育对文化的传承
胡:关于传统教育的问题,现在中学课本里现代文和古文的比例好像有了很多调整,古文、古诗词的比重越来越大,从应试角度来看,古文的考试形式一般是以诵记为主,配以少量的字词理解,现代文的考试形式则主要是阅读理解。您认为这样的现象是好的吗?
陈:我对现在中学的课本是不大了解了,但是我还是倾向于让学生们多学一点古文,因为相对于现代文的学习来说,古文的学习还有一个客观的水平和标准在那里,古文的学习,对提高学生阅读能力和之后的读写能力的训练都有好处,难是难一些,但还是终身受益的。
胡:您再谈谈当年编写的“火凤凰青少年文库”吧,那是关于文学教育,能体现文学在文化传承中起作用的一套书吧?
陈:“火凤凰青少年文库”是我对于美的教育,文学教育的一次推广和实践。九十年代到新世纪的时候正是人心浮动的年代,当时我们几个人还有过一次非常激烈的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原因就是当时知识在社会中的价值开始贬值,“知识无用论”甚嚣尘上。
“火凤凰”系列丛书是我的一次弘扬人文精神的实践。当时编了好几套,形成了一个系列,从给孩子看的《火凤凰青少年文库》到青年批评家的《新批评文丛》,从论述知识分子思想的《火凤凰文库》,再到推介老年学者的学术成果的《火凤凰学术遗产丛书》。其中“火凤凰青少年文库”连着好几辑,大约有一百种,当时就是希望能涉及到方方面面,只要是跟人文有关的,都应该尽可能多的去阅读,最先开始是为台湾一家出版社编的,名目叫做“青年图书馆”,从这个名字也能看得出来,就是想做一个包罗万象的,像过去的“万有文库”一样,只要对中学生有用的,我认为都可以编进来让中学生读,当然是内容比较浅显易懂一点的。不过在台湾没有编下去,后来我就移到大陆来继续出版。现在市面上青少年的读物也是从来不缺少的,缺的是一个教育机制来保障他们的阅读。
从学理上来讲,文学教育也包含了文学史的传承功能,因为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灾难深重的国家。文学史研究是近百年才兴起的西方学科观念,古代中国没有专门研究文学的机构,但是2000多年的优秀文学传统还是保存下来了,它主要的保存渠道不是靠市场运作,而是靠教育体系。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完整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而文艺属于古代经学教育的一部分(如《诗经》),在经史子集的学术分类中,文学其实也占有了很大的比重。到了现代教育制度建立,中文一级学科就成为本民族语言文学的根本之学,也是承载发展中华文化传统源流的重要教育机构,文学教育在它的本义之中,所以对文学教育的忽视、轻视都是错误的。
那我之前编“火凤凰”其实也就是在做延续的事情,这是一种文化生命力延续的传统。我是一个生命意识很重的知识分子。我为什么要编这么多套书?其实就是因为我要体现的是一种生命循环的精神,一种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在我的学术研究和教书生涯中,也是要贯彻这个旨意的。
胡:谢谢陈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