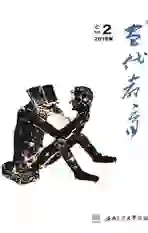童年书趣
2018-08-20孙西远
孙西远
岁临艾杖,回首童年,历历趣事不断袭来,其中跨度最大的,当数那些绵延悠长的读书趣事,一桩桩一件件的,想起来非常舒心惬意,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没有丝毫的陈旧感。
我与“书”结缘,应该是在四五岁的时候。那时候,乡下农村是没有幼儿园的。髫龄同伴们一般是由父母委托村中古稀老人随便看管着,有时还会给上一点晌午之类的东西,饥饿问题是很少发生的。偶尔有之,也会因我们的越墙回家偷吃冷饭而解决。我们的任务就是“玩”。父母也只是希望我们健康有益地玩,玩得平安快乐就行了。
父母在把我们托付给老人之后,往往就匆匆忙忙地出工干活去了,留下的便是我们自由活动的时间。我们喜欢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地在公房前边的谷场上打陀螺、抛毛袋、跳拐、荡秋千等。玩得差不多了,又会到村旁的林子里找鸟巢、拿弹弓打鸟等。只要是感兴趣的,我们都会做。学校也是我们常常光顾的地方,只是到学校里时,要随时提防大同学的欺辱。
我们村就在学校旁边。站在村子门前的沟堤上,从学校上空飘来的朗朗书声如钟如雷,一波一波的,非常洪亮。学校外边,一块无遮无拦的操场上,时常有学生在上面上体育课,列队做操或者打篮球之类的活动是时常有的,同学们看起来非常轻松。球场外的空地上,长满了起垄子的蚊子草和不起眼的铁线草,随时有人坐在上边小憩。我们就喜欢到操场外边的空地上看学生上体育课,特别喜欢看学生的斗拐和蛙跳。偶尔也会溜进校园里听老师讲课,只是老师们随时会驱赶我们。那时家乡的校园不大,就建在上下两块地里,没有围墙。设施也非常简陋,几间土坯房就算是教室。窗户用几根木条钉着,空间很小,里面的东西站在外面也是一览无遗的。桌子很挤,非常陈旧,有的是三个人坐一排。凳子也非常简单,有的在两个木架上搭上一块木板就当作凳子了。黑板是把一块漆成黑色的木板,固定在两根靠墙的圆木上部,看上去黑漆漆的,微微泛着光亮。老师们把要讲的内容写在黑板上后,习惯性地用一根竹棍指着让学生跟读或者认读,或者是边问边讲。一唱一和的声音是非常响亮的。我们喜欢看老师讲课,更喜欢看学生边念笔画顺序边用手在空中写字的肢体变幻。老师们总会在我们看得全神贯注时驱赶我们。当一位老师把我们驱离他们的教室门前时,我们又会跑到其他教室前面,在远一点的地方听别的老师讲课。距离远了,老师的驱赶也就少了,只是我们的专心程度也降低了。
校园里还有一处叫“天井头”的四合院,那是一个改庙为校的封闭大院。里面是初中部的教室,还有老师的生活区和学生的住宿区也在里边。院内的气氛比院外严肃得多,我们一般是不敢进去玩的。即便是在四合院外边玩,大部分时间也都选择在学生上课期间。学生下课期间,我们是连校园里也不会在的。
我们对学生下课是非常敏感的。只要铃声一响,我们便奋不顾身地往校外跑。有时还会吼上几声老师讲课的内容,边吼边跑,边跑边回头看,见没有人追赶我们时,才会把脚步放慢下来,气喘吁吁地走回家边,然后把我们的经历一个劲地讲给看守老人听。老人一般不会责怪我们,只是嘱咐我们不要跟别人吵架。
在给看守老人讲完扣人心弦的校园经历后,我们又会跑到谷场上向其他人炫耀。小伙伴们有的很感兴趣,有的表现得不屑一顾。我们也会在炫耀中开始新的玩活,不知不觉地玩到了傍晚。待劳作了一天的父母回家后,小伙伴们才会渐次从谷场回家。
晚归的父母回家后先做的,大多是生火做饭之类的事。我们也会帮着做些简单的家务。父母总会询问我们白天的玩活,到学校里玩了没有、学到了什么等。我们也会毫不掩饰地把白天的经历告诉他们,特别是在学校里玩的情况。父母并不反对我们到学校里边玩,反而暗含期待地告诉我们:“明年就可以读书了。”
童年的伙伴们对读书有着一种天生的渴望,都希望背着新书包、穿着新衣服到学校开始新的生活,好让小一点的同伴艳羡不已。我的姐姐和哥哥都在学校里读书,家里的读书氛围还是比较浓厚的。有时他们做作业时,还会教我认一些简单的字。我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认识了一些简单的字,偶尔还会教小伙伴们写上几个,小伙伴们对我非常感兴趣。
晚饭后的时间是非常自由的。劳作了一天的父母们会串着门子谈天说地,读书的学生会邀约同学围坐在煤油灯旁做作业,我们年龄相近的伙伴们会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玩各种游戏。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月明星稀时,村边的谷场上更是我们的天下。各式各样的游戏五花八门、精彩纷呈。许多游戏是伴随着童谣进行的,一些童谣甚至成了我们的游戏规则。那一首首童谣,其实就是一篇篇无字文章;那一套套的游戏规则,其实就是一连串的无本之书,字字珠玑,朗朗上口的。我无从考证它们的作者是谁,也记不清是哪些人教我们的。可我知道,它们在我知识积累的过程中,是有着重要作用的。甚至可以说,它们就是我读书生活的萌芽,是最原始最朴素的读书方式。
我的学习生涯应该是从童年的玩耍开始的,学习兴趣也是在孩童时代的玩耍中培养的。玩中也能学,而且学得非常有趣。多年后回首起来,感觉还是挺惬意的。那些作为我童年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童歌童谣,好多仍然历历在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以下几首:
一首是“顶摸摸,拿蛤蛤。拿得着,红果果。拿不着,鸡屎几大坨”;
另外一首是“一个小石头,碾得滑溜溜。金点银点,梅花绣点。小人介绍,拿你蒙脸”;
再一首是“点点斑斑,脚踩南山。南山雾陡,姊妹垭口。新官上任,老官退堂”。
在孩童时代的躲猫猫游戏、老鹰抓小鸡游戏、打岩羊游戏等众多游戏中,各種不同角色的扮演就是通过这些童谣来决定的。还有一首更牛的童谣,可以说是童谣中的最高境界了。这首童谣是:“月亮堂堂,骑马烧香,烧着毛大娘。毛大娘,扯豆荚。豆荚香,向四方。四方矮,过螃蟹。螃蟹过沟,过着泥鳅。泥鳅告状,告着和尚。和尚点灯,点着先生。先生熬油,熬着老牛。老牛不吃江边草,几棒打得遍山跑。”寥寥几十字,不仅涵盖了拟人、顶针等修辞手法,而且外延极为丰富,完全可以拍一部卡通片了,至今仍在故乡童年一代中广为流传。
室外的玩耍是我童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以童谣或儿歌形式呈现的无字之书,是我童年书趣养成的重要元素。我的童年书趣并非完全来自室外玩耍。在家中,爸妈和哥姐也会有意无意地教我一些书本知识,准确地说是一些基础知识。我接触最早的是数数,接着是认识数字。数数是撩拨激情的,也是容易获得家长表扬的。从1数到10难度不大,难度大的是10以后的数字。对于缺乏理解能力的孩童而言,单纯的机械记忆是很容易在十位上犯错的,常常是数到后面后又会从十位上折回前面来。爸妈和哥姐一而再、再而三地开导,我还是很难理解。好在没有经过多长时间,我就能从1数到100了。那几乎是通过机械记忆来完成的,让小伙伴们艳羡不已。好多小伙伴们在发蒙读书时,还不能从1数到100,显然,我在起跑时是位居前列的。
学会简单的数数之后,爸妈和哥姐们教我的便是认识数字了。认识数字也是挺有趣的,只求会认,不求会写。孩童时代对数字的认识,是通过儿歌的形式来完成的。把数字形状跟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常见事物联系起来,再以儿歌的形式呈现,学起来非常形象生动。我的家乡童年一代中,至今还在传唱着“扁担1,鸭子2,耳朵3,椅子4,秤钩5,豆芽6,拐棍7,火镰8,铁锤9,棒棒敲鸡蛋10”的童谣,这也就是我们当年的识数童谣。好多小伙伴对10以内数字的认识,就是在上述童谣中完成的。
在教我认识简单数字的同时,长辈们也会有意无意地培养我对数字的感知。那时没有书本,他们通常都是用“火边坐着几个人、某样东西是多少、加上几个是多少”等问题,来引导我对数字的感悟。我每说对一个,长辈们都会给予夸赞。慢慢地,我也就学会了简单的个位数加减问题。有时其他小伙伴的父母也会同时考我们类似的问题,我随时会先说出答案,感觉总是蛮好的。
我对数字的认识和感知,主要来自父母的启发式引导。对语文的触及,大多来自哥姐的影响。在我入学之前,我的哥哥和姐姐就在村旁的小学读书。晚上他们随时要做家庭作业,有时还要诵读课文。他们诵读,偶尔我也会记得几句。加上我们随时会到学校玩耍,不知不觉中,也就记住了少许小学低段的课文。那时的课文非常简单,有的就是一句话或者两三句话。一天一天地重复,要想忘记都不容易。时间久了,知道的东西也不斷增多。爸爸妈妈也认为我可以读书了,理由就是我能学懂一些一年级的知识。困难是我的身个太小,入学读书会受制于别人。他们总希望我快点成长,快点入学。在我的家乡,可否入学的一个判断标准,就是把右手或左手绕过头顶,看能否摸到另外一侧的耳朵。摸到了,就可以读书了。摸不到,就说明还不行。闲暇之余的父母常常让我摸了试试,我总是摸不着,即使是使尽全力,还是摸不着。有时我也会情不自禁地试试,感觉总差那么一点点,只是觉得一次比一次好。渐渐地,我的左右手都能翻过头顶摸到对面的耳朵了,人长了,入学的年龄也到了。七周岁满后,不时有老师到我家串门说,我可以读书了。在当年的秋季学期,我也就顺理成章地入学读一年级了。
适龄儿童在入学前对读书有着一种天然的冲动。新生报到当天,一年级教室就爆棚了。我是第二天早上才去报到的。看着拥挤不堪的教室,心里有些发悚。班主任老师对我的入学报到非常高兴,他一直认为我有读书的天赋和超群的潜能。在简单地缴纳书杂费之后,他给我安排了一个居中的座位,只是一张桌子三个人,显得有些拥挤。我是第一次跟陌生人挤在一起,心里总是觉得不自在。我想这种感觉不光是我一个人有,其他同学也应该是如此。
在经过一天多的喧闹和嘈杂之后,教室里增加了一些陈旧的桌子和凳子。三个人坐一排的现象少了,老师也开始发新书了。领到新书的第一感觉就是赏心悦目,继之便是爱不释手。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把书放进书包里,生怕有丝毫的弄脏和损坏。一些同学还请老师帮忙写上名字,看上去挺新奇的。少数没有按时领到新书的同学,看着总不是滋味,失落感写在脸上。老师安慰他们说过几天就可以发了,可是他们就是高兴不起来。是啊,读书无书,跟别人看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我是幸运的。
第一批次的新书发完之后,老师开始教大家读书了。我们的启蒙教育是从学习拼音字母和简单的数字开始的,光是“a,o,e”三个拼音字母和“1到10”几个数字就学了好长时间。潜能好一点的同学觉得非常简单,悟性差一点的同学老是学不会,有的甚至选择离开。为了让那些学得慢的同学不掉队,老师总是想方设法地把课讲得生动有趣、易于接受。诸如“a,鸡蛋长尾巴读a;o,圆圈o”等,虽然不够规范,但是朗朗上口的,无需怎么费劲就记住了。渐渐地,我们开始接触拼音、汉字和加减运算了。难度的递增是不言而喻的,同学间的好、中、差组团分层也越来越明显,成绩位居后列的学生流失越来越严重。到小学三年级时,我们班居然没有一个女生,清一色的童子班。不过对于跟得上节奏的同学而言,教学的趣味性也是越来越强的,有的教学甚至就是绝句式教学,诸如在学习调号时,老师让我们记住的是“阴平横过去,阳平爬上去,上声下来有上去,去声沉下去”四句话;在学习声调标注时,老师教我们的是“见着a字a上落,没有a字找oe,iu并排标在后,单独一个不用说”的字母顺序;在讲汉字书写时,老师又别具匠心地给我们讲授了“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外到内,先里头,后封口,先中间,后两边”的书写技巧。这些近乎押韵的语言,让童年时期好些尖深难学的语文知识变得简单易学了。
语文课如此,数学课也是如此。不少数学课是老师用上语文课的方式教我们完成的。那些散见于数学课本中的各类口诀,本身就像语文课程,易学易记的。一些属于数学法则的东西,老师也会用诗歌一般的语言教我们去学去记。我记忆最深的是去括号法则,我们老师形象生动地归纳出了“加号后边去括号,里面各项不变号;减号后边去括号,里面各项都变号”的记忆口诀,我们做题时边念边做,几乎不会出什么错。即使出错,差错率也很小。而让我们背得最多的是乘法口诀,老师要求我们要横向会背,纵向也会背,要互相查着背。不会背的,周末在家也要读了背。我是很早就跟哥哥姐姐学会乘法口诀的。一些不会背的同学还随时请教我。我也会教他们和我一起背,感觉挺愉快的。有时上山割草之类的,我们也会背乘法口诀比赛,让背错的小伙伴帮没背错的干一些劳动。有的一次次出错,又只能硬着头皮一次次地干。想起来还真是有趣。
与乘法口诀比肩的是珠算口诀。背珠算口诀也非常有趣。我们也会在假期劳动中背珠算口诀比赛,并用奖惩的方式来寻找乐趣。寓学于劳,其乐融融的。
赛背口诀的感受是愉快的。背诵诗词反倒显得有些自娱自乐了。那些散见于小学语文中的诗歌词谣,简单易记的,背得一次,一般就长时间不会忘记。鲜有不会背诵的。闲暇之余,我们也会情不自禁地背上一两首,好像能从诗词的韵律中找到特殊的韵味。
诗词易背,课文就不同了。不过每篇课文差不多都是一个故事,特别是寓言全是故事。我们的老师要求非常严格,凡是课文后要求背诵的,他都一篇不少地查着让我们背掉。我们记住课文,也就记住了课文中的故事。好多故事还是非常生动的。我们常常讲给年岁小一点的小伙伴们听,甚而至于讲给大人听。我们的父母也会因势利导地给我们讲一些小故事,或者是猜谜语。猜谜语是非常启智的活动。那时我们接触的谜语,谜底一般都是司空见惯的东西。诸如把棕树说成“高丫脖,细腰杆,穿红衣,打绿伞”;把松树说成“一年十二月,霜炸不落叶,开花无人见,结果人吃得”。我们见到这些东西时,常常会说着谜语让其他小伙伴们猜谜底。猜来猜去的,知识确实增长了不少。猜得多了,还会产生一些思维灵感,让人联想到许许多多的东西。这种联想性思维在后来的作文练习中,不断地拓展着我的思维面,让我在写作文时也能找到别人少有的乐趣,收获不少“写”有小成的快感。我从小就不怕写作文,除了看连环画等课外书给我一些启迪外,还跟我在写作文时也能找到少许乐趣是密不可分的。这些乐趣有时会外溢到其他方面,演绎成更高层次的情趣。
乐中有趣的生活是惬意的。源自课堂的兴趣与课外生活中的乐趣叠加组合,成为我童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的童年生活是非常有趣的。很多生活趣味又是与“书”息息相关的。没有童年书趣,我的童年人生就会单调很多。至今我都常常会忆起小伙伴们簇拥在一起看书的场面,也会在回味中追寻着童年的欢快与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