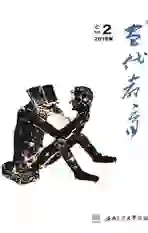孤寂中的生命轨迹
2018-08-20郭勇
郭勇
曾以“农民诗人”闻名黔西北诗坛的管彦博,是位名副其实的诗行者。从1994年在《星星》发表处女作至今,二十多年来,他始终本着“思想和语言统一”的理念,创作了大量既有表达巧妙,又有思想硬度的诗歌作品,其新近问世的诗集《生命证词》就是最好的印证。
《生命证词》从煤油灯下抒发感情开始,采用独特的叙事策略,热切讴歌着人世间至美的生活感悟。乡村、土地、庄稼、孤灯等词语,串成了管彦博的回忆,构成了他的诗歌景观。
管彦博居住的村庄,坐落在贵州的群山之中,距赫章县城70多公里,那里贫困落后的现状,构成了他生活中最熟悉的图景,也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管彦博在《生命证词》的自序中这样说道:“在自己平淡而艰辛的‘乡村活法里,我的文学信仰渐渐清晰丰满起来。我不但用诗歌呐喊和叫劲,还用诗歌表达自己的雄心与梦想。”对管彦博而言,“乡村活法”就是一剂良药,不仅让他找到了生活的真谛,还让他迈上了诗歌创作的航道。
“独坐斗室,独坐在词句和夜的中心/燃烧的灯焰,像杆直立的旗帜/我守住长短不齐的柴草与生命烈火/也守住我与生俱来的消瘦与孤寂”(《独守孤灯》)。灯焰从黑夜沉静的深处,或者说从诗歌的语境中,把个人生活带入了幽冷的处境。管彦博写这样的诗歌时,他的内心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境,乃至他在现实当中又是怎样的奋斗?从《滴血的阵痛》《像常人一样生活》《带着一个春天来看你》等作品来看,管彦博的诗歌,农民一样憨厚、本分……
很多时候,面对管彦博诗集《生命证词》,我不知道这个以农民身份开始行走的诗人,他的诗歌是如何拒绝对个性抹杀的痕迹,如他的《庄稼地里看鸟》:“在庄稼地里抬起头来/我只想看一看天/无意中却看见一只鸟/停在我头顶/一根/随风摇摆的树枝上”。还有《愧对乡土》:“我以羞愧的表情,面对一片闲置的土地/对不起了!没有在春天播下希望/就不想秋天有什么收成。这是一种无奈/无奈之中,却不止一次陷入彷徨”。管彦博对诗歌有独到的理解,并且进行了完美的自我尝试。他说:“早期写诗称得上‘苦吟,而这些诗歌,却写得比较轻松、随意,真正享受到了写作的快乐。”
评论家黄恩鵬认为:每一位诗人都是带“根”的流浪人,问题是如何不丢弃原本的角色,携带自己人生的“根”行走。关于诗歌的“根”,管彦博认为,写作之初功利色彩必不可少。到如今,写作已成为一种习惯、一种信仰。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管彦博的诗歌创作,更大程度上是源于内心的告白,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不仅走出了“无病呻吟”的困境,还成为了支撑他诗歌创作的内在保证。
管彦博在《纸上庄稼》中写道:“我在纸上栽种庄稼/这些纸上的庄稼/却很难走进人们的视野//我伺弄着纸上的庄稼/把头颅高高昂起/我明白我的处境/身陷黑暗/就在内心点一盏灯”。这样的佳作,勾勒出了一条有效的传统“创造性转化”新路径,给人以深深的震撼。正如《安魂曲》的结尾那样:“就让该结束的一切都结束吧/不要让饥饿的眼睛总是抓不住一束稻草”。
读完诗集《生命证词》,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能够引人入胜的作品,从来不靠外力来推动故事,出发点就是故事的发动机。管彦博在诗集《生命证词》中,将自己的生活艰辛、懊恼与感恩付诸于诗歌,娓娓道来。在管彦博笔下,原本看似平淡的诗歌,却超越了时代和年龄的限制,破除了思维“阻隔”,在给读者感受诗歌魅力的同时,显现了他对诗歌创作的驾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