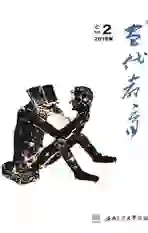文学风景研究的“文化转向”
2018-08-20周爱勇朱伟华
周爱勇 朱伟华
[摘 要]传统的文学风景研究侧重文学风景的审美研究,在诗歌等抒情文体中将风景视为创作的抒情对象;在小说等叙事文体中着重风景的叙事功能和类型研究。进入21世纪后,文学风景研究发生“文化转向”。风景被视为文化建构、解构与重构的产物,文学风景研究即破译风景中隐匿的丰富符码,阐释风景在文本中的深层含义。文学风景研究的“文化转向”主要体现在风景与文学现代性研究、风景与民族身份认同研究、风景与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研究三种研究路径和主流范式。
[关键词]文学风景;文化转向;文学现代性;民族身份认同;意识形态(权力)
Abstract:Traditional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aesthetic study of literary landscape:the landscape is regarded as the lyric object of creation in poetry and other lyrical style,and the narrative function and types of scenery is emphasized in novels and other narrative styles.After entering twenty-first Century,the culture turn on literary landscape research has happen.Literary landscape is regarded as the product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Literary landscape research deciphers the hidden codes of landscapes and explains the meaning of landscapes in texts.There are three research paths and mainstream paradigms on literary landscap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scape and Literary Modernit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scape and national identit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scape and ideology or power.
Keywords:Literary Landscape; Culture Turn;Literary Modernity;National Identity;Ideology (power)
文学风景或许是人类最古老的话题,现今却已成为最时尚的研究领域。风景研究已然跨越了单一的学科范畴,成为容含文学、艺术、地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热门研究领域。作为跨学科术语,各研究领域对“风景”的定义不一;即使同一研究领域,“风景”的内涵外延也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学界倾向于将“自然风景”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人文风景”共同作为研究对象,而当我们说“文学风景”时,并非强调从审美角度定义风景,而是指各学科领域在进行风景例举时,往往取样于文学作品中的风景描绘而非事实的现象景物。
传统的文学风景研究侧重文学风景的审美研究。在诗歌散文等抒情文体中,研究者往往将“风景”视为创作的抒情对象,挖掘风景的象征或隐喻含义,因此“山水比兴”“物我交融”“无(有)我之境”“天人合一”等是核心术语,风景由此成为“意象”的代名词;在小说等叙事文体中,研究者更侧重风景的叙事功能,如“引入与过渡”“烘托与反衬”“调节节奏”“营造氛围”“静呈奥义”“孕育美感”“风格与气派的生成”等;而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不同小说类型中,风景叙事特征也成为影响风格的重要因素。[1]进入21世纪后,在现代理论方法的“烛照”下,文学风景研究发生了“文化转向”,呈现出多元共生的局面和生机盎然的态势。新型的文学风景研究借鉴国外文学风景研究成果,改变了传统研究的单一局面,注重文学风景的现代内涵和文化研究,将文学风景视为文化建构、解构与重构的产物,通过风景这张“文化编码的巨大网络”,[2]破译其中隐匿的丰富符码,阐释风景在文本中深层的结构含义。目前,体现文学风景研究转向的,主要有以下三种研究路径。
一、风景与文学现代性研究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以“风景之发现”来考察日本“现代文学”的形成,这成为我国国内风景与中国文学现代性关系研究的滥觞。[3]此类研究多以小说的风景书写为切入点,探讨风景叙事如何影响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发展,探讨创作主体与现代性的关系,以及风景叙事的流变等问题。
张夏放的博士论文《旗帜上的风景:论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风景描写》认为,中国现代小说中大量“自然风景”的描写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的萌芽和发展;风景已成为现代小说的一种重要特征,现代小说的发展可以在风景描写中看到比较清楚的轨迹。[4]蒋磊的博士论文《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现代旅日作家的文化体验》认为,现代旅日作家的风景体验是“日本体验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发生”的重要一维。[5]金春平在《风景叙事与小说主体的现代性理念流变》一文中认为:文学对自然风景的主体化叙事,标志着现代性所关注的“人”的“主体性”的重新发现。[6]傅元峰的《自然景物叙写与中国现代小说诗性现代化》一文,探讨了风景叙事模式与中国现代小说转型的关系。[7]吴晓东的《郁达夫与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一文,从个案出发阐述作家作品中的风景书写如何體现文学的现代性。[8]
此类研究将文学风景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探讨风景书写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和创作主体的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认为风景书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特征,是文学创作者“主体性”的重要体现。
二、风景与民族身份认同研究
英国学者西蒙·沙玛指出:“风景不仅成为感官的栖息之地,更重要的是,风景还是精神的艺术。风景为记忆深层——正如地壳中的岩层——所建构。风景首先是文化的,其次才是自然的;一草一木,一水一石,均有想像性的建构投诸其上。”[9]国外风景研究认为,没有单纯的自然风景,只有存在于文化背景中的风景,风景是文化的产物,即作为文化想象方式的“想象的共同体”。国内相关研究多以创作主体或拟想受众身份为切入点,探讨文学风景书写与文学主体身份认同、民族性建构的关系。
国内此类研究的较早成果是张箭飞的《风景与民族性的建构——以华特·司各特为例》一文。论文通过细读司各特文本对苏格兰风景的描写,分析“风景”如何体现苏格兰的民族性,以及作者如何把风景描写转变成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表达形式。[10]此后,张箭飞又翻译出版了英国学者达比的专著——《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该书考察了风景在英国阶级关系和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对我国的风景与身份认同(建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11]
厉梅的博士论文——《塞下秋来风景异——抗战文学中的风景描写与民族认同》,采用精神分析等批评方法探讨抗战文学中的风景描写与民族认同的关系,认为风景是民族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是民族的物恋对象,风景描写有利于民族动员和民族认同。[12]马绍玺《边地风景与少数民族诗歌的民族国家想象》、李长中《空间的伦理化与风景的修辞——以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为中心的考察》等论文,从少数民族文学风景书写、地域空间书写等角度探讨风景与民族国家想象、民族身份认同、民族性建构的关系。[13]
此类研究将风景及其再现视为一种“文本”,认为它们像其他文化形式一样是“可读的”,文学中风景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契合和体现了文学主体的身份认同,制约或促进了文学主体的身份建构。
三、风景与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研究
英国学者安德鲁斯指出:“风景是一种‘观看的方式,它是由特殊的历史、文化力量决定的。”[14]“观看的方式”涉及“谁在看”“在看谁”“怎么看”等问题,其实质是风景与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的指涉。因此,风景不仅作为一种“观看的方式”变成“可读的”,还可以因“特殊的历史、文化力量决定”变成“可写的”。正如米切尔所言:“风景不仅仅意味或象征着权力关系,而且是文化权力的生产装置,也许还是权力的代理。”[15]
国内关于文学风景与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探讨外国文学中帝国殖民历史语境下意识形态如何影响文学文本中的风景叙事。正如米切尔所言:“风景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构型,与欧洲帝国主义密切有关。”[16]此类研究的代表有余婉卉的《“圣洁的沉默语言”——论康拉德帝国叙事中的风景》、蒋怡的《风景与帝国的记忆——论石黑一雄〈长日留痕〉中的视觉政治》等论文。[17]
另一类以我国当代文学为研究对象,探讨后“讲话”语境下政治意识形态如何影响文学文本中的风景呈现。朱羽的博士论文——《“社会主义”与“自然”——以1950—60年代中国的文艺实践和美学论争为中心》,以《山乡巨变》等文本为切入口,探讨文学叙述行为的历史含义,追问新的政治意义如何渗入自然表象,在当时普遍信奉的“写实主义”机制中思考“风景”的生产。[18]杜英的《风景、抒情及其他——1949年前后的沈从文》、魏宏瑞的《消失的“风景”线——十七年(1949-1966)乡土小说中的风、花、雪、月》等文,分别从作家个案和文学流派角度探讨政治话语对风景书写的“规训”。[19]张鸿声的《空间的意义转移与社会主义“新北京”——以“十七年”与“文革”诗歌为例》、黄继刚的《政治景观的现代性迁移——新时期文学叙事中的景观变迁》等文,则探析政治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创作主体,从而导致“景观”呈现的变迁。[20]
此类研究不仅将“风景”视为名词,还将其视为动词,意识形态(权力)决定了风景的“可写性”和“可塑性”。如米切尔在《风景与权力》中所言:风景是文化权力的工具,是社会和主体身份赖以形成、阶级概念得以表述的文化实践。
以上三种转向是目前国内文学风景研究的主流范式,它们突破了文学风景研究的单一程式,着力于文学风景现代内涵的文化阐释,拓展了文学风景研究的视野和空间,呈现出多学科融合对文学研究的启迪和深化。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如何在文学风景研究中“引入”文化研究而不“穿透”文学,如何在强化社会文化批判维度的同时不弱化艺术审美批评力度,仍是值得特别关注并需在研究实践中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297-325.
[2][15][16](美)W.J.T.米切尔.风景与权力[M].杨丽,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8,5.
[3](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赵京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4]张夏放.旗帜上的风景:论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风景描写[D].北京:北京大学,2003.
[5]蒋磊.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现代旅日作家的文化体验[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2.
[6]金春平.风景叙事与小说主体的现代性理念流变——以新时期到新世纪的西部边地小说为中心[J].当代作家评论,2014,(3).
[7]傅元峰.自然景物叙写与中国现代小说诗性现代化[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8]吴晓东.郁达夫与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10).
[9](英)西蒙·沙玛.风景与记忆[M].胡淑陈,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9.
[10]张箭飞.风景与民族性的建构——以华特·司各特为例[J].外国文学研究,2004(4).
[11](英)温迪·J.达比.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M].张箭飞,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12]厉梅.塞下秋来风景异——抗战文学中的风景描写与民族认同[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7.
[13]马绍玺.边地风景与少数民族诗歌的民族国家想象——以晓雪、饶阶巴桑、张长早期诗歌为例[J].民族文学研究,2012,(5);李长中.空间的伦理化与风景的修辭——以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为中心的考察[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6).
[14](英)马尔科姆·安德鲁斯.风景与西方艺术[M].张翔,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30.
(美)W.J.T.米切尔.风景与权力[M].杨丽,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8.
[17]余婉卉.“圣洁的沉默语言”——论康拉德帝国叙事中的风景[J].2011,(2);蒋怡.风景与帝国的记忆——论石黑一雄《长日留痕》中的视觉政治[J].外国语言文学,2013(2).
[18]朱羽.“社会主义”与“自然”——以1950—60年代中国的文艺实践和美学论争为中心[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19]杜英.风景、抒情及其他——1949年前后的沈从文[J].民族文学研究,2011,(5);魏宏瑞.消失的“风景”线——十七年(1949-1966)乡土小说中的风、花、雪、月[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1(4).
[20]张鸿声.空间的意义转移与社会主义“新北京”——以“十七年”与“文革”诗歌为例[J].文艺争鸣,2013,(4);黄继刚.政治景观的现代性迁移——新时期文学叙事中的景观变迁[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3).
作者简介:
周爱勇,男,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社科处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朱伟华,女,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地域民俗文化,中西戏剧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