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伴
2018-08-19寇研
寇研
作为一个性格腼腆的人,我人生最初的玩伴和人没关系,没什么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也和玩具没关系,而是一堆奇奇怪怪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那大约是我业余生活最丰富也最自得其乐的时期了。
幼时的第一个玩伴是一只母鸡。这段记忆来自家人的描述,根据他们的叙述,我自行拼凑出我与母鸡和谐共处的图景。在那个画面中,我一岁左右开始自己吃饭,颤巍巍地捏着勺子往嘴里送饭,但勺子往往歪了斜了,喂进嘴里的大半都流了出来,衣襟上一片白花花的米粒。即便这样,我还是把自己喂饱了。
饱了之后就瞌睡。我不哭不闹,随便靠着门槛啊、石墩啊、磨盘啊就能睡着,特别省事。这时,一直在周遭徘徊的母鸡终于逮着机会下嘴了,一颗一颗啄掉我衣襟上的米粒。它总跟着我,一日三餐的点儿也掐得准,时间一到就“咕咕咕”地来报到,因此长得特别富态。
我与母鸡关系良好,公鸡就不一定了。后来家里也曾有一只小公鸡,当它还是个蛋时,我们把它伪装成老鹰蛋,放在屋后树杈上老鹰的窝里。小公鸡是孵出来了,但它对自己的身份认知有些混乱,明明是一只鸡,硬是把自己当成狗,而且还是一只吃里扒外、不认主人的“狗”。每次放学回家,屋后响起我杀猪般的尖叫,院里的人便知道那只高度近视的小公鸡又在上下扑腾着啄我了,非得要权威的老祖母出山,用拐杖戳着地,严厉教育一番,将世间万物归位,小公鸡才幡然醒悟:原来自己只是一只鸡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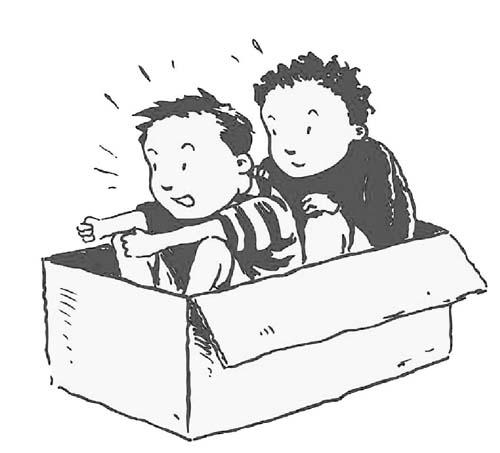
念小学的那些年,一到暑假我就特别忙。大中午的,大人都在午休,我顶着烈日,不辞辛劳地跟踪每一只可能栖落的蜻蜓。我观察它们,尾随它们,注意到那些金灿灿或绿色的小家伙飞得慢了、低了,似乎在打算找地儿歇脚了,就悄悄靠近。等它终于落定,翅膀和尾巴放松伏在枝叶上,我屏住呼吸,蹲下,指头轻轻摁在它的翅膀上。
捉住蜻蜓,我也不会把它怎么样,只想把它当自己的临时宠物。我到处捕蚊子,杀死蚊子献给蜻蜓,还亲自喂它吃。大多数时候,蜻蜓都是有骨气的,不吃嗟来之食。或许是我捕到的蚊子不合它的胃口,喂了又吐,吐出来我还接着喂,乐此不疲。等这个游戏玩够了,或者我自认为蜻蜓吃饱了,便把它放在玉米叶上,任它飞走。用现在的话讲,被我捉住过的蜻蜓,心理阴影面积一定超大,从此以后也许就不吃蚊子,改喝露水了。
我还喜欢看蚂蚁搬家。下雨前,蚂蚁总是要搬家的。蚂蚁大军浩浩荡荡,列队而行,抬着半截苍蝇尸体或是白色的蚁卵。我用树枝、石块拦住它们的去路,有时用湿土在它们行军的路上制造出一个小水坑,让它们感觉,呃,怎么走着走着就到海边了。但它们总有办法恢复行军队列。
院子边上有一个破瓷盆,瓷盆里伏着一窝仙人球。每个晚上,我们洗完脚,顺手就将洗脚水泼出去,刚好淋在仙人球上。仙人球长势旺盛,异常茁壮,于硬扎扎的尖刺中间,育出一株毛茸茸的花苞。花苞吸足了白天的阳光和晚上的洗脚水,一路往上生长,最后出落成一枝毛茸茸的修长的茎秆,顶端站着的花苞,形状像极了手掌朝上、五根手指撮在一起的样子,外面仍有毛毛的叶片包裹着。
直到某个夏夜,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仙人球也等不及要开花了。我提早搬了小板凳,坐在仙人球前,捧着下巴,坐等仙人球开花。夜幕终于完全降临,印象里总是无月的夜,屋里昏黄的灯光洒在院里的青石板上,狭窄的、薄薄的一道光。借着这片微光,我看见仙人球的花苞徐徐张开,毛茸茸的叶片中间,是比竹叶还要修长、纤细许多的白色花瓣,一层叠着一层,符合我对“亭亭玉立”一词的所有设想。
在这样一个漆黑、寂静的夏夜,一大朵圣洁、雪白、风姿绰约的花,于静默中瞬时开放,悄然立在看似丑陋、冷硬的仙人球上,又于第二天太阳升起前枯萎,就像一则美丽的童话。以后在城市里,每次去花市,我首先寻觅的就是记忆中的这株不知品种的仙人球,却再未遇到过。它来得突然,去得不留痕迹,于我的童年,是一个不可再现的奇迹。
幼时所有的玩伴中,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宠物的只有一个———我的猫。它的生命虽然短暂,离世时还是个壮年小伙儿,但在我身边的那些日子,它美美地过了一把做大爷的瘾。它出去打架、鬼混,让我替它善后的糗事,有整整一箩筐。
至今每个夏天去郊区,经过沙沙作响的玉米地,我还会想起它,想起它侧躺在玉米地边的树荫下乘凉、慢慢摇着尾巴的样子,得意忘形至极,就差用一只前爪撑着脑袋,招招另一只前爪,示意我去给它揉腿了。它乘凉,我冒着踩到蛇的危险,奔波在玉米地里给它捉蚂蚱。我捉住一只,双手奉上,猫咪一口咬住,三两下就吞咽下肚,从来也不与我交流味道怎样。
我不稀罕知道蚂蚱的味道,但有件事想起就恨恨的。那是许多年后,我读的一篇科普文章说,猫对甜味是没有知觉的,给它个西瓜,它也吃,而且看上去吃得蛮香,但其实对它而言就是个“大水瓜”而已。我年少时,自己都舍不得花的零花钱,许多都给我的猫买了甜甜的米花糖。它每次吃得狼吞虎咽,喉嚨里发出满足的咕噜声,演技真好啊,真想揪住它,让它还我米花糖。
记忆里那些有趣的户外活动,似乎都是在夏天进行的。夏天是无忧无虑的时节、特别适合在野地里乱窜的时节、爬树下田的时节,也是特别馋的时节。那时的我扎着高高的马尾辫,竹竿一样的细胳膊细腿,是个名副其实的黄毛丫头。我不知疲倦地从老远的山上扛一大枝野山楂回家;坐在井边等一下午,等螃蟹出洞;为了等一个西红柿变红,好拌着白糖吃,一天能去菜园里看七八回。
接下来,仿佛是10岁左右的一个雨天,我在我姐的书包里翻出一本《安徒生童话》,里面有篇《海的女儿》,我来来回回读了十几遍。那个暑假剩下的时间我都在神游中度过,想象着美人鱼海藻般的长发在深海里飞舞的样子;想象着她与女巫交易,每次踮起脚尖旋转,脚趾却像踩在刀刃上一般有锥心之痛;想象着王子和新婚妻子站在甲板上,王子神情略显迷惘,而她冉冉上升,在逐渐变成泡沫飞往天堂的半空中,看着她最亲爱的王子,离她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从此,蜻蜓安全了,蚂蚁安全了,猫咪安全了,西红柿安全了,它们不用担心我没事就去骚扰了。我有了新的玩伴。我在书里寻找童话,寻找情感的、情绪的、生命的慰藉,成了我毕生所想。我的夏天结束了,我的春天开始了。秋天,也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