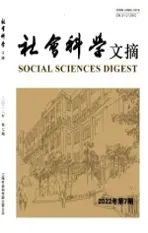作为一门学科的战略思想史
2018-08-15
战略思想史是一门年轻的现代学科。战略探究是自古至今所有国家的国务家和战略家的永恒使命,也是政治学家和战略学家的经久主业,但人们对于战略理论的梳理,或战略思想史及其演进的系统考察,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相对于战略研究具有的当下的社会性、丰富性和多样性,战略思想史这个“行业”却既不时髦也不繁荣,“从业”人员只能依照其个人兴趣和一定意义上的学术自觉或使命感而勉力前行。在这门年轻学科的短暂发展史上,少数杰出的甚至是大师级的战略思想史论者横空出世。他们凭借其系统、深邃而独到的探究和“经典”作品,描绘出了战略思想史研究的“路线图”,包括概念、议题、框架和方向等方面。最重要的是,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独一无二的学术先知先觉、身体力行的不懈探究以及前后一贯的深邃论说,指引着渐次加入这门学科的后来者。
战略思想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战略思想史研究的起点,一般以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米德·厄尔教授编辑的《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希特勒的军事思想》一书的面世作为标志。该书是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学术研究和智库研讨的一项成果,也是当时美、英、法三国学者因应战争需要的集体产物。这本著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的1943年出版,并在其后多次再版,显示了其学术地位和深远影响。一是开拓性。该书是第一部考察近代以来战略思想及其变迁的学术著作,其学术界碑的地位不言自明。在此前各个历史时期,无论在欧美还是亚洲,不乏关于军事史或战争史的专题研究,但关于一个漫长历史时期的军事战略思想及其演变的专门研究却尚付阙如。二是系统性。全书共20章,涉及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希特勒当权期间的30多位战略理论家和实践家,尤其在近现代各个时期各个国家各个领域发挥过全局性影响的战略理论家。三是前瞻性。一方面,该书探究了战争的战略问题和相关理论,如闪电战与歼灭战、运动战与阵地战、战争与社会制度之间以及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之间的关系、作为战争手段的心理和精神、军队纪律的作用、职业军队与民兵的问题。另一方面,该书深入讨论了另外两个更为宏大的方面:其一,国家层次的战略要素,即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背景,以及它们所造就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如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世界政策”;其二,跨越国界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因素,包括重商主义、自由贸易、自由平等与博爱、极权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因为这些与战争的起源和进程大有关联。也就是说,该著作在相当程度上已经采用了大战略的分析框架,从而预示了战略研究和战略思想史考察的未来发展趋势。当然,该著作的主题大体上仍是以战争为重心的,考虑到战争研究发展史的阶段性和成书于大战期间的背景,这是再正常不过了。最重要的是,该书作者团队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和不同年龄段,这种多样性在相当程度上预示了战略思想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以《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为标志,战略思想史研究开始登堂入室。然而,主要由于冷战的爆发和持续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大战甚至核战争的阴影,在很长时间内,战略研究及其主导下的战略思想史考察,仍是“以战争为重心”的。从朝鲜战争结束,经古巴导弹危机,再到越南战争和第四次中东战争,欧美战略界形成了关于有限战争、核战争与核威慑两大战略思想或理论学派,并在各自系统内部衍生出诸多支流,但无一例外地聚集于讨论“战争的战略”。虽然也出现了关于大战略或国家安全战略意义上的探究,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军人与国家》,但却属于凤毛鳞角,只能是旷野呐喊。关于这个时期西方世界和中国对于世界以及各有关国家军事思想史研究的学术成就,在此不予评说,但有两点须明确指出:一是欧美地区(主要是英语世界)的作者开始系统而深入地考察某个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苏联、以色列),某个战略实践家、思想家或理论家(如拿破仑、麦金德、马汉、孙子、毛泽东),以及某个分支领域(如有限战争、游击战、核战争)的战略思想;二是中国学者大体上专注于军事思想史研究,而且主要关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不过,正是以上几场战争和危机,催生了战略研究从纯粹的“以战争为重心”转向“战争与和平的战略”研究,甚至在美苏关系缓和到冷战结束前后,出现了战略概念的泛化趋势和战略研究的繁荣局面:前者主要指战略概念“侵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后者则表现为战略研究扩展到历史时空的各个角落,从而推动了战略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从美苏关系缓和到冷战结束前后,战略思想史研究领域出现了两个呼应战略研究泛化和繁荣的标志性学术成果。一是《现代战略的缔造者》在第1版出版40多年后的1986年修订再版。新版在时间上延展到美苏关系缓和年代,在地理范围上不再坚持欧洲中心,而是包含了俄国与苏联以及亚洲的日本和中国,从而考察了更多的战争形式与战略理论。新版大体上摆脱了1943年编者及主要作者的相对狭义的军事战略思想的限制,走向了十分明确的大战略方向。例如,在内容上涵盖了更多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主要表现为纳入一战和二战期间主要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并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以及二战结束以来的人文战略家的理论及其之间的学术辩论,包括有限战争、游击战和核威慑等理论。总之,新版《现代战略的缔造者》既是一个总结,又是一个新起点;它超越传统的狭义军事战略思想,转而进入大战略或治国方略意义上的战略思想史。二是1994年成书的《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和战争》。该书同样是一部系统而深入的战略思想史著作,编者和作者用17个案例来说明古今历史上最为关键的国家及其战略的缔造过程,其中以两个或两个以上案例来考察英、美、法、德等国的若干关键性时期的战略缔造。同样地,它也是由当时斐声学界的专家或崭露头角的新锐集体创作。然而,该书至少在两个方面大大突破了厄尔和帕雷特的框架:一是在时空维度上不仅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而且包含了欧美以外的关键性国家,如中国和以色列;二是完全从大战略视野出发讨论战略的缔造及其决定性因素和宏大背景,坚决而彻底地转向了战争与和平的战略缔造分析、国家兴衰的战略考察。
以上两部著作及主题虽然完全呼应和总结了当时的战略思想研究现状,但是,如果没有此前战略思想及其各个分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它们的编纂就是不可能的。在此前形成的战略思想研究的学术著作中,主要有:爱德华·勒特韦克的《罗马帝国的大战略》,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遏制战略》。至此,亨廷顿在30多年前开拓的那种先知先觉式的学术探究溪流,终于演变成一条宽阔的理论大河。
在西方兴起大战略研究浪潮前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迅速崛起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战略研究也日益形成一个蓬勃发展的繁荣局面,在传统军事战略之外,大战略研究及其他相应领域的战略的考察,一时领风气之先。中国自身的极为丰富的战略思想资源和渊深流长的战略思想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迸发出新的活力,产生出累累学术成果。以钮先钟先生关于中外战略思想史的系列研究著作(其中影响最为卓著的三种,即《战略家》《西方战略思想史》《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新论》)和吴春秋先生关于大战略理论与实践的系列论述为先河,中国学术界的战略思想史研究一时蔚然成风。自2001年始,解放军出版社陆续推出“当代中国军事学资深学者学术精品丛书”12种,标志着中国战略思想史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此时,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平与冲突研究先驱人物肯尼思·布尔丁提出的社会科学四项衡量标准,即必要的参考书目、开设课程、人才培养和考试、专门期刊,可以肯定无疑地说,无论在欧美还是在中国,战略思想史已经是一门比较完备的学科。
战略思想史研究的主要领域和重要议题
进入21世纪,全球范围内最为活跃的战略研究和战略思想史研究的两大中心,是美国和中国。由于两国战略界和学术界因各自国家的现实战略需求和学术发展进程不同,其战略思想史研究的重点领域和主要特征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但也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并非“巧合”,最主要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崛起,随之形成的中美战略竞争与战略合作,以及由此激发的大国兴衰及其战略竞争与合作关系的历史反思与现实研究。与此同时,在中国和美欧,后者主要在美、英、德三国,传统意义上的战略思想史研究一如继往地展现出令人敬佩的悠久学术传承、广阔时空视野和深邃学术洞察。
在中国军事学术研究和话语体系中,军事思想涵盖了军事战略思想,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群体、理论框架和重要议题。由于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军事战略实践与思想传统,以及中国特色研究群体,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战略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和议题,主要聚焦于中国古代时期。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研究机构军事科学院集体研究成果《中国历代军事战略》《中国历代军事思想》;国防大学承担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计划重点研究课题结项成果《中国军事思想论纲》,在时间上延伸到现代时期,但古代时期仍占五分之三的篇幅。关于当代中国战略思想史的研究,就研究对象来说,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领导人,而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则是重中之重。此外,中国战略思想史研究还形成了若干重点领域或议题:一是中国古代兵书和兵学研究;二是孙子和《孙子兵法》研究;三是先秦军事思想研究。
欧美地区的传统战略思想史研究,学术成果亮点纷呈。
一是克劳塞维茨研究。克劳塞维茨战略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一如孙子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那样,始终是欧美战略思想史研究的一大重心。
二是国别研究和断代史研究,尤其关于特定时期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的战略思想史及其变迁的考察。关于美国战略思想史的著述不胜枚举。这里仅举两例说明欧美战略思想史的演进历程:(1)阿扎尔·加特的《军事思想史》,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了近现代历史时期欧美主要大国的战略思想变迁,以及深入揭示了这些主要国家战略思想和战略传统背后的观念因素;(2)罗伯特·切蒂诺的《德国战争方式》,系统考察了普鲁士及其继承者德意志帝国的战略思想、战争传统及作战模式,尤其是腓特烈大王、毛奇、施利芬等人的地位和影响。
三是专题研究,尤其是现代历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和理论家的地位及影响,一些研究还根据不断发掘的文献资料,力求还原事实或“祛除”迷思。欧美研究者关于现代时期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大国的显要的战争或军事理论家和战略家的专题研究,有一些已堪与克劳塞维茨研究相媲美,如关于利德尔·哈特、约翰·富勒、毛奇、施利芬、德尔布吕克的研究,其系统和深入程度已经涵盖到关于他们的著述、日记、书信以及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有的欧美研究者已开始摆脱纯粹的纵向编年史叙事或分析路径,采取纵与横相交错、大历史时空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考察模式,例如,比阿特丽斯·豪瑟尔的《战略思想的演进》和劳伦斯·弗里德曼的《战略史》,就是其中两项最新的杰出研究成果。
在当代,战略思想史研究形成了两个最为活跃的分支领域,即地缘战略思想史和大战略思想史。这尤其表现为中美两个大国的相关研究进展和学术成果。
美国学者在地缘战略思想史反思方面的研究进展,远远落后于关于地缘战略形势分析和政策规划,后者可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一书的长盛不衰和新闻记者出身的罗伯特·卡普兰的两本地缘政治著作风靡一时的现象中,窥见一斑。美国在地缘战略思想史方面的回顾与反思的泛善可陈,与美国战争与战略研究的传统倾向不无联系,即重视物质和技术而忽视甚至漠视历史经验。相形之下,中国学者由于拥有相当的历史传统优势,因而能够在地缘战略思想史研究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他们呼应中国当下战略需要,对西方传统地缘战略思想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并结合国内外地缘战略思想的发展现状作出相应的评判和展望。例如,郑雪飞和师小芹挖掘了英法两国的并不广为人知的“少数派”海权理论及其影响,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另外两项研究的学术和现实意义更为重大,且均为纵与横相结合的系统研究:一是吴征宇在《地理政治学与大战略》一书中着重指出的地缘战略思想史研究应有的现实战略需要和政策指向的重要性;二是葛汉文在《国际政治的地理基础》一书中所系统展现的当前国内外地缘战略思想的最新发展,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战略思想史研究领域,关于大战略的案例分析及理论归纳最为活跃,而且似乎成为一种显而易见的大国现象,无论是在中国和美国,还是在俄罗斯和印度。这里仅简要评说西方英语世界和中国两地的大战略思想史研究进展。美、英、加学者擅长案例研究,并在两个方面展现出历史时空广泛、案例深入细致的学术特征:
一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战略文化研究,如杰克·斯奈德、江忆恩、彼得·卡赞斯坦对于苏联、中国、德国、日本等国战略文化的创新性研究。西方英语世界的战略文化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逐渐沉寂下去,但这个流派力图揭示战略决策背后的那些经久因素的努力,开拓了一个关于战略传统与战略思想研究的全新领域。
二是大战略史案例研究,尤其历史长河中的帝国和大国的大战略史研究,由战略学家和历史学家合力领此风气之先。如爱德华·勒特韦克、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保罗·肯尼迪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各项研究,以及杰弗里·帕克的《腓力二世的大战略》和勒特韦克后来同样杰出且完全比肩于《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一书的《拜占庭帝国的大战略》,而同类学术论文更是数不胜数。
在中国,大战略思想史领域的研究同样形成了一个繁荣局面。中国学者在战略文化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这些努力主要在于借鉴和归纳,但也不乏理论和方法创新。宫玉振试图梳理中国战略文化及其变迁的线索,但囿于当时理论局限而缺乏对中国战略传统多样性的认识。此后,许多中青年学者陆续对美国、印度、德国以及一些中等强国的战略文化展开研究,并推出一些优秀成果。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在大战略思想史研究方面的归纳、开拓和创新及其成就,令人欣慰甚至兴奋。在归纳方面,周丕启和李枏对于西方大战略理论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系统的归纳和评判,并提出了一些有助于中国大战略研究的思路和建议。在创新方面,继吴春秋先生之后,叶自成、时殷弘、胡鞍钢、张文木等学者呼应中国大战略现实需要,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大战略理论、实践及相关案例。时殷弘先生在开拓和推动中国的战略思想史学科发展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他在主持翻译出版《缔造战略》《现代战略的缔造者》《遏制战略》《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之后,又领衔译出了《腓力二世的大战略》《罗马帝国的大战略》。在探究中西方古典时期,尤其是中国古代大战略传统及其当今含义方面,时殷弘先生也做出了系统努力,推出了一系列影响卓著的学术成果。例如,他在广泛而深入研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中国历史经典的基础上,孜孜探究中国古代大战略传统及其丰富性和多样性,提出了中国古代政治家、战略家、外交家在进攻、防御、迂回、歼灭战、消耗战、远征、朝贡、和亲等各种战略选项之间的取舍,揭示了这些选项或手段之间的非线性逻辑及其复杂的互动关系。他的这些研究旨在说明,中国战略思想传统并不是纯粹孙子式的,中国战略文化也不是天然的或绝对的和平主义,而这正是悠久而丰富的中华文明及战略思想的题中之义。也就是说,他在方法论上间接地提出,简化主义的思想史研究或概括是误入歧途的,也是十分有害的。时殷弘式的中国古代历史经典的战略解读,不仅能够推动中国战略思想史学科大大地向前发展,而且还将展示中国战略传统和战略智慧的当代适应性。
战略思想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
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战略思想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其中,全球范围或各相关国家的军事研究,尤其是战略研究、战争研究以及更广义的安全研究中存在的共性问题,严重制约着战略思想史学科的发展。这些问题的克服,时空维度上的议题扩展,理论和方法的进一步创新,应成为这门学科的未来努力方向。
首先,对应于战略研究的泛化和战争研究的社会化,战略思想史和主要战略思想传统中的“以战争为重心”的传统主题或议题,在此前和当下受到不应该的忽视。战略研究泛化的一大现象是,有关研究者言必称战略或大战略,而对于相关概念、理论、思想传统的变迁,对于更为重要的战争的战略及其战役战术基础和其他各项前提条件,包括领导指挥体制、武器装备水平、后勤供给条件、社会组织动员等物质技术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以及作为大战略的组成部分和资源/手段的分支战略及其相互之间的复杂而精致的关系,既缺乏合理而清醒的认识,又不能作出深入而又细致的研究。另一方面,战争研究的社会化,造成对战争起源和过程所涉及的各项政治、经济及社会因素的细致、深入、系统的研究,而关于战争本身,亦即作战(打仗)本身所涉及的要素,尤其是克劳塞维茨所强调的精神、天才、磨擦等要素,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对战争本身的研究是传统的战略研究的核心任务,也应该是当下和今后战略研究及战略思想史考察的“必需”成分。社会化或空心化还造成另一个消极后果,即战争的起源和后果,与更广泛的国际体系的变化和性质,以及与相关国家的政治社会的变化和性质之间的相互塑造关系,远未得到必要而深刻的研究,而这是战略和战略思想史考察的又一项题中之义。
其次,战略思想史考察的广度和深度,均有待进一步拓展。战略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不应当只是战略理论家和战略实践家,这是战略研究界的共识,但在这门学科的演进过程以及当前研究中,一些研究人员还是有意无意地忽视或无视其他领域的战略思想资源。实际上,当代战略思想史研究正是汲取了战争与战略实践以外的其他学科和领域的思想成分,才获得了长足进展,才打下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基础。例如,作为历史经典,古希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罗撒战争史》为其后直至当代的战略思想史研究所提供的充足养分。部分因为如此,美国最著名的军事史专家唐纳德·卡根以其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研究的多部著作而独步于当今英语世界古希腊战争史研究领域。卡根的多部著作,在修昔底德以及其他研究者以外,提供了关于古希腊战争起源、进程和结局的详细叙事,揭示了古希腊城邦的兴衰过程和原因,以及更为宏大的战略思想因素,包括战争规律、陆海对抗、战争与和平的战略抉择及其困境、战略的道德/伦理维度等一系列大战略问题和议题。
最后,当今战略思想史研究的前瞻性,显而易见有所欠缺。作为一门学科的战略学或战略理论,似乎拥有一些公认的原则或指南,而这主要归因于孙子传统和约米尼传统的影响。然而,战略和战争实践在根本上是有组织的人群之间的对抗行为,因而相关研究不能局限于科学和理性,而应该同时强调人的因素和情感的成分。然而,由于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侵入”,一系列简洁的原则、公式或模型影响甚至主导着战略分析与战略思想考察,那些复杂而具体的领域和情势被抛弃殆尽,包括精神、天才、磨擦等因素,尤其那些涉及社会发展甚至文明演进之核心的社会公平、正义的领域和要素。如果专注科学与理性,而缺乏人文关怀和磨擦因素,战略思想史考察就会在很大程度上缺失多样性和在多样性基础上的前瞻性。
长期以来,战略研究和战略思想考察的前瞻性,或先知先觉,并不表现为顶尖学者的群体性意识和学术研究,虽然不乏个别大师级学者的系统研究和杰出洞见。上面谈及的时殷弘先生及其一系列战略思想史研究成果,其系统性、深邃性、前瞻性,在当下中国战略研究界堪称无可比拟。而这种秉赋或素质的来源,在很大程度上是贯通中西和古今的必然结果。就此而言,战略思想史考察的广度和深度,当成为前瞻性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