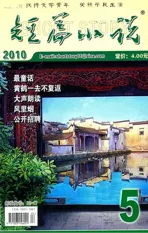奔跑的乡村
2018-08-14何荣芳
◎何荣芳
1
晚上,赵鹏程刚和妻子偎到床上,手机突然不合时宜地响了。赵鹏程很不情愿地趿了鞋,伸手捞着了电视柜上的手机。
“老大,你得回来一趟,家里被搅成一锅粥了!”电话是母亲打来的,她在电话中扯着嗓子尖叫。
赵鹏程的心一紧,手机差点滑落掉。他慌忙问:“到底怎么了?”

母亲说:“还不都是拆迁闹的……”母亲的电话,把她的不满和不安一并从几十里之外传了过来。震得赵鹏程的耳朵嗡嗡直响。
母亲通常不像父亲那样,郑重其事地叫他“鹏程”。母亲几乎都不叫他大名字,平常和人说话提起他就称“大鬼”,多少有点昵称的味道;自豪时称“我儿子”;心疼的时候就称“儿啊”;只有郑重其事的情况下才称他“老大”。赵鹏程在兄妹五人中排行老大,又是家族中唯一一个上过大学、在事业单位舞文弄墨的人,在父母和弟弟妹妹心目中,他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
母亲在电话中称 “老大”,说明了事态的严重性。赵鹏程的妻子才不管事情严重不严重,她一听说和拆迁有关,眼睛立即放出光芒,原先的缱绻迷离顿时无影无踪。老婆问:“这次真的要拆迁了?能分得不少钱吧?”赵鹏程敷衍地嗯了声,伸手想继续他俩的功课,她却把他的手推开,依然兴致勃勃地谈拆迁款的问题。
农村拆迁,这几年在神州大地上几乎成了风气。拆迁要么为了办厂,要么为了修路,要么就是为了扩大城镇开发房地产——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老家村子要拆迁的事,赵鹏程在两年前就已经听到风声了。两年来父亲忧心忡忡,而其他人却都是欢天喜地无限期待。赵家的宅基地宽阔:除了一栋三间两包厢的老房子,还有为弟弟赵小五结婚盖的二层小楼。大家都期待能折现成一大笔的钱,还有相应的安居房。小徽也对拆迁充满了期待,她总觉得丈夫赵鹏程虽然早已脱离了那块土地,但公公婆婆的东西理应有他们的一份。
赵鹏程目不识丁的父亲赵大福,其实是很有主见的人。当年,别人家的父亲只知道让儿女帮着干活,赵大福却执意要供儿子读书。赵鹏程清晰地记得父亲为了给他凑学费,半夜里去山上砍柴,赶着早市把柴卖了,回家时再和大家一样出工干农活。辛苦了大半辈子的父亲,如今儿女们都已成家立业,照说也应该安享晚年了,可他的晚年却不得安宁。
前几年搅得父亲睡不着觉的是土地。
当初土地重新划分承包的时候,父亲手气并不好,抓阄抓了一块“孬”田,一家七口人的田地全集中在“涝八亩”。“涝八亩”当年因为修河堤取走了不少土,不仅土地贫瘠,而且地势低,常年积水。人下去劳作,淤泥常常陷至大腿。“涝八亩”邻近的一块小田被九根抓到了,他就因地制宜在小涝田里种藕养鱼。但闷葫芦一样的父亲,硬是带着一家老小把这块孬田改造成了良田,他似乎要让土地替他说话,让它成了全村人都眼红的大粮仓。
父亲犁田耙地,播种收割,靠着在土地上晒汗水,养大了五个孩子,还把大儿子赵鹏程供养成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如今,“涝八亩”已是种田大户的“农田示范区”的一部分。那里已经被一条宽阔的水泥路切割了,中间还修了一条宽大的灌溉渠。田地里却是衰草连片,棵苗皆无。
赵鹏程后来了解到,“种田大户”往往是打着种田的旗号,骗取政府的扶持基金和奖励款。种田大户们可以利用手中的关系,把实际上承包农田的数字再扩大扩大,好获取更多的钱财。有了这样轻松赚钱的机会,谁还会在土地上下功夫呢?
“涝八亩”一荒就是两年,让父亲心疼得睡不着觉哩。他常常难过地蹲到地头,抠起一块泥土在手中捏着。嗞嗞唦唦的声音,如泣如诉。“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把田地交给他们瞎搞了。早知道这样……”父亲常常像祥林嫂似的絮絮叨叨。
母亲常常拦了他的话题,“你都黄土埋到鼻尖了,瞎操心干什么?在家享你的福不好吗?”
他扭头朝妻子吼道:“有粮才有福!你知道什么?”
赵鹏程知道,父母年纪大了,已经不适合干农活了,弟弟小五和农村绝大部分新生代农民一样,已无意再做农民,其实他们也没有从父辈那里学来做田种地的技能。
土地必须寻找出路,农民已经没有了选择。
只是,江南的水稻田已经越来越少了,少得让父亲心慌,如今世代居住的家园又要被拆,父亲能受得了吗?
这一晚,赵鹏程睡不踏实,长长短短的梦境都在故乡那块土地上纠缠。木槿花的篱笆,摇动金樱子的田埂,村头那棵挂满鞭炮似的花束,顶了几个硕大的鸟窝的老枫杨,还有枫杨树下含羞地拉住他手的小女孩,她曾许诺要给他生个儿子的……小夜曲似的村庄,萦绕到他的骨髓里。有月光的晚上,小伙伴们打仗、偷瓜、撵着萤火虫,欢闹声拥着蛙鸣,从村头漫到村尾,又从村尾漫到村头。那是一副生动有趣的水墨画,船一样异常静谧地泊在他记忆的海湾里。
让人魂牵梦绕的故乡,在现实中早已改头换面了。别墅似的小洋楼,雨后蘑菇般地撑起来;越来越多的水泥地面覆盖了芳草萋萋的泥土。每次回乡,看到故乡日新月异的变化,赵鹏程既感到欣慰,又有几分惆怅。现在,他的故乡,就要在赵家墩子那块活色生香的版图上抹去了吗,就像中学时美术老师抹掉的一面版画?
赵鹏程翻来覆去,最后打定了主意,想办法请个假,一定要在故乡没有彻底抹掉之前回去一趟,牢牢记住它的样子,否则,他只怕是将来梦都无处安放了。
2
半个月之后,赵鹏程在没完没了的开会、出差的空隙里找了个机会,开着他的大众车驰上了回乡之路。一路上看见到处都在拆迁,办厂、修路、建房,大片大片的土地就这样被挥霍掉。到处都是层层相摞的居民楼,有的才有个雏形,还在脚手架中生长;有的已经闪亮登场,仿佛刚刚拆封的玩具积木。
车至赵家墩子村头时,赵鹏程的心紧了紧,一股酸涩的潮水漫了过来。兴建中的厂房已吞噬了芬芳的稻田和热闹的池塘,正一步步地朝村庄逼近。整个村落像被野兽撕咬过,七零八落,满目疮痍。那些先搬走的人家门窗已撬,房子像骷髅一样立在风中哭泣。车在村村通大道上拐了几拐,就看见自家老屋前围了许多人,瘦小的父亲情绪激动地挥舞着短短的胳膊。
“不许砍我的柿树!不许砍我的椿树!不许!谁动动锯子试试!”风把父亲的愤怒灌进了车窗,赵鹏程看见父亲像老鸡护崽似的伸长双臂,从这棵树下,跑到那棵树下。
一台电锯蟒蛇样躺在正开花的柿树下,赵大福拦在柿树前,大有“要砍树先砍我”的架势。
大肚子村主任一手叉着腰,一手指点着赵大福的鼻子,“你以为我们不敢啊?”
他把手抽了回去,插进裤兜,脸唰一下红了。也许我刚才的问题的确难为他了,以前我从没见他的脸这么红过。如果我整夜埋在枕头里哭泣,我也会觉得窘迫。可至少我知道哭的时候怎么掩饰。
穿了一件藏青色风衣的赵鹏程从车里出来了。咵!他狠狠地摔上车门,众人便扭了头过来看他,有人及时地送上笑脸。挺着将军肚的村主任忙过来扯了赵鹏程的衣袖,把他拉到了一边,龇着满嘴的黄牙悄悄说:“都是为了工作,我也是没有办法。你爸死拗,都成钉子户了,你弟已经在征用合同上签字了,你老爸还是不许我们动他的东西。你给做做工作啊……”
赵鹏程调侃道:“老人想不通,工作也要一步步地做是不是?”赵鹏程面带微笑地跟村干部们一一握手,请大家进屋去喝茶。村主任说,不了,不了,你父子先聊,我们改日再来。
赵鹏程转身叫了一声 “爸”,赵大福只在鼻腔里“嗯”了一声。原来像山猴子样亢奋的赵大福,突然就有些萎顿,旧皮革似的脸庞没有一点光泽,目光也显得迟钝了。
赵鹏程踏进父亲的老屋,意外地发现不年不节的,被擦得油光水亮的条几上,供上了三牲,点上了三炷檀香,青烟袅绕在祖父母的黑白照片前。赵鹏程突然明白,袅袅青烟就是倔强的父亲唠唠叨叨的诉求。赵鹏程眼眶一热,同时也因为无力帮助父亲保留家园而心生愧疚。村庄和小城镇的凋零衰败,不是哪一个人伸伸手臂就能够扭转乾坤的,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赵鹏程也不敢看墙上两位老人的眼睛,曾被两位老人当着宝贝疙瘩一样捧在手心里的长孙,却没完成延续赵家香火的重任。少年时,来娣曾经拉着他的手说,要给他生一个儿子。赵鹏程常常不经意间会想起来娣,想起她曾经说过的那句话。赵鹏程不是不喜欢女儿,只是每当面对列祖列宗时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父亲还在生气,坐在八仙桌边闷着头抽烟。赵鹏程陪他坐着,心里乱乱的,也不想开口。父子俩一下午也没有说上几句话。
条几上笨重的老式彩电播放 《新闻联播》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晚饭桌上吃饭了,父亲和小五却都不说话,日光灯铺出卡白的光线,让本该温馨的场景显出了几分惨淡。母亲一边吃饭,一边絮絮叨叨地向赵鹏程抱怨,小五和他爸为拆迁的事差点打起来了,你几个妹妹又常常回家来吵……
母亲把一根鸡腿搛到赵鹏程碗里,说:“家里的笨鸡,香着哩。”赵鹏程又把它搛到了父亲碗中。赵大福看看鸡腿,没有谦让,嗞溜一口吸干了酒盅里的酒,“只怕以后就吃不到笨鸡了。”小五朝大哥使眼色,意思是请大哥说服老爸,叫他不要成天跟大家过不去。赵鹏程装作没有看懂小五的意思,话题一直远远地飘在“新闻联播”的某地灾难里。
晚饭还没有吃完,小五接了个电话,含着饭说:“就去,就去。”母亲问:“又要去哪里?”小五不满地嚷道:“我都是有老婆的人了,你还要管?”
赵鹏程知道,拆迁,对父亲而言,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和老房子,他将失去的是好几代人生活过的家园,是他的老树生根发芽的地方,是他情感的栖息地。现在父亲像鱼一样被扔到了塘埂上,挣扎只能给自己更多的伤害。土地的集中化、集约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小城镇建设是国家从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这些,不是哪一个小老百姓就能改变的。赵鹏程陪父亲聊天,像小学老师一样充满了耐心。又像个老中医,要用灵巧的手法,把堵在父亲心口的那口气给顺过来。
3
赵鹏程从车里走出来,用力摔上车门时,“大众情人”来娣正好在一百多米外的菜地里拔菜。
来娣看见熟悉的身影,心跳猛然加快了半拍。来娣是不种菜的,自从男人带儿子回了他的贵州老家,来娣干事的心气就没有了,像一只趴窝的汽车失去了原动力。她也想过要去贵州把儿子找回来,但贵州那么大,她不知道男人家具体的位置;贵州又那么远,来娣兜里没有许多钱。来娣当“大众情人”仅仅只是为了糊一张嘴,并不是要把“大众情人”当成一种职业。
给她钱给得最多的是村主任。他给的钱,够她穿衣吃饭。想吃小菜的话,她就趁人不注意,随便在谁家菜地里拔几把。被拔了菜的主家虽然心里不高兴,见了面也还会装出一副笑脸来。此时,来娣已经在一块菜地里拔了一把蒜苗,正准备去另一块地里拔几根莴笋。看见赵鹏程回来了,她菜也不拔了,急忙掉头回家。
来娣不敢让赵鹏程看见自己。有几次春节他回乡来,她就躲到外地的亲戚家去了,她怕和赵鹏程不期而遇,或者他会来找她。她花花绿绿的风流韵事,他也一定早就听说了。来娣不在乎别人背后嚼舌头根,却在乎赵鹏程看她的眼光。上学那会儿,同路的孩子都欺负她,常常骂她是捡来的野孩子,只有赵鹏程不骂她。有一次,男娃子们抢了她的书包,把它扔到河堤下,书本、铅笔、擦皮……洒落到草丛里,滚进了河水里。赵鹏程陪着哭泣的她,蹲在地上,下到水里,一个一个把它们找了回来。后来她养父得了肺病,成了药罐子,他常常骑了自行车带她去镇上的药店抓草药……那时候她希望天天见到他,直到被大队夏文书坏了身子才开始躲着他。
她十七岁那年,父亲写了一张申请困难补助的报告,咳着喘着交给她,叫她拿到大队部去找文书盖章。那个姓夏的文书,蓄着几根山羊胡,年纪比她父亲还大。他先用一双贼溜溜的眼睛剥光了她,又用一双干枯的手再次剥光了她。她红艳艳的处女红,换来了困难补助报告上一枚红彤彤的印章。她拿着盖了大队部印章的报告,去乡民政室领回了二十元救济款……
有两个闲汉,站在来娣家门口,叫来娣把麻将摆上玩几牌。来娣摇摇手,说自己有事不玩。
来娣在家等村主任,来娣知道他会过来。
不一会儿,村主任就挺着肚子从赵大福那边过来了,一连声地叫打牌打牌,叫几个人来。来娣坐着沙发上嗑瓜子,不看他。来娣想起了赵大福那夜来找她的情景,赵大福对她说:我求你跟村主任说说,不要拆了我的家……那时候来娣很不高兴,只把赵大福的话当成打她脸的话。
“怎么了,我的姑奶奶?”村主任在来娣脸上轻轻捏了一下。
“你们就不能随他去吗?非要拆他家的房子干什么?”
“这一片都要拆的啊。”
“他家在村尾,留着不碍事,就留着吧。”来娣妖媚地扭扭腰身,向他撒娇。
“又不是你家,你管这闲事干嘛?”村主任挨着来娣坐下,手不老实地伸到来娣身上。
“你就当是我家好了。”来娣后背朝村主任身上靠了靠。
“是你家也不能留。”村主任的呼吸急促起来,目醉神迷,但脑子一点都不糊涂。
村主任伸出一只胳膊,想把来娣扳倒。来娣一扭身子摆脱了,她想到了赵鹏程,无法在这一刻和村主任鬼混。村主任只当是来娣刚才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生气了。他摇摇头,觉得好笑。在他心中,来娣只不过是一块小甜点,而摆在他面前的有一块更大更有色有味的蛋糕,比来娣有味多了。
来娣的不顺从,村主任很不适应,也很不甘心。他从屁股后面的衣兜里掏出皮夹子,粗短的手中从中捏出一叠钞票丢到沙发前的玻璃茶几上,又来扳来娣,来娣就势倒在他怀里。村主任手伸到来娣的胸前,勾头用嘴来拱她的脖子。
“你到底答应不答应嘛?”来娣捏住村主任肥厚的下巴问。
“你管这些闲事干什么?等到赵家墩子村拆完了,我给你在城里买一栋房行了吧?”村主任粗短的手指已经灵活地解开了来娣的衣扣。
来娣拂开村主任躁动的手,“你答应我,留下他家房好吗?”
“这是不可能的。叫你别操这份心。”村主任失去了耐心,变了脸色。来娣挣起来,敞着胸襟,顺手抓起茶几上的那一叠钞票,扔在村主任的身上。红色的钞票纷纷扬扬,像折断的鸟翅。村主任黑了脸,弯腰捡起钞票,口里操了声娘,气咻咻地出了来娣的家门。
4
清早,赵大福就扛着锄头出去了。坝更头有他开荒的三分地,现在都已经到了油菜抽薹开花的时候了。赵鹏程知道,父亲扛了锄头未必是为了薅草,就像文化人出门包里一定都带了笔一样。
小五见父亲出门了,被压抑的兴奋立即抬起头,油嘴滑舌地跟大哥说这说那。说来娣这回给他介绍的女朋友长得不错,说等到回迁房一到手,他就准备和女朋友结婚了,说他要用余下的拆迁款开一家小超市……赵鹏程听到来娣的名字心里咔哒响了一声,像有一只手在一扇门上推了推。他很想问问来娣的近况,却又问不出口。随便问了小五几句他新女友的事,就转换了话题,问小五拆迁补偿款和安居房的情况。
小五站在门前的柿树下抠着鼻子,支支吾吾的,不太想说。只说安居房按每个人口30平米给,不足的自己掏钱买。
这时,村民组长九根抓着一只茶杯,施施然地过来了。他掏出一包好烟,抽出一根来递给赵鹏程。赵鹏程摇摇手,说不抽,昨天抽多了,嗓子不舒服。小五大大咧咧地把九根手中的那根烟抽了过去,给自己点上。九根把好烟揣进上衣口袋,又从屁股后面的裤兜里摸出一包四块五的黄山烟,点着一支叼在自己嘴里。
九根把茶杯放在屁股下当凳子坐着,吐出一口烟来,扳着指头把拆迁款一项一项地跟赵鹏程做着说明:拆迁补偿款,平房每平米补偿500元,楼房每平米补偿800元。每个人头分得30平米的安置房。你觉得不够住可以出钱向开发商买。15平米以内的是平价,大概是当地房价的一半多一点。超过的要按市场价算。这样的话,房子的拆迁款,给新房子一装潢,几乎就没有了。要想装潢好一点,自己还得贴钱。
小五连忙在一旁嚷道:“就是,就是。其实拆迁赚不到什么钱。”
自己还得贴钱?怪不得在网上看到有那么多农民抗拆了。“为什么你还乐颠颠的?”赵鹏程奇怪地看着小五。
小五抓抓打过摩丝的脑袋,吭吭哧哧地说道:“做田没有收入嘛,一亩田一年赚不到一千块。城里找事做总容易些。”
九根又吐了一口烟,把自己的脸模糊在烟雾里,声音也模糊起来:“房子底下的地基还会另算钱,门口的场地和土地都会有转让款,每亩能给到3万块。”小五朝九根使眼色,九根不看他,急得小五直跺脚。
“青苗补偿费也有一些。总的算起来,每个人头大概能摊到八万多。”九根又吸了一口烟,慢慢地吐出来,继续说,“前些年,八万能在镇上买一栋房,现在连个墙拐都买不到了。过几年……唉——”
小五突然一转身走了,脚步声中都透着不满。赵鹏程明白了,小五急切地盼望拆迁,原来早就打算把哥哥姐姐土地的补偿款纳入到他自己的账户上了。
九根又叹了一口气,歪着头闷声不响地只顾吸烟了。他过来,本来是想和赵鹏程聊聊的,他很想知道政府是不是还有更优惠的政策。根据以往的经验,他知道好政策在向下执行的过程中往往会改变,就像夏天里的一盘菜,从城里带到乡下,色香味全都没有了原样。赵鹏程是赵家墩子村唯一一个在事业单位上班的人,对政策的了解应该比村干部更多一些。但九根突然又不想问了,他的疑惑,他的苦闷,他的不甘,他的侥幸的期盼,水泥搅和了水一样,慢慢凝固了,堵在心口,堵得他脸上的表情都木木的。
父亲和九根的郁郁寡欢,像流感一样影响了赵鹏程。他也不说话了,阴郁着脸,低头看着脚下几只兴致勃勃穿行的蚂蚁。每亩三万的补偿款,使赵鹏程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省会城市去年曾以650万元/亩为参考价,按挂牌方式供应商业开发。
九根告辞后,赵鹏程掏出手机,勾头在网上寻找相关的拆迁补偿政策。
他在“一号文件”看到:“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以此看来每亩给三万元补偿款似乎已经不少了。那么六到十年后农民的生活保障呢?小五天真地以为,他们年轻可以在城市另找活路,甚至异想天开地想用拆迁款开一家小超市。赵鹏程知道,没有专长的农民涌进大城市,只会被赶到逼仄的地下室、脏乱的出租房,终有一天他们会梦碎人醒,在热泪中思念曾经的故园。
一号文件上同时也写到:“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这里提到的保障机制是什么?是不是像退休金一样的养老保障机制?农民该不该得到这样的保障机制?
赵鹏程陷入了沉思。
5
听说大哥回来了,赵鹏程的三个妹妹第二天便相继回到了娘家。
赵家墩子村民还没有拿到拆迁款,羞羞答答来借钱的亲戚,几经权衡终于按捺不住欲望的女儿、姑爷们,也来到了赵家墩子村。小五的三姐叶子,在大姐花儿、二姐朵儿的唆使下,曾回娘家哭闹过几回,说父母的那一份财产,她做女儿的本该有一份,她名下的一亩三分地换来的赔偿款,小五若是不给她,那小五就不是人。小五划拉着一支手臂,情绪异常激昂,他骂三姐:你就是只白眼狼。有本事你把田地搬到你婆家去。
赵大福跺着脚吼:“吵什么吵?钱还是公家账本上的数字哩,谁瞧见了?”
赵大福真是老了,跺脚吼叫也没能压下去儿女争吵的气势。母亲把赵鹏程叫回家,主要是解决女儿们和小儿子为拆迁款闹矛盾的问题。
第二天先回家的是叶子。小五一见瘦骨嶙峋的三姐提着一只人造革的红皮包,迈着木偶人一样机械的步子走回来,就委屈地抢先告诉大哥:“就那么几个钱,爸爸还答应发给姐姐们一些,这样我的装修费都不够了。姐姐们也真不要脸……”小五一转脸看见了叶子正瞪着他,立即把后半截话咽了回去。
叶子一看见大哥就照直不拐弯地谈起了赔偿款的事。她说:“大哥你给评评理,我的田地还在娘家,土地赔偿款怎么就没有我的份?”不容赵鹏程答话,小五涨红着脸跟叶子争辩起来。父亲赵大福本来在喝茶看电视里的新闻,一听姐弟俩抬杠就起身出去了。顺手从门后操起锄头扛在肩上,一直朝村外走去,想来是躲清静去了。不久,一辆农用车冒着黑烟,嘎的一声停在了大门口,秃顶的大妹夫开着农用车把花儿和朵儿姐妹俩快速地送回到娘家。
叶子一看两个姐姐也回来了,说话的底气更足了。说:“该我们的,我们凭什么不要?”小五急赤白脸的,尖着嗓子骂他的三姐不要脸,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怎么好意思回娘家来分一杯羹?
叶子也不示弱,站起来挥舞着一只胳膊大声地争辩,满头爆炸的头发好像燃烧的火焰。赵鹏程的大妹花儿站在一边抑制不住地兴奋,她用目光鼓励着小妹。朵儿立即插嘴说:“八万块钱哩,又不是八百,要是八百我也就不要了。”
小五说:“八毛钱你们也别想!这么多年田地谁经管的,都是我在种呢。”
“你种?都是老爸老妈在种呢。你做房子借我们的钱还没有还呢。”朵儿指着小五的鼻子尖叫。母亲凄苦着一张脸,求助的眼神不住地望向赵鹏程。赵鹏程终于忍无可忍,大吼了一声:“都给我住嘴!”
大家一起看着赵鹏程。赵鹏程说:“瞧瞧你们一个个成什么样子,也不怕别人笑话?……多大的事情,就吵成这样?”他有点激动,因为激动而语无伦次;又因为语无伦次而使他的威信打了折扣。短暂的宁静之后,叶子又挑起了事端,她斜乜着赵鹏程问:“大哥,你的那份,你敢说你不要吗?”
赵鹏程一摆手,硬着嗓子说:“我没有打算要。”
叶子皮笑肉不笑地说:“你不要,嫂子那里可能通过吗?”
“这点你们放心。”赵鹏程知道妻子那里也还要做工作,但现在顾不上这点了,只好打包票。
朵儿撇撇嘴,连珠炮似的说道:“你不要,是因为你喝的墨水多你觉悟高。你不要,是因为你在城里有工作你条件好。”花儿在一旁哼了一声,声虽不大,却人人都听得见,她的哼声等于把赵鹏程的意见全盘否决了,他倒成了一个假装好人的伪君子了。
争吵声再次响起,三个姐姐围着孱弱的小五唾沫横飞,小五言语上占不了上风,开始耍横。他推了一掌挤到他身边的大姐,叫她滚。一直坐着一旁抽烟的大姐夫终于吐掉烟蒂站了起来,“你还想动手啊?”大姐夫一把揪住小五的衣襟,母亲哭着扑上去抱住了秃顶女婿的手。
赵鹏程说:“大家都别吵,听我说一句。”他提议把所有的拆迁款交给父母保管。
秃顶的大妹婿嘀咕道:爸爸妈妈偏心小儿子,给爸爸妈妈保管,还不等于交给了小五。
二妹朵儿便抢着说:“小五是爸妈的儿子,又不是我们的儿子,我们凭什么要宠着他惯着他?他要是真有个什么急事难事倒也还好商量,偏偏又是个好吃懒做的主……”
小五立即屁股下着了火似的跳了起来,涨红着脸连连责问朵儿:“我什么时候好吃懒做了?我这么多年是你养着的?”
赵鹏程狠狠地瞪了一眼小五,小五才气哼哼地又剥他的指甲去了。赵鹏程叫大家坐到一起,心平气和地商量。他首先表示,他的那一份他不好意思要,也决不会要。
赵鹏程说几个妹妹和妹婿都是通情达理的人,平时也都孝顺爸妈。现在应该怎么孝顺呢?最重要的是不要让爸妈伤心难过。爸爸妈妈和小五在一块过呢。爸妈老了、病了、不能动弹了,还不是指望他能多出点力吗?现在的事,不是几万块钱的事,而是涉及到做人的事。为了几万块钱,连血脉亲情都不要了,这还不让外人戳脊梁骨吗……
赵鹏程后来又把小五拉到外面,小声地给他普了一回法。劝说他给姐姐姐夫一个台阶下。小五回到屋里,向几个姐姐和大姐夫道歉,说愿意给每家拿一万块钱意思一下,其余的就算他先借她们的。花儿、朵儿和叶子终于不再争吵,最终也都心不甘情不愿地统一了认识:亲情大过钱财,小五最小,大家看在同一个奶头上吊过的份上,伸手帮帮他。
6
来娣从理发师留下的墙面镜里,忽然看见了抬头四处张望的赵鹏程。
来娣从转椅里跳起来,惊喜地叫了声“鹏程哥”!
赵鹏程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很意外地瞪大了眼睛。“你开理发店?”
“不是,我是租进来的。还没来得及改造它。”来娣拿了条毛巾抽打着本来就干净的椅子,“快来坐。”
来娣本来是不愿意让赵鹏程看见自己的,但赵鹏程突然站到了自己的家门口,她就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她也没法不打招呼。
赵鹏程一边环顾着室内的陈设,一边解释他是在给爸爸妈妈找房子。来娣柔声说:“这事你交给我好了,我找好了给小五打电话。”
赵鹏程笑了笑,说:“那太好了。这地方我不熟。”
赵鹏程不熟的还有现在的来娣。赵鹏程熟悉的是过去的来娣。那时候两人在一个教室里读书,来娣坐着他的后面,经常用笔杆捣他的后背,要他给释疑解惑。其实她成绩不错,不至于有那么多的疑问。那时候少男少女的心里埋着一个共同的秘密:一同走出故乡,一同去外发展。那个秘密里也包含着“一同生活”的意味。他没有想到来娣突然不读书了,突然间去外面打工了。那之后,两人就天各一方,再没有见面。他考上大学后给她写过信,却没有收到过她片言只语的回复。他知道她在疏远他,他不明白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还是来娣的心变了。结婚前他每次回到故乡,有事无事都喜欢在来娣家门前的路上走走,期待能够突然遇到她……
来娣给赵鹏程端过来一杯热茶。来娣穿着无袖衫,白皙丰腴的手臂像肥沃的土地一样袒露着。晃得赵鹏程睁不开眼。赵鹏程又想起,那时放学后,他骑自行车回家,她坐在他的后座上,一只手臂揽着他的腰……赵鹏程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瞟向来娣的手臂,心里泛起一股暖意。
在茶水热气袅绕的时光里,两人面对面地坐着聊着过去的事情。来娣不住地用手掩着嘴咯咯地笑着。
赵鹏程喝干了一杯茶水,来娣起身又给他续上热水。
赵鹏程不知不觉又把一杯茶喝干了。来娣站起身要去拿暖瓶,赵鹏程也站起身,制止道:“不用了,我也该回去了。房子的事情就拜托你了啊。”
“放心吧。”来娣说。来娣告诉赵鹏程,赵家墩子的乡亲基本上都在新民小镇租房住下了。老镇政府搬走了,这里的空房间多了起来,而且租金也便宜。像她租下的老理发店,上下两层,四室一厅,一年也才五千块钱。
来娣说着,便引着赵鹏程一处一处看她的房子。她说:“我准备把这里改造成棋牌室,收点桌费过日子。”
在来娣的卧室里,赵鹏程看见床头柜上放着一张小男孩的照片,三四岁的样子,笨拙地抱着一只篮球,咧嘴冲着赵鹏程笑着。
“我儿子。”来娣见赵鹏程盯着照片看,温柔地介绍了。
“儿子?”赵鹏程依然盯着小男孩,他觉得小男孩应该是他儿子。他想起了有一天来娣做值日,冬天夜晚来得早,他们回到村里时,月亮已在东边的树顶上探出头来。老枫杨树下,来娣突然拉住了他的手,羞怯怯地看着他,“我要为你生个儿子。”赵鹏程整个人就被她的话电着了,木呆呆地张着嘴。来娣见他没有反应,掩面快速地逃了。
自己要是有一个儿子就好了,赵鹏程心里涌起了一股厚望。那样的话,他站在祖宗的牌位前就不会心虚得像脚踩在棉花上了。他扭过头看来娣,目光烫烫的。来娣不敢接他的目光,扭了头看别处。
赵鹏程没有逮住来娣的目光,他逮住了她的手。来娣的手柔若无骨,滑溜溜地像想要出逃的泥鳅。赵鹏程伸出另外一只手,把来娣揽进了怀里。
“给我生一个儿子。”赵鹏程一边亲吻着她的脖子,一边喃喃道。
来娣猫一样温顺地靠在他的怀里,幸福得想流泪。“已经生不了了。”来娣好遗憾。
赵鹏程突然僵住了,来娣感受到了赵鹏程身上传递过来的寒意,她抬起目光寻找赵鹏程的眼睛,她希望还能看到熔化人的火。赵鹏程的目光呆呆的,怔怔地看着床头柜上抱着篮球的小家伙。
赵鹏程松开了抱着来娣的双臂,心中空落落的。家乡的土地流失了,家园被拆了,青梅竹马的女人也不能生育了。它们像一条河流一样流出了他的生命,全然不顾他的眷恋,自顾自地流走了。赵鹏程心里空得痛。
来娣泪眼朦胧中,看见赵鹏程踉踉跄跄地下楼去。
7
晨曦从东山挤破黑色的帷幕,迅速地占领了广袤的原野和静谧的村庄。厨房里已经有了动静,母亲放出了鸡鸭,开始从黝黑的大瓦缸里舀水洗锅,生火做饭。檐下响起了父亲的咳嗽声,像啄木鸟啄着一段朽木。敞开的窗口灌进来甜丝丝的夹杂着青草味的空气,赵鹏程贪婪地深吸了几口,跃身起床。
赵鹏程洗漱完回到堂屋,看见父亲赵大福已经在油光水亮的条几上摆上半生不熟的三碟鸡、鸭、鱼,给青花瓷的小酒盅中斟满糯米酒酿,泡上三杯自家炒制的清茶,点燃三炷上好的檀香。
父亲花白的脑袋在檀香的青烟中一起一伏,他合起双掌连连作揖,口中念念有词。礼毕,父亲转过身来对赵鹏程说:“你今天要回去了?临走前也给祖宗们上炷香吧。”父亲说,“以后换了地方,只怕他们找不着了。就是找着了,门神不认识他们,也未必会放他们进屋。”父亲说完,站到了一边,看着赵鹏程。
赵鹏程走到条几前,从香盒中抽出三支檀香来,用打火机点着了,举过头顶,朝中堂画上贴着的列祖列宗的名字和墙壁上悬挂的祖父母的黑白照片,恭恭敬敬地鞠了三次躬,小心地把燃着的香插进香炉里。赵鹏程也想像父亲那样跟祖宗们说些什么,一时间却又找不到要说的话题,心中反而生出一种愧意。他尴尬地朝父亲看看,父亲已经转过脸去,呆呆愣愣地看着门前的树木和树木底下欢快的鸡群。
吃罢早饭准备回城前,赵鹏程拿出手机,打开录像功能,在老屋的前前后后转了一圈。小时候躲过猫猫的犄角旮旯、总是对着树根撒尿的老杏树、打陀螺滚铁环的晒场、瓜果诱人的菜地……他统统都要装进手机里带走。扎着头巾的母亲站在檐下,善解人意地看着他笑。父亲跟着他身后转悠,说:“拍吧,拍吧,你下次回来这些恐怕就没有了。”
赵鹏程删除了手机内存中其它的内容,来到坝更头的高地上,对着整个村庄慢慢拍摄。村尾的那棵老桑树,还能结出乌紫的桑椹吗?它的树干曾被小伙伴们爬得光光溜溜的。九根门口的池塘里,一到夏天就铺满了碧绿的荷叶和洁白的菡萏,他为它写的诗文还发在了省刊上。新龙河是小伙伴暑期的游乐场,他们白鳍豚一样在水里钻来钻去,可惜现在河水已经不再清澈。他戴着破草帽,高卷起裤脚干活的“涝八亩”也不见了……
赵鹏程开车驶离赵家墩子时,在坝埂头再一次停下,他拉开车门走下车,久久地凝视他的故乡。他看见枫杨树下一个穿白衣的女子,正站在那里朝自己凝望,南风吹动起她的衣袂飘飘扬扬。是来娣吗?她来送我吗?还是来通知小五,她给找到了出租房?赵鹏程看不真切。他取下眼镜用纸巾擦擦镜片,用手臂揉揉酸涩的眼睛,重新戴上眼镜,再朝老枫杨树下看时,白衣人已经没有了踪影,只有老枫杨一树的葱绿在那里静谧着。
赵鹏程不再去寻找白衣女人。他打开车门,临上车前,目光又缓缓地把赵家墩子村从东抚摸到西。
“来年此时,我还能在这里看到你吗?我的诗歌即便有萤火虫的照亮,还能涉水着陆,停在你的掌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