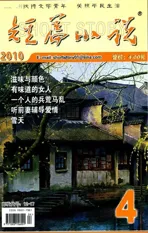杀死牡丹花
2018-08-11叶凉初
◎叶凉初
昨夜是这个月的最后一个夜班,因此早上比平时提前一小时换班,开着电动车回家,时间不过六点,隆冬清寒的路上,行人稀少,同样稀薄的空气,钻心的冷,特别是一双膝盖,像是不住地往上面浇凉水,手指也麻木了,不听指挥。
我在楼下的小卖部里买了方便面和薯条,磕磕绊绊地将电动车推进车库,抱着东西往楼上冲。
“小东,你下班了?”
我看到冯阿姨,她用一块蓝花布包着头发,身上系着做饭用的围单,趿着一双黑色棉拖鞋,要不是她唤我,我简直认不出她来。冯阿姨是个和蔼的小学老师,两年前搬来我们小区,平日总是打扮得规规距距,一丝不苟。我们这小区没有物业,也不收物业费,也没有专人搞卫生,楼梯上总是脏乱不堪,但冯阿姨来了就不一样了,她至少每个月会扫一次,这半年,楼梯洁净,连扶手都锃亮。
冯阿姨在我面前直起身来,看了看我手中的食物说,就吃这个哪?上了一大晚上的班,要吃点好的,好好睡一觉才行。我马上就好,你过来和牡丹一起吃早饭。
牡丹是冯阿姨的女儿,读六年级,成绩好,是个清秀的小女生,她刚刚起床,正在梳头。看到我,大眼睛惊喜地闪了闪,小东哥哥!她叫我。
冯阿姨给我端来一碗热乎乎的红豆粥,又下了一碗青菜肉丝面,看我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她笑了,说,男孩子就是好,你看牡丹,吃的跟个小猫似的。
我回对门的家里睡觉,冯阿姨带着牡丹去学校。
我的家,像一只冰窟隆,有时,我真希望开门进去时,突然发生点什么事,这家里有钥匙的另外两个人,谁回来了。可是,没有,一只老鼠也没有窜过,茶几上厚厚的积灰,一个杯底的印子仍然完好无缺。别人的白天是我的夜晚,但我不怎么想睡觉,我坐在床头,点了一支烟。
我叫袁小东,今年十八岁,春天时过的生日,那时,我还在市中等职业学校读书,六月份毕业后,玩了三个月,九月,我去找居委会的王主任,才有了现在这份工作,在派出所做联防队员,一个月有近两千块钱的工资,我想,十八岁,自立,我做到了。冯阿姨却很不赞成我的工作,她觉得既然我不上大学,读书的路走不通,应该去学个手艺,到底,我还太小了,同龄人都还在学校里,联防队员又不能做一辈子的。可是我决定上班,我能学什么呢?我什么都学不进去,而且,学徒又没有收入,我怎么养活我自己?我十八岁了,我怎么能像从前那样靠爷爷奶奶养活呢?我只想有收入,不用动脑筋的工作,我只想麻木地活着,我十八岁的身躯里,有一颗八十岁的心。我看牡丹,她比我小五岁,可我们像是两代人,她那么天真烂漫,快乐得令我难过。
我躺进被窝时想到,快过年了,真快啊,一年又一年,妈妈走了三年了,爸爸走了也快两年了,我不大想起他们,也不在乎他们想不想我,但每到逢年过节,思绪便不受控制地胡思乱想,我望了望灰蒙蒙的墙壁,突然有了主意。
小的时候,在乡下,每到过年,都要大扫除,大人们把大件的家俱搬到场院上,用热水一遍遍抹洗,爸爸用稻草做一个草把子,让我举着,四处掸檐尘,离春节还有好几天呢,那浓浓的年味就扑面而来。我的主意,就是在过年前把这个家好好打扫一遍。因为心里有了着落,我很快沉沉睡去,醒来时已是半下午,阳光晃眼,暖暖地撩拨着我的眼皮。
我把家里所有的窗帘都卸了下来,它们从未被拆洗过,连拉开的时日都很少,生涩的拉链哧哧地响,惊动了无数的尘埃,密密地在阳光里舞蹈,我不由自主地掩住了口鼻。
洗衣机欢快转动的同时,我把地板仔细擦抹了一遍,扔掉了两大袋垃圾,找齐了所有的厨房用具。深夜十二点,我坐在光洁一新的客厅里抽烟,客厅的窗帘还没干透,没挂窗帘的窗户有些异样,像光着身子的人,虽然我没有开灯,窗外是沉沉黑夜,但仍然像在透明之中,没有安全感。我折回卧室,新洗的窗帘散发着阳光的味道。往常这个钟点,我们会在吴平路上巡逻一圈,深夜的马路上寂静无人,显得我们渺小,大家推推搡搡的,相互壮着胆子。他们都比我大,但我的胆子比他们大,我真想不出有什么可怕的。
我了无睡意,抽了一地的烟,打开窗户,一股冷空气像候在那儿似的,呼一声扑进来,令人精神一爽,令我惊喜的是,当空一轮明月,瘦,洁白,明亮,发出寒剑似的光芒,冷冷地看着我,我也看着它,离过年,应该还有十五天吧,它告诉我。我突然想,今年,去哪过年呢?
爷爷奶奶一定是盼着我去的,可是,想想回到村子里,四邻八舍的眼神,我就不寒而栗。可想到如果我不回去,就得由爷爷奶奶来抵挡这样的眼光,我又觉得必须回去,到底,我是个十八岁的男人了。
爷爷奶奶的家,也就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就在这城市边上,不过十多公里远的一个村子,我小的时候,村子像一座桃花岛,四面环水,只有一座小石桥与外界相接,一条河流绕着村子,人家面水而居,河边种着桃树,春天时,桃花绽放,雨后凋谢,把整条河水都染红了。也就突然之间,小石桥被加宽,村里涌进来许多外地人,爸爸是最早一个把家前屋后的空地都修了房子的,共有一百二十多间,哗的一下,家里到处是人,充斥着各种方言,宽大的院子被挤小了,我紧紧拉着奶奶的衣襟,紧张地看着这些人,从我们家的水龙头里放水,在我家的场院上晾衣服,大声说话,后来,村里几乎每家都是这样子了,我们从农民变成了房东,他们是房客,来自四面八方。
我的爸爸本来是个木匠,他能在一块普通的木头上雕刻出繁复美丽的花纹,他给我做的木头手枪精致轻巧,别在腰间可以以假乱真。但很快,爸爸就不上班了,跟着他学木匠的小徒弟也回掉了,他的生活变得悠闲自在,睡觉和打麻将,和妈妈吵架,有一个晚上吵得厉害,楼下的爷爷奶奶都起来了,第二天,妈妈就离开了家,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隔壁的婶婶说她跟一个老板走了,但半年后,妈妈又回来了,不多久,又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几个月后,爸爸也住到邻村的一个女人家里去了。我在初中时学习不错,也有过远大的梦想,可是,在爸爸妈妈走后,一切都变得不再有意义。爸爸有很多钱,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问题不是钱能解决得了的。我小的时候,总想挣很多钱,孝敬爷爷奶奶,可是现在也不用了,爷爷奶奶也不缺钱花,他们缺的是快乐,体面的生活,这也不是我能做到的,这是我长时间无法回到村上去的原因。我在村子里没有玩伴,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村子里有很多人,但都不是我认识的,这不是我从小熟悉的村子,我对那里没有思念,因此也没有回去过年的期待。
我在黑夜里无法入眠,这不是我的睡眠时间,四下里那么安静,我像飘浮在黑色的海面上,海浪轻柔无声地涌动,我慢慢合上了眼睛。
突然,门口传来剧烈的敲门声,我支起半个身子,仔细谛听,发现敲的不是我们家的门,而是对面冯老师家的门,听起来,来者不善,这半夜三更的,冯老师母女一定吓坏了,我正要开门过去,对门的门吱一声开了,借着楼道里微弱的灯光,我看到一个中年男人的身影,挤进了冯老师的家门。
已经三点多了,我搬了张椅子坐在门边,随时观察着对面的动静,但一切平静无波,我抽了一支烟,回到了床上。
等我再次醒来时,已是下午两点,这是我平常醒来的时间,这个月,我要上白班了,我得把时间颠倒过来。我在床上翻动着身子,心里有一种流动着的不踏实,但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它像一条狡猾的小鱼儿,在我的身体里乱窜,却怎么也抓不住它。
门口传来微弱的敲门声,怯怯的,犹豫不决地,我腾地一下跳起来,是了,昨夜冯老师家的敲门声,正是我身体里的小鱼儿。
我打开门,门口站着牡丹,她低着头,头发散乱着,看我开门,飞快地跳进来,像一只敏捷的兔子。
怎么了,牡丹?
小东哥哥,我在你家待一会儿。
牡丹,你怎么没有去上学?还是已经放学了?
学校已经放寒假了,我爸爸来了。他们在吵架。牡丹小心地指了指自己的家门,轻声说。
你爸爸为什么来吵架?你爸妈不是已经离婚了么?我给牡丹倒了一杯水。
不知道,为了钱或者为了我。牡丹摇摇头,用手指拂了拂头发。我看了看自己粗短的手指,牡丹的手指洁白纤长,她在学钢琴,这样的手指,天生就是为了弹钢琴的。
你爸妈,为了什么离婚?我问牡丹。
我不知道。牡丹的声音很低。
那是谁的不好呢?孩子的世界就是这样一清二楚,非此即彼,我们家,我以为是爸爸的错,至少他错在先,听说他和邻村的女人有染之后,妈妈才和他吵架,才离开家的。冯老师那么优雅知性,一定是牡丹爸爸的错。
是、是我爸的错,他做生意失败了,从此就赖着我妈妈。牡丹说这话时,目光投向三千里之外,我知道,她一定在想从前,从前,对我们来说,都有过短暂的好时光,爸爸和妈妈,都在一个家里住着,哪怕吵架呢!
小东哥哥,你为什么一个人住呢?妈妈说你是个好孩子,可为什么你没有爸爸妈妈呢?牡丹问我。
我长大了,十八岁就该一个人住了。我不想告诉牡丹我们家的故事,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但冯老师说我是个好孩子,这令我高兴,很久没有人这么夸我,何况是老师呢。可是,在学校里,至少像牡丹那么大时,我的确是个好孩子。我确信我没有变坏,但我在别人眼里却已经很久不是个好孩子了,比如我没有考上高中,我在职高里谈了一场恋爱,我的女朋友思思有一阵子就住在我家里,这一张张标签,把我变成了坏孩子,可是我不在乎,这标签不能给我带来痛苦,就像我在深夜空无一人的马路上不能感到害怕一样。
天渐渐黑了,我问牡丹饿不饿,我想带她出去吃顿好的。她缩着身子摇摇头,目光担忧地望着门外,对门安静如故,他们既不争吵也不说话,我叫牡丹发了条短信给冯老师,然后,我拉着她下楼了。
她一路都不开心,踢着一粒石子走,回头问我,小东哥哥,我以前听说我爸爸不喜欢我是个女孩子,可你是男孩子,你爸怎么也不喜欢呢?
我不知道,因为我是个男孩子,我倒从未在这个问题上纠结过,我小的时候总是想,爸爸和妈妈都那么忙,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关心我,那为什么要生下我呢?可我现在不那么想了,我十八岁了,是个大人了,可以解决生活中的一切难题,我看了看牡丹,为她细弱的身子发愁,她比我小五岁,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力气撑到自己长大,到十八岁。
我带牡丹去喝羊汤,因为她说她喜欢,我自己不太喜欢这么腥膻的东西,喝了还会长痘痘,可是牡丹说得对,喝了身子很暖,有力气。满街的藏书羊肉店,我们挑了灯光最亮的一间,每家的格局都差不多,门口用玻璃隔着一个小柜台,里面放着羊肉冻羊糕油条,一摞摞的蓝边大碗。我和牡丹坐在桌子的两侧,桌子中间有一只电磁灶,开关绑在桌腿上,红色信号灯一闪一闪的。
我们叫了一个明炉,要了很多羊肉。这两年来,我在牡丹家里吃了不知道多少回早餐,却没有机会回请她,所以我叫她使劲吃,完了再给冯老师打包一份回去。
这种小型的羊肉店一般都是夫妻老婆店,这家也是,丈夫精瘦,妻子却胖胖的,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子趴在桌子上玩电脑,不像是顾客,果然,过了一会,老板叫他帮我们拿碗筷,他极不情愿地站起来,眼睛却像粘在屏幕上似的。老板快步从我们身边走过去,旋起一股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合上了笔记本电脑,儿子白了一眼,没敢吭声,将两套消毒碗筷放到我和牡丹面前。我呆呆地看着这一切,久久才回过神来,心里不是滋味,牡丹也是,看得连脖子都扭过去了。我心里一痛,这种寻常不过的父子之情,于我和她,都是一种触痛。
牡丹回家时,她父亲已经走了,冯老师垂着头,右眼眶显著地红肿着,但她飞快地关上门,我什么也没有来得及问。
看着焕然一新的家,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我不想去村里过年,又不想爷爷奶奶独自过年,可以把他们接来城里,这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可是,爷爷在电话里说,今年有好几家租客不回去过年,所以他也不能离开家太长时间,把家交给外人。我真想不通,那些租我家房子的人,把幼小的孩子留在老家,独自或者夫妻俩出来打工,过年也不回去,难道就不会想家想孩子么?我告诉爷爷,过年我会回家,等我吃年夜饭。爷爷沉默了一下,说,听说你爸和你妈都回来了,可都没在自己家住,过年,你叫上他们一起回家吧。
我爸和我妈都回来了,可是没在村里的家住,也没在城里的家住,我不知道他们住在了哪里,因为他们的家太多了。可是,回来总是一件好事,想着他们也和我一样生活在附近,在这片土地上,我心里有一种安定,相比不知道他们身在何处。
很快,我就知道他们为什么回来了,因为村子要拆迁了。为房子,爸爸和妈妈又续上了从前吵架的日子,因为爸爸认为,妈妈既然自己从这个家里搬出去了,就不该再回来,更不应该独得一套房子。妈妈则认为爸爸有错在先,道德败坏,更没有资格得这套房子,应该直接写到我的名下,省得到时分给外人。妈妈所说的外人,我很明白,爸爸还年轻,他很可能与别的女人再生孩子。我很快离开了家,我觉得这个吵吵闹闹的地方,还不如我一个人的家,虽然孤独,但是安静。按规定,我们家可以分到四套房子,加上城里的这套,我们家的五个人,每人都有一套房,可是,却没有一个家。
牡丹说,她们要搬家了。我问她搬去哪,她说不知道,总是在这个城市里转悠呗,因为妈妈有工作,她们不能去别的地方,但搬来搬去,总是不出半年就让爸爸找到了,然后,寻找另外一处地方。
你爸爸,到底想要干嘛?他们不是已经离婚了么?我真是不理解,为什么大人们总是这么纠缠不清呢!
我想他是想要钱,总是以看我为由头,妈妈说法院规定十八岁之前他都有权力来看我。牡丹低着头,玩着自己细长的手指。我又一次感觉到成年的好处,十八岁,有一种真正的人生自由。可是对牡丹来说,十八岁还很遥远,他们将继续在这城市里辗转么?
那他到底要多少钱才能放过你们呢?我问牡丹。
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很多钱吧,可是多少算很多呢?妈妈说她的工资只够我们俩租房和生活,并没有余下的钱。他们总是为这个吵起来,以妈妈被打为结束,小东哥哥,你说我妈妈会不会有一天被打死?牡丹的眼睛,还很清亮,那种一尘不染的干净,我没有办法回答她,因为我也不知道,但听起来,她爸爸好像有严重的心理疾病,以打她妈妈为发泄,这是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
在村书记的调停下,我们家的争吵终于尘埃落定,四套房子各归各住,但都写在了我的名下,我不过十八岁,名下有五套房子,俨然是一个新生代的土豪,可是我一点也不开心,我要五套房子来做什么呢?我又不能跑来跑去轮流住,房子不是家,我仍然是一个没有家的孩子。
这个周日,我休息,冯阿姨叫我一起包饺子,她说快过年了,咱仨一起吃顿饺子算过年了,因为她们母女俩要回牡丹的姥姥家过年。一大早,我去买菜,虽然独自生活,但我对买菜没有什么经验,因为我很少自己弄吃的,一个人,兴冲冲地做好了饭,吃的心情却没有了,所以我不做饭。但我会做饭,以前在村子里时,我常常做饭给爷爷奶奶吃,奶奶说我有天赋,会做菜的男人是爱家的。冯阿姨看了我买的菜,笑着说我是一个暖男。我们三个人都笑了,牡丹说,他们班的女生都喜欢暖男,暖男可能不太帅,但很温暖,小东哥哥既帅又温暖。
冯阿姨包了三个巧克力饺子混在其中当彩头,她问我去哪里过年,我说我要回村上,陪爷爷奶奶过年。她点点头,说,小东你真是个好孩子,也是个穷得只剩下钱的孩子,可你还有这份孝心。气压有点低,牡丹端出三杯咖啡来,她正在尝试喝咖啡,说小资而有味道的女人都爱喝咖啡。说着,她用细长的右手端起咖啡杯,优雅地站到了窗前,还扭身朝我们摆了个pose。牡丹穿着一件灰色毛衣,一条紧身彩条裤,颀长的身子楚楚动人。我正想对冯老师说,看,咱牡丹是个大姑娘了。冯老师的神情有些古怪,她几乎是眼不错珠地看着牡丹,心醉神迷。这样子吸引我,我想不起我的妈妈是否曾这样看过我,仿佛我是这世上无与伦比的瑰宝。
这顿提前的年夜饭吃得很开心,最开心的是我们仨都吃到了巧克力饺子,不多不少,一人一个,这预示着来年我们都会有好运气。
年二十八那天,爸爸和妈妈都打电话来请我去过年,顺便说一下,拆迁房安置结束后,他们已经正式离了婚。我选择了年二十九去爸爸那儿过年,说不上为什么,与其面对另一个陌生男人的尴尬,仿佛面对一个陌生女人更容易些。
妈妈是有先见之明的,爸爸的女人已经怀孕了,她看起来很年轻,和我打招呼时,脸上的笑容还有羞涩的味道,她看起来像我的同龄人,腹中却怀着我的弟弟。父子俩多年没见,更没有好好聊过,气氛有一些些僵持,但一顿饭的时间毕竟可以忍耐,我无厘头地想,下次见面,也许弟弟可以满地爬了,我得记得带点孩子用的东西来。
饭后,爸爸送我出来,我坚持不要,就隔着几幢楼的距离,但他说他也想回家看看爷爷奶奶,我不好再拒绝。
夜色如墨,淡淡的路灯光,这个拆迁小区还很新,树木还没有长成,光秃秃地站在冬天的夜里,不知道冷不冷。楼上人家的灯光,从窗户里泄下来,倒是有些暖意,我们一路走着,没有说话,即便是亲父子,也觉得无从说起,可是,也就在这一刻,我突然原谅了他,我能感觉到他的沉默里那股忏悔的气息,他只是说不出口,但已经从他的毛孔里散发出来了,因为我闻得见那股味道。也许,人生真像走路一样,走岔了道,只好一路错下去,无法回头,那便是另一条路了。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幸好我已经长大,我十八岁了,我像个大人一样原谅了父亲,这让我多少有点得意。
爷爷奶奶与爸爸之间,比起我和他,看上去好多了,也许和他们的年岁有关,奶奶甚至还问了小珏的身体,那是她的新儿媳,怀着她的新孙子,我在心里笑了笑,我不妒忌,我想,人能忘怀过去朝前走,总是好的。但这个家,这些人,与我的关系因此而更淡薄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感觉如此真切,像指缝里的水,眼睁睁看它流走了。
年三十的早上,我在小区门口遇到大军,他是我的童年玩伴之一,那时,我和他,还有秦鹏住在同一个村子里,他们俩和我一样,也没有考上好的高中,便也没有读大学。大军穿着时尚,染着鲜黄色的头发,看上去十分的萨马特。我们很久不见面了,偶尔在微信上沟通一下,所以这样突然的见面让我们都有一丝本能的羞涩,但很快就交谈自如了,像淡淡的初雪,阳光一照就融成了水。大军告诉我一个让我十分震惊的消息,他说,秦鹏进去了,就在几天前,因为吸毒。秦鹏,是我们三个中最小,也是最老实的一个孩子,我只知道他高中毕业在家,后来去学过几天理发,怎的就吸毒了呢?大军四下望了望,悄声说,给带坏了呗,村子里有好几个人吸毒呢。毒品,曾经是离我们多么遥远的东西啊,只在电影电视里见过,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童年时的小伙伴有一天会也沾染这个。
大年三十,对于我们来说是最空闲的时间,像水果店卖不掉的甘蔗,站东边也不是,站西边也不是。拆迁小区和别的小区不同,巴掌大的空地都种上了菜,有人甚至养起了鸡鸭,一到冬天,好多人家都生了煤炉,墙角屋后都堆着干柴垛。我和大军在小区里无聊地绕来绕去,要把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消耗掉。大军说,不如,去看秦鹏吧。
看守所是新搬的,离市区有点路,我想开电动车去,大军说太冷了,打的。
也许是因为大年三十,来探望的人很多,看守所里很热闹,填完了单子,我们很快就见到了秦鹏,他看上去瘦了好多,缩着身子,像一只可怜的小鸡仔,我不知道他吸毒多久了,但他看上去真像一个有毒瘾的人。看到我们,秦鹏的眼圈刷地红了。我和大军没有经验,虽然是大年三十,却是空着手来的,钱倒是有,不知道秦鹏在里面能不能用得上。果然,他摇摇头,说不需要。还说他妈妈早上来看过他了,也带了吃的。秦鹏一直垂着头,不怎么说话,我们仨,相对无言地坐了一会,秦鹏说,你们还是回去吧,快吃年夜饭了。
年夜饭的规矩,再远也要回到家,和家人们一起吃,这个,秦鹏做不到,其实我也做不到,很可能,我永远没有和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吃年夜饭的机会了。可是秦鹏失了自由,觉得外面的什么都是珍贵的。他一定会想起,我们一起住在村子里时,年夜饭开饭前,我们几个东奔西窜,看谁家的菜式多,花样新,比来比去。大人们做饭,我们把小卖店里的小爆竹包圆儿了,点燃后快速扔到小河里,沉闷的响声,飞溅的水花,我们畅快淋漓的笑声。
出了看守所的大门,大军递给我一支烟,我们靠在路边的大树上,边抽烟边等出租车,谁也没有说话,天空阴暗苍茫,很像大年三十,也很像我们此刻的心情,大军鲜黄色的头发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一副不良少年的样子。我突然想,大军会不会也吸毒,只是没有被发现?但我没有问他,我没有勇气,也觉得没有意义。我们在小区门口分手,大军说,他倒是能和自己的爸妈一起吃年夜饭,可是他爸妈为了生不生二胎的事情天天吵架,烦。我倒有点羡慕他,大军和我一样大,过了那么多年,他爸爸妈妈想生二胎,那得多牢固的感情呐,我的爸妈,都和别人生二胎去了。我问大军想不想要弟弟妹妹,他摇摇头说不想。大军家也分到了四套房子,如果有了弟弟或妹妹,他将来继承的财产就会少一半,可他说才不是为了财产呢,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对谁都没有深厚的感情,他说他的心里存不住感情,心底像漏了一样,从十三岁到现在,他都没有再哭过了,爱没有,恨也没有,有点像个木头人。他苦笑了一下,扔掉手中的烟头,像个大侠似的扬扬手,回身走了。看着他的背影,时尚鲜艳的头发,像阴郁天空下的一丛火苗,我给他发了一条微信,哥们,新年快乐!
读书时,大军的作文很好,没想到他现在的表达也很到位,其实我和他一样,也对什么都没感情,无法投入,难道这是我们这代人的通病?一切都来得太容易了,无需努力争取,便什么也不珍惜,没有得到过浓酽的爱,因此也无法付出。纷繁的世界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全心全意的事情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做到。可是我有点想念牡丹和冯老师,也许因为相似的境遇,才让我和她们格外亲近吧,牡丹就像是我的妹妹,而冯老师像我理想中的妈妈,像牡丹这么大时,我还在我的好日子中,我迟迟留恋不愿离开,像在冰凉的黑夜里回想春天的阳光,那种暖融融的感觉是多么美好。
更确切地说,我有点担心她们,因为前几天,牡丹在微信上和我说,她们回到了姥姥家,没想到她爸爸早早在那儿等着她们了,姥姥家里的人不知道爸妈已经离婚了,所以大家过得很辛苦,她们打算提前回来了。
我说你爸究竟想干嘛?牡丹说,想钱呗,还能想着我们啊,可是妈妈真的没有钱。牡丹黯然地说。
冯阿姨没有钱,可我有钱啊,我就是不知道牡丹爸爸想要多少钱才肯放过她们。我想到拆迁分到的房子,爸爸妈妈各住一套,爷爷奶奶一套,另有一套空着,如果把它卖了,应该可以应付牡丹爸爸。有时,我觉得牡丹比我更可怜,她们母女像电影里被围堵追杀的人,东躲西藏的,没一天安稳日子,如果牡丹爸爸得了钱不来纠缠了,她们还是可以过得很快乐的。如果将来牡丹去外面读书了,我可以照顾冯阿姨,像她的亲儿子一样。我为自己能为她们出点力而兴奋不已,想象着她们因意外而吃惊又感激的样子,我醉心地笑了。
我猜她们会赶在大年三十回来吧。在奶奶家吃完年三十的晚饭,虽然喝了一点酒,我仍然坚持回城里的家,开电瓶车,没有人查酒驾。刚刚的饭桌上,爷爷说他可以用拆迁得到的补偿给我买一辆车,我不需要,我上班下班,无处可去,也没有想去的地方,我只愿每天待在家里,我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我已经疏于和外界接触,我是一个暗地里的病孩子,你看不出我哪里不对了,只有我自己知道。
乡下的晚饭吃得早,因为知道我要赶回城里,爷爷奶奶也不劝酒,更因为,这祖孙两代三个人的年夜饭,不仅没有团圆的喜悦,看起来有一股说不出的凄凉,奶奶准备了一桌子的菜,三个人不过草草几口就吃完了,她回厨房找饭盒,张罗着给我带菜,那臃肿的、略显蹒跚的身影一下子令我热泪上涌。我更不敢待下去了。
回到城里时不过九点。小区里却异常的热闹,据我所知,这个破旧的小区里大多是外来打工人员租住的,大部分人过年都回家了,这大年夜不同寻常的热闹预示种种不安,果然,人群都聚集在我们那幢楼前,红色的消防车在暗淡的路灯光下触目惊心地闪着光,有消防员已经顺着梯子爬到了四楼。
听说我也是四楼的住户,一个警官模样的人立即叫一个战士跟我上楼,看有没有办法从我家的窗户进到隔壁的人家。这时,我才知道因为楼道里弥漫了浓烈的煤气味,有人报了警,警察认为是由于403的煤气严重泄漏。
我听罢,一颗心笔直荡了下去,掉进了万丈深渊,我想起牡丹前些天和我说过的话,她们可能回来过年了,因为她爸爸追到了她姥姥家。
夜色中,没有人注意到我瞬间惨白的脸,我只是平静地说,不用那么麻烦,我有403的钥匙。冯阿姨临走的时候叫我看着房子,便把钥匙给了我。
走过呛人的楼道,打开403,据说煤气浓度达到某个值时,连灯也不能开,电话也不能接,我身边的战士一个箭步进去,第一时间打开了客厅的窗户,大年三十寒凉的空气扑进来,窗和门形成了强烈的对流,室内的煤气味很快减轻了。
这是一套一室一厅40多平米的房子,北边是厨房和卫生间,中间是客厅兼过道,客厅有一扇窗子,南边是卧室带阳台,室内所有的门都打开着,煤气是从厨房涌过来的,总阀半开着,煤气灶的一个开关也打开着,明显的,是故意而不是疏忽。卧室的大床上,牡丹穿着睡衣,身子蜷着,冯阿姨则衣着整齐,一手放在胸前,另一手搂着牡丹。两个人都已陷入深度昏迷,再也没有醒来。
一切归于平静之后,我在楼道上见过那个失魂落魄的男人,我以为我会暴揍他一顿,可是我没有,悲哀让我失去了力气。牡丹长得很像她爸爸,眉目之间更是神似,可是,牡丹,那清亮的眼神,银铃般的笑声,永远地消失了。我知道,牡丹其实不怕死,她说有时活着比死去更难过,我也不怕死,虽然我们不知道死是什么,但我们知道比死更难受的痛,我为牡丹不用再承受这样的疼痛而欣慰。
我读书少,却无端地想起了一句话,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事情摧毁了给你看。那更大的悲剧是不是,一生,连美好也没有见过,或者无从分辨而肆意摧毁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