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路:是影像实验,还是身份焦虑?
2018-08-09海杰
海杰

在看完成都麓湖·A4美術馆举办的“回路—2000年以来的西南影像实验”后,我在微信朋友圈写了这样的话:“这是一个烧脑的展览,也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讨论的展览。”烧脑之处在于,展览部分作品对于直觉的摒弃,而过度依赖知识,将观众引诱到光学原理、物理学原理及天文学之中。
策展人李杰和蔡丽媛将这个展览放置在“2000年以来”的语境之中,并且在展厅前言附近用醒目清晰的个体创作时间轴和整体时间演进构成了一个2000年以来的成都摄影主体谱系。这也为整个展览定调,即展览展示这些艺术家们的最新作品,但解读依托于对其个体创作脉络的回溯,因而我们可以从策展人提供的个体展览线索里切入。
作品不再仅仅是平面摄影,还包括文字、影像装置、幻灯片、图像制造设备演示、现成品等,某种程度上,这是美术馆愿意看到的,表现在对于声光电的渴求与社交单元对于展览奇绝喜好的获取。展览名单里,除了黎晨驰是新人之外,其他参展者均是在国内外重要奖项中攻城略地的人。黎晨驰的作品回到个体自我,将自己在家里不停运动的行为作长时间曝光,进而构成作品中对于身体的虚幻展示,以至于重新让时间为身体轨迹塑型,这不同于以往一些艺术家们对于身体所附着的各种社会议题的讨论。而这种“去社会性”的作品几乎占据了整个展场一层的“暗室”—策展人将展场分为暗室(向内反观与语言实验)与明室(作品外延)。骆丹的作品被放置在入口的第一个空间,激光装置不定时地照射着周围颜色不同的小玻璃面,从而产生不同的光影图像。就是在这样的原理下,骆丹拍摄了一系列有如瀑布暴泻或钢水四溅的激光图像,从这些图像回溯到《何时离去》乃至之前的三部曲,可以看出骆丹对于作品社会性的厌倦,并试图回到摄影语言的实验上去,只是这种经过激光偶发获得的图像跟现实看到的图像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李俊依旧在坚持一种对于观看中的时间与空间的胶着,他的《记之暗面》将各种日常生活的废旧底片叠加放在相机的皮腔里,得到经过二次观看的有些模糊不具的图像,他甚至把展场的观看视角也做了同样的设置与改造。阿斗也意外地回到语言实验中来,之所以说意外,是因为新作不再是之前《沙马拉达》里的生命观察,变成了他在灯箱上进行书写,然后拍摄获得图像,更像是在进行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光绘练习,这似乎更加回应展览总题“回路”:一种退后的机制。唯一的女艺术家陈潇伊的作品既吸引观众又考验观众,她用从图片库购买和从网上免费下载的月球图片制作的移动影像在一个狭长的展厅上下左右缓慢移动,不时映射在地面破碎的锌板上。
作为明室部分的二楼,既有对于图像的认知和探讨,又有作为图像外延的社会问题表达。张晋的作品开启二楼的展览叙事,他早已摆脱早期《又一季》对于文化地理的探访。在张晋的展览里,他将自己对于莫霍利-纳吉1925年发表的文章《绘画·摄影·电影》(Painting Photography Film)英文版的阅读和圈点作为展览讨论的关键入口,来试图重新强化纳吉提出的“新视野”。在他的展览主体里,显示的是使用磁力搅拌器和磁力粉笔在医用胶片上让偶发的磁力轨迹制造的图像,同时,他将声音振动波及到水的波纹图像同步传输到对面展墙的显示器上。这是否就是一种“新视野”还不好定论,但这种相对数字科技而言的低科技制造图像的行为,也是张晋有意想要去扩展摄影概念的外延。张克纯依然延续河流的脉络,只不过这次不是自己拍摄,而是从网络上征集到长江不同地段取到的水,并让参与者拍摄一张取水之地的风景照用手机发给自己,自己再用宝丽来介质打印展出。黎朗此次的关注从父亲与艺术家自己的生命和记忆互动里走到了个人记忆对于官方记忆塑造的叙述和甄别中来。在他的展览单元,“1974”这个开启了黎朗记忆元年(《新闻联播》对于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的批判)的数字,在投影里模糊又令人印象深刻,官方视角的1974年大事件年表用印刷体文字贴在墙上,390张收来的家庭照片,全部框定在6×6的尺寸内,放置在五个方向各异的幻灯机里,每张照片上都有1974年的字样,但事实是,这些照片并没有准确的年代,而是被黎朗构建在1974年,最终的叙述走向是展览尾部艺术家手写的个人记忆事件和这段文字四川话语音。展览叙事编排从官方新闻到构建的时代影像,从艺术家手写造假的日期到同样是个人手写的个体记忆与反思,从自我记忆亢奋到自我对图像真实与谎言认知后的深思。黎朗展厅的三部分分切清晰又不至于分离。




回到图像的讨论,就是走过自我记忆的河流进而对于图像生产机制和权力进行揭秘。张晓依然“艳俗”,他的视窗与精致无关,而是根植时代记忆,续接《他们》、《海岸线》和《故乡》系列的脉络,新作《甜蜜的爱恋》和一位乡村摄影师合作,借用其近十年来为村民制作的婚纱照进行展示:海边礁石上一模一样的婚纱摄影场景,套上客户的头像,在288件图像构成的矩阵里释放着快速高效又具有集体记忆的审美经验。如果说木格之前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达路径是“回家”的话,那么此次的展览,他展示的是“出走”的欲望,一种“想看看自己乡村外的乡村”的好奇心,他拍摄了一系列北方风景。在艺术家的初衷里,以“墙”为线索,希望以风景来承载和发散政治隐喻,只是这些面对观众的风景图像,似乎在这个层面显得有些虚妄与无力,而更像是对于荒野的描摹。冯立保持以往的创作势头,依然快照和爆闪,影像犀利,而此次展出的作品在展陈上做足了功夫,从美术馆门口的公共活动区墙上的灯箱开始,冯立的作品就被安插在展厅的各处,直到最后集中展示区。不做装裱,主体作品尺寸巨大,编排带着对于图像本身的思考,比如两个人打架的照片悬挂在隔着玻璃的楼道,观众看照片里的事件,如同隔岸观火,这恰恰回应了摄影的旁观属性。
如以上叙述描绘出的展览的结构,“回路”展意在以处于成都的A4美术馆为展览发声地,借此强烈展示出这11个人所具有的在地性的样本意义,进而提炼出“成都”这个艺术家生活的地域在中国摄影地缘中的重要性。在开幕前的研讨会上,围绕展览标题中的“西南”地缘界定与艺术家们本身所生活的“成都”成为讨论的热点,很显然,用“成都”来概括“西南”虽然在艺术实践上有足够的话语权,但就其定义来说,这样的域名扩展与对于所辐射地域艺术创作的丰富性来说,会构成屏蔽。毕竟,就这11位艺术家的创作来说,他们都是以个体独立创作来确立他们在中国摄影链条中的位置与声望,恰巧他们都生活在成都,是否构成“成都现象”,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辨析的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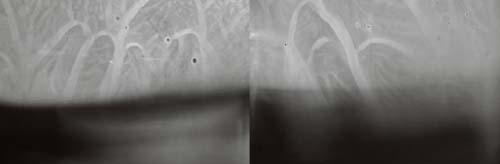
從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展览所讨论的话题由于参展艺术家本身在中国摄影纬度上的重要性,因而也变成中国摄影的话题讨论。是峰回路转,还是回到老路?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作品中所显示的部分艺术家脉络的中断与大跨度转向,其中携带着被当代艺术流行样式所吸引和挟裹的样式焦虑症,以及部分脱离社会问题情境意欲急切转型的身份焦虑与诗意晕染。这使得相应的展场作品精致、绚烂得如同年底高端客户答谢会,却难以触摸到杂糅了新媒介和逼仄的社会困境的时代语境,这似乎正成为新的展厅政治,一种面向屏幕和市场的优雅姿态;而这一情形一再提醒我们,对于展厅的祛魅和对于野生的渴望已成为一个急迫的任务,而“回路”也成为中国摄影在新阶段现状和问题的窥镜。当然,我们不应该就此抹除“回路”展在“明室”单元提供的部分优秀案例,它们重视直觉和思考,不弃蔽情感,依然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