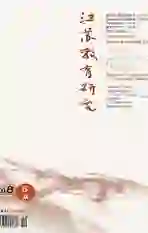巴赫金狂欢化诗学视角下的校园另类童谣
2018-07-28瞿一丹
瞿一丹
摘要: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作为一种关注非正统文化的理论学说,与教育学场域中另类童谣在现实地位、反叛姿态、价值取向等方面有着较高的契合度。狂欢化诗学视角下,另类童谣具有诙谐性、冒犯性、宣泄性等话语表征,包含隐性诉求和集体无意识双重文本隐喻。在另类童谣的狂欢派对中,学生消解权威的独尊地位,参与教育场域的话语体系重构。对待另类童谣不能一味地否定或是打压,而要给予学生更多个性化言说的契机,彰显作为另类童谣言说主体的学生的生命立场。
关键词:另类童谣;狂欢化诗学;话语表征;文本隐喻;生命立场
中图分类号:G4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8)05A-0027-06
童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于其句式精简、韵律和谐、内容积极,被广泛流传、吟唱,有些甚至被标为教育范本,代代相传。而如今,校园内外流传着一些“另类童谣”(又称“灰色童谣”)。近年来,已有不少的研究对“另类童谣”作了探讨,但是已有的研究多是立足主流文化立场,关注另类童谣的在场姿态,即关注另类童谣的表现形式、文本内容、传播方式及其消极影响,而忽视了另类童谣的文本隐喻、“不在场”的言说主体及其存在的意义。事实上,另类童谣作为一种区别于主流童谣的言说方式,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正统”对立面的姿态出场的。因此,如果单纯地从主流文化的视角去审视另类童谣,必然会使研究主体对另类童谣持否定的态度。要对另类童谣进行全面、客观、辩证的评价,就必须选取新的视角。
一、狂欢盛宴:另类童谣与狂欢化诗学的相遇
狂欢化诗学理论是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毕生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它以一种另类的言说方式、另类的探究视野参与到巴赫金的话语体系之中。狂欢化诗学的理论体系十分庞杂,涉及面极广,涵盖了神话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等众多学科[1]。面对如此庞杂的体系,我们或许可以借鉴程正民先生的观点,对狂欢化诗学理论做层次上的分类。程正民认为:“巴赫金作为一个文艺学家和文艺批评家,他是透过文学作品中狂欢化的描写,通过文学中狂欢体裁的研究,看到了隐藏在作品背后的和文学体裁背后的人类的狂欢精神,人类对生活的一种独特的世界感受。”[2]结合这一论述,我们至少可以将狂欢化诗学划分为狂欢节、狂欢文学以及狂欢精神三大层次,而这三大层次分别可以对应狂欢诗学的现实原型与表征、文本显现以及精神根基。
另类童谣作为一种现实存在,与狂欢化诗学有着多个维度的契合。两者之间的相遇与对话,更像是一种不期而遇的狂欢盛宴。在这场狂欢盛宴上,两者相互观照、相互启发,共同释放被权威所压抑的激情、所遮蔽的“民间”力量。另类童谣与狂欢化诗学的契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场姿态上,两者多数情况下都是作為权威的对立面与反抗者显现的,都是相对隐性的存在,是大一统局面下“涌动的暗流”。另类童谣以“另类”的言说方式,有意或是无意地反抗权威与正统,狂欢化诗学则关注备受压抑的民间文化,坚信非正统的力量。
第二,两者的参与主体上都具有相对广泛性。狂欢化诗学的现实表征(狂欢节)的参与者不是某个社会团体或是特权阶级,而是社会所有成员,具有全民性。另类童谣的参与主体与传统童谣有所不同:传统童谣的主体低龄化,多为幼儿;而另类童谣由于其创作与传播方式的匿名性,被中小学生广泛地接受和传唱,甚至出现在大学校园内。
第三,两者在对抗策略上极其相似。狂欢化诗学通过“加冕”边缘文化,迫使权威“脱冕”以改变其“一元独霸”的局面。另类童谣则以其另类的言说方式冲击权威的地位,以戏谑的“笑”冲击严肃的正统文化。
第四,两者在价值取向上都反对一切“独白”与“一元”模式。狂欢化诗学反对崇尚中心与权威,反对“意识形态的独白性原则”[3];关照边缘的声音,“让边缘与中心恢复对话与对流,并让区分开的二元在冲撞、交流、对话中发出新的性质和功能”[4]。另类童谣的发声,无论有意与否,其存在本身就是对权威与中心的挑战,就是试图建构交互的话语体系。当然,这种挑战并非要“取而代之”,而是为了获得关注的目光与言说的机会。
第五,在结局上,狂欢化诗学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局限性直接导致了其“昙花一现”的结局。另类童谣亦是如此:由于其存在场域的特殊性、创作主体与接受对象的发展性等,导致其终究只是言说主体的荒诞救赎。
借鉴狂欢化诗学对官方节日与狂欢节(即第一种生活与第二种生活)的区分,或许我们能够由此探寻另类童谣在教育场域中的地位,并构建出另类童谣的整体框架。巴赫金将官方、法定的生活视为“第一种生活”,狂欢节广场上的生活视为“第二种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说,民间文化的第二种生活、第二个世界是作为对日常生活,即非狂欢节生活的戏仿,是作为‘颠倒的世界而建立的”[5]。教育场域中,同样存在着第一种生活与第二种生活的划分。第一种生活是严肃、规范、线性的,以常规的、线性的学校教育教学为代表。第二种生活是狂欢、异类、流动、隐性的,常常以第一种生活对立面的姿态出场,对第一种生活的权威地位有一定的冲击;因此,权威不得不与其展开对话,并在某些方面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但是,第二种生活毕竟只是处于边缘,很难对第一种生活的权威地位产生颠覆性的威胁。
另类童谣作为教育场域中第二种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通常以“狂欢”的姿态出场,即其话语通常表征为巴赫金所描述的四种“狂欢式世界感受”。但是狂欢、发泄与无穷尽的戏谑只是另类童谣的表层,另类童谣所蕴含的学生深层次诉求与欲望则暗涌于表层之下。这些藏匿的“隐喻”与表面的“狂欢”虽然发生在两个彼此分离的层次,但是它们却是同构的。另类童谣的双层隐喻(即共时层面的“隐性诉求”与历时层面的“集体无意识”)总是能突破障碍,逃逸到另类童谣的文本表征中。
二、狂欢表征:另类童谣的在场姿态
狂欢节是一种民间的节日庆典活动,同时也是狂欢化诗学的理论渊源、现实参照与显性表达。巴赫金将狂欢节式的庆贺、礼仪以及形式的总和称为“狂欢式”。虽然,狂欢式“随着时代、民族和庆典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变形和色彩”[6],但是对其进行“寻根式”的溯源时,可以发现多种多样的“狂欢式”仍有一定的共性。巴赫金将这些共性称为“狂欢的世界感受”,并概括为四个范畴。第一个范畴是“随便而又亲昵的接触”,即“决定着普通的即非狂欢生活的规矩和秩序的那些法令、禁令和限制,在狂欢节一段时间里被取消了”[7],权威走下神坛预示着全民性与开放性的呈现。第二个范畴是“插科打诨”,它“使人性的潜在方面得以通过具体感性的形式,揭示并表现出来”[8],其主要体现为各式各样的笑。第三个范畴是“俯就”,主要体现在狂欢节“加冕”与“脱冕”的仪式上。第四个范畴是“粗鄙”,即对神圣文字和箴言进行戏谑式的模仿与讥讽,让权威与高贵“降格”。巴赫金所描述的四种“狂欢的世界感受”,与另类童谣的在场姿态高度契合。
(一)开放性
开放性即“随便而又亲昵的接触”。由于匿名性,所谓的规则在另类童谣的文本表征或是流传中被消解了,主体平时被压抑的情绪与不满、嬉笑与怒骂,甚至是被官方所贬斥的“低俗”都涌入另类童谣的狂欢广场,与权威进行“随便而又亲昵的接触”。开放性最集中体现于另类童谣的文本内容与传播形式上。
在“一次创作”环节,另类童谣的文本内容除了学生对自身在教育场域内存在状态的极力控诉之外,还有学生彼此之间的调侃、戏谑与取乐,与此同时还伴随着社会低俗文化与不良风气的混入,这在极大程度上标明了另类童谣对任何能够接触到的材料与内容都能给予“开放性”的邀请与吸收,可谓“来者不拒”。如“读书苦,读书累,读书还要交学费。不如加入黑社会,有的吃,有的穿,还有美女陪着睡!”,前一句是对沉重学习负担的控诉,而后一句则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社会风气的“开放”。发泄的意图与不良风气的无意识模仿,两者相邀进入狂欢现场,以“读书无用、金钱至上”为表征开启了狂欢盛宴。同时,传播过程也是开放的。在原始作品的传播过程中,仍会有二次、三次,甚至是多次的“创作”,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对一次成果的“修改”与“润色”之中,最终致使相近的内容与主题会有多个不同的表述版本。另外,另类童谣在传播形式上也体现了其开放性。另类童谣的传播除了网络、手机、课桌、墙壁等较为显性、可控的载体之外,还有学生间口头相传、学生群体中流传等一系列隐性、难以控制的方式,致使传播呈现出所谓的“高效性”“多样性”以及“广泛性”。另类童谣“狂欢派对”的开放性与无限制性甚至吸引了社会“利益集团”的参与。一些社会上的谋利者以此为契机,抓住学生的群体效应与效仿心理,也加入了传播的行列。比如,部分商家将流行于学生之间的“另类童谣”印刷在文具上,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引发学生购买欲望。正是无限制的开放性,另类童谣的传播速度与广度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二)诙谐性
诙谐性即“插科打诨”。区别于主流童谣的教育与感化意图,另类童谣的创作目的仅仅只是发泄与欢谑。因此,另类童谣中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笑:冷嘲热讽的笑,发泄诉苦的笑,自我解嘲的笑,纵情肆意的笑,等等。如:“找点空闲,找点时间,独自在家,把电视看看;带上倦容,带上心烦,打开书柜,把小说翻翻。……把电视看看,小说翻翻,哪怕被爸爸发现被妈妈看见,我们不图电视小说占多长时间,长时间总学习也得暂时消遣……”这段另类童谣是对流行歌曲《常回家看看》的仿拟,本来充满亲情的歌曲成了学生们调侃的对象。将真诚抒情歌词进行“娱乐性”改编与传唱,这一行为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诙谐性”,只是感同身受的学生群体读来,多了一些对现实无奈的苦笑与释放学业压力的纵情欢笑。
(三)冒犯性
冒犯性即“俯就”。部分另类童谣的创作意图本身就存在着“冒犯性”,它们对权威进行讽刺、嘲笑。在这些另类童谣的“狂欢派对”中,权威被强行“脱冕”,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与话语权被剥夺。如:“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我去炸学校,老师不知道,一拉弦,赶快跑,轰隆一声,学校炸没了。”这首另类童谣以“炸学校”为反叛方式,嘲笑、消解的行为直指权威的代表——学校,毫无掩饰地表达了排斥学校生活的情感倾向。这种“炸学校”的言语内容与“狂欢式”的表达方式无疑是一种直白的冒犯。
当然,也有部分另类童谣只是为了娱乐,并没有威胁、冒犯权威的直接意图。但是,不可否认,娱乐性质的另类童谣同样在结果上冒犯了权威,同样参与了“脱冕”仪式,因为其存在本身就是对规则与权威的嘲笑与反叛。如:“考场风光,千里纸飘,万里眼瞟。望教室内外,风景甚好,交头接耳,互打手势,欲与考官试比高。”这段童谣主要的调侃对象是考试作弊的行为。仿作并非有意冒犯原作与官方的考试制度,仅仅只是为了娱乐。但是正是因为这无意的娱乐性改编,严肃的考试制度以及原作磅礴的语言气势、崇高的文本内容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与冒犯。总的来说,冒犯性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以权威(包括教师、家长与学校)与规则(如学校制度等)为靶子,对其进行尽情地讽刺与取乐;在形式上集中体现为对著名文学作品、流行歌曲进行改编。
(四)宣泄性
宣泄性即“粗鄙”。巴赫金认为,狂欢是人们意欲摆脱现实重负、战胜恐惧的一种心理宣泄。这种宣泄乃是生命本能的一种冲动,带有相当的粗鄙性;同时,压抑得越久,压抑得越深,苦闷与欲望也就会以一种越强烈的方式爆发出来。由于创作与传播的匿名性,学生可以尽情地在另类童谣开启的“狂欢盛宴”中宣泄心中的不满,力求获得对现实压抑的心理补偿。宣泄的“随心所欲”与“一气呵成”致使另类童谣语言形式不再循规蹈矩,甚至极力破坏正统的文学语言,而以一种粗俗的、幼稚的口语来痛快地发泄情绪、排遣苦闷。如:“今天的阳光多灿烂,我们的学校破破烂烂。一百个同学,九十九个笨蛋;十个老师,九个土蛋;两个校长,一个杀人犯。”这段另类童谣的用词十分粗鄙,只是一味地追求疯狂的宣泄與肆意的欢笑。
三、狂欢背后:另类童谣的文本隐喻
巴赫金在《1970—1971笔记》中写道:“人类日常生活永远是装饰起来的,而这种装饰永远是仪典式的。”巴赫金在这里所说的“人类日常生活”是指通过语言叙述出来的“人类日常生活”,而这种语言性的“装饰”都包含着一定的隐喻结构,且这种隐喻是可以追溯到原始人类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同样,另类童谣“狂欢式”的在场姿态背后也蕴含着一定的隐喻结构与价值诉求,只是权威不愿俯下身,去倾听另类童谣言说主体(学生)的呼声与诉求;也未曾透过所谓另类的、疯狂的以及粗俗的表象,去探求文字中的隐喻与“集体无意识”。
(一)第一层隐喻:隐性诉求
这一层隐喻是共时层面的意识渗透,是学生基于现实生存状况所做出的情感上的宣泄与压力的释放。另类童谣“嬉笑怒骂”的背后,“狂欢节”发泄与戏谑的背后是言说主体(学生)承受繁重的学业压力、被束缚于不完善的学校制度、背负家长过高的期待、接受大众文化的渗透、面对话语权的缺失等现实生存状态。这一系列现实的生存状态夹杂着学生的群体效应、学生个体的表现欲等复杂的心理因素,隐匿在言说主体的潜意识之中。在权威控制的常态生活中(即第一种生活),这种潜意识或被理性强行压抑着,或以极其微妙的形式加以表露。然而,一旦有机会进入狂欢现场(第二种生活),这种潜意识就会以某种激烈的形式爆发。另类童谣的狂欢盛宴正是一种爆发的契机——言说主体利用文字工具转述这种潜意识。
基于以上分析,另类童谣的第一层隐喻,即其“狂欢在场”背后的“隐性诉求”,是学生由于理想的生命状态与现实的生存境遇存在着巨大的落差,缺乏话语权,只能在宣泄与欢谑的遮掩下,借另类童谣这一“物理文本”加以表达,从而致使实际的诉求与意图变得隐晦,甚至连言说主体(学生)都难以察觉。另类童谣的“隐性诉求”主要包括减小学业压力、变革不合理的制度、寻求对话与言说等。
(二)第二层隐喻:集体无意识
第二层隐喻是历时层面的意识渗透,即人类“集体无意识”遗留在主体的言说之中。遗留在另类童谣中的集体无意识主要有快乐至上的“酒神精神”与富有浪漫色彩的“乌托邦情结”。当然,酒神精神与乌托邦情结并非另类童谣创作主体所特有,而是人类所共有。只是另类童谣作为特定场域内的特殊言说,为这两种“集体无意识”在学生群体的无意表露提供契机。总的来说,酒神精神指导另类童谣的欢谑意图,而乌托邦情结支配另类童谣的发泄趋向。
“狂欢节”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或是更早时期,它不仅是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的现实显现,更是其理论的渊源——“狂欢化的渊源就是狂欢节本身”[9]。而所谓的“狂欢节”则是“源于神话与仪式,是以酒神崇拜为核心不断扩展的深刻的欧洲文化积淀”[10],且这种文化积淀是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存在的。而另类童谣作为教育场域的狂欢节,必将习得这种以无意识形态运作的“酒神精神”,并以欢笑、狂欢与戏谑消解现实的压抑与苦闷,给予学生生命体原始的快乐。同时,由于第一层潜意识(即隐性诉求)的下渗,现实的生存状态引发了言说主体(学生)对“乌托邦”的强烈向往。学生渴求对话、力量与自由,渴望在另类童谣狂欢派对上所拥有的神力与权力,并以此为基点构筑教育场域内乌托邦的幻梦。
四、狂欢意义:另类童谣的主体言说
另类童谣的狂欢盛宴最大的意义莫过于赋予学生在“第一种生活”中所缺失的言说权利,并提供言说的渠道,从而在另类童谣的狂欢派对中消解权威的独尊地位,有了参与教育场域话语体系重构的契机。
(一)消解“一元独尊”
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的狂欢思维是反对一切“中心主义”与“一元论”的,而承认边缘声音的力量与价值。巴赫金认为,建基于逻各斯主义的正统世界观高居统治地位,致使所谓的正统排挤、压制一切异己的声音。而狂欢思维则向绝对真理与绝对权威提出了挑战,通过“脱冕”“加冕”“冒犯”等方式,试图消解其“一元独尊”的局面。另类童谣作为教育场域中与权威相对立的存在,以主流、严肃的话题为靶子,以改编为表征方式,以口语化、粗鄙性的语言,以嬉笑怒骂的态度,将权威拉下神坛。无论另类童谣创作主体是否有意与权威对抗,另类童谣的存在都是对“权威”与“中心”的否定与嘲讽。如:“我们学校,四面通风。电灯不亮,水管不通。校长上吊,老师抽风。学生跳楼,没有师生。”尽管这段童谣对学校的现实状况做了过于夸张的表述,但其确实表达了学生对现有存在状态的不满,对教育场域内不合理制度的抗议。在这段童谣中,不可动摇的权威形象已经“轰然倒塌”。
(二)话语体系的重建
与解构主义“毁灭性的解构”不同的是,巴赫金狂欢化诗学对独白世界的解构与颠覆本身不是目的,所谓的颠覆是为了更好地重构。因此,巴赫金所要建构的新话语体系是一个进行性的、多元化的体系。另类童谣试图建构的同样是一个对话的、未完成的话语体系。在另类童谣的狂欢中,言说主体不仅打破了大一统的局面,而且获得了言说的权利。当然,另类童谣对权威的挑战,并非要使权威边缘化,或是使自己中心化,而是为了打破中心主义,让边缘与中心恢复对话与交流,试图建构一个交互的话语体系。如:“老师心太黑呀,布置的作业一大堆呀,嘿嘿,一大堆呀!半夜三更别想睡呀!不睡就不睡,大不了上课打瞌睡呀!”在这段童谣中,学生对“教师作业布置太多”进行“控诉”并非为了取代教师的地位,而是希望教师能够关注自己的生存状态,能够体谅自己的处境,并希望自己与教师能有平等对话的机会。学生期望参与教育场域话语体系的建构,且其所寻求的话语体系是开放的、流通的、未完成的,而不是唯我独尊、拒绝多元的封闭空间。
五、狂欢局限:另类童谣的荒诞救赎
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立足于民间文化,将“狂欢节”理论化,构建了一个开放的“狂欢式”话语体系,并在不断的对话中,将其“发展成为一种反抗威权、建构理想世界的文化策略”[11]。纵观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其功绩与贡献是巨大的,但是也存在着理论上的缺憾与现实运用中的局限,而这些缺憾与局限同样反映在另类童谣的“狂欢”限度上。
第一,在理论的建构上,狂欢化诗学过分注重狂欢节民俗与民间文化的正向作用,而相对忽视了其具有的破坏性因素。“人类天性被压制的力量这样突然爆发,常常堕落为肉欲罪恶的狂欢纵欲。”[12]狂欢節只是常态生活的暂时抽离,压抑已久的欲望在此间隙之中得到了暂时释放的机会,但狂欢节式的恣意放纵往往会产生极具破坏性的力量。另类童谣作为教育场域内暂时性的“第二种生活”,同样如此。另类童谣非常态化与匿名性极其容易导致“狂欢现场”的失控。粗俗的语言表述、鄙俗的大众文化、扭曲的价值观是另类童谣极为明显、也是最让人诟病的缺陷。而学生作为具有正向发展潜力的主体,实在不应将另类童谣作为发泄与戏谑的正向途径与常规方式。
第二,正如乌格里诺维奇所言,“中世纪的狂欢节仅只暂时地使人们摆脱阶层隔阂和人身依附,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被教会神圣化的封建社会支柱”[13],狂欢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迷梦。在现实中,即在第一种生活中,狂欢节及其所孕育的狂欢式的力量,无法真正撼动权威——因为权威的背后是“约定俗成”与人们(包括狂欢的民众)的惯习和崇拜。因此,狂欢只能被框定在暂时的、短期的“第二种生活”之中,狂欢节所追求的酒神精神与乌托邦式的绝对自由也只能是一种难以持久的迷梦。正如狂欢节的短暂与虚无,另类童谣与其创作主体所追求的“在‘第一种生活中完全消解权威的独尊地位,从而获得对话的权利与平等的地位”,只能是一场遥远的幻梦;学生于另类童谣中的呐喊与宣泄只是对现实的暂时逃离,另类童谣开启的狂欢派对只是一次“荒诞的救赎”。面对言说主体(学生)被压抑的欲望与无法消解的苦闷,另类童谣只能以一种荒诞的方式、暂时性的狂欢来救赎一个个鲜活却被压制的生命。
六、狂欢主体:生命立场的彰显
另类童谣“狂欢化诗学”式的解读透过另类童谣近乎疯狂的在场姿态,倾听暗涌着的呼声与诉求,探求文字中的隐喻与“无意识”。这种在场姿态背后的主体言说与文本隐喻作为一种动力机制,使得另类童谣构建了“消解一元独尊”与“重构教育场域内的话语体系”的美好愿景。同时,在“局外人”式的理性审视中,逐步地认清了另类童谣狂欢的粗俗常态化与过度化必将对生命意义产生亵渎,并厘清了狂欢幻象与严肃现实之间悬殊的地位落差。在这种近乎“主客位研究式”的融入与审视中,我们不再单纯“就事论事”,而是将视线转移到了另类童谣背后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习得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又处于特殊阶段的言说主体——学生。
学生作为生命性的存在,拥有自由选择与自由发展的权利。“自由之为自由,仅仅是由于这个选择永远是无条件的、无根据的,它只是由它自己给自己规定动机。这样,以个人的道德上的自由为内容的主观内在的确信,就成为人做出自由选择的合理性的唯一标准。”[14]另类童谣作为一种既存的言说方式,尽管被权威视为荒谬、粗俗、不可理喻的“典型代表”,但是仍具有“被选择”的权利与价值。权威(包括学校、家长、社会)往往以自己的意志去压制、阻挡这些选择的可能性,从而遮蔽了学生的生命光芒。自由选择与自由发展是人类作为生命体的共同价值取向,学生自然继承这种追求并获得追求自由的权利。因此,权威不能滥用权力,对学生对于这种言说方式的选择进行压制和恐吓,而应该与同为生命体的学生进行平等沟通与交流,创造更多符合学生发展方向的选择,倾听学生“生命式”的呐喊与诉说。
另外,作为生命性的存在,学生拥有言说与参与体系建构的权利。另类童谣这一言说方式为教育场域内学生集体沉默的“失语症”与表达的同质化、虚假性提供了一个突破与扭转的契机。虽然,另类童谣的粗俗性不可避免,但它毕竟是学生个性语言复归的征兆,且这种言说权利的“失而复得”冲击了权威独尊的地位,将学生生活由“一元模式”引向“二元”甚至“多元”模式。学生作为生命场域内极具发展潜力的特殊群体,他们全面而个性的发展需要多元开放的环境与多样异质的选择,而非权威依仗“被赋予”的权力与威严,或是出于自以为是的“保护”与“关怀”所铸造的封闭囚笼。
总而言之,另类童谣的“狂欢化诗学”式的解读突破了以往研究以主流、权威为视角的局限,观照另类童谣本身及其背后的言说主体(学生),探寻另类童谣的文本隐喻,倾听言说主体的诉求与欢笑。同时,在充分接纳、理解另类童谣的基础上,自觉地从“狂欢派对”中抽离出来,借鉴狂欢化诗学理论,对另类童谣进行理性审视与辩证评价。在对另类童谣作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思索与探讨后,我们发现:在教育场域内,另类童谣背后是学生生命活力的张扬与生命立场的彰显,是生命形式的另类表征。因此,对待另类童谣绝不能一味地否定或是打压,而要给予学生更多个性化的言说契机,为学生提供更多具有发展性的选择,创设更加多元的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1][4][10]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俄国形式主义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10.18.63.
[2]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78.
[3]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198:123.
[5]巴赫金.拉伯雷研究[M].李兆林,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13.
[6][7][8][9]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M].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160.161.162.172-173.
[11]王焱.灰段子的狂欢表征、意义及其限度[J].文艺争鸣, 2013(6):115-118.
[12]弗雷泽.金枝[M].徐育新,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829.
[13]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M].王先睿,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1987:224.
[14]徐崇温.存在主义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24.
責任编辑:杨孝如
Alternative Nursery Rhymes on Campus from the Angle of Bakhtins Carnival Poetics
QU Yi-dan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Bakhtins carnival poetics, as a kind of theory focusing on unorthodox culture,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alternative nursery rhymes in education in terms of realistic status, rebellious posture and value orientation. From the angle of carnival poetics, alternative nursery rhymes have the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of wittiness, offense and ventilation, containing double textual metaphors of implicit pursuit and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At the carnival party of alternative nursery rhymes, students dispel the authoritative status and participate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system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We should not always deny or suppress alternative nursery rhymes but give students more chances of personalized voices and highlighting the subjective position of students in alternative nursery rhymes.
Key words: alternative nursery rhyme; carnival poetics;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textual metaphor; life s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