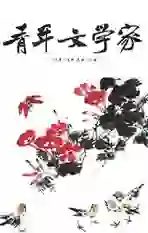魏晋南朝王谢家族诗歌交往研究
2018-07-27刘伟
摘 要:魏晋南北朝不仅是“乱”与“篡”的时代,更是世家大族大放异彩的时期。本文将从现存的诗歌来探析两个侨姓大族“王、谢”之间的交往,呈现两个家族成员之间复杂的关系,探索诗歌交游背后深层的政治历史因素,以及王谢家族文学交往和当时出现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王谢”家族;文学交往;玄言诗;山水诗
作者简介:刘伟(1993-),女,汉族,河北邢台人,文学硕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隋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02
在魏晋南朝这样一个朝代更迭频繁的时段,家族诗歌研究算是一个重大主题,而在家族诗歌的研究中尤以对王谢家族的研究较为完善,但这两个家族的研究成果,多是在论述各自的家风家学,关于他们之间诗歌交往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本文从王、谢家族在这段时期的文学交往入手,一探王谢家族的诗歌交往,二探其诗歌交往和当时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关系。
一、集体创作
东晋南朝时期,涉及到王谢家族成员之间诗歌交往的集体创作,主要有兰亭修禊和以竟陵八友为代表的西邸文人集团的集会。
晋穆帝永和九年农历三月三日修禊盛会,当时有四十二位明贤时彦聚首兰亭,同题赋诗。以王羲之为代表的琅琊王氏参与创作的有九人,产生的《兰亭诗》计十五首,谢氏家族参与创作两人,《兰亭诗》各二首。当时与会的人员除去王氏父子和谢氏兄弟是当时著名的世家大族外,其余人士也多是士族出身,几乎全是贵族子弟。虽然兰亭会的时候,王羲之和谢安、謝万还没有结为儿女亲家,但共游东山也是常有之事,兰亭集会不过是以王羲之、谢安为代表的贵族子弟闲暇之余借修禊组织的一次聚会。
这次兰亭集会产生的诗作几乎全涉玄理,只是创作主体在借修禊机会寄托和诉说,并非是彼此之间的赠答之作:
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王羲之《兰亭诗》)
醇醑陶丹府,兀若游羲唐。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1](谢安《兰亭诗》)
以兰亭集会为典型,在东晋朝廷,以群体出现的王谢家族成员的文学交往中,其生产的诗作大多可以归类为玄言诗。东晋时,王谢家族具有优越的政治地位,兼具充裕的经济基础,虽然朝廷实行了“土断”[2]的经济政策,但是仍然不可能侵犯世家大族的利益,抢田占地,携藏户口的现象仍然存在。王谢家族,偏安一隅,他们希望君主不作为,以保证门阀政治持续存在,他们推崇无为而治的老庄,反映在文学上便是家族成员之间谈玄论道,大作玄言诗。
南朝时期,王谢家族成员以群体形式赋诗赠答的聚会中,规模最大的当属西邸文士的集会了。《梁书·武帝纪上》说:“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梁武帝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并游焉,号曰八友。”[3]八友大多与王俭有密切的联系,谢朓曾在永明初年做过王俭的祭酒。“竟陵八友或奉诏而作,或相互唱和,其集中创作而又有时间可考的主要有四次”[4],其中齐武帝永明九年(491年)上巳节的芳林修禊可谓规模盛大,当时齐武帝幸芳林园华光殿,西邸文士奉旨参加,竟陵王府宾客聚于一处,四十五人。谢朓、王融在西邸文人集团中甘做文学侍从,以乞垂爱,其实是当时家族地位被削弱,寒士崛起,皇权加强的局面下不想被体制边缘化的表现,二人之间也产生了部分赠答的诗作。
除去芳林的这次集会,西邸文人还热衷于同题咏唱,郭茂倩《乐府诗集》说:“《永明乐歌》者,竟陵王子良与诸文士造奏之。人为十曲。”[5]王融、谢朓现各存十首。这些作品几乎全是五言诗,其内容缺乏深刻的思想,也没有深沉的情感,主要是当时西邸文士生活侧面的描绘。西邸文士的集会的内容大同小异,或聚众讲佛,或奉召咏唱,或离别赋诗。
《南齐书·陆厥传》记载:“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毅,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水明体。”[6]“永明体”与四声紧密联系,四声的发现促进了“永明体”的产生,“永明体”诗歌的大量创作便是对四声应用到诗歌中的具体实践,而四声的发现与佛教的发展密切相关。据相关史料记载,周颙曾追随过鸠摩罗什的徒弟僧朗,并且竟陵王萧子良笃信佛学且爱好文学,谢朓、王融等常常聚集在萧子良身边,时常会和僧人打交道,那些僧人谈佛诵经的音调便影响到文士的创作,王融本人也作过不少“称赞佛经教义的诗文,如《净住子颂》、《法门颂启》《法乐辞》等”[7]。谢朓、王融等人在永明年间大量实践这种新诗体,据《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中所记载的诗歌来看,二人创作永明体诗歌的具体数量是“谢朓76首,王融42首”[8],“永明体”因为他们的实践而获得更多文士的认可和推崇。
通过上文我们了解到,无论是玄言诗还是永明体,领军人物都是王谢家族的成员,不同的是,前者是王谢故意而为之,后者却是以文学侍从的身份去顺应当权者的喜好而为之,但不论是东晋还是南朝,王谢家族成员参与的集会都难脱功利性。通过王谢家族成员之间的文学交往,也给了我们一个角度一窥魏晋六朝时期皇权和士权的情况。
二、个人赠答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风流宰相”谢安的著作在梁时还有集十多卷,现多散佚,除两首《兰亭诗》外,还有一首六章的《与王胡之诗》存世,王胡之也曾作《答谢安诗》一首八章,这十四章诗述理想、叙友情、谈人格以及说志趣,是较完整地展现了王、谢二人之间的赠答唱和。《与王胡之诗》中“余与仁友,不涂不笱。默匪严穴,语无滞事。”[9]写二人无话不谈,心领神会的深厚友情,整首诗下来清新雅致且颇有玄言色彩,既赠王胡之也是其生活和志趣的写照。王胡之回赠谢安的《答谢安诗》其情感基调和事理言说和谢安的赠诗基本一致,“哲人秀兴,和璧夜朗。”[10],不无对谢安人格才能的仰慕与称赞,“利交甘绝,仰违玄指。君子淡亲,湛若澄水”[11],表达了他与谢安通达共显贵,忧伤同悲戚的君子之交。琅琊王胡之未出仕时生活贫困,《世说新语·容止篇》记载,乌程(今浙江吴兴南)令陶范送米给王胡之,王胡之不接受:“王修龄(王胡之字)若饥,自当就谢仁祖食,不须陶胡奴米。”[12]一来是王胡之与谢尚之间关系密切的佐证,二也反映了其对寒门士族的不屑。
这十四章是四言诗,诗中谈玄论道,阐述佛理,是东晋时较为典型的玄言诗。谢安出将入相,位极人臣,采用玄言诗的形式,除去他本人推崇老庄,喜好谈玄之外,多作玄言诗可以顺应东晋文坛玄风盛行的风尚,标榜清雅,取誉士林。在世家大族把持朝政的时代,文学与政治都在家族中传承,谢安陈郡谢氏的家族地位和他本人的仕途位遇,加速了玄言诗的生产,同时玄言诗的大量创作,也助其愈发显达。
王弘和谢氏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他本人是琅琊王氏,名重当时,在《南史·谢晦传附谢瞻传》中提到谢瞻“尝作《喜霁诗》,灵运写之,混咏之。王弘在坐,以为三绝”[13],可见王弘对三人在文学上的造诣十分推崇,但是在《宋书·王弘传》中,也有记载当时官至尚书仆射的王弘以“罔顾宪轨,忿杀自由”[14]为弹词,上书弹劾谢灵运,致使谢灵运被免官。除此在《宋书·谢晦传》中,刘义隆在杀掉辅国大臣徐羡之、傅亮以及谢晦在朝做官的家属后,又遣兵征讨谢晦,在这时候谢晦上表除了陈述自己的心迹,为徐羡之和傅亮辨白,就是反复指责“王弘兄弟,轻躁昧进”[15],但谢晦的表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很快和他的兄弟子侄都被杀害。然而这次事件之后不久,王弘成为宰相。宋少帝景平元年,谢灵运创作了《辨宗论》、《答王卫军问辨宗论》,于时谢灵运三十九岁,谢晦三十四岁。自宋元嘉三年,谢晦被杀,到元嘉九年,王谢家族成员之间的文学交往十分单薄。
永明十年,谢朓在荆州与王秀之时有唱和。王秀之有《卧疾叙意诗》致谢朓,谢朓也答之以《和王长史卧病诗》,但这并不能说明两人关系亲昵,谢朓在跟随萧子隆来到荆州之前便是西邸文人中的一员,宴饮唱和本就是日常,而萧子隆本身当时不足二十,谢朓也不过三十岁,“流连晤对,不舍日夕”[16],王秀之当时是以镇西长史、南郡太守的身份担任萧子隆的幕僚,辅佐萧子隆处理荆州的日常政务,故两人生活有交集,时有唱和也很是正常。当时山水隐逸在士林中是一种风尚,唱和诗一般所写皆是此类的主题,王秀之“隐沦迹有违,宰官功未树。”[17]谢朓相和“愿缉吴山杜,宁袂楚池荷。”[18]在归隐已经成为雅言的氛围下,二人唱和只是对时代的一种顺应。很多书籍中都提到,谢朓在永明十一年被遣还都,实则是为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动”[19]的密告中伤,但这恐怕并不完全是中伤,由上文可知,谢朓和王秀之在荆州有诗作来往,且二人向来没有恩怨,无端中伤实难属实,且王秀之当时年纪已高,为人严肃认真,对谢朓和萧子隆宴饮唱和、懈怠政事有所不满,他以辅佐人主政事的态度向武帝汇报他的看法,其实是他的责任,附会成中伤有所失真。
在魏晋南朝,世家大族之间通过联姻来巩固家族地位是很普遍的现象。“珣兄弟皆谢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与珣绝婚,又离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衅。”[20]在这段婚姻中不乏轶事:
晋中书令王珉,捉白团扇,与嫂婢谢芳姿有爱,情好甚笃。嫂捶婢过苦,王东亭(王珣)闻而止之,芳姿素善歌,嫂令歌一曲,当赦之。应声歌曰:“白团扇,辛苦五流连,是郎眼所见。”珉闻,更问之:“汝歌何遗?”芳姿即改云:“白团扇,憔悴非昔容,羞于郎相见。”后人因歌之。[21]
王珣娶谢万女为妻,谢芳姿为谢万女儿的陪嫁丫头,谢芳姿应声赋歌,可以想见谢氏家族人才之盛。
魏晋南朝时期王谢家族成员之间的诗歌交往多呈现群体性,即以集会的形式聚众谈玄或同题赋诗。由东晋进入南朝,寒士逐渐崛起,这种集体性质的活动对士族的门第放宽,但王谢家族的成员在其中多是领头羊的角色。他们之间的往来在集会活动中不乏功利性色彩,这主要归咎于两个家族的成员兼具政治家和文学家的身份,故王谢家族成员之间的诗文往来不仅仅促进了两个家族的家学发展,更对两个家族地位的巩固起到一定的作用。
注释:
[1]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8年,第895-907頁。
[2]王连儒:《汉魏六朝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研究》.见[梁]萧子显:《南齐书》卷四十七《王融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17—822页。
[3][唐]李延寿等:《南史》卷四十八《陆厥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2页。
[4]跃进:《永明文人集团论述》.浙江学刊(双月刊),1992年第6期。
[5]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黑龙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187
[6][唐]李延寿等:《南史》卷四十八《陆厥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96页。
[7]赵静:《试论王融与“永明体”创立之关系》.山东师范大学,250014,2010
[8]王辉斌:《谢朓与西邸文学集团》.襄樊学院,441053,2006
[9]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401页。
[10]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885页。
[11]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885页。
[12]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刘孝标注,杨勇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39页。
[13][唐]李延寿等:《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46页。
[14][唐]李延寿等:《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75页。
[15][唐]李延寿等:《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45页。
[16]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黑龙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90页。
[17]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878页。
[18]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905页。
[19]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第190页。
[20]刘义庆:《世说新语》,第695页。
[21]萧华荣:《簪缨世家-两晋南朝琅琊王氏传奇》.北京.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5年,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