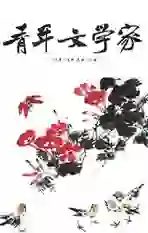支遁养马故事之流变
2018-07-27焦梅
摘 要:支遁养马的故事首见于《世说新语·言语》,支遁养马被人讥笑与僧侣身份不合,支遁反驳以“重其神骏”。此后这一典故频频出现于历代与马相关的诗文中,“神骏”也成为后人论马时屡次提及的一个词。到了唐代,开始出现“支遁养鹰”的说法,“神骏”一词也被用来形容鹰。据《世说新语》,支遁爱马且爱鹤,但并未提及“鹰”。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荆公诗注”一节的补注中曾提及这一点,笔者受其启发,拟从和支遁养马、养鹰相关的记载入手,试梳理支遁养马到支遁养鹰这一说法的变化过程。
关键词:支遁;养马;养鹰;《初学记》
作者简介:焦梅(1993-),女,汉族,四川巴中市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宋元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02
支遁,东晋高僧,生平最早见于《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其引《高逸沙门传》:“支遁,字道林。河内林虑人,或曰陈留人。本姓关氏,少而任心独往,风期高亮,家世奉法。尝于余杭山沈思道行,泠然独畅。年二十五始释形入道,年五十三终于洛阳。”[1]支遁生活的年代清谈之风盛行,支遁精通老庄学说,又有较深的佛法造诣,与当时的名士交往颇多,《世说新语》中关于他的记载就多达四十余条。其中,支遁养马这一条是本文探究的出发点。
《世说新语·言语》载:“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2]在该篇中,还有支遁爱鹤的记载:“支公好鹤,住剡东峁山。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这两处记载清楚地表明,支遁因赏其神骏而养马,因怜其凌霄之姿而养鹤,后又纵鹤。慧皎《高僧传》则将二者合并一处:“人尝有遗遁马者,遁爱而养之。时或有讥之者,遁曰:‘爱其神骏。聊复畜耳。后有饷鹤者,遁谓鹤曰:‘尔冲天之物,宁为耳目之翫乎?遂放之。”[3]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中也记载了此事,与《高僧传》大致无二。以上的记载中,关于支遁养马、养鹤的说法都是比较清晰的。
到了唐代,在相关记载中,与支遁有关的除了马和鹤,还出现了鹰。如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三道释部:“《高僧传》曰:支遁常养一鹰。人问之:‘何以?答曰:‘赏其神俊。”[4]此处所引的《高僧传》,与通行的《高僧传》原文有较大出入,易“马”为“鹰”,且易“神骏”为“神俊”,这有可能是《高僧传》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讹误。后来南宋《能改斋漫录》中引用《高僧传》这一条,也出现了类似的讹误:“《世说》载:支遁道林常养马数匹,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云:‘贫道重其神骏。《高僧传》载:支遁常养一鹰,人问之:‘何以?答曰:‘赏其神俊。然世但称其赏马,不称其赏鹰。”[5]又司空图在《退栖》一诗中则明确地说:“燕昭不是空怜马,支遁何妨亦爱鹰。”
除了诗文,史类记载中也不乏支遁养鹰的说法。《建康实录》是唐人许嵩编纂的一部六朝史料集,在第八卷的注中论及支遁:“案《许玄度集》:遁,字道林,常隐剡东山,不涉人事。好养鹰马而不乗放,人或讥之。遁曰:‘贫道爱其神骏。”[6]许玄度即询,东晋时期名士,《世说新语》刘孝标注:“《续晋阳秋》曰:许询,字玄度。髙阳人,魏中领军允玄孙。总角秀惠,众称神童。”[7]《建康实录》题“高阳许嵩撰”,《四库全书总目》考其生平云:“嵩自署曰‘高阳,盖其郡望。”张忱石先生在《建康实录》点校本中也肯定了这一点。笔者推测由于许询的名气以及二人郡望相同的原因,许嵩对许询有着较多的关注,且为许询立了传。而许询与支遁为同时期人,二人曾有交游。《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中兴书》曰:安元居会稽,与支道林、王羲之、许询共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谈说属文,未尝有处世意也。”[8]钱钟书先生据此认为,唐人用“支遁养鹰”故事,当是本于许询的记载。世人只知支遁养马而未知其养鹰,可能是因为在许询集未亡佚之前,《世说新语》和《高僧传》的流传远远广于许询集。[9]
许询集虽现已亡佚,但《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皆有载,表明许询集在有唐一代及唐以前都有流傳,唐人有看到许询集的机会,只是他记载的支遁养鹰马的故事没有广泛流传,未成为主流的说法。联系《建康实录》的体例,许嵩在序中称“述而不作,窃思好古,今质正传,旁采遗文,……具六朝君臣行事,事有详简,文有机要,不必备举。若土地山川,城池宫苑,当时制置,或互兴毁,各明处所,用存古迹;其有异事别闻,辞不相属,则皆注记,以益见知”[10],凡与正文说法不一致或被认为比较次要的有关材料,则用夹注的形式选择部分入录。支遁养鹰马的故事就是以“夹注”的形式记载,因为当时主要的说法是支遁养马,养鹰马则为“辞不相属”。
同时钱钟书还提到了张九龄《鹰鹘图赞序》:“工人图其状,以象武备,以彰才美;虽未极其天姿,有以见其风骨矣。昔支遁道林常养名马,自云重其神骏。斯图也,非彼人之徒欤?”[11]这篇序题为“鹰鹘图”,但是在最后张九龄只引用了支遁养马,却没有鹰马并举。钱钟书认为是因为张九龄没有看到许询集,因此不知道支遁养鹰的说法,不然就不会“引道林养马来搭天桥作陪衬”。张九龄《鹰鹘图赞序》描写的主要对象是鹰和鹘,开篇介绍“鸟之鸷者,曰鹰曰鹘:鹰也者,名扬于尚父,义见于《诗》;鹘也者,迹隐于古人。”后面写能工巧匠画鹰鹘图,“工人图其状,以象武备,以彰才美,虽未极其天姿,有以见其风骨矣”,就是说工人所画的鹰鹘图,虽然没有画出鹰鹘最趋极致的美好姿态,但还是能让看画之人领略到鹰鹘的风骨。风骨,即刚正的气概,刚健遒劲的格调。鹰鹘二者,为鸟之鸷者,风骨正是它们最具个性的地方,超越于天姿。鹰鹘的风骨,与支遁爱马所重的神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张九龄年辈早于许嵩,许嵩看到了许询集引用了支遁养鹰的说法,而张九龄没有,这也符合前面许询集流传范围不广的推测。
以上所论,乃钱钟书先生关于唐人用支遁养鹰故事所本为何的观点。这种推测从看似合情合理,实则存在一定的漏洞,即忽略了《初学记》中的记载。前文已经说过,《初学记》在第二十三卷中引《高僧传》,直言“支遁常养一鹰”。如前所述,这条记载虽然与通行的《高僧传》原文不符,这又牵涉到《高僧传》在流传过程中的版本问题,此处暂且不论,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初学记》对于“支遁养鹰”故事的流传作用。《大唐新語·九》云:
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诏以《初学记》为名。[12]
这段话对于《初学记》的编纂、命名,以及它为何比一般的类书简单概括,做了具体的说明。唐初承六朝余绪,骈文还很盛行,文章讲究辞藻典故。《初学记》的编纂原为便于玄宗诸皇子作文时检查事类,故名《初学记》。
《初学记》是唐代最为精良的类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评价《初学记》:“在唐人类书中,博不及《艺文类聚》,而精则胜之。若《北堂书钞》及《六帖》,则出此书下远矣。”[13]古代的类书相当于今天的工具书,本身具有巨大的实用性。从功用上来说,首先是可以查找史料。类书内容丰富,多摘抄古代文献原典,囊括天文历史、民俗典制等,许多已经佚失的历史记载,都能从类书中找到踪迹。其次是可以查找辞藻。类书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帮助人们创作诗歌,类书分门别类,为学习诗歌写作的人们提供了方便。此外类书在辑佚和校勘上也有重大的作用。由此而言,类书的影响范围极其广泛,上至帝王、大臣,下到科举、诗人,乃至童蒙,对不同身份的人皆有不同的作用。类书巨大的包容性决定了它流传的广泛性,所以《初学记》的记载在当时是有一定影响的。由此,笔者猜测,唐人用“支遁养应”故事,可能更多地受到了《初学记》中引用的《高僧传》的影响。
钱钟书先生从《建康实录》的记载推断,“支遁养鹰”应本于许询集,笔者之所对这种推测有所怀疑,是因为这里还存在两个有待商榷的问题:一是《建康实录》与《初学记》的成书时间先后比较。已有学者考证出,《建康实录》为许嵩一人所撰且成书于肃宗之世[14]。关于《初学记》的成书时间,其书序中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但从其他的一些书籍记载中能够略作推论。据《唐会要》记载:“初,十四年四月,侍御史潘好礼闻上欲以惠妃为皇后,进疏谏曰:‘臣尝闻《礼记》曰……又见人间盛言,尚书左丞相张说,自被停知政事之后,每谄附惠妃,诱荡上心,欲取立后之功。”[15]《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十五年二月……己巳,尚书右丞相张说、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以朋党相构,制说致仕。”[16]可以看出,开元十五年二月,张说致仕。又据《新唐书·张说传》:“常典集贤图书之任,间虽致仕一岁,亦修史于家。”[17]可见张说致仕持续了一年时间,按照古人惯例,往往将领衔编纂者署作者。正如上文所说,《初学记》既然署名徐坚,那么应是张说致仕期间成书。如此看来,《初学记》最有可能成书时间应是开元十五年期间。而《建康实录》成书于肃宗之世,晚于《初学记》。比较而言,在对后来的影响方面,《初学记》胜于《建康实录》。二是许询集与《初学记》的流传比较问题。钱钟书先生的论述中也指出了,支遁养鹰的说法未广传于世的原因是许询集流传范围不如《世说新语》和《高僧传》广,那它就更不能和玄宗亲命编纂的类书《初学记》相比了。所以从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上来说,当然也是《初学记》要更胜一筹。
综上两点基本可以推测,《初学记》中“支遁常养一鹰”的记载,在推动唐代“支遁养鹰”说法流传的方面,应当比钱钟书先生所说的“许玄度集”有着更直接的影响。但这个推论也存在可再商榷的空间,重点在于《初学记》所引用的《高僧传》版本问题。至于前文所提到的《能改斋漫录》也有相同的引文,很有可能后者也是根据《初学记》的记载而来。
注释:
[1]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6月,第68页。
[2]同上。
[3]慧皎《高僧传》,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4]徐坚《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57页。
[5]吴曾《能改斋漫録》,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81页。
[6]许嵩《建康实録》,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6页。
[7]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1页。
[8]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06页
[9]钱钟书《谈艺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92页。
[10]许嵩《建康实録》,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
[11]张九龄《张九龄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910页。
[12]刘肃《大唐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7页。
[13]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43页。
[14]谢秉洪《<建康实录>作者与成书时代新论》,南京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9月第5期。
[15]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7页。
[16]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0页。
[17]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10页。
参考文献:
[1]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
[2]钱钟书《谈艺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3]徐坚《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4]谢秉洪《<建康实录>作者与成书时代新论》,南京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9月第5期。
[5]戎冰《<初学记>及其对唐诗的影晌》,河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