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属于我的家,开启了我的梦想
2018-07-19李琼
李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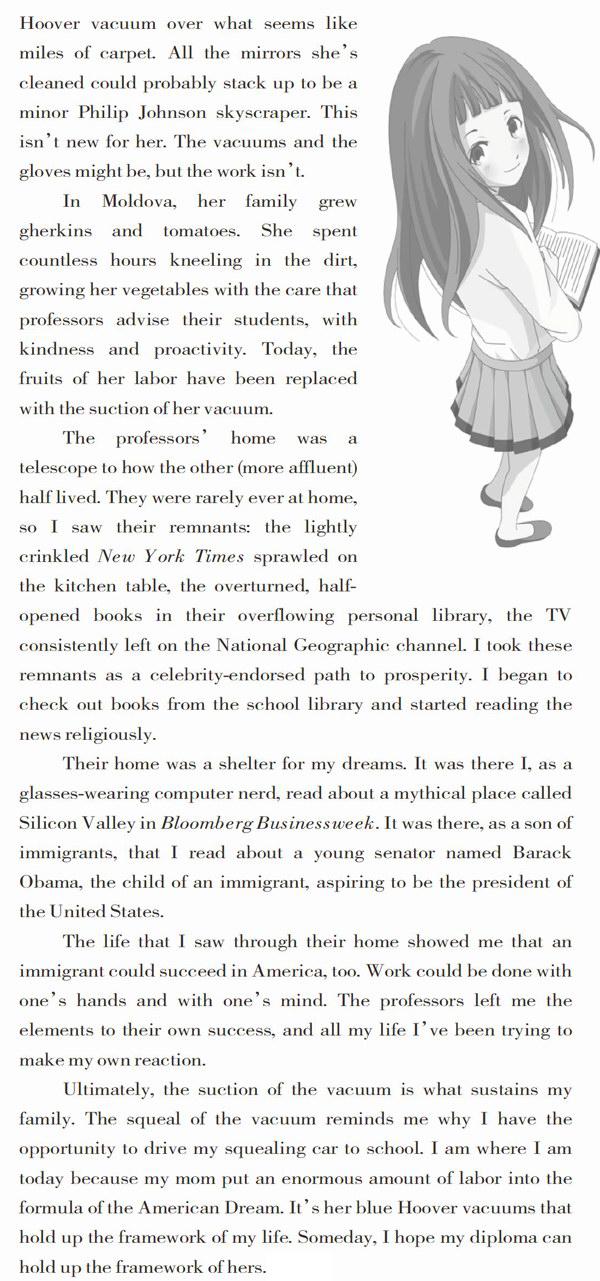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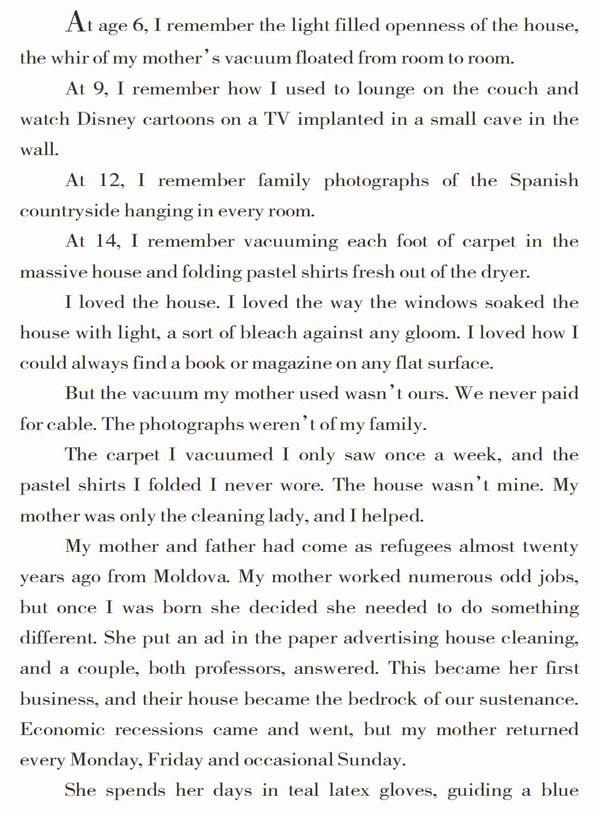
我还记得6岁那年,光线填满宽敞的房间,母亲手中吸尘器的嗡嗡声从一个房间传到另一个房间。
我还记得9岁那年,我常常懒洋洋地躺在长沙发上,看迪士尼卡通片,电视机放在墙上的一个内嵌空间里。
我还记得12岁那年,每个房间都挂着在西班牙乡间拍摄的家人照片。
我还记得14岁那年,我在偌大的房子里一点点地给地毯除尘,折叠刚刚烘干的色彩柔和的衬衫。
我喜欢那栋房子。我喜欢阳光透过窗户倾洒进来的样子,仿佛可以扫清所有愁云。我喜欢自己总是可以在任何一个平坦的物体表面找到一本书或杂志。
但母亲使用的吸尘器不属于我们。我们从未付过有线电视费。照片上的人物也不是我的家人。
我一周只能见到一次自己清理的地毯,我从未穿过自己折叠的那些色彩柔和的衬衫。那栋房子不是我的。母亲只是清洁工,我是她的帮手。
大约20年前,我的父母以难民的身份从摩尔多瓦来到美国。母亲打过许多种零工,但我一出生,她就认定自己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她在报纸上登了一则提供房屋保洁服务的广告,一对教授夫妇联系了她。这成了她的第一单业务,他们的房子成了我们维持生计的基石。经济衰退未了又去,但母亲每逢周一和周五都要去那里,有时周日也过去。
她整日戴着蓝绿色的乳胶手套,手持蓝色的胡佛吸尘器,给仿佛有几米长的地毯除尘。她擦过的镜子没准可以堆叠成小型的菲利普·约翰逊摩天大楼。这对她来说并不新鲜。吸尘器和手套或许有些新鲜,但这份工作并非如此。
在摩尔多瓦,她曾在家里种黄瓜和西红柿。她曾花无数个小时跪在泥土里,像教授指导学生那样用心,以善良和积极主动的态度侍弄她的蔬菜。现在,她耕耘的蔬果被吸尘器取而代之。
那两位教授的家让我得以一窥(更富裕的)另一半人的生活。他们很少待在家,于是我便观察他们留下的痕迹:摊在厨房桌子上稍稍发皱的《纽约时报》,满满当当的私人图书馆中翻到一半就倒扣着的书,总是停留在国家地理频道的电视。我把这些痕迹当成名人效应下的成功之路。我开始从学校的图书馆往外借书,并经常看新闻。
他们的家为我的梦想提供了庇护之处。在那里,我这个戴着眼镜的电脑迷从《彭博商业周刊》上知道了一个名叫硅谷的神秘地方。在那里,我这个移民的儿子读到了一个名叫巴拉克·奥巴马的年轻参议员立志要做美国总统的故事——他也是移民之子。
我从教授家看到过的生活告诉我,在美国,移民也可以成功。工作可以用双手和头脑来完成。两位教授让我看到了他们获得成功的要素,我也一直在努力寻找自己的路。
最终,吸尘器的吸力养活了我们一家。吸尘器的嗡嗡声提醒着我,我为什么有机会开着叮当乱响的小汽车去上学。我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我,是因为我的妈妈往美国梦的公式中倾注了大量劳动。她用蓝色胡佛吸塵器为我的生活撑起了一片天。有朝一日,我希望能用自己的毕业证书为她撑起一片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