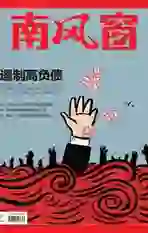欧盟有能力走出急流险滩吗?
2018-07-18尹子轩
尹子轩

2008年以来,每年一度让小报编辑们下“欧盟即将解体”之类标题的时候又来了—外有和美国的贸易争端,内有因难民问题责任不均,民粹势力乘虚冲击而引发的冲突,从表面上看,欧盟是步履蹒跚。
的确,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移民问题及欧元区经济管治问题上,遇到了姐妹党基社盟的挑战,而早前欧盟16国“迷你峰会”也未能就难民责任问题达成共识;波兰和匈牙利等国政府,接连有破坏欧盟原则、挑战欧盟权威的动作;在外部,欧盟承受着美国对自由贸易和伊朗核协议的攻击,更不用说特朗普厌恶北约以及英国脱欧将引致的欧盟共同防御问题了。
但是,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动摇到欧盟真正的根基—欧元以及单一市场所带来的国际保护伞,而且成员国就这些问题在欧盟体制内的角力,实际是有益于欧盟机构的茁壮成长,以至整个欧洲统合进程的。
难民问题终需欧洲合作
难民问题作为民粹和民族主义者的稻草人,在国家层面及欧盟层面都带来麻烦。欧盟峰会之前一度威胁德国大联合政府稳定的动荡,便是一例。但是,即便难民问题助长了许多欧盟国家的民粹主义,这个不稳定因素也并非德国政府及欧盟架构无法消化的,更非一个可以将欧盟超国家架构击坠的因素。
在国家层面,有欧盟平台作为缓冲及协调的机制,默克尔避免了和长期盟友巴伐利亚基社盟决裂的后果。
6月15日,德国基民盟长久以来权倾巴伐利亚的姐妹党基社盟的领袖、现任内政大臣泽霍费尔(Horst Seehofer),选择在州选举之前发难,以两党关系为赌注要挟默克尔实施他制定的难民限额计划。
泽霍费尔此举,其实是一个在政治上自保的举动。这位默克尔的老对头,在巴伐利亚以政治光谱上更右翼、更保守的立场,去辅佐基民盟默克尔所代表的中间派保守主义基本盘。可是在上届大选中,基社盟不但创下历年得票率的新低,更在议会失去了10席,许多票源被在移民问题上更右的另类选择党(AfD)夺走。在10月州选举前,泽霍费尔感到他们必须重振声势,以保在州政府长年的绝对多数不受AfD威胁。
然而,泽霍费尔这场背弃盟友的豪赌风险甚大。根据民调机构Forsa在6月21-22日收罗的数据,基社盟在巴伐利亚的支持率依然停留在40%,并未回复到上届2013年州选举接近49%的支持率。在民调中,不仅54%原本基社盟在巴伐利亚的选民表态称,会在两党决裂后“转投”进军州选举的基民盟,更有39%的选民将基社盟选为“困扰巴伐利亚最大因素”,排在难民(30%)和房地产市场(24%)之前。显然,基社盟一旦和基民盟决裂,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
欧盟委员会及欧洲理事会(即欧盟首脑会议)6月下旬的两次会议,可以说是拯救了默克尔的联合政府。围绕着两次会议有关移民问题的博弈,可简约至两个阵营:在难民抵达前线,急需其他成员国遵守欧盟委员会有关难民分配额度法案的国家,比如说意大利和希腊等;以及强调控制边境,对于移民过境问题极为强硬的国家,比如匈牙利和波兰。
在欧盟轮值主席国奥地利的“85后”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口中,柏林、罗马和维也纳之间所谓的“意愿轴心”,正是这种博弈下的产物。意大利政府尽管现正由两个民粹政党联合执政,但是始终位处地中海难民抵达前线的意大利,在移民问题上的天然盟友只可能是德奥两国,而非中欧国家们。
有欧盟平台作为缓冲及协调的机制,默克尔避免了和长期盟友巴伐利亚基社盟决裂的后果。
最终,6月29日凌晨4时多欧盟成员国首脑之间的协议,奇迹般地满足了这两个阵营的需求,并为默克尔之后和西班牙、希腊等国就转移德奥边境难民的双边协议铺平了道路。
协议的逻辑,主要在于利用欧盟共同资源,在欧盟境外如北非地区设立难民营,以减少抵达欧盟成员国的难民数量;而已经抵达欧盟成员国的难民,则交由成员国共同设立分流中心进行筛选,除了因人道危机而必须予以救助的难民,都将被遣返。
在限制入德难民人数的要求得到部分满足后,7月2日泽霍费尔收回辞呈,继续拥护默克尔的领导。难民问题所引发的德国政治闹剧,在欧洲各国参与政策协调后告一段落,正说明了欧盟制度的生命力。通过多国在欧盟层面合作决策,欧盟成员国们无需仅以双边主义手段去处理跨国问题,欧洲大陆的平稳由此多了一重保障。
民粹政党难抛欧盟建制
2017年以来,波兰、匈牙利两个逐渐走向威权主义的国家,开始挑战欧盟的自由、民主和法治原则,引起了欧盟的制裁警告。
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PiS)政府一再地尝试削弱波兰的司法独立,加强控制媒体以及攻击公民社会的行径,违反了当初入盟时许诺的“哥本哈根标准”。今年初,欧洲议会在法德两国元首支持下,正式通过欧盟委员会向波兰当局启动欧盟《里斯本条约》第七条的动议,亦即惩治违反欧盟自由民主精神之成员国的所谓“法律核选项”。该选项一旦通过,理论上波兰是可以被欧盟暂停一切欧盟议事投票权的。
当然,正如所有欧盟管制成员国的条款一样,该选项必须获得包括波兰盟友匈牙利—另一个被欧洲议会以打压公民社会为由,在今年4月建议启动《里斯本条约》第七条予以警告的国家—在内的欧洲理事会代表的4/5,即22个成员国元首的通过。而目前来看,波匈两国离在政治上被制裁的日子尚远。
说到底,欧盟并没有将两国“逐出”的选项,但华沙和布达佩斯亦没有任何立场去脱欧。这主要因为,民粹威权政府的管治合法性,往往反映在經济表现上,而正是此因素令波、匈两国政府都不可能切断和欧盟的纽带。
在PiS上台之前,波兰曾被视为东欧集团在欧盟内的楷模。作为成员国中少数快速走出欧债危机,自2010年开始维持增长的国家,波兰一步步地利用了欧盟单一市场机制,以及同周边国家贸易的优势,仿效德国模式加强出口,在东欧地区建立起某种领导地位。波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出口增加值,仅仅13%来自欧盟以外国家。换句话说,欧盟单一市场带来的红利,是PiS主席兼创始人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声称波兰“付得起(改革)代价”之底气的由来。
已经被青民盟掌握达7年之久的匈牙利,相比波兰更“进取”,不仅同样地利用欧盟带来的机遇,其总理欧尔班的寡头伙伴,更是在六成由欧盟结构基金支付的政府基建合约上大快朵颐。这种以经济甜头和民族主义情绪鼓动选民投票,另一方面侵害公民社会以及司法独立、滋润党羽的伎俩,正是新世纪欧洲民粹政治经济模型的核心。
目前,波匈两国是欧盟基金第一和第四大获益国家,再加上两国本身对于单一市场的依赖,经济上和欧盟的纽带无可根绝,“聪明”的波兰PiS和匈牙利青民盟政府也自是心知肚明。
至于政治上藉强人挑战组织权威,在欧盟史上也不是没有过。1966年,认为刚诞生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前身)权力过大,威胁到法国所获农业补贴的戴高乐将军,杯葛所有欧共体会议将近一年,最后凭借其战后欧洲大国的身份得到了欧洲其他国家的让步,即所谓“卢森堡协议”。该协议规定欧洲市场整合的经济统理权由成员国间制定,而非由超国家组织负责。
但是,这种博弈的长远得益是属于欧盟整体,而非单一国家的。当时法国的短期得益,依赖于其他国家在盟内的合作,这反而维护了欧共体本身。卢森堡协议之后,欧盟引入了将成员国人口加入投票决定考虑因素的“有效多数表决制”;欧洲议会在《里斯本条约》后又获得批准法案的实权,这些都让成员国“提案脱离欧盟”的成本无限地超过得益。
虽然波兰和匈牙利目前有恃无恐,但两国脱欧乃至触发骨牌效应引致欧盟解体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面对下一个欧盟七年财政预算(2021-2027)的谈判前景,患得患失的应该是华沙和布达佩斯当局,而非法德等预算净支出国。
民粹威权政府的管治合法性往往反映在经济表现上,而正是此因素令波、匈政府都不可能切断和欧盟的纽带。
欧盟治或乱的核心因素
难民政策的分歧和民粹政治,都无法撼动欧盟的根基,但是再一次的欧元区危机却会。
使用欧元,可以说是欧盟成员国加入欧洲整合进程最大的里程碑;使用共同货币,是让欧元区国民个人福祉,由退休金到个人投资永久性地以汇价捆绑在一起的大锚。选民对于脱离欧元区的利益权衡,先在法国阻绝了勒庞和梅朗雄的总统之路,后在意大利堵住了民粹政党们号召脱欧之门。
不过,目前欧元区经济的回暖和稳定,是建立在欧洲央行几乎无限的资源所支持的量化宽松政策上的,欧元区本质的南北分野仍旧存在,共担风险的改革依然迟迟未见落实。原本,6月的欧盟峰会是讨论法德之间已谈妥的《梅塞堡宣言》、商议欧元区共同预算,以及将“欧洲稳定机制”扩宽到一个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市机制的场合,但难民问题引起的声浪却将这个议题盖过了。
就设立欧元区共同预算而言,操作的政治风险就很高,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花费良久才说服德国同意。何况,尽管欧债危机将欧元区的结构性弱点曝光,但要说服北欧选民在欧盟整体预算即将从全欧盟GDP的1%增加到1.3%之外,再以共同预算分担南欧国家的债务风险,中间的博弈恐会极耗欧盟心神。
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计划将在今年底结束,过去几年改革未如理想的欧元区国家(譬如意大利)一旦再次出现突发性的债务危机,欧盟团结的根基将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换言之,虽然欧盟共同资源暂时保障了欧元的稳定性,但结构性改革缓慢的欧元区,并无任何自满的本钱。
通过应对2008年以来多个共同的危机,欧盟架构本身的权力,随着各成员国使用欧盟平台去与邻居协调的频率愈发频密而壮大。欧洲整合超过70年的进程,让各国在经济上的纽带无可割裂,亦让根植于欧盟机构内的共同决策机制随之成长。但是,正如欧元潜在风险所揭示的,只要歐盟各国依然对财政转移有保留,欧盟就仍是一个半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