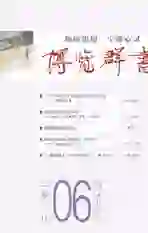大彻大悟钱锺书
2018-07-11伊岚
伊岚
对于“天下谁人不识君”的钱锺书,在其逝世二十年后,有必要重新审视。在此之前,先要对本文中其名字的显示形式进行界定。钱锺书生前并不认可自己名字中出现“钟”字,而在手迹中使用“鍾”字。后来折中之下,其名字出现时中间的字往往是“锺”字,杨绛再手稿中就使用此字。但本文要使用“钟”字,以示中立。使用“锺”字,是表达对钱锺书的崇敬与尊重的一种方式。但是,简化汉字是我国法定的国家通用文字,使用“钟”字,是符合规范的,是合理合法的。尤其是本文想尽量以一种公平公允公正的态度正视历史中的钱锺书,就更想避免因为使用“锺”字而散发出非理性的膜拜情结。
重新审视钱锺书的意义
钱锺书粉丝众多,因为他是几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因为他与杨绛活出了人人羡慕的爱情样式,因为他特立独行而绝不接受媒体采访。但也有人对于钱锺书的形象被神化、被美化提出反对,希望人们能对钱锺书作出客观评价。针对这种看法,又有人认为这些人根本不懂钱锺书,只是嫉妒。于是便陷入类似偶像的粉丝与黑粉间的无休止的争论。事实上,我却找不到太多真正理解钱锺书的资料。一些反对者虽然在学术上成就斐然,但却未对钱锺书所在的文学领域十分熟悉与深入。而粉丝们因为能力有限,加之长期仰视,也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评价。
比较之下,我认为张文江的《钱锺书传:营造巴比塔的智者》是重新审视钱锺书的好资料。我所使用的版本是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现在最新的版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但与199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初版《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锺书传》相比变动都不大。张文江本身学术功力深厚,对于文学又充满热爱,更有学术责任心。難道我是在瞧不起那些不从事学术研究的粉丝?当然不是。张文江在《自序》中说:“我觉得我不一定是写作钱锺书传记的合适人选。这不仅因为钱锺书是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领域里的巨匠,学问浩博无涯,极难研究和评价。”因此,粉丝们的反驳往往苍白无力——他们往往在表达敬仰之后就表示钱锺书的学问广博,自己无力窥视钱学之全貌。迷失在广博中的粉丝于是便难以胜任反证的工作。传记对于客观评价一个人的成就得失最为便利,但钱锺书并未留下自传,世面上较好的传记就是张文江这部,其他传记甚至未能进入钱锺书的精神世界。
但这部传记也有不足。张文江自己指出:“关于传记本身,钱锺书早年有过名言:‘自传就是他传,他传就是自传。如果除去当初的尖锐讽刺意味,这段话也可以是传记的正面标准,它实际揭示了传主和传记作者之间互相补充和沟通的双向过程。”张文江表示,自己在志向上与钱锺书有相当程度的不同,因此没再深入。此书是1993年出版的,后来重版,也因为“当年的情怀已然不再”故主要作了局部修订而已。因此,这部传记在1993年之后的新资料方面有所缺失。张文江在《潘雨廷先生的绝学》一文中谈到自己遇到古籍所的潘雨廷先生后就跟随他学《易》,可见张文江后来的学术旨趣转移到《易》上了一大部分。文中也提到了《管锥编》主要是个资料集,里面有形形色色的内容,初看起来杂乱无章,细心捡拾,则可各取所需。这样看待钱锺书的著作也非常客观。
其实,钱锺书到70岁才成名。张文江说:“钱锺书是比较幸运的,80年代以后钱锺书的声名如日中天……现在的青年人也许想象不到在当时的课堂上从教师到学生都不知道钱锺书的情形,但这却是我当年读书时的真实状况。”钱锺书真是幸运的,有许多有思想有学问的老学者后来籍籍无名,就是因为没有理解者、没有学生而思想无法流传。
就我自身而言,我觉得张文江的传记还有一处偏颇之处,在于一定的地域局限性。张文江指出自己在现代文学史上最喜欢三家——鲁迅、钱锺书、金庸。张文江本人是上海人,又专门提及鲁迅生于绍兴,钱锺书生于无锡,恐怕再深入,还要提到金庸生于浙江嘉兴海宁。因此,在读此传记时,更要避免这种倾向的影响。
张文江写此传记时,钱锺书仍然在世。此后至今,对钱锺书的研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突破。不过,相关材料有所补充,这就要归功于杨绛。杨绛才华横溢,又颇长寿,她为丈夫钱锺书写了不少回忆性的著作。而这部分材料,也要谨慎对待。仔细梳理钱杨二人的文字,不难发现,钱锺书很少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回忆,至多在《围城》中略带自传色彩、反映了钱锺书的一些人身态度。钱锺书的相关经历,大多经由杨绛之手写出。一方面,杨绛非常了解钱锺书相关人生选择的情况,保证了材料的真实可靠。另一方面,妻子难免会为丈夫粉饰,毕竟“情人眼里出西施”。更重要的是,这些材料是孤证,也缺乏其他证据的支撑。比如涉及钱锺书与他人的冲突时,要说钱锺书没有一点过错,是令人难以信服的。尤其是钱锺书在干校时生活的艰辛,要被置于历史大背景之中,看到那时知识分子的生活都是艰辛的,更要看到当时城乡二元对立体制下农村农民生活的更艰辛。
人生轨迹中的钱锺书
钱锺书是真天才。一般谈及钱锺书的天才时,总要说到他考清华数学只考了15分而中英文都得到满分而被破格录取这件事。天才只可远观不可亵玩,有时会对周围的人造成伤害。比如堂弟钱钟韩考大学时受到钱锺书天才的影响。钱钟韩的数理成绩非常优秀,文科也并不逊色。钱锺书报考清华,钱钟韩也报考了,钱锺书的成绩是57名,而钱钟韩是所有人中的第2名。不过钱钟韩也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因何故弃清华而选择交大不得而知,或许也有堂兄“美名”的压力。在交大的入学考试中,因其国文考卷太过出色,柳诒徵以为是专攻文史的宿儒,结果待到拆卷子时才知道是位年轻工科生的卷子。钱钟韩后来是中科院院士,是热工自动化学专家,真论及其贡献,未必不如钱锺书。才华高的人往往会恃才傲物,要么情商低,要么成为高度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钱锺书是真聪明的人,是真正的天才,并没有沦为那样的人。
纵观钱锺书的一生,他的不少选择可谓十分明智,考虑到其性格,不得不让人佩服其冷静。钱锺书的性格,是典型的才子性格。比如才子苏东坡,其侍妾朝云说他的大肚子装的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苏东坡也因其不合时宜而不被新党旧党待见,无论谁上台,总是被打压。说钱锺书是才子,就是因为他张狂刻薄、口无遮拦,这一特点一生未变,到英国留学后,甚至与英国人式的毒舌趣味结合在一起,《围城》里就处处挖苦人。不过这一性格是从小形成的。
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有一兄及一孪生弟弟。因为钱基博的兄长钱基成仅有一个女儿,二房长子钱锺书就被过继给伯父。钱家的长房总是在事业上没出息,但钱基成对于钱锺书却是慈爱宽容,甚至可谓溺爱,使得钱锺书数学极差,又养成了晚睡晚起、贪吃贪玩的习惯,可文科却在这自由的氛围中成绩优异。钱基成怕“坟上风水”在连累自己之外还连累钱锺书,因此买了几斤头发埋在祖坟上首几排树的根旁,跟钱锺书说“将来你做大总统”。后来钱锺书作为长房,声名如日中天,或许真与伯父的努力有关。钱锺书就在这种环境中变得口无遮拦。
钱锺书的父母都是严谨严肃稳重的人,难免会对儿子担心。十岁左右,伯父去世,虽然钱锺书仍旧跟着伯母一起生活,但教育他的任务从伯父转入父亲手中。于是,钱基博专门改其字为“默存”,就是因为小小的钱锺书常口无遮拦,父亲希望他记住“沉默是金”的道理。对于父亲的期许,钱锺书开始警觉——自己过于直言坦率,容易招致祸患。因此,钱锺书竟在风云变幻的历史环境中保全了自己。
钱锺书最天才的地方,就是他不仅做到了“默存”的“慎于言”,还做到了“敏于事”,甚至近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1949年,知识分子面临人生的抉择。钱锺书思考之后,决定留在大陆。即使香港、台湾提出相当丰厚的条件,他也不愿仰洋人鼻息。他们夫妇看了不少苏联小说,因此“鸣放”时,钱氏家族进行讨论,只有钱锺书夫妇坚持表示不鸣放,后来在各种场合也是咬紧牙关一言不发,最终得以保全。即使有参加了《毛选》翻译的工作,也与胡乔木、乔冠华等是清华的同学的有利因素,那时钱锺书能做到这样,实为不易。
钱锺书的沉默,并不是愚昧,他的天才使得他對于人情世故有相当的洞察,但他没有像苏东坡那样不合时宜。钟叔河谈到钱锺书,讲的是奥林匹斯山上的学艺之神同时又是谐谑之神,以锐利而又狡狯的目光俯视着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这种说法太形象了。钱锺书从来就不是道学中的君子形象,他是大彻大悟的,他是机智又刻薄的,他绝不迷信权威,绝不沽名钓誉,绝不会被道德绑架,绝不会被小人要挟,绝不会被声名所威胁。他的一生在践行着自己的名与字,钟情于书,而存有沉默。
钱锺书的学术
钱锺书的学术水平如何,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有人认为钱锺书是20世纪至今中国最有学问的人。不过,凡是用到“最”字的时候,我觉得都该严谨一些。可是“学问”本来就难以量化,也保不齐更有学问的人未被世人了解。更重要更关键的问题是,“有学问”对学术到底有什么意义,以及意义有多大。钱锺书有学问,是毫无疑问的,有人评价他是“一座学贯中西、记忆超群的活体图书馆,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学理论家,一个功能强劲的搜索数据库”,这是比较公允的。但是,有更方便的数据库,为什么要去问钱老先生?以“有学问”与否判断学术,是一种错误的取向,本身就是对钱锺书的误解。
这实际又回到张文江提到的问题——钱锺书是天才,又很勤奋,可谓巨匠,一般人很难评价。李敖是个充满争议的人,但他有《北京法源寺》这样的原创作品,因此可与钱锺书进行一番对话。于是狂人李敖曾在《锵锵三人行》中评价钱锺书,说钱锺书会读书,读书很多很细,能把外国同类主题的书弄到一起,这方面是一流高手,但思考力不够,死读书。余英时认为钱锺书的学术是“一地散钱——都有价值,但面值都不大”,也有人指出钱锺书在学术中没提出理论,没解决有价值的问题。
但钱锺书其实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学术选择与学术特色,似乎未被其他学者所理解。张文江指出,钱锺书有一层极为可贵的思想,为“破体”思想,即“破体为用”,就是要从具体的例证出发,不谈根本的理论,而根本的理论已含于具体的例证之中。钱锺书的这种思想颇有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味,确实解释了钱锺书为何不提出创见的问题。
张文江指出:“钱锺书著作较多注意句子层面,而较少注意典籍的整体思想,并不完全是不能,有时往往是不愿。”《管锥编》的《读〈拉奥孔〉》一文中写道:“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断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
这表明,钱锺书的想法与哲学家、历史学家很不相同,他颇为反对学院派式的体系思维。这样并非没有道理,反逻辑、反体系也是思想史上的一种进步,比如禅宗思想、比如后现代主义。当然,这种想法在钱锺书的学术中处于怎样的地位,是否支配着钱锺书的学术研究,实在不得而知。但确实又反映了钱锺书在学术上的大彻大悟。很多学者,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希望自己在学术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归根到底,这些作品都有其历史局限性,不可能是绝对真理,而自己,也不过是历史中的匆匆过客。
但是我不觉得大家都能理解钱锺书。比如,上海交通大学的夏中义教授认为,“《管锥编》表明钱有极深刻的思想,因为他是在当代语境探讨这一有重大意义的公共伦理命题:一个无权者,政治上未享有特权的个人(包括普通学人、知识分子在内),在面对历史特殊时期时,究竟该如何有尊严地言说,同时又可能是安全的?他不仅提出了这问题,而且还默默地践履,走出了一条独特路径。”可是连该访谈的编辑对夏教授的表达都不得不质疑,题目定为“钱锺书不仅是大学问家,而且是重量级思想家?”,这个问号,用得实在太巧妙。
钱锺书在提出“破体”之后,不太可能贪恋“思想家”的虚名,不太可能去建构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那么夏中义所用心用力读出的“公共伦理问题”,到底是钱锺书的思想,还是夏中义的思想?
一个美国女士读了《围城》后十分钦佩,费尽周折联系上了钱锺书,表示想去拜访,钱锺书拒绝了:“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钱锺书不想做因为蛋好而被宠爱的母鸡。一个真实的钱锺书,是直率的,是机智的,是深刻的,是彻悟的。希望人们能真正地理解钱锺书。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