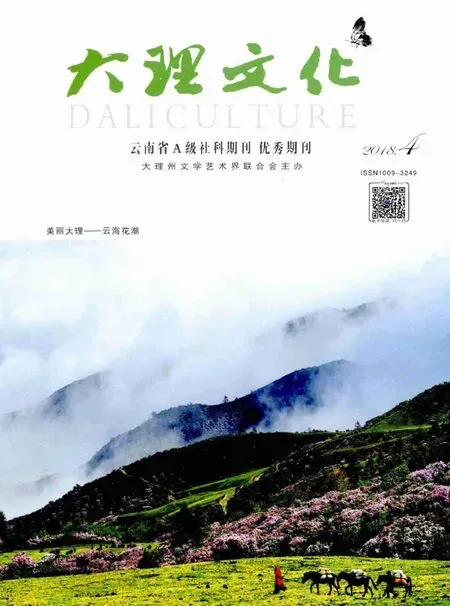师范那三年
2018-07-05张明曾
●张明曾
1957年,我初中毕业,被保送入大理师范,回到家里等待师范学校开学。可是左等右等,过了三个月都没有开学的消息,我心里很焦急。生产队安排我去正在孕穗扬花的稻田里吆麻雀。我每天太阳升时出工,拿上一床蓑衣,拎上一壶水,从早至晚在田埂子上转悠。我手中舞动着一支带枝叶的长竹竿,吼叫着追赶胆大的落进谷田中的麻雀。时间越长,我盼望开学上课的心情就越来越强烈。我曾两次跑到喜洲大理二中找过老师,打听开学的消息。可是学校里只有一位守校门的师傅,老师们都集中到大理古城整风学习了。
这个漫长的暑假,我白天到谷田里吆谷雀,晚上和几个同学自动组合起来,去各生产队扫盲班读报,教识字。报纸上大量刊登“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文章,篇篇文章把右派分子说得十分嚣张,大有变天的危险。我在心里为国家焦急,盼望党中央尽快做出决策,挽救国家的政治危局。一天,在报纸上读到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书已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我高兴得手舞足蹈,立马跑到喜洲书店买了一本,跑回家躲到牛厩楼上,躺在稻草窝里,一口气连读三遍。我觉得这下子满天乌云就要消散,党中央毛主席开口说话,严重的政治危机可以得到平息了。每天晚上,我拿上这本毛主席的书,到扫盲班读给社员听。杨家登扫盲班读了,到李家登扫盲班读,李家登扫盲班读了,到王家登扫盲班读……来听的群众越来越多。在读给大家听的同时,我还把自己的体会认识讲给大家。反复讲解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应当如何正确处理。那段日子,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位自觉的宣传战士,自己的命运前途已经与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连接在一起了。我清晰地认识到一个人只是像个芝麻一样微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伟大的,个人的命运前途与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紧密连接起来,微小的个体才会充满生命活力。

大理师范 陈彬 提供
九月下旬,终于接到大理师范学校开学报到的通知。我意气风发、兴高采烈地背上简单行李,告别爹妈、大哥大嫂和四哥,坐着堂兄赶的马车,从家乡仁里邑出发,在弹石公路上颠簸了一个上午,到达了大理师范。我们这一届1957年入校的两个班学生,是大理师范学校从大理古城搬迁来到自治州首府下关的第一届学生,加上原来在校的二年级、三年级四个班,全校学生只有六个班三百多人。校舍是崭新的,教学大楼、大礼堂(兼食堂)、教师宿舍、学生宿舍,一色的白墙青瓦,十分壮丽。道路、花园、体育场,都还是大片空地,等待着以后继续建设。我们一入学,每天在课后就按各班分派的任务开展建校劳动,把从农民手里征用过来的稻田菜地开挖平整成体育场,在大楼之间铺筑弹石路。经过一年努力,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跑道和各种体操、田径场地以及校园道路基本成型。每天课后,各项体育活动开展得热火朝天。
初到下关,从乡村进到城市,对我来说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所见所闻都让我感到好奇。一进教学大楼,中央大厅两边各是两面墙,一面墙上是广告栏,公布各种校内讯息和校方通知;另一面墙上是贴报栏,阅读上面张贴的报纸,可以及时知晓国内外大事。教学楼一层,除了教室、实验室之外,还有专设的音乐教室、阅览室和医务室。教学楼二层除教务处、教研室之外,全部是教室。学生宿舍分东边的男生宿舍和西边的女生宿舍。男生宿舍一层的开头分别设有理发室、沐浴室、缝纫室、体育器材室和琴房。师生理发、洗澡、看病、缝补衣服、打针吃药不必跑到城里。琴房中常常传出优雅动听的琴声和歌声。这里的教学设施体现出培养人民教师的专业特色。
当时的大理师范周围都是农田。东边隔着一片田坝便是青光山。青光山不高,长满了松、白杨、水冬瓜等树种,风景清幽,在交椅状的山腹间有一片豪华西式建筑是喜洲董家的别墅。我们常在星期天去爬山,到董家别墅看书。南方有一片小树林,树林边的小村庄约有七八户人家,村里不时传出鸡鸣狗叫之声,让我们的校园也带上了许多乡土田园气息。西边紧挨沙河埂,沙河两岸长满柳树、杨树,哗哗流淌的河水清澈见底,布满河滩的鹅卵石晶莹透亮。我们喜欢下河洗澡、洗衣,洗好的衣服晒在干净的鹅卵石上,澡洗好了,读一会儿书,衣服也晒干了。学校北边,隔着一大片田坝是火柴厂和汽车总站。汽车喇叭和工厂机器的响声,在学校里隐约可闻,透露出下关这个城市欣欣向荣、臻臻日上的发展景象。
学校也是一派新气象。崭新的校舍,美轮美奂。新分来一大批青年教师,个个风华正茂、才华横溢,教学工作、建校劳动都在有序开展。刚进学校,我被指定为中师20班的班长。我暗自下决心努力学习,好好工作。我们最喜欢的课程是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大课。教这门课的是杨向春校长从昆明师范学院请来的李老师。他是祥云县人,白族,三十多岁,操一口白族口音的普通话。他讲起课来,神采飞扬,逻辑性强,深入浅出,能把纷繁博大的理论阐发得明晰精确,让我们听来不觉得乏味枯燥、艰深难懂,好像一下子打开了洞察世事的眼眸。
寒假收假以后,同学们按时回到学校。学校接到指示,要大理师范师生全体出动,停课支援西洱河水电站建设。我们每天早出晚归,到电站建设工地敲碎石。每人每天要完成半个立方的碎石任务。在风城下关的来风孔道西洱河谷,从早至晚,风尘卷扬着千万人敲打石头和人喊车吼的声涛。头一天,好些人的手掌心磨起了血泡,火烧火燎地疼。可是谁都不叫苦,为新电站的诞生做贡献的想法鼓舞着大家。我们每天太阳落山时蓬头垢面地回到学校,忙着打饭吃。开始的几天,大家还争着去沐浴室洗澡,几天后,由于过于疲劳,都不争着洗澡了,都直接脱了衣裳到宿舍外使劲抖几下,拿干毛巾拍打头发里的尘土,擦擦身上的灰尘就倒在床上睡了。我们这些同学绝大多数来自农村,不怕劳动。可是,敲石头任务实在艰巨。我们一开始没有经验,老老实实捡河里的鹅卵石来敲。鹅卵石经过千百年的急流冲磨,如果不是最坚硬的石质,早就在岁月洪流中消失了。年纪大的同学有经验,他们去搬垮塌在山脚的石块来敲,容易砸破敲碎。我作为班长,及时采纳这个办法,组织一部分同学去搬容易破裂的石块,供给其他同学砸敲,完成任务有了保障。
敲了一个多月碎石,学校接着大力开展勤工俭学活动。一开始,学校建起简易猪厩,学生轮班喂猪。当时,农村兴办集体大食堂,我们学校食堂开始实行米饭定量,男生饭量大,都争着约女生同桌,这样女生就可以多分一点饭给男生。后来实行“蒸盒蒸饭”的制度,许多同学都叫吃不饱。同时,开展“又红又专”教育,反对只顾埋头读书的行为,强调提高政治思想,一切不利于集体的言行都被扣上“白专”的帽子。我们有个同学因肚子饿,在帮厨时偷了几个馒头被发现,受到群众性的批判,他受不了就卷铺盖回了家。为了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学校创办了《红专园地》校刊,指定我担任《红专园地》主编。我辞去班长的职务,开始担任起校刊主编。《红专园地》是将教室里淘汰出来的十来块木质黑板,支到教学大楼墙外作为版面。每个班选一个通讯员,负责撰稿组稿。语文教研室每期都供稿给我们,每两个月出一期。内容包括语文教学研究、语文知识讲座、学生作文选登、散文、诗歌、小小说、文章选读。这些内容都用广告颜料毛笔刊写。每期都由我们几个同学创作刊头插画。《红专园地》吸引了许多师生驻足阅读。到三年级时,学校又创办了 《学语文》《学艺术》两份壁报,《学语文》由郭世修老师任主编,我任副主编。《学艺术》由夏斌文老师任主编。两份壁报是纸质壁报,用墨书写,用广告颜色制作刊头和插画。我在第一期和第二期上发表 《论师范生的口才》《再论师范生的口才》两篇文章。戴宏亮、李正芳我们三个同学在壁报上对电影《五朵金花》发表过三人谈。由于我们的《学语文》壁报办得丰富多彩,生动活泼,表现出一定水平,曾获得原版入展云南省勤工俭学展览的殊荣。
1958年,我在杨德举老师指导下,借得杨老师的一把木刻三角刀,一把圆口刀,在一块小小的水冬瓜板上创作了木刻版画《饲养员》。内容是学校养猪场里,一个书生意气的小伙子,身挂白布围腰,胸佩大理师范校徽,正在往猪食槽里倾倒猪食。一群大猪小猪争抢着进食,被挤到一旁的两只小猪憨厚地抬头望着饲养员哥哥。我原本不知道怎么进行木刻,凭着自己的理解,学着白族民间艺人刻甲马纸的方法,留下造型线条,铲去线条以外的木面,保留住刀痕和未铲干净的木痕,用油印机滚筒铺油墨,铺上白纸,拿薄薄的废报纸盖上,用手掌反复轻轻按摩,揭起来,便成就了我平生第一件美术作品。这件作品内容表现勤工俭学的故事,手法洗练,有民间传统美术艺术特色,入展了1958年大理州首届美术作品展。
大理州首届美术作品展是配合州政府召开的大跃进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举办的。大跃进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在下关召开。我被抽调参加大会筹备组,为作家、画家们当帮手,为他们拉布标、剪字、贴字,发送宣传材料,倒茶倒水,收集大跃进民歌。表彰大会结束后,我被派到大理七里桥圣麓公园大理州农业大跃进图片展览馆,完成了展览的图案装饰工作。
1958年对我是有意义的一年。我作为一个在校学生被派到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在下关召开的西南区民族文化工作会议的筹备组中工作。在老师们指导下,收集白族民间建筑和服饰上的图案,供老师们布置会议场所,设计节目单、请柬时参考。另外,秘书处指定我负责订做一束开幕式主席台插在主讲桌花瓶里的绢花。下关振兴街一家绢花店负责做这束绢花。我担心误事,开幕前几天,每天都去催促察看。开幕那天早晨,我打早跑到花店叫醒店主,店主说现用现炀蜡才新鲜、逼真。我守在旁边,师傅一炀完蜡,我就拿着往开幕式会场下关电影院跑。开幕式在上午九点钟举行,当我将绢花插入桌上的花瓶时,时间是九点差一刻。两台早架设好的电影摄影机开始了拍摄,发出嚓嚓嚓的响声。这次会议上,我现场聆听了文化部部长的讲话,观看了傣剧《千瓣莲花》、彝剧《半夜羊叫》、白剧《杜朝选》,还观看了壮剧、藏剧。这些民族剧目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代表们评论“白剧比较成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过了六十多年,我还记忆犹初。
暑假,学校介绍我们几个同学到州粮食局打工,工作是在一本绝密的精致小手册的表格里填写粮点的位置、储存粮数,在空地图上标注重要城镇名称、粮点。这个工作要求准确无误,书写规整,严格保密。一个假期过去,除供伙食外,还得到二十八元工资。这钱是我长大以来属于自己的最大的一笔钱。我用这笔钱给自己和一个与我关系最好的男同学各买了一双大理人做的黑色大头皮鞋。还剩下十多元钱,每星期六放学后,我拿着这些钱跑到西大街牛肉馆吃一碗红烧牛肉。另外,还买了一些水彩画颜料和画纸。
那几年,大理师范有一个很好的传统,除《红专园地》和《学语文》《学艺术》壁报,学生自办理发、缝纫之外,星期六学生常常自办文艺晚会,表演歌舞、戏剧节目,举办各种游艺活动。师范三年,我创作过三个剧本,一个是话剧《邱泽康》,以当时上海著名医生邱泽康为一位轧钢工人断手再植成功的惊人事迹为题材,歌颂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忘我劳动和震惊世界的医学成就;一个是话剧《不能走那条路》,内容是勤工俭学中的真实故事,不做书呆子,反对“白专”道路,提倡“又红又专”;一个是诗朗诵剧《赶过英国佬》,全剧用诗朗诵作为背景台词,形式是滇剧钢铁元帅升帐,抒发我国争取钢铁产量超过英国的壮志豪情。三个节目都由我自己导演并亲自参加表演。在星期六我们班自办晚会演出。三个节目都曾引起轰动,引发热烈讨论。尤其诗朗诵剧《赶过英国佬》,形式新颖,深受领导和师生赞扬。大理州教师工会举办文艺会演,殷世勤老师还向我要走剧本,组织教职工排演,参加全州教工文艺会演,获得良好的演出效果。
说起师范学生生活,有趣的事情也很多。那时候全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学俄语,唱苏联歌曲,读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高尔基的书,跳哥萨克舞。苏联花布在下关倾销,学校提倡穿哥萨克服装,女生剪短头发。我们班十多个女生都剪掉了长发,留了儿子头。在课间活动和上食堂的路上,谁是男谁是女,都分不清。多次闹出男生搂上女生,把女生吓得大叫的笑话。
学校发动学生到南山割香叶卖给供销社熬芳香油,扭松球做风窝煤引火柴卖,到西洱河捞海草集肥支援农业生产,到凤仪割麦子,到下鸡邑抢收淹没在海水中的稻子。1959年,秋收时节即将到来,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消灭麻雀的风潮。说麻雀吃掉的粮食足够五分之一人口的口粮,麻雀罪大恶极。学校组织我们到下关附近的稻田里追赶麻雀。我们每天早晨赶到田坝里,挥舞手中的长竹竿,东追西赶,大吼大叫,敲锣打鼓,吹哨子,试图吓跑麻雀,不让一只麻雀飞落到稻田中。
大跃进,大战钢铁。大理师范在校园内建起两座土高炉,师生被派到洱海东岸文武山挖铁矿,背矿石,留下一部分学生在学校里烧煤炭炼钢,我也在其中。留校学生只有二十多人,排班坚守,日夜苦战,保证两座土高炉内的火熊熊燃烧,决不让膛火小下来。烧掉了堆得像山头一样的几座煤山,用坏了几台鼓风机。可是无论怎样努力,两个多月过去,两座土高炉仍没流出大家所企盼看到的钢水。为让全校师生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苦战有个 “句号”,我们还是抬着一块从炉膛里取出的“铁屎”,挂上红绸彩带,敲锣打鼓,在迎风飘扬的校旗引领下,到州人委报了喜。
在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到巍山、到漾濞烧煤炭。我们班被分到平坡。我们到了平坡山上的密林中,首先砍出一片排球场大的空地,用砍下来的栗树、松树搭成了一个长方形的窝棚,中间栅上一道墙,一隔两半,大的一半男生住,小的一半女生住。睡的都是树叶茅草铺垫的通排地铺。在这排宿舍的开头,另搭了一个小窝棚作为厨房。老师指派段文兰煮饭。每天派两个男生帮厨,负责挑水、捡柴、洗菜、烧火。其他人为烧炭的主力军。先请一位漾濞村里有经验的烧炭人指导造炭窑。一部分人在师傅指挥下挖山造窑,我们其余的十多个人便钻入密林去砍烧炭用的栗柴和做燃料的杂柴,柴砍够了,炭窑也造好了。烧炭师傅参与了砍山烧炭,就得遵照烧炭习俗,举行拜山神、树神、水神的仪式,非如此,得罪了山中神灵,就烧不成炭。我们举行过庄严而又简单的开窑仪式,点了火之后,同学们又分成了两拨人,一拨人继续完成砍烧柴的任务,一拨人值班凑火烧窑。我们吃的大米、油盐酱醋、蔬菜,都由学校派车从下关送到山下,每隔几天,都得有人去跟车。车来到,大家去山下把东西搬上山来。为保证烧炭,后勤保障占用不少人力。在山上吃饭,饭量猛增,吃什么都觉得有味。段文兰煮的饭又好吃。每当她煮好饭,叫:“吃饭了!”我们便从山林里钻出来,欢呼着“放卫星了!放卫星了!”那时候,各行各业都讲“放卫星”,“放卫星”成了一句玩笑话,连吃饭都叫“放卫星”,意思是放开肚皮吃。
一窑炭烧好了,遵照师傅的指点,将窑门封严实,叫“焖炭”,意思是把炭焖熟些,同时叫炭窑慢慢冷却下来。在平坡山中三十天,我们三十多人,吃了不少大米蔬菜,烧成了一窑优质栗炭,每根栗炭皮面有一层白白的“霜”,手指轻轻一弹,发出敲金属棒一样的叮当脆响。学校调选了一捆,在炭捆子腰里扎上一道红绸,陈列到勤工俭学展览厅里。那时的勤工俭学,其实只强调了锻炼学生,勤和俭并没做到,相反人力物力浪费了不少;天天去劳动,没上课,也谈不上工和学。
烧炭回校后,我们接着参加了栽水稻卫星田的战斗。我们早出晚归,在金星村田里,先把稻田挖开,挖得一人深,就像盖大房子的石脚槽子。每挖开一条,就填满优质厩肥,然后重新挖一条,用挖出来的生土把原先填满厩肥的一条盖住。这样一丘田都挖完了,放水,再撒满厩肥,搅拌成肥水泥浆,然后将拔来的秧把拍成薄片,一片紧贴一片栽到肥水泥浆田里。按照指导我们栽秧的人说,这丘田必定要产几万斤。我们心中惦念这丘高产万斤的试验田,过了一星期,跑去看,眼前的情景叫人目瞪口呆,整丘田的秧苗发黄变黑,全枯死了。跑去看稀奇的人多得像赶街。人们七嘴八舌议论:“这么密不透风,秧苗闷死了。”“秧苗栽在肥堆上,被肥料呛死了。”“这丘田以后都种不成庄稼了。”……
1959年春耕大忙时节,州委组成赴鹤庆抗旱工作团,支援抗旱抢栽。由州法院贺政委任团长,我被指定担任副团长。工作团开赴鹤庆那天,车过北衙,载着我们的三辆大卡车驰入了马鞍山密林中。突然间,天气忽变,狂风暴雨大作,霎时间,山洪滚滚而下,公路成了洪涛滚滚的瀑流。三辆大卡车无论怎么使劲都无法爬坡。全体人员冒雨奋力推车,车轮飞速空转,推车的老师同学浑身上下都溅满泥浆。驾驶员在轮胎上缚上防滑铁链,也无效用。大雨仍在倾盆,天时已近傍晚。驾驶员发动大家折松枝来垫在车轮前,汽车加油使劲,人们合力推车,喊声震撼夜空。汽车在铺垫成的松枝路上一截截往山上挪动前行。待翻越了马鞍山,下坡到松桂,雨停了,夜已深沉。人人肚子都饿瘪了。领队的老贺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担心大家受饥寒生病,赶快到达县城,取暖吃饭才好。”到达县招待所,三大盆通红的栗炭火在等待我们,整个饭堂灯火通明,暖意融融,烤干了衣服,个个都忙着揉搓衣服上的泥垢。
第二天,我们班四十多个同学分成两组,我这个组驻到甸南金墩招待所,贺团长随我们驻到金墩公社;另一组驻到甸北辛屯。起先,我们每天跟随社员下田拔秧、挑秧、挖老板田、撒粪。因为那段时间,狼下到坝子,金墩地区发生了多起狼袭击人,拖走社员家猪羊的事件。我们男生每人手握一柄长刀,站在田埂上为社员放哨。后来,贺团长叫我带着一位双目失明、拉二胡的老人和一位唢呐师傅,每天到田间演奏二胡和唢呐,即兴编唱白族调,鼓舞劳动士气。我每天把统计来的栽插和其他劳动项目的进度、采访到的新鲜事、收录的白族调,进行编辑,刻写油印成《春耕战报》,第二天再到田间读给社员听。
鹤庆农村耕牛奇缺,栽秧田都靠挖板田翻耕。对准干裂的缝子一钉耙挖下去,挖起的土垡都有柜子大,几个人一齐使力都难得翻过来。由于干水,上垡子捣不碎。挖板田的进度太慢,栽插进度也就上不去。可是季节不等人,必须按季度完成栽插才能保证好收成。为了解决缺乏耕牛的困难,县里决定派我和查育鹏以及县委书记的通信员小李与金墩公社的两位干部,组成一个借牛小分队,攀越东山,到山区六合公社去借牛。
跋涉了一个白天,天黑了还没有到达六合。我们在霏霏冷雨中,既不能前进,又不敢在密林里寻找路径。身背步枪的县委通信员小李说不能瞎摸乱闯,傈僳族同胞在林中安着捕野兽的扣子,人踏上扣子会受重伤。远处的夜空中,有两三点火光闪烁。有人提议,请小李鸣枪,引人赶来,以便脱离困境。可是小李说不行,这样会引起误会,不安全。大家被雨水淋得个个像落汤鸡,肚子饿得咕咕响。心里急得火烧火燎。还是当过兵的小李有办法,他叫大家蹲下身,睁大眼睛,尽量看清前边两三步路,双手摸索着路面,连爬带滚慢慢往前挪。很幸运,不一会儿,我们就摸进了一个村庄。可是,我们眼前一团漆黑,没有一点灯光,无意间摸上了一个高坎台阶,摸到门边悬挂着门牌,都争去啪啪拍门。不一会,大门缝里射出了亮光,门后发出 “什么人?”的严肃询问。县委通信员和公社干部都报了自己的名字,大门嘎地一声重响,开了。我们这群落魄、疲惫、饥渴的人被热情地迎进院子里。原来,这是六合供销社。大家没有多说几句话,两位公社干部和供销社干部小郭就忙着煮饭。我实在疲惫难耐,随手拉过两张包装货物的草帘子,往木板地上一铺,躺下了。一躺就睡了一觉。等到我被拍醒,浓浓的饭香直扑鼻孔。我们一伙人狼吞虎咽,不一会儿,一大锅火腿肉焖饭就被一扫而光。可以说,这顿饭是我到鹤庆后吃到的最香甜最满足的一顿饭了。
第二天打早,我和查育鹏被分为一组到生产队去借牛。我们在一个六合小伙子的引领下,爬了一上午山路,到了生产队。队长不在,他领着社员到山上烧地了。我们又到了烧地的地方。眼前所见的一幕让我吃惊。社员们在密匝的原始森林中砍倒了一大片树木,大树干放置在周边,中间烧起一大堆熊熊大火,火焰冲天,燃烧着碧绿沁油的枝叶,噼啪作响。队长明白了我们的来意之后,对社员交代了几句话,躬身从火堆边掏出了一些烤熟的野鸡蛋,拍掉灰烬,分给查育鹏和我吃。然后,队长挎上铮亮的猎枪,朝前下山。队长打光脚,在满是岩石的山路上健步如飞,我们在他身后有些跟不上。这一趟进山,让我目睹了刀耕火种的场景,觉得格外新奇,心中隐隐不安,亦有一种对森林被毁的痛惜。
回到队长家已是晚饭时分。我和查育鹏被招呼在火塘边休息,队长和他父亲忙着煮饭。傈僳族人家的火塘就在房间中间,煮饭煨茶都在火塘上,睡觉就在火塘边。火塘两边是两张床,床是两块十分厚重的木板。多少代人都睡过这两块木板,在上面过完一生。木板被磨得油光水滑,中间还微微凹陷。队长首先将铁三角架上火塘,拿来一个铜锣锅,掺上水,把泡发的小白豆放入锣锅煮着,然后就到村里布置借牛的事去了。等到队长回来,火上的白豆煮熟了。只见队长往锅中放盐,撮一瓢玉米糁慢慢往白豆锅里倒,一边倒一边拿一双长筷子不停搅动。锅里的白豆和玉米糁越搅越稠,直到搅不动了,饭也做好了。
这时屋外下起了毛毛细雨,队长到房后采来一大把带雨水和绿叶的青椒,在手里揉碎放进一个瓷钵里,冲上开水,给每人盛一碗香气扑鼻的白豆玉米糊。只见队长和他父亲各自舀一些青椒水拌饭,吃得很舒爽。我也学他俩舀了一勺青椒水浇到饭上,吃了一口,就被麻得爆发式地打起嗝来,没有吃成一口饭,一夜打嗝。每打一次嗝,肠子肚子被扭得一阵巨痛,一夜无安睡。我心里想,这辈子可能就这样打嗝了。第二天打早,我们一行人忙前跑后,在山路上吆喝着十多头腰肥体壮的一路抵架的黄牛往金墩赶,我不知什么时候停止了打嗝。
回到金墩美美地睡了一夜,起了床,我将浸透汗汁的衣裳换下来,准备到河边去洗。公社一个年轻人跑到我面前,通知说叫我们明天回县城集中,后天回州。查育鹏立刻决定约我们到他家看看。查育鹏家离金墩街只有四五里路。到了他家,在他家果园里消磨了一阵,查妈妈就炕好了一撂燕麦粑粑,查爸爸为我们泡了一锑壶茶,我们三个同学一阵狂吃,把三十多个燕麦粑粑扫光了。这顿饭算是我在鹤庆吃的第二顿最满足的饭。
1960年夏天,学校遵照政府指令,指派学生组成小分队,到周边各县去推广小球藻,说小球藻富有营养,可以填补粮食欠缺,解决群众营养不足问题。我们五个同学分到巍山,我被指定为组长。我们乘车到达巍山县城招待所,吃过中饭,背上行李,在向导带领下,翻山越岭,步行整整一下午。在太阳落山之前,我们赶到巍山县最南部与云县接壤的青华公社驻地,住进了生产队打场的通敞平房里。我们刚放下行李,就与生产队长商量建小球藻池的事。生产队干部们最听上级的话,一说大家思想就统一了。两天时间,在晒场上建起了一个三十多平方公尺的小球藻池。等石灰干透放入清水和小球藻苗,按比例加入人尿。过了一个星期,池里的水现出透绿的颜色,小球藻生长起来了。十天后队长分配碧绿的小球藻水给社员家烧开水饮用。
我们推广小球藻的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受到县里的表扬。一位副县长专程来到青华看望我们。那时,国家处在三年困难中,群众生活很苦。我们在青华住了一个月,基本没吃过米饭,最好的饭食是苞谷糊,有时只吃红苕。有两天,煮饭的大嫂没东西煮,只得到山田里割蚕豆尖来煮给我们吃。我们几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饿得心慌,手脚发软。一天,我们去山上闲逛,发现山坡一个凹坪里,有一片房院废墟,断墙下有几棵香橼树,叶子稀疏发黄,僵硬的枝条上挂着十来个大小不等的香橼果,金灿灿的,散出阵阵果香。我们几个人没有商量,不约而同地伸手摘下香橼果便啃起来。香橼果虽然硬得咬不动,苦涩难咽,我们还是把肚子撑得饱饱的。有一天,我们窜进苞谷田,因为肚子饿得实在难熬,便把嘴冲着尚在灌浆的苞谷穗,啃吸起苞谷浆来。
一个月过去,我们接到州里通知,小球藻推广组出村回州。生产队干部与我们开了总结座谈会。老会计从家里抱来一个金灿灿的大南瓜,煮了一锅南瓜与四季豆。队长拎来一瓶甘蔗渣酒,同我们吃告别饭。吃完饭,已是傍晚时分,我们背上行李,踏着在群山中朦胧的月光,跟随向导,翻越了无数雾气深重的山岭,头发和脸颊被凉丝丝的夜露打湿了,身上冒着热汗,终于在第二天清晨回到了巍山县招待所。刚跨进招待所大门,那位到青华看望过我们的副县长就走上前来迎接我们。他陪我们吃过中饭,我们就乘车驶上回程。在汽车上,我也在想,推广小球藻也许不能够彻底帮助山区群众摆脱困境,但能让山区群众看到党和政府对他们是关心的;也让我们几个学生看到山区群众还处在贫穷困苦中,使我们经受了锻炼。
从鹤庆回到学校,离毕业只有不足三个学期了。可能考虑到再不好好上课,我们这届学生毕业出校是否能成为合格的师范生,就成问题了。于是,学校把所有的课程开齐,新开了教育学、心理学、语文教学法、数学教学法、学校管理等课程,每天七节课,课表排得满满的。杨向春老师还给我们开了高等数学课。师范三年,我像海棉一样汲取了多方面的知识,一有时间就钻进阅览室,最喜读的杂志是 《边疆文艺》《新观察》《民间文学》《少年文艺》。我随身带着练习本,读着有心得体会,就在练习本上写起来。
三年时间,好像一转眼就过去了。记得毕业离校前夜,李正芳在《边疆文艺》上发表了小小说《谷堆》,前两天领到了一笔稿费。他请我们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到下关文化馆茶苑喝茶,一边嗑瓜子,一边喝茶聊天。明天大家就要挥手告别同学,告别师长,告别母校。今夜欢聚,我们几个书生,豪情大发,心中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师范的三年时光,对我而言,既是短暂,又是漫长的。长夜漫漫,未来似乎就隐藏在这黑夜之下,等待着我们亲自去开启。
编辑手记:
校园时光,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异常珍贵的。在作者张明曾读书的那个年代里,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又带给他一段与众不同且难以忘怀的校园时光。时光荏苒,这些回忆并没有在作者的记忆之城里漫漶,反而在他的笔下显得真挚、生动。跟随作者的回忆,大理师范的旧貌与师范生的往事被他娓娓道来。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就读于大理师范,那时国家正处于百废待兴、积极发展国民经济的阶段,政治运动的浪潮已打破校园生活的平静,也将学生提早推入社会这个大熔炉里。作者在读书之余,必须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社会活动,如修建水电站、参与各种会议的筹备工作、大炼钢铁、烧栗炭、栽水稻放卫星、推广小球藻……也许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学生们已经无法“一心只读圣贤书”了,各种各样的劳动经历让他们提早饱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学生的单纯与稚嫩,使他们在与大自然搏斗的过程中显得异常弱小,然而团结与坚持成为他们对抗一切的力量。学生的特殊身份也使他们在社会舞台上始终扮演着一个小小的配角,只能随波逐流。被时代浪潮所卷裹的每一个师范生,心中也许会有一丝迷惘和无奈,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也让我们体会到这一辈人艰苦朴素、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