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网络权力”
2018-07-03黄湘
黄湘
自从基于互联网2.0技术的社交媒体诞生伊始,对它的价值判断便一直趋于两极化。支持者认为,社交媒体使得那些过去只能扮演信息“接受者“角色的大众转变为主动的”传播者“,从而令多元的声音可以真切地在公共领域中相互讨论;反对者则认为,社交媒体所提供的只是高度碎片化的交流,容易造成偏见的自我强化,以及诉诸情感而非理性的群体认同和偶像崇拜,结果导致民粹主义大行其道。
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政治冲击力迅猛飙升,西方主流传统媒体对它的评价经历了从褒到贬的大转变。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之时,西方各大媒体无不欢呼社交媒体推动了这场在中东地区史无前例的社会革命;然而,到了2016年,大多数西方主流传统媒体又哀叹社交媒体引发的民粹主义狂潮颠覆了西方社会的政治秩序,导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全球政治经济也随之险象环生。
如何看待社交媒体对政治经济秩序的冲击?它在人类历史上是不是前所未有的现象?抑或曾经有过类似的先例?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广场与塔:从共济会到Facebook的网络与权力》一书,通过对“网络权力”和“等级权力”两种权力类型的分析,重构了近代以来的历史叙事。弗格森将当今时代界定为“第二网络化时代”,与西方世界从15世纪后期到1790年代的“第一网络化时代”相对照,为理解人类文明的当前处境和走向提供了历史的镜鉴。
《广场与塔》的书名本身就隐喻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权力。在广场上,人们在水平的层级上非正式地相遇杂处,形成网络化的交往结构;而塔则象征着上层控制下层的等级化结构。弗格森声称,历史学家对等级化实体—诸如国家、政府、军队、公司等—投入了过多的关注,对于相对松散的社会网络结构却研究甚少。一个主要原因是历史学家所依赖的史料大多数来自等级化实体所留存的档案,有关社会网络结构的记录则往往杳然难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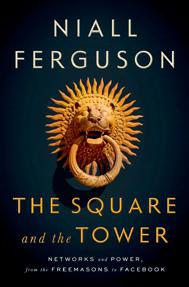
此书首先体现了弗格森梳理史料重现社会网络的史学功力。
弗格森指出,自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社会长期由“等级权力”主导。然而,到了15世纪后期,随着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和新大陆的发现,西方世界“等级权力”之塔被颠覆了,取而代之的是众声喧哗的“网络权力”,西方世界进入了“第一网络化时代”。
德国发明家古腾堡在15世纪中叶首次将活字印刷所需要的各个环节组合成一个有效的生产系统,可以实现大规模的印刷生产。1517年,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提出了《九十五条论纲》,公开否定了罗马天主教会所宣扬的只有通过教会和教皇才能赎罪的说教,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早在路德此举一百年前,捷克也曾经爆发反对天主教会销售赎罪券的“胡斯运动”,但并未形成燎原之势。马丁·路德则幸运得多。由于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他的言论被广为传播。据统计,在16世纪,路德的著作有近5000种版本付印,他的《圣经》德文译本有近3000种版本付印。
弗格森指出,“第一網络化时代”为西方世界打开了“现代化”之门,旧的权威被打破了,新的思想和组织层出不穷,最终体现为经济与社会的除旧布新。而西方之外的其他任何一种文明都没有这样的机遇。
但是,对于生活在其中的普通民众来说,“第一网络化时代”却又是一个动荡不已的乱世。宗教改革摧毁了中世纪统一的基督教世界,令西方走向教派分裂,从1562年到1598年,法国发生了旷日持久的号称“胡格诺战争”的宗教战争。从1618年到1648年,欧洲主要国家均卷入了天主教联盟和新教联盟之间的“三十年战争”,日耳曼各邦国在战争中被消灭了近60%的人口。正是当时的乱世使得英国政治思想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将人类的“自然状态”设想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只有当所有人将自己的权利转让给一个人或一组人并签订社会契约,人类才能获得和平,而这意味着号称“利维坦”的专制国家的诞生。换言之,霍布斯是在“网络权力”横行的时代呼唤“等级权力”,将后者视为投进深渊的一束光明。
“第一网络化时代”的顶峰是1789年大革命前夜的法国。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将法国大革命的关键肇因归结为18世纪法国盛行的“文人政治”。各种沙龙、期刊、印刷品遍地开花,重构了公共舆论的“广场”,王权的神圣性在文人的犀利谈锋下销蚀殆尽。而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残酷也是空前的,正如死在革命中的罗兰夫人临终时所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物极必反。从法国大革命中崛起的拿破仑通过建立帝国、颁布法典而重建了“等级权力”,弗格森称拿破仑是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独裁者。“等级权力”在欧洲的全面恢复,则是始于拿破仑战败之后,欧洲列强在1814和1815年所召开的“维也纳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号称“维也纳体系”的国际体系,一方面通过压制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和人权等理念来维持社会的保守与稳定,另一方面通过维持列强之间的权力平衡来确保和平。从1815年到1914年,欧洲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维持了长达百年的和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维也纳体系”因此得到了基辛格的盛赞:“令人惊奇的不是解决办法如何欠妥,而是这种方法是多么明智;也不在于解决方法如何‘反动,而在于如何取得均衡。”—弗格森极其推崇基辛格,他在《广场与塔》之前出版的上一部著作就是关于基辛格早年生涯的传记。
弗格森提醒读者,不受约束的“网络权力”同样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其危害程度不亚于不受约束的“等级权力”。
然而,“等级权力”在20世纪的极权国家达到了顶峰,从中产生了奥斯维辛和古拉格的罪孽与恐怖。两者都是“等级权力”暴力统治逻辑的产物,也验证了“等级权力”下的个体是何其容易无条件服从、甚至是变本加厉地执行上级的命令,从而成为制度的帮凶。切近而惨痛的历史记忆,使得当今世界的公共舆论普遍对“等级权力”深具戒心,而对“网络权力”则评价相对正面,即使有所批评也颇多恕辞。但是,弗格森提醒读者,不受约束的“网络权力”同样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其危害程度不亚于不受约束的“等级权力”。
自从1969年10月互联网诞生以来,人类进入了“第二网络化时代”。社交媒体的崛起和移动互联的流行,使得人类时时刻刻处在海量信息的流通和观点的碰撞中。但事实表明,这反而导致了公共话语的崩溃。《科学》(Science)杂志2018年3月9日发表麻省理工学院学者沃索基(Soroush Vosoughi)等人的研究报告指出,在Twitter上向1500名用户传播假消息的速度,比传播真实新闻平均快6倍。此项研究结果同样适用于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在无序凌乱且真伪不明的网络话语冲击之下,公共议程的建构备受挑衅和扭曲,各种民粹主义和极端思潮则甚嚣尘上,势不可遏。
2016年,牛津词典宣布将“后真相”(Post-Truth)作为当年的英文年度词汇,意指“相对于情感及个人信念,客观事实对形成民意只有相对小的影响”。人类社会从此进入了“后真相时代”,相形之下,无论是古腾堡印刷术所催化的宗教分裂,还是18世纪法国沙龙所孵化的“文人政治”,都不免瞠乎其后,这似乎预示着一个大混乱的时代即将到来。
弗格森指出,在网络化结构中,那些处在高密度连接的节点位置的人或组织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巨大资源,产生“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从而强化不平等。在当今世界,Facebook、亚马逊等互联网巨头都只用了短短十几年时间便富可敌国,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垄断地位所带来的租金。对于它们的监管和问责可谓刻不容缓。
今年4月,在美国国会针对Facebook的听证会上,扎克伯格一口咬定,Facebook不是一家媒体,而只是一家技术公司,因此不需要承担媒体社会责任以及相应的严格法律监管。他的狡辩遭到了业内众多有识之士的驳斥。正所谓“杀龙勇士最终长出龙鳞”,今日的互联网巨头早已不是重新分配“等级权力”所控制的資源,而是凭借马太效应聚敛资源。《广场与塔》的启示在于,人类对一切权力都应当保持警惕,无论是“等级权力”,还是“网络权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