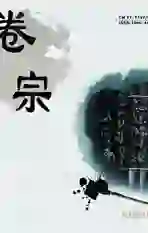与亚里士多德对照:王国维“第三种悲剧”之美感三维分析
2018-06-30金永芝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借用叔本华“第三种悲剧”的说法研究中国悲剧美学的本质和美感特质。它认为美术的任务在于描述人生困境并提出解决之道,而悲剧的使命就是展示人生欲望与痛苦的生存困境,进而提出缓解存在之惑的精神超脱之道。比较西方悲剧美学的开山鼻祖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实则发现中西悲剧美学的出发点与终极追求的一致性,然而起点到达终点的过程却呈现不同的风貌,展示不同的悲剧美感特质。本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探析王国维与亚里士多德悲剧美学的共质:悲剧本质存于人的缺陷,悲剧价值在于实现平衡。第二部分,王国维“第三种悲剧”之美感三维分析。具体如下:其一,人生情趣:非致力理想而安于现状;其二,心灵开解:非重视行动而冥思苦想;其三,自悟自救:非英雄精神而凡人主义。
王国维悲剧美学思想精髓集中体现文艺理论著作《红楼梦评论》之中。该评论在探讨“第三种悲剧”美学特质之前对人生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望,而痛苦源于与生俱来的欲望,有欲望必然伴随痛苦,这种痛苦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排解因为欲望是人的本性。人生面临的死劫,恰恰造成了人生的各种悲剧,这种人生之“劫”与亚里士多德的“失误”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学术界在分析中西悲剧美学相同之处之时总是弥漫着命运感的原质,认为两种文化语境下的悲剧都被一种隐形的命运所统摄,其实这种说法看似合理其实不符合逻辑。其实,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从来没有提及“命运”这样的说法,而且还明确地谴责古希腊戏剧所用的“机械降神”,即遇到无法解决的情境就请神来解决的办法。在论述悲剧人物应该如何设置时这样描述:“还有一种人,介乎这两者之间:他不以美德或正义著称,他所以陷入否运,并非因其邪德败行,而是由于错误。”③悲剧人物之所以陷入灾难并非具有主观故意作恶的可能,而是由于自身疏忽大意或者由于认知缺陷而导致毁灭性后果。正是因为在主观上不可能避免那些潜藏的失误,再加上古希腊人一种强烈的命运感,很容易轻信希腊悲剧被命运所笼罩。如果抛开过于主观性的论断,重新解读亚氏悲剧实质上它非但不附合命运而且是排斥命运的,它强调的是命运对立面——人。与其说希腊悲剧重视命运,毋宁说它更重视人本身的价值。人在行动之前没有意识到失误,不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的天意,这种失误不是天意所为而是人本身的缺陷所致。
王国维在分析贾宝玉之玉来历时这样描述:“此可知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过此欲之发现也。”这是在说欲望是先于人而存在的,在人还没有存在这个世界之前,就先验的存在那里,而人生的阅历不是形成欲望的外在条件,它只是一个展现欲望的舞台而已。乍一看来,这种说法具有一种凭天由命的宿命论倾向。但是有这种错觉并不代表王国维强调悲剧美学意象的命运意识,作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王国维自然不会游离于中国式的人生情怀。关注人生关注人本身才是王国维悲剧美学的初衷。它发现人本身具有一种顽疾,这种顽疾就是欲望,而欲望会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简言之,人的缺陷是造成悲剧的根源。
为此,中西的悲剧美学在起点上不约而同的都达成了一致。正是因为人本身的缺陷,才会导致人的困难,而人的缺陷是先天固有根本无法解除,为此悲剧无法规避。这种残酷的现实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为此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将希望寄托在悲剧艺术之上,尽管在探索的过程呈现不同的路径,但是它们的终极目标却是一致的。
正是因为人生的缺陷,才需要艺术来化解人生的顽疾并开拓一条出路。为此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悲剧的净化说,而王国维开辟了一条解脱之道。
关于净化的内涵一般都停留在表面化和抽象化的揭示,并没有进行穿透性和层进式地分析。其实,根据“卡塔西斯”术语的提示,净化本身应该包含净罪、宣泄和陶冶三层子美感。它们何以产生又如何层层推进的呢?所谓净罪,就是悲剧人物对因为自身的缺陷造成可怕的后果,这是人本身的罪过,就应该由人本身来受罚。所谓宣泄,悲剧人物无不犹豫的为追求更高理想而宁愿承担风险的精神,让审美主体领悟承担毁灭肉体成全精神的永恒灵魂不死精神力量,为此那种害怕肉体毁灭人生就此终结的痛苦随着高尚的精神追求烟消云散。所谓,陶冶,就是情感的领悟促使人的自主性完美人格的形成,人的精神品格为此达到一个新维度。西方悲剧更多强调在破环性的代价中创造整体地和谐与秩序。
王国维强调,《红楼梦》的精神在于描述人生地欲望与痛苦,并且为化解人生欲望与痛苦探寻了一条精神出路。“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① 生活的本质充满欲望,欲望作为一种人性的恶,是一种罪过,是罪过就要受到痛苦的处罚,这是一种自然正义。人类自己本质地错误需要自己来惩罚,而自己的痛苦需要自己来解脱。最后实现精神与肉体,理想与现实的和谐,达到一种整体的平衡。
通过与亚里士多德悲剧美学的比较,发现中西悲剧美学确实存在可沟通指出,并且折射悲剧美学具有跨越民族的普适性。同时,在比对中也发现王国维“第三种悲剧”所具有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悲剧美学的独特美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凡人主义之人生旨向
所谓第三种悲剧,即“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第三种悲剧是针对前两种悲剧提出的,第一种悲剧是由坏人使坏造成的,第二种悲剧是盲目的行动导致的。而第三种悲剧既没有极恶毒的人陷害,也没有遇到像西方悲剧那种夸张地灾难,它只是描写普通的人普通的境遇常规的隐痛。王国维认为,第三种悲剧之所以感人至深超过前两者,就是因为它不是偶然的例外的,而是人生固有无处不在的。这种悲剧,以一种合理存在的方式足以破环人生的福祉,而这种破环却得不到救济,反而以冠冕堂皇的合理性加诸其它人不断地蔓延成为人生不可组成部分。所以这种悲剧写得是普通人,在人生洪流中非善非恶拥有人的复杂性大众化的人。这种人物设置显然有别于亚里士多德选取的悲剧人物,像俄狄浦斯是人中之精英,是有缺陷的人中人。
其一、安于现状之心灵开解
两种人物的设置的区别,反映悲剧精神追求的指向的差异。亚里士多德悲剧人物是非常热衷于精神追求的,但是精神追求本身不是目的,而为了实现人的理想渴望挖掘人的潜能的生命力促使它们在面对信念时义无反顾。即便遭到灭顶之灾也在所不辞,因为他们坚信,对人而言,还有比肉身更重要的就是信仰,肉身是短暂的,而信仰是永恒的。王国维悲剧人物的思维方式则是把视点落在现世人生上,人生才是人的全部,而人身则是人生的主体,没有身体的保存,其它皆是虚无飘渺的。所以,在面对困境之时,王国维反对那种过激的追求更排斥身体的损坏。他之所以提出解脫之道,主要是考虑缓解人在生活中的各种痛苦,同时也为疏通精神的郁结。这样就保存了肉身与精神的平衡,保持了人的完整性,更多追求的人生的情绪,而不是纯精神的信仰。
其二、冥思苦想之自悟自救
亚里士多德悲剧人物特别注重行动性,理想不是停留在心里层面,它更多是促使人物义无反顾行动的原动力。即便行动存在代价和风险,但是也阻碍不了自主选择的步伐。行动彰显的是一种的一种自主能力,为充分验证自我的存在感,必须在行动中脱颖而出。王国维的悲剧美感恰恰走了另外一个路径。正是浓烈的人生意识,所以不会轻易去追求人的完整性理性而毁灭人真实存在的完整性。所以,在行动面前小心谨慎,甚至通过以静制动的方式保持现实与理想的平衡。这不代表无作为,因为无作为还没有解决人生中人的精神困境。王国维认为,人的精神力不在于用精神指导行动,而在于精神的自我疏解,当精神的郁结被打开,精神就获得了自由,这种自悟自救的方式最终使人的存在就呈现一种圆满。
参考文献
[1]聂振斌.选编《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王国维卷》浙江大学出版社 第121页.
作者简介
金永芝(1981-),女,蒙古族,内蒙古。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艺术美学。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