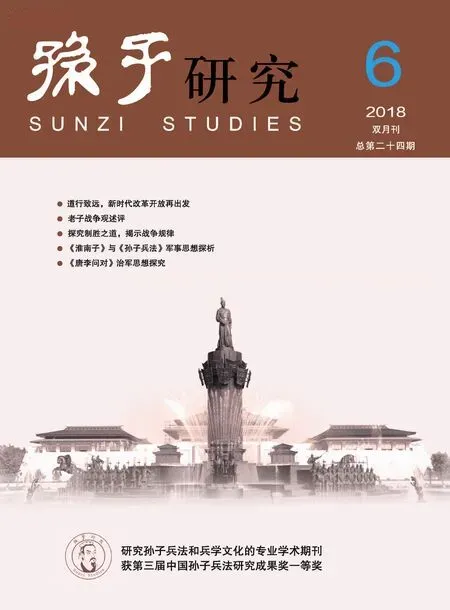“救国之道”
——胡焕庸的国防地理研究
2018-06-21朱梦中
朱梦中
说起胡焕庸,人们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大概多是著名的“胡焕庸线”,而非胡焕庸其人。确实,胡焕庸教授于1935年提出的这条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早已成为中国地理学最广为人知的概念之一①2009年,在由中国地理学会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联合发起的“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评选活动中,“胡焕庸线”当选为30项大发现成果之一,详见Great geographical discoveries of China in 100 years. Chinese National Geography, 2009, 10。,近年来更是由于李克强总理提出的“胡焕庸线能否突破”之问而再度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以致作为学术成果的“胡焕庸线”似乎已经完全盖过其提出者本身。②据笔者在中国知网的搜索,自2014年至今(截至2018年10月),以“胡焕庸”为主题的文献共有159篇,而以“胡焕庸线”为主题的则有151篇。
对“胡焕庸线”的集中关注固然说明这一学术成就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但另一方面也容易使我们忽略胡焕庸在其他学术领域的贡献,甚至只知其言而不知其人。实际上,胡焕庸不仅在人口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领域卓有建树③近来有学者开始重新发掘胡焕庸在经济学领域的成就,见孙大权《中国经济史学的新探索——民国经济学术史中的胡焕庸》,《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他的国防地理研究同样值得重视,但遗憾的是学界对此尚无人关注。④对胡焕庸及其学术成就的介绍和研究论著主要有:金祖孟《胡焕庸教授地理工作六十年》,《人文地理》1989年第3期;金祖孟《胡焕庸教授传略》,《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1年第3期;徐铭东《胡焕庸教授——中国人口地理学之父》,《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吴传钧《胡焕庸大师对发展中国地理学的贡献》《人文地理》2001年第5期;单树模、金祖孟《中国地理学家、人口学家——胡焕庸教授》,《钟山风雨》2002年第3期;唐博《胡焕庸与神秘的“胡焕庸线”》,《地图》2011年第4期;胡建中《梅花香自苦寒来——纪念先父胡焕庸教授诞辰110周年》,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印制,2011年。但上述文献尚无一篇提到胡焕庸的国防地理研究,甚至连胡焕庸本人在《治学经历述略》(《中国科技史料》1991年第1期)一文中对此也没有提及。笔者认为,胡焕庸的国防地理研究是其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认识胡焕庸不可或缺的内容。本文即旨在对胡焕庸的国防地理研究作一梳理与回顾,以期为全面认识胡焕庸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胡焕庸的国防地理研究主要出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而尤集中于抗战时期,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是抗日战争的产物,即胡焕庸对救亡图存的紧张局势所作出的一种回应。但若要全面认识胡焕庸的国防地理研究,我们必须将其置于胡焕庸本人的学术脉络中去理解。要而言之,国防地理研究不仅是胡焕庸地理学术的有机构成,更是他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治学思想和爱国救国之心的重要体现。
一、其来有自:经世致用与胡焕庸国防地理思想之形成(1919—1930)
1919年,胡焕庸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①1920年扩建为东南大学。文史地部。次年,留美归国的竺可桢来校任教,创建了闻名后世的地学系,并先后组织创办《史地学报》《史学与地学》《地理杂志》等刊物,使东南大学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地理学的一大重镇。耳濡目染于如此良好的学术环境,胡焕庸很快就崭露头角,开始积极在各种刊物上发表文章,并逐渐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治学目标。
(一)对时局与政治的关注
胡焕庸的大学时代,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紧张的国际形势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年轻的胡焕庸展现了极大的爱国热情,他自治学之初即表现出对时局与政治的高度重视,这从他撰写和译述的《华府会议之目的与限制军备》②《时事月刊》1921年第10期。、《欧战大事记》③《史地学报》1921年第1期。、《日本之海上政策与殖民政策》④《史地学报》1922年第3期。等文章中可见一斑。如他译述原载于美国“The World’s Work”杂志的《日本之海上政策与殖民政策》一文,目的正在于警示国人对日本的扩张政策予以重新认识。他在文中指出,“吾国人每以日本地小,人满为患;不知日人之图扩展,意别有在”,日本之所以大力推行海上政策、扩张海军,绝非因为本国“人口过庶”,而是作为施行帝国主义殖民侵略计划的前奏。
胡焕庸强烈的现实关怀是与东南大学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分不开的。当时的东南大学集中了大批留学归来的青年专家学者,对国际时事和学术前沿都保持着密切关注。自1922年春起,在竺可桢的指导下,胡焕庸与同窗张其昀、王学素、向达等人开始着手翻译美国地理学家鲍曼(Isaiah Bowman)的《新世界》一书⑤后署名《战后新世界》出版,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详细介绍了“一战”后的世界政治地理及各国疆界的变迁情况。可见,东南大学的学习经历不仅奠定了胡焕庸的学术基础,也使他逐渐形成了关注时局政治的治学倾向。
(二)从西方地理学中汲取养分
胡焕庸的地理学思想一开始就打下了深刻的西学烙印,他源源不断地从西方现代地理学中汲取养分。试观他大学期间发表于《史地学报》上的《读书录:各国历史所受地理之支配》⑥《史地学报》1922年第4期,1923年第2、3、5、6期。、《新书介绍:“美国国民史”The History of American People》⑦《史地学报》1923年第3期,1924年第1~8期。、《新书介绍 :“新地理”NewGeography》①《史地学报》1923年第3期。等一系列文章,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思想源泉。1926年,胡焕庸赴法国巴黎大学地理系和法兰西学院地理系进修深造。在留学期间,除了在课堂内外刻苦研读,他还利用各种机会到欧洲各地进行考察游学,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地理学最先进的学术理念。这段难得的求学经历对胡焕庸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也造就了他的第一个学术高峰。从1928年起,他先后发表了《约翰白吕纳之人生地理学》②《地理杂志》1928年第1期。、《法国研究地理学之近况》③《地理杂志》1928年第3期。、《巴黎地理教育》④《史学与地学》1928年第4期;《地理杂志》1929年第3期。、《西洋人文地理学晚近之发展》⑤《地理杂志》1929年第3期。、《欧西各国之地理学》⑥《地理杂志》1930年第4期。等一批重要文章,在中国现代地理学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浓厚的一笔。
在对西方地理学的长期研习中,胡焕庸逐渐奠定了以人地关系为核心的地理思想。⑦吴传钧:《胡焕庸大师对发展中国地理学的贡献》,《人文地理》2001年第5期。他的国防地理思想正是直接来源于此。身临西方地理学学术中心的近距离观察,使胡焕庸深刻认识到地理学与政治、军事等领域的密切关系。长年的战争推动了西方地理学的迅速发展,而地理学的进步反过来也被广泛用于政治和军事目的。他对法国的地理学有如此描述:“(法国)研究地理,有大学为其中心,学会为之辅助,惟国家行政各部,如陆军部,海军部,农部,以至殖民部,外交部均与地理有密切关系,学者研究,须取材于各机关,各机关行政,亦必受专家之指导。”“陆军部设陆军地理局,主之者多军界中人,其职责在制作详细而正确之各地地形图,以供军用。”“局中且常与学术界联络”并“特设地理工作中央委员会,加入者多地理学家,襄助其事”。⑧胡焕庸:《法国研究地理之近况》,《史地学报》1928年第3期。在《西洋人文地理学晚近之发展》一文中,胡焕庸详细介绍了西方政治地理学的研究现状,指出“政治地理,乃一种地方政治景色之研究,其内容当分三部:一行政中心,如国都省会,二国界,三国防线与国防地”,而作为政治地理别支的军事地理,则是“以专门地理学家分析战事的地理关系”。他列举了约翰生、鲍曼、雷次儿、白吕纳等著名地理学家的政治地理研究,认为政治地理的研究对象“有一国国力之基础,和平战争之财源,国家防线,海上交通,以及民族生活之地盘诸端,皆国计民生之大本也”⑨胡焕庸:《西洋人文地理学晚近之发展》,《地理杂志》1929年第3期。。
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防地理或曰军事地理,是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分支而被“西游取经”的胡焕庸注意到的。
(三)经世致用——“我国地理学家之责任”
在胡焕庸看来,地理学是一门有用于世的学问。他深受法国地理学派的影响,认为“举凡人生衣食住行,乡村都市之盛衰,国家社会之兴替,一切须在地理状况中研究其所以然,然后求取立身处世治国平天下之准则”,因此,地理学是“民生日用,定国安邦,必不可少之科学”,是“人人必修之科学”。地理学如此重要,地理学者自然应肩负经世致用的重任。胡焕庸选择地理学为自己的志业,正是希望以此作为自己“学术报国”的路径。
需要指出,胡焕庸对学术与政治关系的认识是客观而理性的。在他看来,学术与政治二者相辅相成,互相影响,而地理学因其本身的实用性与现实性等学科特点,长期被视作政治的工具。他曾指出,政治地理“以其与实际政治关系太密,故治之者每不免杂有爱国私情,其研究结果,因亦视人而异。如所谓‘自然疆界’、‘地理单位’诸说,被人利用,多少国际纠纷,由之而起”。既然学术与政治的纠葛难以避免,那么一位有责任心的学者就应该正视这种关系,并尽可能地发挥学术对现实和政治的正面作用。正因为“外国地理学家多为帝国主义侵略之领导”,所以“我国未来地理学家之责任,当从解放中国所受不平等束缚始”,“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也。一般被侵略之民族,不思解脱侵略者之羁绁则亦已矣,如欲解脱侵略者之羁绁者,当自研究政治经济地理始”。因此,“我国今日研究地理,当从解除国际对我国不平等束缚,向边境移民,及收回失地诸问题着手”。学术的进步离不开国家社会的重视和帮助,为此胡焕庸呼吁“我国欲求学术进步,亦当自政府学界携手始”。①胡焕庸:《法国研究地理之近况》,《史地学报》1928年第3期;《西洋人文地理学晚近之发展》,《地理杂志》1929年第3期。
由上可见,胡焕庸的国防地理思想虽然并非一开始就独立存在,但其来有自,它是胡焕庸地理学思想的一条支流,与他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经世致用思想相伴相随。当战争来临、国防危机成为国家的重中之重时,这条涓涓细流逐渐汇成了波澜壮阔的大河,焕发出澎湃的力量。
二、“救国之道”:抗日战争与胡焕庸的国防地理研究(1931-1945)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的帷幕从此拉开。日蹙紧张的局势时刻牵动着胡焕庸的神经,并深刻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为了响应抗日救国,其时兼任苏州中学校长的胡焕庸立即在其主编的《苏中校刊》上开辟了一期“反日救国专号”,号召全校师生同心协力,奋起救国。在“弁言”中,他慷慨激昂地写道:“自暴日强占东省以来,全国奋激,反日运动,风起云涌。文字之宣传,亦已弥漫全国,自而我校犹复不惜楮墨,以追随于出版界者,岂为趋时以迎合潮流乎?抑非此不足以示我反日之忱乎?非也,亦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以共谋救国之道而已。”②胡焕庸:《反日救国特刊弁言》,《苏中校刊》1931年第57、58期。其爱国救国之心跃然纸上。为躬先表率,胡焕庸以地理学作为自己的“救国之道”,开始迈向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高峰。
从1931年到1945年间,胡焕庸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的地理学论著,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乃至时局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宏观地看,他的论著范围比较广泛,包括地理教育、气象学、人口地理、经济地理、区域地理、国防地理等③吊诡的是,以往学界有关胡焕庸学术成就的研究,对其在地理教育、人口地理、经济地理和区域地理等领域均有提及,但对他的国防地理研究没有任何相关论述。,但提纲挈领地说,“经世致用”始终是贯穿其中的核心思想。他力倡地理教育,目的在于唤醒国人对祖国的认识与热爱,进而为国家民族做贡献;他的经济地理研究,侧重于水利、盐务、垦务、人口分布与农业区域这类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主题,以资引起政府的重视;他的区域地理研究,不仅注重介绍国内各地区的人地关系,也紧密关注不断变迁的国际政治军事形势。而在这些领域之中,国防地理研究则是他经世致用思想及其“救国之道”最为集中的体现。
据笔者统计,胡焕庸在1931—1945年间一共发表论著约200种,其中有关国防地理的论著约60种,在其发表成果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尤其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一比重大为增长。通过以下图表①据胡建中编“胡焕庸教授著述目录”(《梅花香自苦寒来——纪念先父胡焕庸教授诞辰110周年》,第158~166页)、“全国报刊索引”、超星等学术平台数据绘制。由于时代和资料所限,吴传钧在《胡焕庸大师对发展中国地理学的贡献》一文中所制作的“胡焕庸著作分类统计表”数据多有误差。如他认为从1937—1949年,“由于环境不安,又缺乏发表条件”,胡焕庸平均每年仅发表1.3种。但实际上的数据远高于此,抗战期间是胡焕庸学术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我们不难窥见胡焕庸的国防地理研究在其学术成果中的重要地位,更能清晰地看到时局的变化如何深刻影响着他的研究倾向。
正交和反交可判断基因位于X染色体的非同源区段或位于XY染色体的同源区段。若正交和反交后F1雌性均为显性性状,F1雄性均为显性性状或均为隐形性状,则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的非同源区段,遗传图解如图1、图6所示;若正交和反交后F1雌雄均为显性性状,则基因可能位于XY染色体的同源区段上,遗传图解如图2、图7所示。

以内容观之,胡焕庸在抗战期间发表的国防地理论著大致可以分为国防地理教育、国防地理学术研究及世界局势动向三个部分。
(一)“国难与地理教育”
胡焕庸的国防地理思想首先体现在他在地理教育中对国防问题的强调。自1928年至1949年,胡焕庸主要任职于中央大学,先后担任地理系主任、大学教务长等职务,这期间还一度兼任苏州中学的校长。常年处在教育一线的胡焕庸对地理教育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心血。他认为,“学校乃教师学生研习之所;以学术相切磋,以气节相砥砺,以健康相勖勉。其教育目的,不仅为培植建设之材,以应承平之势也;一旦国家有变,挺身赴难,以戡乱除暴,为天下倡,抑亦士人所应有之素养”②胡焕庸:《反日救国特刊弁言》,《苏中校刊》1931年第57、58期。。在他看来,地理学就是这样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地理知识是每个爱国公民都应该具备的常识,而在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大力推行地理学尤其是国防地理的教育更有刻不容缓之势。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外侮日亟,国防教育逐渐被提上议程。在胡焕庸看来,地理教育应作为国防教育的核心。他认为,“就学校中实施国防教育之各科目言之,则地理一科,实可称为最重要之中心,因为各种关系国防之研究问题,实多数寄托于地理学科之内:例如国际形势之探讨;本国疆域之叙述;边地争执之形势;经济侵略之焦点;乃至一国物产之分布;交通之干道;要塞之设施;地形与战略等等,无不包括于地理教材之中”,因此“中小学任何学科,其对于国防教育之重要,无有超过于地理者”。③胡焕庸:《国防教育与中小学课程》,《教与学》1936年第7期。他强烈反对空言爱国救国的现象,在《国难与地理教育》一文中,他痛心地说道:“近年以来,疆土日蹙,外患日亟,爱国救国之呼声于是洋溢乎全境,人人竞言东北被占为国家最可痛心最为耻辱之事。然试叩问以四省之地理情况何若?四省沦陷以后对于全国所生之经济影响又何若?乃不特大多数之国民茫然无以为对,即号称领袖群众之知识阶级亦多讷讷不能作答,此犹一家之库房失窃,失主对其库房内所藏之物,乃竟不能指其名,举其数,计算其损失;一家之人,对于自家所有之物既茫然如此,则其被窃也不亦宜乎?”他尖锐地指出,“苟一国国民对于其本国地理情形尚茫然无知,又何能知其国家之可爱?更何由而救其国家?爱国救国之呼声亦徒托空言,聊充口号而已!”为此,他高声呼吁,“我国民如尚有爱国救国之真忱者,其唯一实行之法,当自研究本国地理始,当自提倡地理教育始”。①胡焕庸:《国难与地理教育》,《地理教育》1936年第3期。
胡焕庸对教育事业寄予厚望。他认为“学校之训练学生,不宜局促于一时,应作准备于将来;眼光远大,计划周详,则教育之效力,终有显著之一日”②胡焕庸:《反日救国特刊弁言》,《苏中校刊》1931年第57、58期。。但随着抗战局势的日益恶化,他的思想逐渐发生转变。1935年,日本接连制造一系列事端,华北事变爆发,国防形势急剧严峻。为了更切实地推行国防地理教育,胡焕庸提倡对地理课程进行改造,“当今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吾人讲授地理,尤当删繁就简,去芜存菁,集中时间,注重国防教材,其与国防无甚关系者,不妨暂时从略,对于政治社会随时发生之地理问题,尤须相加剖析,务使学生彻底了解,俾便应付事变”②胡焕庸:《反日救国特刊弁言》,《苏中校刊》1931年第57、58期。。
(二)国防地理研究论著述要
国防地理教育的推行固然重要,但作为一名地理学家,胡焕庸更注重能直接作用于现实的国防地理学术研究。在抗战期间,他撰述了大量有关国防地理的文章,举其重要者如下:《就政治地理立场研讨中国外交关系》④《外交评论》1934年第7期,本文作者署名“吴焕庸”,但从内容上看应是胡焕庸的作品无疑。、《国界与国防》⑤《地理教育》1936年第4期。、《国防前线之绥远现状及其前途》⑥《国立中央大学日刊》1936年第1798、1799期。、《经济侵略与土地侵略》⑦《地理教育》1937年第2期;《闽侯教育辅导》1937年第10、11期。、《川滇黔三省在国防上之地位》⑧《公论众书》1938年第2期;《民族公论》1938年第2期。、《铁路与国防》⑨《浙光》1938年第5期;《新民族》1938年第14期。、《保卫大武汉之军事形势》⑩《国是公论》1938年第4期。、《鄂东抗战形势蠡测》⑪《国是公论》1938年第9期。、《陕甘在国防上的地位》⑫《教育通讯》1939年第31期。、《宁青二省在国防上的地位》⑬《教育通讯》1940年第32期。、《西藏在国防上的地位》⑭《教育通讯》1940年第6、7期。、《新疆在国防上的地位》⑮《教育通讯》1940年第36-38期。、《国防建设与经济地理》⑯《中国青年》1941年第3期。、《地理学与国防》⑰《仙游教育》1942年第4、5期。等,此外还有《国防地理》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1938年。、《地理与国防》⑲正中书局印行,1941年。、《最新国防地理》⑳国防文化出版社,1944年,此书内容与《国防地理》一书相同。等专著,成果不可谓不丰硕。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胡焕庸正是通过上述著述作为自己“学术救国”的主要路径。由于《国防地理》和《地理与国防》两本专著是胡焕庸国防地理思想的集中体现,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二者,对胡焕庸的国防地理研究略作概述。
《国防地理》一书于1938年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是军事学校战时的政治教程之一,可见该书在当时之受重视程度。全书分“疆域”“人民”“交通”“资源”“边防”“海防”六章,深入浅出地论述了有关国防地理的方方面面。《地理与国防》则由胡焕庸在抗战期间撰写的一系列国防地理文章集结成书,全书分为“国界与国防”“川滇黔三省在国防上之地位”“西康建省的意义”“西藏在国防上的地位”“陕甘在国防上的地位”“宁青在国防上的地位”“新疆在国防上的地位”七篇,并附录“中国西部地理大势与公路交通建设问题”一章。要而言之,胡焕庸的国防地理研究可分为以下几方面内容:
(2)统筹全局的国防观。随着日军的侵略逐步加剧,中国的国土不断被侵占,胡焕庸对此焦虑不已,强烈的爱国心促使他对中国各地区在国防上的地位进行了重点研究。从东北、绥远、武汉,到川滇黔、陕甘宁青、新疆西藏,胡焕庸对全国各地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国防地理考察。他始终以一种统筹全局的整体目光来审视各地区的国防地位,在他看来,各地区之间是唇齿相依、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这一点在他论述陕西的国防地位时有明显体现,他指出,“陕西的地位,东面靠着山西,北门接着绥远,在目前的抗战阶段之中,已经是国防前线的省区;再加东沿陇海铁路,可以直趋洛阳、郑州,西出西兰公路,可以直通甘肃、新疆;南下栈道,可达四川;东南顺汉水而下,可以直趋武汉”,因此,“山西是西北的门户,也是接通中原和西南的锁钥,地位的重要,于此可以想见”。胡焕庸写作此文时,日军已侵入山西达一年之久,陕西成为国防前线,故他一再强调坚守陕西的重要性:“守陕西,所以保西北,陕西失,则甘肃新疆即不可保;守陕西,所以保西南,陕西失,则西北与西南的联系即不易维持;守陕西,所以保山西,陕西失,则山西的接济,即无法供给;守陕西,所以保河南,陇海路上,我们的前卫,还在郑州以东,要是潼关西安有意外,那末河南的形势,即不易维持;守陕西,所以保湖北,陕西湖北之间,以汉水为一大动脉,顺汉水而下,可以直趋武汉,规复下游”。②胡焕庸:《地理与国防》,正中书局印行,1941年,第40~45页。
(3)国防与经济统一、抗战与建国并重。胡焕庸认为国防与经济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国防地理与经济地理则是抗战建国最重要的知识基础。他鲜明地指出,“我们现在要谋抗战建国,当以军事和经济并重。开发经济,在求支持抗战;努力抗战,在求保障开发”①胡焕庸:《地理与国防》,正中书局印行,1941年,第51页。。在他看来,“一切经济物质,多是产生于地,民生日用的东西,固靠地来生长,强国胜敌的方法,也靠地来运用;我们谈抗战谈国防,要是离开了地,离开了经济,那都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因此国防计划实际上“就是一部经济建设方案”“我们要想开发经济,建立国防,经济地理的研究,确是最重要的基础”。②胡焕庸:《国防建设与经济地理》,《中国青年(重庆)》1941年第3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胡焕庸以国防地理和经济地理作为自己研究的重心,在论述国防地理时特别注重对经济地理尤其是与国防直接相关的粮食、衣料、矿产、交通等资源的介绍,而在经济地理研究中也极为重视对于国防及生产建设的作用。
(4)人力重于地利,追求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人地关系是胡焕庸地理思想的重要核心,在国防地理研究中,他高度重视人力对地利的经营与利用。如他在论述西藏在国防上的地位时,指出“西藏是我们西南方面最大也是最好的一个屏障”,但“我们不能老以喜马拉雅可作天埑,因此永可高枕而卧”“西藏高原,喜马拉雅山减少些外力内侵的机会则有之,要说他是天埑,不加人力经营,永远可作国家保障,那是没有的事”。因此对于西藏,我们绝不可听其自然,而务必积极经营开发,“应该从速改进现有的交通”“加紧西藏对于内地的联系”。③胡焕庸:《地理与国防》,正中书局印行,1941年,第35~39页。胡焕庸并非只是纸上谈兵,他尤其注重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常基于自己扎实的地理研究对政策提出客观理性的建议。如他谈西康建省的意义时,在详细论述了西康的自然环境、资源状况、人口民族等问题后,指出“西康现在的情形,可说是地瘠民贫,交通既不便,产业又不发达,宗教势力太深,民知不能开发”,对此他提出了自己关于建设西康的种种建议:“第一,当于全省各地,举行精密考察,以为一切建设的根据,不要草率从事浪费精力。第二,当于康定及早设立较高级之人才训练,学术研究,以及技术试验之中心设备,以为一切施政之指南。第三,应当努力举办语文教育,消除民族隔阂,增加开发效力。第四,厉行廉洁政治,实施经济开发,以完成新西康的建设事业。”④胡焕庸:《地理与国防》,正中书局印行,1941年,第20~30页。
(三)从中国看世界:对世界局势动向的关注
胡焕庸自治学之初即对时局政治高度关注,在抗战期间他更进一步撰述大量关于外国地理的专著,密切注意世界局势的新动向。正如胡焕庸所言,“中国与世界不可分,世界与中国亦不可分,欲谈中国问题,必与世界问题联系”⑤胡焕庸:《世界经济与战后中国》,《民主评论》1945年第2期。。在世界已联为整体的20世纪、在以政治和战争为最大主题的特殊时期,实有必要对世界给予更多的重视和认识。胡焕庸的《太平洋问题》⑥《苏州振华女学校刊》,1933年4月。、《法日觊觎之南海诸岛》⑦《外交评论》1934年第5期。、《日俄交恶声中之西伯利亚》⑧《外交评论》1936年第4期。、《德奥合并以后》①《新民族》1938年第6期。、《世界经济地理》②青年书店出版社,1939年。、《欧洲大局与未来世界》③《中国青年》1939年创刊号。、《苏联经济概况与最近发展》④《中国青年》1939年第4期。、《最近苏联外交的检讨》⑤《中国青年)》1939年第4期。、《中国与苏联》⑥《青年中国季刊》1939年创刊号。、《太平洋形势展望》⑦《新民族》1939年第12期;《沙磁文化月刊》1940年第1期。、《世界经济与战后中国》⑧《民主评论》1945年第2期。等一系列论著,虽并非专门的国防地理研究,但体现的恰是他对中国国防形势与世界变局关系的宏观观察,因而可视作他国防地理研究的延伸。
需要指出,胡焕庸对世界局势和动向的关注始终是以中国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如他讲述“欧洲大局与世界未来”,并非“想讲欧洲大战何时发生,大战之后,谁胜谁负”,而是“就地理历史两方面的要素,来分析欧洲的现局,同时还想从欧洲的过去,很概括地推测世界的未来,并且从这未来的世界之中,约略推测我们中国的前途”。⑨胡焕庸:《欧洲大局与世界未来》,《中国青年》1939年创刊号。再如他对苏联经济发展的考察,意在阐明其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模范作用,“我国地大物博而人稠,农牧林矿,无一不丰,有优越之天然禀赋,自然条件不让于苏联,以苏联十年之经济检核,其成就已可惊人,吾人当知所取法矣”⑩胡焕庸:《苏联经济概况与最近发展》,《中国青年》1939年第4期。。可见,“中国”始终是胡焕庸学术研究最重要的底色。
三、余论
1945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最后胜利。此后,胡焕庸还陆续写了《日本领土应如何处置》⑪《社会公论》1947年第1期。、《对日和约与对日通商问题》⑫《问世》1947年第3期。、《从对日和约谈到日本前途》⑬《问世》1947年第7期。等文章,他的国防地理研究也渐入尾声。然而短暂的和平后,风云再起,中国再度陷于战争之中。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后,胡焕庸积极地投入到祖国的经济建设浪潮中去,继续以其地理学的知识为国家做贡献。
遗憾的是,胡焕庸的国防地理研究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了,需要追问的是,胡焕庸的国防地理研究何以会被忽略?最大的原因或许在于国防地理研究本身的“时效性”,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以抵御外侮、救亡图存为目的,其生命力亦随着战争的盛衰而荣枯。到20世纪40年末,胡焕庸的国防地理研究逐渐告一段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国家建设取代国防危机成为时代的新主题,胡焕庸遂将学术重心转至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水利地理研究中去,继续践行自己的“报国之道”。长此以往,他的国防地理研究逐渐“退居幕后”,乃至被最终遗忘。而从更宏观的学术史角度看,这种遗忘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学术热潮被忽视的一个缩影。在抗战期间,中国学术界曾涌现出一大批关于国防地理的论著,形成了一股澎湃的时代思潮。可惜的是,它在相关学术史的回顾中也长期被忽略了。
显然,对胡焕庸国防地理研究的忽视是不合理也是不应该的。它不仅是胡焕庸学术成就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它映照着一个学者真实而鲜活的形象,透过这些沉重热忱的文字,我们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在那个动荡时代下一个以救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赤子之心,同时看到时局与政治如何对学术研究产生着深切的影响。因此,我们实有必要对胡焕庸的国防地理研究予以重新整理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