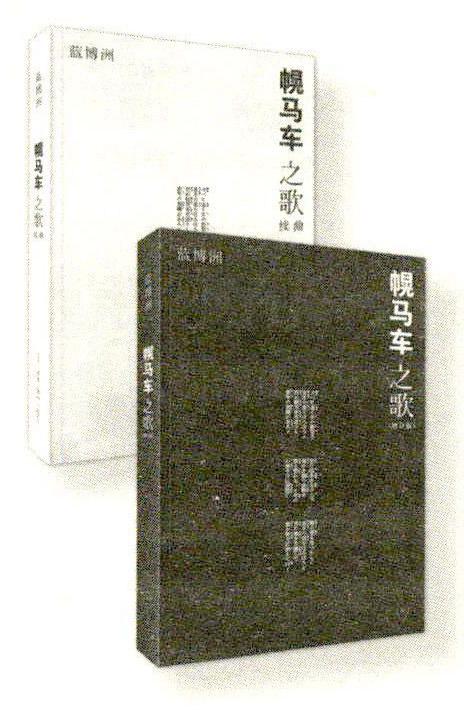“翰档”之憾
2018-06-09王中忱
王中忱
一、备受尊崇的冷遇:陈翰笙学术遗产的当下境遇
享年一百零八岁的陈翰笙(一八九七年二月五日二00四年三月十三日)一生跨越了三个世纪,其晚年的自传题名《四个时代的我》,本为平实描述,却令人顿感沧桑。即使只作为一个历史的旁观者,“阅尽人间春色”的经历亦已弥足珍贵,而陈既是一个怀持共产主义理念且自觉践行的革命家,又是一个在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亚太区域历史、政治与外交关系等领域都留下了开拓性研究业绩的渊博学者,爱泼斯坦说“他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出现在革命蓬勃发展的年代,而且是个敢于将自己的先进思想付诸行动的人”,这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陈翰笙所参与的实际革命活动,有相当一部分处于隐蔽战线。据他的学生潘维转述,陈曾说:“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参与者的缄默、档案的缺失和秘藏,都为重新复原历史面貌增添了巨大困难。虽然包括陈翰笙本人在内的一些历史当事人晚年曾披露过一些片段,一些研究者也做了发掘和考辨,但陈翰笙的“地下工作”全貌还远远没有得到呈现,一些重要的环节仍不知其详。比较而言,作为学者的陈翰笙得到了更多关注,据叶恒《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陈翰笙研究综述》一文所载,自一九八五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纪念陈翰笙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座谈会以来,至二00五年为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和中国太平洋学会为陈翰笙召开的座谈会、纪念会、学术会和追思会至少有五次”。如果加上二0一七年五月由数家学术机构联合召开的“纪念陈翰笙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暨陈翰笙学术思想研讨会”,可以说,对陈翰笙的学术纪念活动一直在持续进行。与此同时,有关陈的学术工作的研究论著亦陆续出现,尤其是他所主持创建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被公认为同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如龚育之所说:陈翰笙是“载入了党的史册”的人物,这当然是不同于一般学者的殊荣。
但不必讳言,在“后革命”的氛围中,陈翰笙也由此被贴上了“革命”的标签,从某种意义上便意味着被视为陈旧之物,至多是已经过时了的“正论”。即使是有意识基于陈翰笙的乡村调查继续展开研究的学者,也在把陈的成果归为“用‘革命史范式撰写的乡村史”的前提下,认为此范式已“遭到越来越多的诟病,逐渐从史学界淡出”(参见汪效驷:《江南乡村社会的近代转型——基于陈翰笙无锡调查的研究》);还有学者把陈翰笙称为“分配学派”,并在将之与以卜凯为代表的“技术学派”进行比较时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之后,中国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农业生产成了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此时陈翰笙‘分配学派的见解则时过境迁,而卜凯‘技术学派的观点却颇具参考价值。”(参见张婷:《“技术学派”与“分配学派”民国农村经济落后根源之争》)于是,陈翰笙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农村派”便陷入了这样的境遇:虽经常在历史纪念的意义上被不断循例提起,却很少被纳入到当下学术生产的场域和脉络,这恰恰和他们曾经的论争和批判对象——各种立于改良立场的中国乡村论述——在现今学界不断被作为具有再生产能力的话题重新提起的热闹景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给陈贴上“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标签本身并无不妥,问题主要在于这种贴标签方式最易让人们以为陈的农村研究只是为了证实现成的“主义”。这其实是对其研究的简单化理解。如所周知,陈翰笙一九一五年留学美国,先后在波莫纳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历史学专业就读,后转到德国柏林大学,《四个时代的我》里提到当年选修的课程,有美国宪法史、埃及古代史、世界经济等,大都在今天一般所说的“世界史”或“全球史”范围。一九二四年陈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讲授欧美通史、美国宪法史等课程,在此期间,受李大钊影响,开始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间,陈翰笙在苏联任共产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的研究员,接触有关中国社会性质、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的论争,受到刺激,遂决意回国“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并在一九二九年应蔡元培之聘任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后付诸实施。陈执笔撰写的社研所社会学组一九二九至一九三0年的年度报告,既是阶段性工作小结,亦带有阐述研究宗旨的性质。该报告曾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为题单独发表,开篇即云:“社会科学中有两种重要科学,非专究社会生活某一方面如经济、法制、宗教等等,而以至周密之方法整个观察社会生活之全部者。此即史学与社会学也。”结合前述陈的求学经历和学术历程,不难看出,由史学而社会学,并在总体观察社会生活之点上,使二者交错融汇,既非突然生出的奇想,亦非随风逐潮之举,实为其多年知识积累和学术探索的自然结果。
《发轫》叙述陈所组织的农村调查,强调从“复杂之田权与租佃制度”以及“雇佣制度、农产价格、副业收入、借贷制度”等要素入手,显然出自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论的观察视点,同时也未惮言借鉴马克斯·韦伯、保罗·维诺格拉多夫等欧洲学者“关于欧洲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成果。与《发轫》同样刊行于一九三。年的《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可能是陈翰笙为自己也为相关调查人员写下的一份工作指南,文中广泛征引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欧洲和苏联、日本学者关于封建社会农村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归类,从中提出“赋役制”“强役制”“工偿制”三种类型,并对每种类型的特征给予细致的规定。不过,陈翰笙编制此索引式手册,并不是要在中国寻找相类似的样品,而是因为在他看来,这几种制度在当时的中国“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可是绝不占农村生产关系的主要地位”。曾经直接受到陈翰笙指导的陈洪进说:“封建主义的生產方式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方式,全世界究竟有多少模式,时至今天,也还没有定论。当时,我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理论指导,作为实地调查的指南,但不能沉湎于这样的理论探讨。陈翰笙的这项研究,在某种意义上类似化学家门捷列夫在一八六0年所写的《元素周期表》,把确知的元素,按原子序数排列出来,以便把后来发现的元素排列在适当的位置上。因为纯理论的科学研究不是当时生灵涂炭的国家所能进行的。”可谓恰当地说明了陈翰笙的农村研究和国际学术界相关研究的联系和区别。陈有意识地把中国农村研究放置在全球史的视域,他和他的团队通过实地调查发现的新“元素”,无疑会和国际学术界已有的“通说”或“定论”构成有力的对话,但这并不是他们的目的所在。进一步说,陈翰笙团队农村研究的创造性贡献,甚至主要不在于论证了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而在于提供了体现着“性质”而又不能完全还原于“性质”的丰富生动的实际类型,以此为构想改造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的实践道路提供了依据和参照。
现在无疑早已具备了深入探讨陈翰笙们通过调查获得的新“元素”之理论内涵的条件,而必要的前提自然是整理他的学术遗产。提及这一话题,却不能不遗憾地说,备受尊崇的冷遇,也同样体现在陈翰笙著作的整理和出版上。几篇介绍他学术生涯的文章谈及他的著述,或说其“撰写的专著和文章约四百多种”(《(陈翰笙集)编者的话》),或说其“全部著作不下二百种”(《“中共对美外交第一人”辞世》,《瞭望周刊》记者程瑛、胡奎撰稿),说法不一,且都有些含糊其辞,应该都不是基于严密的调查统计。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版的几部陈翰笙著作集,无论书名称“文集”还是“选集”,其实都只是一卷本的容量,所收内容和一般所说的几百种数量颇不相称。
陈翰笙去世后,于光远曾呼吁:“需要有几个有志于长期研究陈翰笙历史和思想的人,写出篇幅大的《陈翰笙传》来。”
二、《四个时代的我》:一部需要详加考订和注释的回忆录
要写出一部严谨可信的陈翰笙学术和思想传记,或者编印全面收录陈翰笙著述的文集,当务之急也许首先应该是编写出一部详尽可靠的著作目录或年谱长编。由于陈涉足的领域广泛,其著述散见于国内外,有些文本的形成过程复杂,如何辨识和厘定,其实也并非易事,需要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分专题考察和跨学科合作,从最基础的整理工作扎实做起。
在此仅以陈翰笙的晚年回忆录《四个时代的我》为例,探讨整理其著作的难度和应采取的态度。此书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陈翰笙的回忆录,一部分是陈的友人和学生所写的评论和介绍文字。比较而言,无疑是陈本人的回忆录部分更值得珍视,这是陈翰笙唯一一部系统讲述自己人生经历、革命活动和学术研究的作品。作为一部回忆录文本,《四个时代的我》也有其局限,需要参照相关史料加以考辨检证。
首先应了解这部文本的形成过程。任雪芳在《我所认识的陈翰笙教授》一文中说:“一九八四年春天,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朋友邀请我参加陈翰笙传的撰写工作,使我有机会连续三个月,每周两个半天坐在翰老身边,听他娓娓动听地讲述他那坎坷、传奇的人生之路。后由于一些原因,传记的撰写工作停顿下来。我十分着急,认为写翰老的传记,不是单为他个人树碑立传,而是通过传记,反映出他所处的那个波澜壮阔的革命时代。因此,我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一九八八年完成了陈翰笙传——《四个时代的我》,并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张椿年、陆国俊主编:《陈翰笙百岁华诞集》)按照任的描述,《四个时代的我》是由陈翰笙本人讲述,由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任雪芳记录整理而成的,全书采取第一人称的叙述口吻,确切地说更近似于一部口述实录。
据《四个时代的我》所述,陈翰笙自一九六九年下放干校劳动时患眼疾,至一九八三年几近失明,而那时他承担多项学术领导工作,又指导多名研究生,无暇或无意集中精力撰写自传,也无力多方查核史料对任、陈二人的笔录稿进行订正补充,则都在情理之中,而正因如此,最后形诸文字的《四个时代的我》便难免存在缺憾:或事件叙述过于简略,或史实抵牾错漏。在此仅举两例。
(一)有关陈翰笙和史沫特莱见面的时间。《四个时代的我》之“为革命不避风险”一节这样写道:“一九二八年她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身份来到中国,是由德国共产党员尤里安·古姆佩尔茨介绍来的。我到上海不久(大约是一九二九年二月),就在宋庆龄的住处认识她了。”这段文字当然是了解陈翰笙和史沫特莱交往的重要资料,但其中所说两人最初相见的时间却不够准确。据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所述,她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经由苏联来中国,一九二九年一月到达哈尔滨,不久到沈阳,“在东北住了将近三个月”,到南京时“正赶上国民党召开代表大会”。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九年三月在南京召开,史沫特莱到达南京应在此期间。
史沫特莱还写到前往中山陵参观途中和官方指派的翻译官谈话时曾提及“孙夫人”,明确说她现在“流亡”在外。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八日,宋庆龄到达北京,六月一日在南京参加为孙中山举行的国葬仪式,当晚即回上海,同年九月二十一日又为孙中山铜像事赴法国……综合这些因素,不难判断,陈翰笙在宋庆龄的上海寓所和史沫特莱的最初相遇,不可能在“一九二九年二月”,而只能在一九二九年六月二日之后至九月二十一日之前。
(二)任职中央研究院时期的人与事。陈翰笙对中国农村开创性的调查和研究,是在他应蔡元培之聘就职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并主持该所社会学组工作之后得以实现的,开始的时间在一九二九年春。据《四个时代的我》之“三十年代的农村调查”一节所述:“我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虽然蔡元培先生自己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但所内的具体工作,全部放手让我主持,他从不干扰。”而关于农村调查工作的受阻乃至最后调查人员被迫星散,包括陈本人的辞职,在回忆录里主要归咎于傅斯年。回忆录写道:“傅斯年和蔡元培很接近,却对我抱有成见,常在蔡先生面前讲我的坏话……傅斯年并不罢休,又故意提议将社会科学研究所搬到南京去。由于他在国民党中有关系,蔡元培、杨杏佛拗不过他,社科研究所于一九三三年四月搬到了南京鸡鸣寺。”“社科研究所迁到南京两个月,即发生杨杏佛被刺的事,这之后,傅斯年又对研究所工作横加干涉,对我下面的工作人员继续排挤,第一个被开除的就是钱俊瑞。我很气愤,预料到傅斯年还会压迫我们,因此我们就一一设法离开了。”
陈、傅二人不僅政治立场不同,学术研究取向也大有差异,只要把陈翰笙撰写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和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对比阅读,即可一目了然。陈企望通过“有意识有组织之农村经济调查”,探寻“根本解决农村经济问题”之途径,主要是从“民”的境遇着眼,而傅强调以近代历史学和语言学为工具,“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科学客观)”,从而和西方的东方学争胜,实现“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目标,则更多是从“国”的地位出发。陈与傅并非同路之人,当无疑义。但陈所述傅对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干预,也不无令人困惑难解之处。傅斯年当时的职务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而史语所当时设址于北平,说他向蔡元培讲“坏话”尚有可能,但他为何能够干涉社会科学研究所迁址乃至人员的聘用?以其当时位置,究竟能够干涉到怎样的程度?对这些问题,回忆者当然可以从自己的感受去臆测,研究者欲确认史实,则需有相应的史料予以佐证。
而这样的史料是可以查找到一些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二十一年度报告》第一条述该所人事的变动,云:“至二十一年末,蔡院长因无暇兼任,特请前总干事杨铨兼代(所长);至本年四月,又改请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兼代。”中研院的《年度报告》皆于次年编制刊行,故此处所云“本年”实即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再查社科研究所《二十二年度报告》,有关所长的人事变动则云:“本年度初,本所拟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合并,故由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君副所长李济君兼任所长副所长。至二十三年四月,本所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并之议成熟,又改聘调查所所长陶孟和君任所长。”由此可知,一九三三年四月至一九三四年四月,傅斯年有整整一年时间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他能实际干预该所事务,主要应该在这一时期。
从近年整理出版的《傅斯年遗札》所收傅氏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分别写给朱家骅、蔡元培的信看,把史语所和社会科学所“合并”以及由傅斯年出任所长之议,首先出自蔡元培和时任总干事的杨铨(杏佛)。在同年二月二十一日致蔡元培、杨铨的信里,傅已经开始积极考虑两所合并的具体事宜。傅对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状况也做了分析,认为该所“民俗方面与史语所原有者本可交融,即法制、经济之但有历史意义者,亦未始不可契合,独经济、社会两端之与今日国计民生有关者,真与史语所不在一线中也”。“难处转在经济、社会一路究与史语所一路如何打成一气也”,所以建议“其經济等似必维持其独立”,或者“合并后经济的工作不发展之”。从此信不难读出,傅斯年的“合并”构想,并非两所的平等汇流,而是以能否与史语所“打成一气”为标准,凡和史语所“不在一线中”的学术,纵然不能将之拒之门外,亦计划在合并后将之搁置冻结。这样的构想,等于要把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本有的多元学术导向一元,明显有别于蔡元培秉持的“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近些年来媒体竞相讲述“史语所学术”,几乎渲染为“神话”,而当年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故事却少被提起,这不能不说是对现代学术史的一种简化。
需要补充说明,碍于中研院当时的“组织法”规定,史语所和社研所的合并未能施行,最后改为由傅斯年兼任社研所的所长。陈翰笙回忆录所述傅斯年对社会学组的打压,绝非空穴来风。不过,有关社会科学研究所迁址南京的原因,前引《四个时代的我》里的说法却未必确切。查该所《十八年度报告》,曾言及该所在上海租用的办公房屋皆为“临时性质”。而刊于《国际劳工消息》第四卷第二期(一九三三)上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概况》,对此叙述更详:“本所为将来发展计,故有自营建筑之计划,原拟在上海白利南路中央研究院新置基地,与物理化学工程等研究所合建巨厦,会以国民政府令中央研究院各机关集中首都,本所遵即勘定南京钦天山东麓隙地计划建筑。兹此项建筑已于二十年十二月全部落成。在未落成前,本所民族学经济学两组及图书馆等,已遵奉院令于二十年九月先行迁京,暂借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余屋办公。迨新屋落成,遂于二十一年一月正式迁入,四月末,复继续将上海之社会学法制学两组迁来。”据此可知,促使社会科学研究所定址南京的主要因素当为“国民政府令”,傅斯年即使从中有所作为,似乎也不宜高估。此外,据《概况》,社研所迁往南京的时间并非陈的回忆录所说的一九三三年四月。
三、“翰档”:有待利用、整理和充实的文献库
必须说,全面整理陈翰笙学术遗产的有利条件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中之一就是“翰档”——收藏陈翰笙档案资料机构——的存在。早在一九九四年,陈翰笙便将家中所存“著作、日记、诗稿、照片等赠予北大图书馆”;二00四年北京大学宣布成立“陈翰笙研究中心”(二0一四年改称“陈翰笙世界政治经济研究中心”),据该中心的“简介”,这里“收集整理了大量关于陈翰笙个人及其学术思想的文献资料,是国内外保存陈翰笙个人资料最齐全的研究机构”。而在二00四年十二月,陈翰笙的家属还曾向无锡市革命陈列馆捐赠陈的部分手稿、藏书、信件及相关物品,该馆亦设立专室陈列。无锡所藏,笔者尚未得见,而北京大学图书馆确已开设网络版的《陈翰笙档案资料库》,分类公布了陈翰笙手稿、论著、传记、采访录音、媒体报道及相关纪念文章,其中一份手写的“参考书书目”和“有关资料索引”的封面页上,题有“翰档”两字。
如果从一九九四年“翰档”资料入藏北大图书馆算起,至今已经二十多年,坦率地说,这批珍贵文献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也没有被充分利用。仅举一例:《四个时代的我》说到陈翰笙在芝加哥大学的硕士论文为《茶叶出口与中国内地商业的发展》,在柏林大学的博士论文是《一九一一年瓜分阿尔巴尼亚的伦敦六国使节会议》,但近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熊鹰女士在“翰档”查到陈翰笙提交给芝加哥大学的论文申请和论文打印稿,上面明确写着论文题目:THE CONFRENCE OF AMBASSADORS IN LONDON,1912-13,ANDTHE CREAT ON ALBANIAN STATE:A DIPLOMATIC STUDY。而在同藏于“翰档”的一份题为《陈翰笙先生的论著》手写稿上,列在第一条的就是“一九二一年芝加哥大学的硕士论文瓜分阿尔巴尼亚(英文稿)”。根据这些资料可知,陈翰笙硕士论文所研究的,其实是有关一九一二年阿尔巴尼亚建立独立的民族政府后,英、奥、法、德、意、俄六国召开伦敦会议,以承认其独立的方式进行实际控制这一重大国际事件。但迄今所见各种叙述陈翰笙生平的文章及年鉴、辞典的相关词条,都采用《四个时代的我》的说法,坊间流行的几本陈翰笙传记亦讹误相袭,甚至夸张渲染,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翰档”所藏,既有已经公开出版的陈翰笙著作,亦有相当数量的未刊手稿,如陈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访问苏联、东欧以及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亚洲国家会议时所写日记,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六年间考察安徽、黔中、浙江、山西、甘肃等地的日记等,无论对于考察其生平思想,还是研究他所关联的时代、社会,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惜至今仍沉睡库中。这当然不尽为收藏者之责,网络版《陈翰笙档案资料库》的公开,使得查阅更为便利,如有更多研究者积极利用,参与整理,不仅珍贵的文献可以充分发挥其用,“翰档”的收藏也会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丰富。这应是可以期待的。
《幌马车之歌[增订版]》
蓝博洲著 定价:55.00元
通过台湾革命青年锺浩东短暂而炽热的一生,将扭曲的台湾近现代史还原重现。历三十年常销不衰的台湾纪实文学经典,侯孝贤作品《悲情城市》
《好男好女》的故事原型。
《幌马车之歌续曲》
蓝博洲著 定价:52.00元
作者在历史残简的喑哑处苦心求索,呈现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牺牲的三位台湾青年李苍降、蓝明谷、邱连球的生命故事,将岁月掩埋的身影铺展为时代的证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