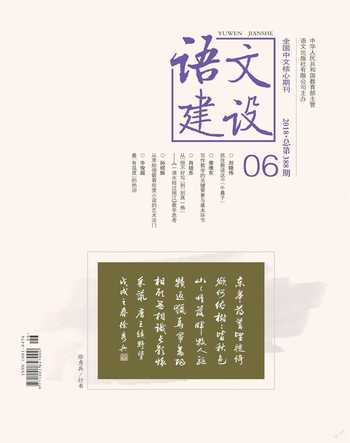从草船借箭看欣赏小说的艺术法门
2018-05-30孙绍振
孙绍振
一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经相当苛刻地批评《三国演义》写孔明之失为“多智而近妖”。这个批评当然不无道理,孔明的多智,从现实主义小说家的眼光来看,的确是超人的,或者说是神化的。但是,鲁迅说话有鲁迅的特点,他不说超人,不说神化,而说“近妖”,即不是人,而是妖怪。从现实主义小说所谓“细节的真实”来看,《三国演义》的确有不现实、不真实之处。以著名的草船借箭为例,诸葛亮料定三天以后有大雾,其准确性大大超过了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如果拿这个准则去衡量鲁迅的《呐喊》《彷徨》尚可,以之衡量《故事新编》就不通了,里面“近妖”的人物多得很。例如他自己最喜欢的《铸剑》中,那个复仇的孩子眉间尺,那个无条件代替孩子去杀暴君的黑衣人,还有那个国王,三人的头杀到油锅里,翻上翻下还会唱歌。这其实很简单,《三国演义》和《铸剑》都是一种假定的想象,何况《三国演义》还是中古传奇,其想象的自由度要大得多。关键在于,这种想象是不是有利于表现人物之间的错位心灵。
不管鲁迅多么伟大,不管他的文学见解多有权威,依然阻挡不了中国(还有日本、越南、朝鲜)读者对《三国演义》的赞赏甚至着迷。鲁迅的权威无论如何也敌不过历经几百年历史淘洗的阅读实践的权威。这个问题光是从现成的文本,一味以读者接受的眼光来看,是不可能弄清楚的。欧美文学理论在文本解读上不得不承认,他们在遇到具体文学作品时“陷入一种令人吃惊的、一筹莫展的境地”。他们似乎都忽略了海德格尔的教导:
作品的被创作存在只有在创作过程中才能为我们所把握。在这一事实的强迫下,我们不得不深入领会艺术家的活动,以便达到艺术作品的本源。完全根据作品自身来描述作品的作品存在,这种做法业已证明是行不通的。
海德格尔说得很明白,“完全根据作品自身来描述作品的作品存在,这种做法业已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样,只能是被动地接受。要真正理解作品的奥秘,就要化被动为主动,进入作品的“被创作过程”,也就是想象出作家如何创作,与之对话。西方文论在文学审美解读方面之所以“一筹莫展”,原因盖在满足于被动地接受。其极端者,还将之理论化日“接受美学”。究其原因,他们总是拘泥于被动地接受现成的文本,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不但把文学形象的艺术精彩消解了,而且把文学的存在都虚无化了。只有从作者的创作实践过程中,才有可能揭示出文学奥秘来。鲁迅满足于被动地接受现成的草船借箭这个文本,不但没有看出什么名堂来,反而作出了与几百年来读者惊心动魄的阅读体验相悖的结论。从其创作的过程来看,固然很难探索其中奥秘,因为作者已死,他又没有说自己是如何取舍、提炼、重构、升华的。但是,对于许多经典文本来说,历史的素材并不罕见。关于草船借箭,原本的素材在《三国志》裴松之注本中,裴松之注引的是《魏略》:
权乘大船来观军,公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
这里强调年方三十岁左右的孙权临危不乱的机智。到了差不多一千年后的《三国志平话》中是这样的:
周瑜一只大船、十只小船出,每只船一千军,射住曹军。蒯越、蔡瑁令人数千,放箭相射。却说周瑜用帐幕船只。曹操一发箭,周瑜船射了左面,令扮棹人回船,却射右边。移时,箭满于船。周瑜回,约得数百万只箭。周瑜喜道:“丞相,谢箭。”
二者細节上虽有所不同,但针对的对象同样是曹操,在性质上则完全是实用理性的机智。到了《三国演义》的“草船借箭”中,则发生了根本的性质的改变。第一,保留了战船中箭这一核心情节,把针对的对象改为诸葛亮的盟友周瑜。第二,为了引出曹军射箭,增加两个元素:大雾,诸葛亮准确预测。这样准确的天气预测,在当时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鲁迅说诸葛亮“多智近妖”的原因。但是,鲁迅作为小说大师,忘记了小说家虚构的权利。
二
当然,并非一切虚构都是艺术的,可这个预测大雾的虚构却具有不朽的经典性。因为这样一虚构,诸葛亮超人的、“近妖”的多智,使得他的盟友周瑜不舒服,难受。作者设计了周瑜这个好人,他有一个心理毛病:多妒。他的多妒有个特点:近距离的。他不妒忌曹操,也不妒忌孙权,他就妒忌诸葛亮。为什么呢?两个人地位差不多,具有现成的可比性。这是人性的弱点:妒忌往往产生于地位相当的人之间。周瑜的妒忌是很高级的,他妒忌的是人的才智。他很有自尊,不能忍受身边的人在才智上超越自己。诸葛亮越是多智到超人,周瑜就越是多妒。如果鲁迅生活在罗贯中身边,给他提意见,不让诸葛亮多智到“近妖”的程度,那就让预测失败,其结果是诸葛亮不能完成任务,按立下的军令状,被周瑜合法地推出斩首。这不但没有艺术的审美价值,而且小说也写不下去了。罗贯中构思的精彩就在于,把这场战事的焦点不放在实用理性的胜负上,而是放在情绪争胜上;甚至不放在斗智上,而是放在斗气上。周瑜要诸葛亮限期造箭,表面上是为了打败曹操,实际是要合法地整死诸葛亮。
罗贯中的艺术才华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第一,诸葛亮的多智是被盟友周瑜逼出来的。第二,诸葛亮超人的天气预测成功以后,还有一点冒险主义,开着满载稻草人的船大张旗鼓地向曹营进军。第三,曹操多疑而自信,当他得知诸葛亮大雾中来犯,就认定诸葛亮为人谨慎,不会冒险,如今这样冒险,必有诡计,下令不要出战,用箭射住水寨阵脚,于是箭如飞蝗。这时,罗贯中把原始素材孙权横向调船改为纵向,让诸葛亮下令“船头朝东,船尾朝西”。一方面是让船尾的稻草束也充分受箭,另一方面也是便于回师江东。这里显示了罗贯中小说家的艺术天才:多妒逼出多智,多智的冒险又遭遇多疑,形成一个情绪连锁性的错位。此后多妒的更加多妒,多智的更加多智,最后是诸葛亮三气周瑜,周瑜终于意识到自己智不如人,就活不下去了,临死不怪自己还怪老天,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长叹。这是妒忌学上的伟大发现,直到六百年后,世界妒忌心理学在这方面还没有达到如此水平。
但是,这样伟大的文学创造,许多学者都没有认识到。最近,刘再复先生在他的《双典批判》中就说:这是对历史上的周瑜“抹黑”。他认同“既生瑜,何生亮”是“杜撰”,还引用了学者盛巽昌的著作《(三国演义)补正本》:
据史传,周瑜气量宽宏,赤壁之战时,蒋干奉曹操命来说降周瑜,回去后说,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词所间……《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说他“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对此刘备也说他“器量广大”。他的器度和谦让是为诸家所认同的。
这是很没有道理的。小说,尤其是历史演义本来就是以虚构取胜的。不虚构,照搬史实,哪里来的艺术?问题的关键在于,虚构的水平如何,对人物内心深处探索得如何。何况,《三国演义》把周瑜当作正面人物、好人。他在赤壁之战中的英勇、智慧,如苦肉计、连环计,对蒋干说降,采取将计就计导致曹操上当,在水战之前杀了水军统领,这一切都是赤壁之战克敌制胜的关键,显然这是个以少胜多的军事家、英雄豪杰。但是,艺术家罗贯中让周瑜有一种心理不健康的毛病,最后导致了自己的死亡,其实就是写他心胸狭隘、多妒。周瑜对诸葛亮的多妒,是为了吴国的前途;以他的政治远见,判定将来吴国与刘备之间必有冲突,留下诸葛亮这个智慧高明的人物,对吴不利,故在联合之时,就设法合法地除掉他,这仅仅从道德范畴来看谈不上“抹黑”。
海德格尔所说的被创作的过程,就是从非艺术的素材提炼到艺术的形象体系的完成,是一个从实用理性上升为审美情感循环的过程。对于草船借箭来说,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准确预测三天以后有大雾,正是这个“近妖”,使其成为不朽的文学经典。
三
鲁迅在此所犯的原则上的错误,至少有两点:第一,把科学的理性当作文学审美的评价标准,忽略了小说的功能主要是表现人的情感为核心的内心世界;第二,孤立地评论小说中的个人行为。小说是在人与人的情感关系的互动、错位中揭示人的内在深层奥秘的。不管是欣赏还是创作小说,基本训练就该从这里开始,首先学会把科学理性和情感的审美价值区别开来,超越日常生活中理性的优势,拉开错位的幅度的过程,就是艺术产生的过程。
除了科学理性的真实与情感的虚拟以外,小说还得处理理性的实用与情感的不实用之间的关系。契诃夫的《万卡》,如果只有万卡向祖父诉苦,恳求祖父把自己从城里接回去,免除当皮鞋店学徒的种种苦难等内容,那么,契诃夫与热衷于表述对劳动者的同情的民粹派小说家没什么两样。小说的最动人之处在于:由于万卡写的地址太笼统,信是不可能被祖父收到的。也就是说,其实用价值等于零。可万卡却以为爷爷一定会收到,并且做着爷爷收到信的甜蜜的梦。也就是说,在他的情感深处,这封信具有救命的价值。正是由于这两种意义或者说这两种价值拉开了距离,发生了错位,小万卡的情感世界才能得到充分的显现,其形象的感染力才强烈。如果这封信被万卡的爷爷顺利收到,实用价值提高了,情感价值就降低了。
大家都读过《麦琪的礼物》。表现人物心灵最动人的就是在圣诞节,按基督教国家的风俗,亲人之间要互送礼物。可是这一对夫妻很穷,买不起什么像样的礼物。于是妻子把自己最美丽的头发卖了,为丈夫最珍贵的怀表买了一个表链。她期待丈夫的欢欣,但是丈夫却一脸困惑,原因是丈夫也没有钱为妻子买礼物,只好把自己的怀表卖了,为妻子买了一套发夹。双方的礼物都没有用处了,但是小说借此表现了双方最珍贵的感情,这是最有审美价值的。
决定小说人物生动性还有一个规律,那就是让相亲的人物在情感上发生错位。注意,这里说的是错位,不是矛盾,矛盾是对立的,但单纯的对立,并不一定动人。我国古典小说甚至现代武侠小说中,有许多仇人相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仇人死于非命的情节,但都没有给读者留下太深的印象。倒是那些本来甚相亲相爱的人,产生了矛盾,拉开了心理距离,发生了错位,反而更动人。就像《红楼梦》中,最相爱的贾宝玉和林黛玉,吵闹斗嘴得最厉害,才生动。贾宝玉和薛宝钗从来不吵闹,因为他们不相爱,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错位。
《西游记》中的“三打白骨精”为什么成为经典情节呢?因为在取经的曲折过程中,在大部分情况下,遇到妖怪时,师徒四人是一致的,共同对敌,这样很有诗意,却没有性格可言,只有拉开距离才能凸显性格。白骨精一出现,在唐僧看来这是个善良的女子,在孙悟空看来这是个妖怪,在八戒看来这是个有姿色的女性,三人不同的心理就拉开了错位的幅度。孙悟空将其打死,如果八戒没有私心,而是同心同德,就会告诉唐僧那是妖怪;但八戒平时受孙悟空欺侮,这回要刁难他一下,就说孙悟空生性残忍。结果,孙悟空被赶走了,唐僧被白骨精逮住了。拉开了错位距离,人物的性格就鲜明了。其中有一个人没有拉开心理错位,就是沙僧,他什么个性也没有,也就没有感染力。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里有一个最根本的心理学解释,即维戈茨基的“情感逆行”学说。与读者的同情相反,他举了一个例子,是狼和小羊的故事:狼和小羊一起到小溪边喝水,狼大叫一声,你把我的水弄脏了,羊说不对呀,你在上游,我在下游,怎么会将水弄脏呢?狼又说,去年你曾经把水弄脏,小羊说,对不起,去年我还没有出生呢!狼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小羊吃掉了。
维戈茨基分析,小羊的理由越充足,读者越感到安慰,它的命运就越坏,读者就越忧虑。读者希望小羊脱险,希望小羊说得有理,但小羊越是有理,狼就越有不讲理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分析沙和尚、孙悟空、猪八戒的性格时就是这样,我们越是同情孙悟空,他就越遭难,唐僧就越倒霉,八戒就越得意,这时的每一个动机,中间都会分化,于是孫悟空被赶走了,唐僧被抓住了,读者又难受又高兴,难受是因为唐僧受苦,高兴是因为他非得把孙悟空请回来不可。这就是“情感逆行”学说,里面包含情怀和忧虑两重性。
这个道理有相当的普遍性,连第一人称的叙述者与人物间的情感都应该错位。如《祝福》中的叙述者“我”与祥林嫂就拉开了距离。祥林嫂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希望“我”说出人死了没有灵魂,那死了也就不会到阎王那里锯成两半了,但“我”偏偏说得含含糊糊,使她死前怀着更多的恐惧。这样,文章就加深了悲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