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澎:中国当代艺术已经“心力衰竭”
2018-05-29吕澎
吕澎 ,1956年出生于四川重庆,1982—1985年任《戏剧与电影》杂志社编辑;1986—1991年任四川戏剧家协会副秘书长;1990年—1993年任《艺术 · 市场》杂志执行主编;1992年为“广州双年展”艺术主持;2005—2016年任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2011—2014年任成都当代美术馆馆长,现为那特艺术学院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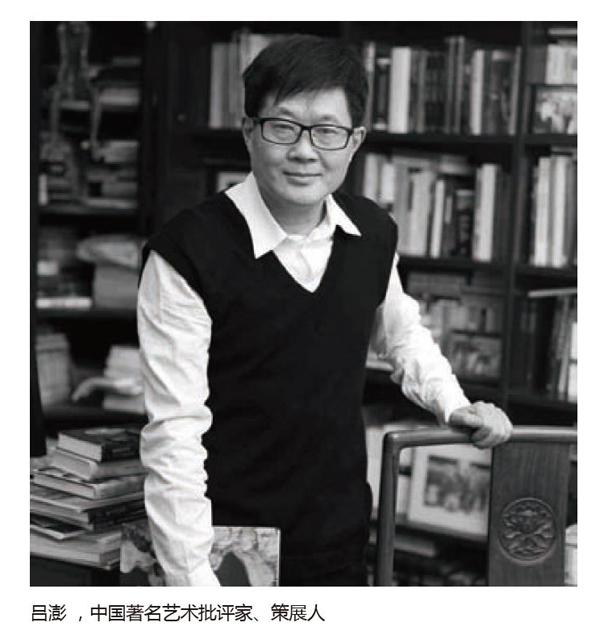
当代艺术是否已经终结?
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当代艺术就逐步表现出心力的“衰竭”。在之前的好几年里,当代艺术都处于狂欢中——拍卖场上的叫卖声与市场中的细语交织成一片,形成了引起广泛效应的声响,以致引发了太多的质疑、嫉妒与谩骂。尽管质疑、嫉妒与谩骂的语言粗俗不堪、缺乏理性与教养,但他们中间没有人承认这种质疑是非理性的,他们每一个人都竭力向公众表明:被质疑的狂欢是堕落的,甚至狂欢本身仅仅是一种未被识破的谎言。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那些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自由艺术家似乎有了值得骄傲但又难以启齿的可能性,市场经济将艺术家的肉体托上,开始了物质主义的旅程。可是,精神呢?有人带着不安地问。之前,当代艺术有一个让人激奋的名称叫“现代主义”。可是,现代主义具有的愤世嫉俗特征阻止了艺术家对“庸俗的”金钱的公开敬意。尽管圆明园一个个幽灵总是热衷在昏暗的灯光、酒精与女人中间穿梭,以满足灵魂的需要,但实际上他们本能地希望肉体要有实在的栖身之地。直到90年代上半叶,开始被称之为“当代艺术家”的那些现代主义的“后裔”仍然以羞怯的态度面对物质的世界,他们还是勉强地坚持:“艺术”总是精神的和神圣不容金钱侵犯的,不过同时已经有不少的艺术家接受了市场经济的现实,之前的苦难与让人焦虑的生活告诉他们:无论如何美金或者金钱是重要的。
中国“当代艺术”的成就

早在80年代,年轻艺术家带着一种人类理想主义的惯性,展开了对历史的批判和对未来的憧憬。1989年,尽管现代主义的激进分子在中国美术馆有一次肆无忌惮的狂欢,可是跟着,他们的感觉与行为被阻断,那些尖锐的思想与激情似乎失去了投射的方向,灵魂找不到安放的地方。于是,玩世现实主义提示了另一种存活的路径:如果没有可能讽刺社会,似乎可以嘲笑自己——批评家将其说成“自我拯救”;还有一种态度也让人难以定论: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为什么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融为一体,这不是搞笑,这是政治波普提出的一个问题。接着,艺术家不再坚守本质论的规矩,理想、真理这类词汇失去了意义,人们能够感受到的是,批判性的话语不是演变成没有智商的口号,就是彻底消失殆尽。
很快,中国艺术家就在姿态与敏感性上适应了新的游戏,直至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有批评家对中国当代艺术大胆地使用了“合法性”这样的词汇,好像时代真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之后的展览中,艺术家甚至对公众也胆敢表现出肆无忌惮的调戏。总之,从80年代燃情岁月走来的当代艺术,获得了似是而非的成功效应。
市场似乎在帮助当代艺术一路凯歌,以致官方艺术机构也需要认真对待这个事情,通过设置当代艺术院或者形式上对当代艺术家的接纳成为人们质疑的“招安”或者“同流合污”的物理代名词。人们很难说清楚,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中国“当代艺术”到今天已经没落
当代艺术的队伍早就被打散了,其打击的力量来自四面八方:来自意识形态领域、来自无所不在的市场、来自自作聪明的观念、来自所谓的“艺术批评家”的“批评”、来自利欲熏心、来自嫉妒与仇恨、来自心理疾病、来自丧心病狂、来自貧困、来自金钱、来自任何一个有意无意瓦解艺术心灵的角落。在这样的情况下,真正的艺术家只能再一次地退守内心,退到没有人知道的迷茫与未知领域,听凭内心的需要重新寻找活力的可能性。
享乐与苟且成为普遍的风气,如果可能,一位被称之为“艺术家”的人可以随时准备调整任何立场和位置,面向官方、面向市场、面向机构、面向名利,面向任何可能性,只要这是自己的或者大家的“艺术”与“事业”的需要。
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实状况是,曾经充满活力的生命正处于可怜的衰竭之中。
向西方学习并不是复制
如果我们简单地说,由于这些艺术家的风格、语言,其实西方早就有了,中国人不过就是重复了一遍。这么看问题就显得非常的肤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看待问题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去分析他们语言的相似性,而是要去分析任何一种艺术现象,为什么没有在一百年前发生,而在一百年之后发生,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他的发生的原因是什么?他对社会对我们的艺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才是我们真正要去关注的问题。如果我们按照技术、风格和方法来评判一个艺术家的话,今天去看徐悲鸿的作品就显得很普通、很一般,凡是学欧洲艺术史的人都会说这种绘画水准,都能够在欧洲、在西方找到更加优秀的范例。
我们今天看到大量的国内院校里的绘画,里面都有极其优秀的西方油画技法,还有极其优秀的老师和学生。难道他们的作品就不重要吗?这也是我非常想强调的。当我们走进展厅看到任何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我们也许会去关注这个艺术家的作品像谁的,或接近于谁,然后你的内心就会产生疑问,这样的艺术他究竟有多大的重要性,这是我们经常会遭遇的问题。
可是当我们把一个艺术家,一个艺术家的成长和他的艺术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当中去分析和判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因为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当中,中国人没有这样观看世界的习惯,更没有这样去表现视觉的习惯。
西方文明继20、30年代对中国年轻一代再次产生影响——这个影响的确有力地推进到了今天。在几乎整个80年代,中国年轻艺术家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了西方艺术及其文明背景,与早期认识西方艺术不同。这个时候,现代主义的语言和样式成为新艺术的主流,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抽象主义在绘画中的影响非常普遍。
这个时候的中国,绘画语言不过是在画家的目的论的指引下,根据自己的性格、气质、技能来选择的。80年代初期,四川主要以写实(主要是俄罗斯与苏联绘画)为主体,而在北京的年轻人却以表现主义和毕加索为旗子。这个时期,“艺术自由”是主要的观念,至于语言方式,则由艺术家自己决定。80年代中期,人们熟悉不少口号,“观念更新”是其中之一,而这个时期的“观念”也许与今天的观念绘画的“观念”也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不过是提醒人们破除思维习惯,视觉的习惯,对艺术思想与出发点以及方法要有新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