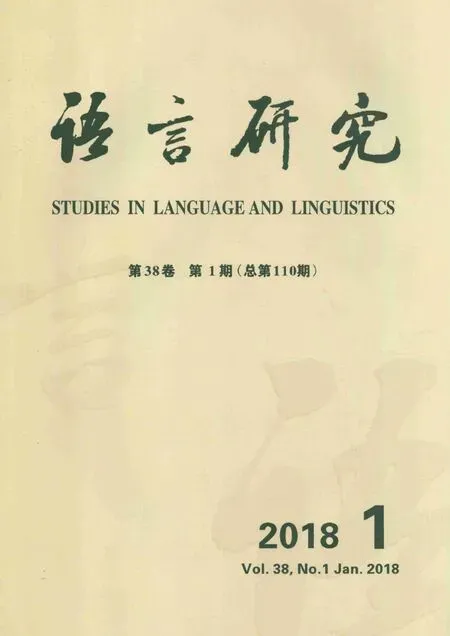汉语交互关系的判定标准及典型性分析
2018-05-28刘云峰,石锓
刘 云 峰,石 锓
汉语交互关系的判定标准及典型性分析
刘 云 峰1, 2,石 锓1
(1.湖北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62; 2.豫章师范学院 人文系,南昌 330103)
汉语交互结构的判定标准是:深层语义上的主语为复数且不带宾语;主语之间或主宾语之间在语义上为“同为施受”关系;或者主语构成成员间为相互依存的共事关系。汉语交互关系的典型性表现为:有形式标记的交互结构比没标记的更典型;没有交互标记时,交互事件参与者间的时空距离越近越典型;个体交互比全体交互更典型;互为施受交互结构的典型性强于单方施受的交互性。
交互式;判定标准;典型范畴
反身和交互是重要的回指现象。国内外对反身的讨论已非常充分,涌现了大量优秀研究成果,其中生成语法的管约理论更是影响深远;相对而言,交互的研究比较薄弱。这种情况近些年来有所改善:国外对语言交互现象的研究日渐兴起,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专题著作和论文(集);国内相关的研究也日渐活跃。但大部分国内研究还局限于具体的,诸如交互动词(吕叔湘 1980;朱德熙1982;刘丹青1987a、2008;陶红印1987;袁毓林1989;张谊生1997等)、交互副词(吕叔湘 1988;赵静1999;汪兰2004;唐贤清 2006;颜明 2012;李兰霞 2014;魏海平 2015等)、交互代名词(刘丹青1983;周国光1990;刘探宙2003等)和交互形容词(刘丹青1987b、2000;谭景春1992)等词类的形态、用法和功能的探讨,研究范围相对比较狭窄;相关基本概念和范畴等的研究也比较滞后,专题性的著作和论文更为罕见。本文从基本概念出发,就汉语交互的判定条件、范畴的典型性两个方面提出粗浅的看法,就正于方家。
一 判定标准
(一)已有的相关标准研究
逻辑学上下定义常用“种差加属概念”的方式,描写清楚了“种差”(事物区别性特征),事物的性质也就容易判定了。从这个角度上看,“种差”就是判定事物的条件或标准。国内外学者对交互判定标准的研究大多沿着这一逻辑思路进行。首先是语义特征的描述。吕叔湘(1980:239)以为互相“表示甲对乙和乙对甲进行相同的动作或具有相同的关系。”唐贤清(2006)认为交互就是“彼此互为施受”。刘丹青(2008:191)认为“相互义……是对先行词的回指,就行为来说,都是施受同一的现象”。
与国内学者相比,国外学者论述则更加详细些。Nedjalkova(2007:6)认为典型的交互义通常解释为用于描述参与者的情况:“它们处于彼此完全相反的关系中,即(它们是)相同的语义论元,具有相同的语义内涵”(in the identical reverse relation to each other, i.e. the semantic arguments have the same semantic content);“它们各自担任两个完全相反的语义角色(施事和受事)”(they perform two identical semantic roles (e.g. of agent and patient) each)。
国内学者大都从语义的角度上,认为交互是“彼此互为施受”或“施受同一”(或相似表述)。但是,他们没有回答什么是“施受同一”?“施受同一”具体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也没有解释“彼此互为施受”的具体表现。而且交互事件参与者的“彼此互为施受”也不能涵盖汉语交互的所有情况,因此其概括性应受到质疑。Nedjalkova则侧重语义角色上来解释,但考虑尚未周全。
从语义上来界定交互概念无可厚非,但是语义标准的弊端是可操作性不强。在具体语境中,人们对话语是否表达了交互义的看法往往见仁见智。因此,学者们又从形式功能等角度,进一步描写交互结构的特征,以便于人们判定。
Nedjalkova和Dixon从类型学角度提出了代词、动词、附缀及其绑定、重叠等等形态标记;同时提出了交互的功能特征,认为交互句的施事与受事间有交集,交互事件参与者充当的主宾语至少要两个人以上等。这些都是对人类语言共性做出的趋势概括,对具体语言研究有很强的指导性,但其结论并不能替代具体语言自己的判定标准。这些还要结合具体语言的实际情况,归纳出妥当的标准。事实上,Dixon在自己著作中也举出了反例(Dixon 2012:148)。
国内学者也从形态和功能角度,进一步提出了交互判定的参照标准。刘丹青(2008:191-192)指出“相互关系强制性要求先行词是至少为二的复数,其功能是交叉回指复数先行词内自己以外的个体。”“典型的相互义中先行词是意义上的双方……扩展用法则可以涉及一个更大的群体”。这些参照标准虽然加强了判定交互的可操作性,但仍稍嫌不够全面。英语和汉语中都存在一个先行词的交互句(如下文例3)。张谊生(1997)提出了现代汉语交互动词判定的两个框架和三点补充。现代汉语是现实中的活语言,可以通过内省法来判定转换后句子的合理合法性。然而这个方法并不适用于古汉语相关研究,古汉语交互结构的判断只能建立在对现存古汉语语料的分析和研读上,而不能依靠口头语感通过内省来判断。
(二)可能的判定标准
尽管前贤的研究成果给了我们诸多有益的借鉴,我们认为仍有必要继续深入探讨交互现象,提出更全面的可操作性强的判定标准。根据对语言实际语料的考察和前人研究成果,汉语交互结构的较显著的“种差”,可以从以下方面去考虑。
(1)形态标记
汉语交互标记是指明确表示交互义的代词、副词或词素等语言形态,如:彼此、相互、互相、交互、自相、相-、互-、对-。但是,这些标记并必然表交互义。如古汉语中有些句子虽然带有交互标记“相”,但并不表交互义,而仅仅是个偏义复词表示单向义。如:
1) 苟富贵,无相忘。(《史记·陈涉世家》)
句中的“相忘”单指飞黄腾达后的一方对另一方,并没有交互的意思。不仅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也有部分动词带有交互标记但仍表示单向义。如,相传、相烦、相继、相瞒、相劝、相让、相思、相扰等(颜明2012)。因此,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要准确判定是否表示交互义,我们有必要参考其他条件。
(2)语义施受
有学者说交互结构是“施受同一”,其实这是不确切的说法。“施受同一”有两种不同的意思,一是“施事和受事为同一个(群)人或事物”,而这指的是反身现象。
“施受同一”的另一种意思是“同为施受”①,此时才可用于表述交互现象。按照交互事件参与者间关系的不同,这种“同为施受”关系也可以分两类:一类是,交互事件参与者内部成员间,两两彼此为对方的施事和受事,我们称之为“互为施受”的交互关系。另一类是,交互事件参与者内部成员间按顺序依次为施事和受事,称为“依次施受”交互关系,见下例。
2) a 肖明和李静很早就认识,却从来没有机会见面。
b 这些尸体彼此堆叠在一起。
例2)a中“肖明”和“李静”两人彼此充当对方“认识”和“见面”的施事和受事。例2)b指的是尸体按照线性顺序依次堆叠起来,对于任何两具相邻的尸体而言,它们互相不同时充当彼此的施事和受事,但对所有的尸体而言,它们是彼此堆叠的,是“依次施受”关系,因此也是交互句。综上,事件参与者间的“同为施受”关系,是交互结构重要语义特点之一。
汉语缺乏形态标记,即使有标记,它们往往也是“兼职”的。比如,“相”是汉语中交互的形态标志之一,但是它还有表单向义的功能,如果人们忽视了其后者的功能,常常就会犯错,如例1)。而那些没有标记的句子,往往又表示交互义。如,
2) c 武则天的后宫生活很丰富,当时她的姐姐武顺,因为与李治眉来眼去,被她搞死了。(倪方六《中国人盗墓史》)
武顺和李治是“眉来眼去”的彼此施受者,为“互为施受”关系,显然是交互句。
由此看来,形式标记,在汉语中只能作为一个参考条件,而事件参与者间的“同为施受”关系,是判断交互的一个更重要参数。
(3)句法功能
首先,深层主语为复数(交互对象为两个或以上)。
Dixon(2012)认为,交互结构的主语指的是包含及物主语和宾语在内的参与者合集,因此主语必须是非单数的指称。国内学者观点也持相似观点。但是,汉语和英语中却经常看到单数主语的交互句:
3) a 我今天遇见小明了。 b Tom married Mary.
怎么解释这种现象?Dixon等人的观点是否错了呢?我们认为Dixon的“非单数指称”应从深层逻辑语义上来理解。从深层语义上看,例3)a中的“遇见”是指双方互相看见对方并打招呼的情况。因此逻辑主语是“我”和“小明”,为“非单数指称”。同理,例3)b中的深层主语为Tom和Mary,也是复数。
其次,深层语义上谓词不带宾语。
深层逻辑语义上的交互事件的参与者常常是施受同体,且它们通常是位于主语的位置上,因此其后的谓语动词以不带宾语为常。如,
4) a 他俩很早就认识,却从来没有机会见面。
据张谊生(1997)“认识”是一个“伪交互动词”,其交互义只是句子的语用义,而“见面”才是真正的交互动词。所以虽然“认识”是及物动词,但不表交互义;而“见面”是一个不及物性的动宾结构离合词,它们后面都没带宾语。
有的语言交互动词后面可以带宾语,如例3)中的“遇见”和“marry”。我们认为,在深层语义上,带宾语的交互句谓语仍然是不及物的。例3)a的深层语义就是“我和小明今天相遇了”,其中主语“我和小明”同时也是“相遇”的逻辑宾语。此时的谓语动词显然不能再带宾语,为不及物动词。用一个带宾语的表层及物句形式来表示不带宾语的深层交互义,只能说是言说者语用的需要。
另外据刘丹青(1986),现代汉语及物性交互动词绝的对数量虽然不少,但在交互动词中仍然是占比仍然很小②。有意思的是,在表层结构中,现代汉语交互结构动词能否带宾语与其主语是否为单数有一定的关联:带有“相”“互”等显性交互标志的动词,其后一般都不再带宾语,其主语也是非单数指称,如“相遇”、“互助”等等;而没有交互标志的动词,或者由“竞”、“结”、“对”等隐性交互语素构成的交互动词,却常常可带宾语,其主语往往可以是单数,如“竞争”、“对唱”、“结识”、“商量”、“讨论”等等。例如,
4) b 我们要互助共进。 c 王强碰见了李项。
d 我们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e 我和老爸曾对唱“扎红头绳”。
例4)b动词带交互标记“互”,其后没有带宾语;其他几句动词没有交互标记,但是后面都带宾语。
(4)认知角度
交互事件的参与者大都是生命度等级高的施事或受事,通常是人、人身体部位或拟人化的事物。如,
5) a 大家都E来E去 ,文字是键盘敲出来的,签字用数字签名,情书是e-mail,建交按添加、绝交按删除…… (《厦门日报·未来网络世界》)
b 他俩拳来腿去,打得难解难分。
句中表达交互义的谓词短语“E来E去”“拳来腿去”的主语“大家”和“他俩”都是生命度等级最高的人,而5)b中谓词部分的动词“来”“去”的主语“拳”和“腿”也还是身体的一部分。因此有学者认为生命度等级高也是交互结构的重要特征。但是,如果我们把例2)b中的“尸体”换成无生命的“碗”“碟子”等,句子仍然成立,交互义也没有变化。所以,我们认为,交互事件参与者的生命度等级高,可能只是一个大致的趋势还不是区别性特征。
(三)小结
我们用表格的形式,把上述交互结构的几个特点和所用例句来综合分析。
表1

例句 项目 有无显性交互标记同为施受深层语义主语为复生命度等级高深层语义不带宾语交互义强弱 互为施受依次施受主语宾语 例1+ (伪)--±+++无交互义但易混淆 例2a)-+-++++弱 例2b)+-++--+较强 例2c)-+-++++弱 例3a)-+-++++弱 例3b)-+-++++弱 例4a)---++++弱 例4b)-+-++++较强 例4c)-+-++++弱 例4d)-±±++-+弱 例4e)---++-+弱 例5a)---++++弱 例5b)-+-++++弱
由上表的比较,我们可以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汉语中交互义的表达,没有形式标记的硬性规定。但是,有形式标记的交互结构其表达的交互义要远强于没有标记的结构。甚至,有些没有交互义的单向伪交互标记动词,还常常给人们正确理解带来误导。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认为这和它们交互义的表达方式有关。汉语中的交互标记,交互义已经进入了其义项,成为不受语境影响的固定意义。而没有标记的的交互结构,其交互义仅仅是以语义蕴涵(Riemer 2010;胡平2016)的形式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语用和语境的制约。人们在理解时,首先按照义项义进行理解,然后才会考虑结合语境等外部因素。义项义是约定俗成凝固了的,不会因人而变,其表义当然强烈而固定。但是要结合外部因素理解的蕴涵义,其表义隐约而不确定,故而常因人而异,见仁见智。由此可知,义项义的表义强度和给人们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蕴涵义。
2 表1显示除例1)不是交互句外,交互句在深层语义上的“同为施受”、“主语为复”(两个或两个以上)和“不带宾语”等这些参数上都是正值。由此可推知,它们是交互表达的必备条件。而“同为施受”就蕴涵了交互结构在深层语义上的“主语为复数”和“不带宾语”特点。在深层语义中,交互事件的参与者就是“同为施受”者,它们既是逻辑主语又充当逻辑宾语。交互事件的主语必不可少,因此逻辑语义中的宾语就不再需要。例4)d似乎是一个例外,“行动计划”是“商量”的受事宾语,怎么说不需要宾语呢?我们认为,“行动计划”虽然是“商量”的受事宾语,但它并非交互事件中的宾语。“我们商量下一步行动计划”可以分解为两个子事件:一个是,我们在商量;另一个是,商量下一步行动计划。第一个事件是交互事件,第二个事件为普通事件。因此,我们认为,“行动计划”不是交互事件的宾语,它只是普通事件中的受事宾语。
3 上表显示,除例4)d、e两句外,满足“互为施受”关系的交互句,与满足“依次施受”的交互句呈互补分布状态。
例4)d、e也是交互句。与其他句子着眼于参与者个体间交互关系不同,它们从参与者全体的角度来表述交互关系。例4)d、e主语的构成个体在语义上彼此并不是施受关系,而是共事关系④(刘丹青(2000:223)称为“施事当事”)。带有共事主语的交互句,其事件参与者间的语义关系是互相依存⑤的关系,相互间不可或缺,是一种静态的交互关系。与施受关系交互句同为交互的特点不同,在共事关系交互句中,相互依存性是一个重要的显著特征。
4 综上,交互结构的特点可以减缩为以下几点:
第一,深层语义上的主语为复数且不带宾语⑥;
第二,主语之间或主宾语之间是施受关系的交互句,语义上为“同为施受”关系;
第三,主语构成成员间为共事关系的交互句,其成员间具有相互依存的特点;
第四,交互标志并不是汉语交互结构的必然参项,但仍然是最直观的特点。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认为,这四个特点可以作为话语交互义的判定标准。
二 典型性分析
语言是个连续统,各个语言范畴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不宜做非此即彼的强行分割。从认知的原型范畴理论出发,把范畴分为“典型范畴”和“非典型范畴”是明智的做法。典型范畴内的成分其属性是明晰的,不存在争论;而非典型范畴则相当于两个或几个典型范畴间的中间灰色地带,它们是连续统的衔接部分,其内部的成员属性是不明晰的,其归类可以见仁见智。
交互范畴是一个语用范畴,除了少数交互词语通过义项的方式标记交互范畴外,很大部分交互义的表达是依赖语境通过蕴涵义的方式表达的。在实际的话语分析中,虽然我们有判定标准可供依据,但是仍然存在难以判定是否为交互情况。如:
6) 他们一个挨一个的走出黑屋子。
此外,表1所列举的各个例句,除了有标记交互句(例2)b和例4)b)表达的交互范畴比较典型,容易辨别外,其他句子的交互义均较隐晦,也不甚容易判别。虽然隐晦,它们间的交互义仍然存在着强弱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分辨这些差异?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我们对话语结构交互义典型性的分析和描写。
我们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去了解和分析交互范畴的典型性:
(一)是否有明确的形态标记
有标记的交互就是典型的交互。如,汉语句子中带有“互相”、“彼此”或者词语中带有词素“互”“相”的均是典型交互。如,“他们彼此写信”比“他们写信给对方”交互义要强很多。
(二)参与者的时空关系
句子中没有交互标记时,我们认为可以根据认知上距离相似性原理来判断交互性的强弱。Lakoff 认为“紧密度就是效果强度”(closeness is strength effect),也就是说,物体间距离越近,它们的关系越密切。空间上更接近的“完全交互”⑦比“线性交互”更为典型;时间上更为接近的“同时交互”又比“相继交互”更为典型。时间上的距离其实是空间距离在时间轴上的投射,所以在同等条件下,空间上的交互范畴要强于时间上的。如,
7) a 他们打量对方。 b 他们俩一块丢沙包。 c?这排柱子距离2米。
“他们打量对方”表示还是互相打量的意思,是比较典型的交互。其预设前提是双方在空间上面对面,时间上同时的互相上下看。“他们俩一起丢沙包”则有两种理解:
7) b′ 他们俩一块互相丢沙包。 b′′ 他们分别和其他人丢沙包。
按照例7)b′的理解,例7)b是交互句;表示双方空间上在一起,“丢沙包”的动作在时间序列上是相继的。如果按照例7)b′′的理解,那例7)b就不表交互义了,因为他们空间上没在一块玩沙包,只不过丢沙包的时间相同而已。“这排柱子距离2米”,是一个表意不完整的句子,也有两种理解:
7) c′ 柱子间相距2米。 c′′ 这排柱子与其他参照物(房子等)距离2米。
例7)c′′更符合汉语母语者的理解习惯,除了苟简了参照对象外,也不表示交互义,因为句子没有表达各个柱子彼此间的空间关系。例7)c′虽然表示交互义,但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同样的意思,人们通常说“这排柱子间距2米”,而不会说成例7)c这样句子。“间距”就是“之间距离”的省略表达,是明显的空间位置关系的表达。综上,例7)各句交互义强弱(交互的典型性)顺序如下,“他们打量对方”>“他们俩一起丢沙包”>“这排柱子距离2米”(“>”表示“强于”)。
(三)施受成分关系
首先,交互的施受成分构成来看,“个体交互”⑧的交互关系比“全体交互”的交互关系更具典型性。其实,“个体交互”和“全体交互”的关系只是空间位置关系的隐喻表达或者说是在交互事件参与者内的投射而已。内部成员间的空间当然比所有成员构成的总体空间要小,距离要短。所以,“与会的伴郎伴娘都是情侣”比“我们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的交互典型性更强,而后者若非提醒或细致分析,则很难认为表达了交互义。
其次,互为施受的交互结构典型性强于单方施受的交互结构。如下两例,
8) a 两人转眼手来手去 ,劈挡撩打,身上衣物,片片碎裂翻飞
b 此时他正和张飞打的热闹,刀来矛去的,连续打了几十个回合了
两句的施受关系可以分别图解如下:

例8)a句中的主语“两人”是“手来手去”打击的共同对象,因而施受同体,是典型的交互句。而例8)b就有不同了:如果把“他和张飞”中的两人分别对待,那么“他”只是“刀来”的施事,“矛去”的受事;“张飞”只是“矛去”的施事,“刀来”的受事;它们都不是“刀来矛去”的共同施受体。这种只表示单一方向的施受关系,我们称之为“单方施受”。但是,在日常识解过程中,人们通过“组块”心理把“他和张飞”视为一个集合,把“刀来矛去”视为一个集合。然后在类推的作用下,把组块后的“他和张飞”与“刀来矛去”视作同为施受关系,句子因而具有了交互义。真因为例8)b的交互义是经过几重心理认知转折而来,所以它表现出的交互义,其强度明显弱于例8)a。这种判断与我们的语感也是相符合的。
两句的不同也可以用语义指向来分析:例8)a中“手来手去”的语义共同指向“两人”即打架的双方;例8)b的谓词“刀来”指向“张飞”,而“矛去”的对象是“他”。语义指向的对象不同,导致句子表达交互义的强弱也存在差异。
三 结语
交互现象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人类社会关系在语言中的投射。汉语是形态标记缺乏的语言,其交互义常常以蕴含的方式表达,所以汉语交互结构如何判定,学者们也是见仁见智,没有一致的观点。本文从汉语交互式的区别特征出发,归纳出四条参考标准来帮助我们判定汉语交互句:
第一,深层语义上的主语为复数且不带宾语⑨;
第二,主语之间或主宾语之间是施受关系时,语义上应该为“同为施受”关系;
第三,主语构成成员间为共事关系时,其成员间应该具有相互依存的特点;
第四,交互标志并不是汉语交互结构的必然参项,但仍然是最直观的特点。
语言概念范畴间的具有连续性和界限模糊性的特点,因此,将语言作为典型性由弱到强的连续统来研究,有时可能更加适切些。汉语交互式的典型性,可以从以下几条来观察:
首先,有明确的形式标记的交互比没有标记的交互事件更典型。
其次,句子中没有交互标记时,交互事件参与者间的时空距离越近,交互性就越典型。
第三,着眼于交互事件参与者个体间的交互关系比着眼于全体的交互关系更具典型性。
第四,互为施受交互结构的典型性强于单方施受的交互性。
汉语的交互表达方式有多种,有交互词语、交互句式和语用交互,而交互句式包括交互性单句和交互复句。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单句内的交互,其他交互形式在句法结构、语法功能、语义特征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附记】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切中肯綮的意见,文中尚存纰漏,悉归笔者。
胡平 2016 论“隐涵义规约化”对多义词形成的作用——以“婊子”为个案,《汉语史研究集刊》第21辑,巴蜀书社。
李兰霞、王若江 2014 试论交互语素构词模式,《语文学习》第2期。
李临定 1990 《现代汉语动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丹青 1983 亲属关系名词的综合研究,《语文研究》第4期。
刘丹青 1987a 汉语相向动词初探,《语言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
刘丹青 1987b 形名同现及形容词的向,《南京师大学报》第3期。
刘丹青 2000 汉语相互性实词配价及其教学,沈阳主编《配价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刘丹青 2008 《语法调查手册》,上海教育出版社。
吕叔湘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吕叔湘 1988 说互相,《汉语学习》第1期。
谭景春 1992 双向和多指形容词及相关的句法关系,《中国语文》第2期。
唐贤清 2006 副词“互相”、“相互”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古汉语研究》第4期。
陶红印 1987 相互动词及相互动词句,《句型和动词》,语文出版社。
魏海平 2015 交互义语素“相”、“互”与双音节词汇的搭配限制研究,《语言学刊》第6期。
颜明、肖奚强 2012 “相”“互”及“相V”“互V”句法功能论略,《语言研究》第3期。
张谊生 1996 交互类短语与连介兼类词的分化,《中国语文》第5期。
张谊生 1997 交互动词的配价研究,《语言研究》第1期。
赵静 1999 试论“互相”类副词的功能、分布及其语义指向,《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周国光 1990 关系集合名词及其判断句,《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en 2003,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rtin Haspelmath 2007 Further remarks on reciprocal constructions,, 1-30.
Riemer Nick 201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 M. W. Dixon 201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ladimir P. Nedjalkov 2007,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①本文所谓“同为施受”指的是,事件的参与者同时充当彼此的施事和受事两种语义角色的语言现象。
②刘丹青(1986)研究表明,A2、A3和B2、B3类动词均为带宾语的及物交互动词。据他统计,现代汉语中所有的及物类交互动词共104个,占所有497个交互动词的20.9%,是少数派
③表中的“+”表示肯定,“-”表示否定,“±”则表示不确定。
④现实话语中,主语成分间、主宾语间除了施受关系、共事关系外,还有与事等语义关系。例如:
a 我遇见他。 b 我帮他学汉语。 c 我向他敬酒。 d 我和他商量这件事。
a句,是交互句,“我”和“他”是典型的施事主语和受事宾语;在深层语义上该句的主语为“我和他”,没有受事宾语。详见前面讨论。
b句是个连动句(传统语法称为兼语句),句子包含两个次事件:一是我帮他,另一是他学汉语。两个子事件虽然都是施受关系,但都是单向施受关系而非“同为施受”关系,因而不是交互句。一旦构成复句“我帮他学汉语,他帮我学英语”,则表达了交互义。刘丹青(2008:195)把这种情况称为“回环格式”。人们在识解回环格式时,在格赖斯数量原则的作用下,将复句重新组块成“我和他互相帮助,我们学习汉语和英语”。故而,在深层语义上,该类复句表达了比较明显的交互意义。
c句中“我”是施事,“酒”是受事,而“他”则是与事宾语(间接宾语)。句c已是最小子事件,不能下分次事件,句子的主语和宾语间不存在同为施受的关系。但如果句子组成“我向他敬酒,他向我敬酒”,就又构成了表交互义的回环格式了。另外,句子“我敬他”则有两种可能的理解:一是,“我敬他(烟、酒等东西)”;二是,“我尊敬他”。前者的“他”是与事宾语,后者是“受事宾语”,两种理解的主宾语之间都不存在“同为施受”关系,因此都没有交互义。
d句所表述的整体事件由两个子事件构成,一个是“我和他商量”,另一个是“商量这件事”;前者是交互事件,后者为一般事件。交互子事件不带宾语,它的施事主语是“我和他”,是共事关系,他们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否则子事件就不能自足。“商量”等本身就表示交互义的词语,其主语必须为复数,其共事主语或者全在表层结构表现出来,或者隐含一部分;前者如句4(d),后者如“我在商量问题”。由于受自身语义限制,“商量”不能接具体物质名词,如不能说“*我商量他”或“*他们在商量笔”,而只能说“我在商量他上学的事”或“他们在商量笔的销售问题”。
(*本部分根据匿名评审专家的重要意见而补充,谨致谢忱!为了保持正文结构的完整性,本部分放在注释中来讨论。)
⑤所谓“相互依存”就是指事件参与者以彼此为对象或目标而展开行为的关系,缺了任何一方该事件都不自足。
⑥这里所说的宾语是专指交互事件中的受事宾语而言,不包括非交互事件中的宾语,也不含交互事件中与事等其他语义角色宾语。
⑦Dixon(2012)根据交互主体的空间位置关系,将交互分为“完全交互”(full reciprocal)和“线性交互”(linear reciprocal)。“完全交互”指的是主语参与者成员两两互为施受关系,空间上两两一一对应。如句子(1)Aisha and Pedro pinched each other(本例取自Haspelmath 2007)这句话可以做如下扩展理解:
(1)a Aisha pinched Pedro b Pedro pinched Aisha.
Pedro的施事和受事都是Aisha,反之,Aisha的施事和受事亦然。他们互为施受关系。“线性交互指”的是主语参与者在空间上依次先后为施事和受事。如:
(2)The guests followed each other.
句中guests是follow的施事和受事,但是具体的每个guest所施加动作follow的对象和接受动作follow的来源并不是同一个人,而是在线性空间上的前后guest。因此,这句话只能扩展为:
(2)a The guests followed the front guest b The guests be followed by the behind guest.
显然,前后guest并非同一人。
根据主语参与者间交互动作发生的时间序列不同,Dixon(2012)又把交互分为“共时交互”和“相继交互”。“共时交互”指的是交互动作同时发生,如“John and Mary are married to each other”句中John和Mary结婚是同时进行的。“相继交互”指的是参与者前后相继给对方施加同一动作。如“Peter and Bill write letters to each other”中,“write letter” 显然不可能同时发生而只能是依次交替进行。
Dixon从交互参与者的空间位置关系和动作行为的时间先后关系,对交互进行了下位切分。该切分深入到了交互发生的具体时空层面,可谓细致入微,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⑧着眼于参与者全体的交互式施受关系称为“全体交互”施受关系,把着眼于参与者个体的交互式施受关系称为“个体交互”施受关系。如,“贫苦百姓团结起来闹革命”强调全体成员 “团结起来”(他们既是“团结”的主语,又是它的宾语),而不是个体间两两团结。因此,该句就是“全体交互”施受关系。
⑨这里所说的宾语是专指交互事件中的受事宾语而言,不包括非交互事件中的宾语,也不含交互事件中与事等其他语义角色宾语。
The Criterions and the Typicality Analysis of Chinese Reciprocal Relation
LIU Yun-feng1,2and SHI Qin1
(1.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ubei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62, China;2. The humanities Department, Yuzh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103, China)
The criterions of determining Chinese reciprocal constructions are such: the subject are plural and without object in underlying semantics; the semantic relation between subjects or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is “act as agent and patient simultaneous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subject is codependence. The typicality of Chinese reciprocal constructions is such: The reciprocal structure with markers is more typical than without ones; when without markers, the participants of reciprocal events which have the closer distance in space-time between each other are more typical; the individual reciprocal is more typical than the general ones; the reciprocal whose participants act as agent and patient mutually is more typical than act as agent and patient alone.
Reciprocal; Criterions; Typical category
H146
A
1000-1263(2018)01-0022-08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类型学视角下的明清汉语语法研究”(15ZDB098)
刘云峰,男,1975 年生,江西峡江人,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史、语言学;石锓,男,l962 年生,湖南临澧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史、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