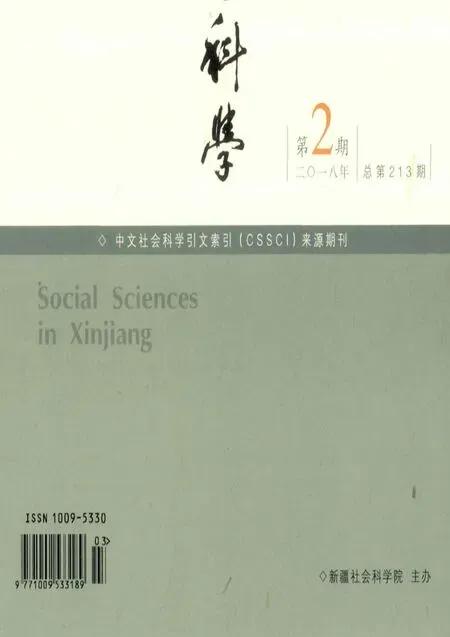“新奥斯曼主义”:历史嬗变与影响
2018-05-24张向荣
张向荣
近年来“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成为国内外媒体和学者频繁提到的一个词汇,往往用来特指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政府的外交理念和外交路线。不过,“新奥斯曼主义”这一概念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现,当时用来指代厄扎尔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有学者指出正发党政府提出了“新奥斯曼主义”的外交政策,这种说法有待商榷,因为正发党从来没有提出名为“新奥斯曼主义”的外交战略或者外交政策,其领导人埃尔多安和达武特奥卢多次反对外界将其外交政策称为“新奥斯曼主义”。也有学者在文章中谈到“新奥斯曼主义”用来论述正发党亲近中东、疏远西方的伊斯兰化的外交倾向,其实是将“新奥斯曼主义”等同于“伊斯兰主义”。巴尔干国家的部分学者则将土耳其任何介入国外事务的政策称为“新奥斯曼主义”。此外,那些用“新奥斯曼主义”来表述正发党对外政策的学者对于这一政策的具体内容也有不同的看法。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同、指代的含义不同,造成了这一词汇在使用中出现了认知上的混乱和逻辑上的矛盾。本文将对 “新奥斯曼主义”这一概念进行辨析,分析其历史渊源及演化过程,并探讨它对当代土耳其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影响。
一、“新奥斯曼主义”的概念辨析
“新奥斯曼主义”并非一个新词,戴维德·巴查德(David Barchard)1985年首次提出这一词汇,用来指代时任土耳其总理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Özal)*厄扎尔是土耳其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政治家,1983~1989年任土耳其共和国总理,1989~1993年当选土耳其总统。在80年代中后期迥异于凯末尔主义的经济改革和外交理念。*David Barchard,Turkey and the West,Bost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1985,p.91.凯末尔·卡尔帕特(Kemal Karpat)则认为“新奥斯曼主义”这一术语最早是在1974年土耳其军队出兵塞浦路斯后被希腊媒体用来谴责土耳其对外政策中的扩张倾向,*Kemal Karpat, Studies on Ottoman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Selected Articles and Essays,Brill,2002,p.524.因而是一个明显带有贬义的词。媒体和学术界广泛使用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在21世纪初期正发党在土耳其执政以后。格雷厄姆·富勒(Graham Fuller)在1992年将“新奥斯曼主义”解释为“重新恢复的对前奥斯曼帝国统治区域及当地穆斯林的关注和兴趣”*Graham Fuller,Turkey Faces East: New Orientations toward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old Soviet Union,Santa Monica,Rand Corporation,1992,p.13.。也有学者认为“新奥斯曼主义”一词是由坚吉兹·钱达尔(Cengiz Çandar)提出来的。*④ Alexander Murinson, The Strategic Depth Doctrin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42,No.6,2006,p.946、947.坚吉兹·钱达尔曾担任厄扎尔的政策顾问,对厄扎尔的“新奥斯曼主义”路线有重要影响,1993年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凯末尔主义使土耳其孤立自守,现在是时候重新思考这一政策了”④。
1993年,厄扎尔突然去世,“新奥斯曼主义”失去动力,这一词汇很少再见诸报端。正发党执政后,这一概念重新被学者和媒体采用,并引发了一场争论。但不管是厄扎尔、还是正发党的领导人从来不使用这一词汇,担心会给外界造成“帝国主义”和“扩张野心”的印象。达武特奥卢多次明确反对“新奥斯曼主义”这一提法,2009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从来没用过这个词,这一术语从来就不是一个善意的词汇”*Hakan Ovunc Ongur, Identifying Ottomanisms:The Discursive Evolution of Ottoman Pasts in the Turkish Presents,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51,No.3,2015,p.425.;2011年他再次强调“新奥斯曼主义是一个别有用心的词汇……我不是一个新奥斯曼主义者,事实上不存在这样的政策”*Davutoglu,I am not a Neo-Ottoman,Balkan Insight,No.26,April 2011, http://www.balkaninsight.com/en/article/davutoglu-i-m-not-a-neo-ottoman, 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0月21日。。不过,将“新奥斯曼主义”作为理解厄扎尔和正发党政治外交理念的框架是有价值的。总体来说,厄扎尔时期(1983~1993年)是“新奥斯曼主义”形成的第一个阶段,而正发党执政以来(2002年至今)是“新奥斯曼主义”的第二个阶段;厄扎尔和达武特奥卢是影响“新奥斯曼主义”形成和发展的两个关键人物。要理解“新奥斯曼主义”,有必要追溯到“奥斯曼主义”并考察其内涵及影响。当然,本文主要探讨它对后来的“新奥斯曼主义”产生直接影响的思想元素。
二、帝国的衰落与“奥斯曼主义”
从18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逐渐衰落,与开启了工业化进程的欧洲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土耳其国内有识之士认识到实行西方化改革势在必行。1839年,帝国颁布《坦齐马特法令》,开启了著名的“坦齐马特改革”,其中有一项法令首次规定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成为“奥斯曼主义”的雏形。*Gülalp Haldun,Using Islam as Political Ideology:Turk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ultural Dynamics,2002,Vol.14, No.1,p.23.19世纪60年代奥斯曼帝国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思想家,他们意识到“坦齐马特改革”的种种问题,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要求限制苏丹的权力,建立议会。他们组建了一个秘密的政治社团,名为“爱国联盟”,也称“青年奥斯曼党”,凯末尔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试图探索一种将伊斯兰教与民主制相融合的制度,*Ahmet Sö zen,A Paradigm Shift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Transition and Challenges,Turkish Studies,2010,Vol.11,No.1,p.106.这在后来成为土耳其“伊斯兰民主”的滥觞。凯末尔可谓“奥斯曼主义”的真正奠基人,他明确提出,居住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人,无论何种信仰和语言,都是奥斯曼人,有学者将这一思想称为“奥斯曼主义”。*悉纳·阿克辛:《土耳其的崛起》,吴奇俊、刘春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2页。凯末尔强调伊斯兰作为爱国主义的基础,但并未将非穆斯林排除在奥斯曼共同体之外,在他看来,宗教、语言、族群的多元共存并非奥斯曼国家形成的障碍,而有效的教育是解决问题、减少文化差异的关键,可以在年轻人中间激发爱国主义。*Ahmet eyhum,Islamist Thinkers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Turkish Republic,Brill,2015,p.9.这种“奥斯曼主义”后来逐渐被奥斯曼政府接受,成为一种官方哲学和主流意识形态,对1876年宪法的颁布产生了直接影响。

事实证明,“奥斯曼主义”不但没有弥合帝国境内不同宗教、种族的差异和裂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各种矛盾,甚至使彼此的冲突更早地爆发。基督徒将“奥斯曼主义”视为巩固和扩张穆斯林权力的一种手段,而穆斯林认为“奥斯曼主义”中的世俗主义倾向会削弱他们的文化自治传统,甚至怀疑政府要放弃伊斯兰教在帝国享有的尊崇地位。*Kemal H.Karpat,Ottoman Past and Today's Turkey,Brill,2000,p.7、8.正是由于“奥斯曼主义”的内在困境,奥斯曼官方往往根据不同的听众,对奥斯曼主义作出不同的解释。*Hannes Grandits,Conficting Loyalties in The Balkans:The Great Powers, the Ottomans Empire and Nation-Building,I.b.Tauris and Co Ltd,2011,p.164.如果说1912年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等非穆斯林发起的巴尔干战争重创了奥斯曼主义,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穆斯林同胞——阿拉伯人的“反叛”则彻底击碎了奥斯曼共同体的幻梦,证明了这种强行将各民族粘合在一起的奥斯曼主义在新兴的民族主义大潮面前是多么不合时宜。青年土耳其党(1908~1918年)和凯末尔主义者以穆斯林为基础建构了新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来取代“奥斯曼主义”。*L.Carl Brown,Imperical Legacy:The Ottoman Imprint on the Balkans and the Middle East Brow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 p.139.
土耳其民族主义与“奥斯曼主义”既有本质的差别,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奥斯曼主义”是奥斯曼帝国框架下的一种特殊的民族主义,是青年奥斯曼人试图对抗帝国境内非穆斯林群体带有分离倾向的民族主义而提出的,仍然是一种传统的臣民概念;而土耳其民族主义是为构建一种新的政治实体认同,挽救国家危亡,后来被凯末尔主义者所继承和发展,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内涵。“奥斯曼主义”虽赋予了非穆斯林群体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但其基础仍然是伊斯兰认同;而土耳其主义则放弃了帝国外衣,本质上与巴尔干民族主义一样,是一种以单一种族为核心的民族主义,但由于其社会的特殊性,伊斯兰认同仍然是土耳其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奥斯曼主义”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主张以国家的力量创造一个奥斯曼民族,“赋予奥斯曼民族一个统归于单一国家的新的民族性,有点类似于美利坚民族”*昝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15页。。而凯末尔的民族主义采取现实主义态度,由于国家实力所限,构建以安纳托利亚为中心的国族,将“土耳其人”严格限定在土耳其现有疆域内。凯末尔拒绝一切脱离实际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凯末尔主义者将奥斯曼的遗产视为负担和包袱,认为土耳其和其他巴尔干国家一样,是一个新生的国家,也是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受害者,试图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摆脱奥斯曼的负面影响。
三、冷战变局与厄扎尔时期的“新奥斯曼主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为厄扎尔的“新奥斯曼主义”提供了土壤。从国际环境和地缘格局来讲,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土耳其周边地缘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长期以来被土耳其视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苏联消失,俄罗斯实力大幅缩水,土耳其的安全环境得以缓解。新出现的中亚五国都是穆斯林为主的国家,除塔吉克斯坦外,其他四国都属于突厥语族国家,在族源和语言方面与土耳其存在较深的联系,对土耳其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外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成为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新的地缘屏障和缓冲地带。更重要的是,从阿塞拜疆经里海到中亚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突厥语族国家带,这对于土耳其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地缘现实和战略机遇。以厄扎尔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家、学者认为土耳其正面临着四百年来未有之机遇,在新形势下土耳其应该具备“帝国视野”并寻求在原奥斯曼统治地区的领导权。*aban Çali,Turkey’s Balkan Policy in the Early 1990s,Turkish Studies,Vol.2,No.1, 2001,p.136.厄扎尔一方面利用伊斯兰教和共同的历史文化积极发展与原奥斯曼统治区域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他的视野突破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框架,远及中亚和中国新疆。厄扎尔等人的一些言论,如“从亚得里亚海到中国的长城的突厥世界”“下个世纪是土耳其人(突厥人)的世纪”,清楚地表明了土耳其“新奥斯曼主义”的狂热和躁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土耳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83年担任总理的厄扎尔在国内推行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推动了土耳其经济的恢复和增长,在国内外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厄扎尔领导的祖国党在1983年选举中赢得了45%的支持率,厄扎尔挽救了土耳其的经济,在他任期内土耳其的经济和进出口增长率非常高,有人称之为“厄扎尔革命”。经济自由化改革和对媒体管制的放松创造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土耳其国内各种社会思潮空前活跃。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人分离运动愈演愈烈,库尔德问题上升为土耳其国内政治中的主要议题。土耳其社会出现了反思凯末尔主义的思潮,有人认为凯末尔在1922年废除哈里发引发了库尔德人的反叛,凯末尔“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建构使得传统联结库尔德人的宗教纽带消失。他们主张重新审视奥斯曼遗产,试图从历史中寻求一种类似于奥斯曼帝国时期可以让不同族群普遍接受的共同认同。
在国内政治层面,厄扎尔试图用“新奥斯曼主义”解决土耳其国内社会不同群体多元认同的紧张关系;在对外关系方面,则以“新奥斯曼主义”为武器,在巩固与西方关系的同时,积极增强在中东伊斯兰国家、中亚突厥语族国家中独特的影响力,追求土耳其的大国地位。从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两个维度来说,厄扎尔的“新奥斯曼主义”有如下特点:
1.重新思考宗教与国家的关系
凯末尔将宗教置于国家的控制和监督之下,清除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并严格限定伊斯兰教在社会中的活动范围,最终目的是与欧洲文明接轨,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厄扎尔的“新奥斯曼主义”在国内层面上最重要的特征是重新思考宗教和世俗国家的关系,认为宗教是土耳其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该给伊斯兰教更多表达的权利,而伊斯兰教并不是必然反西方的。*Mustafa Gokhan Sahin,Turkey and Neo-Ottomanism:Domestic Sources,Dynamics and Foreign Policy,Dissertations & Theses,Gradworks,2010, p.177、175.在厄扎尔等人看来,土耳其应该在传统社会与现代化变革之间走第三条道路,既不拒绝变革、也不盲目地接受西方化,他们辩解说不是要挑战凯末尔遗产、也不是要伊斯兰化,而是在新形势下对凯末尔世俗主义的一种修正。
2.重新看待“奥斯曼遗产”
凯末尔主义者认为奥斯曼的政治体制和宗教文化导致土耳其的落后和腐败,为融入欧洲文明体系,凯末尔强力推动宗教和文字改革,从文化和语言上切断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厄扎尔则主张重新对待奥斯曼遗产,他将奥斯曼的历史视为土耳其加入“西方俱乐部”的优势而非负担。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厄扎尔与土耳其不同时期的伊斯兰运动都有密切的联系。据说他是纳克什班迪教团的成员,曾经参加埃尔巴坎创立的伊斯兰政党救国党,也是居伦运动的支持者。*Mustafa Gokhan Sahin,Turkey and Neo-Ottomanism:Domestic Sources,Dynamics and Foreign Policy,Dissertations & Theses,Gradworks,2010, p.177、175.厄扎尔说:“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正如在帝国时代那样,我们能够维持一种超越种族差异的文化和政治认同,我相信伊斯兰是构成这种认同的最重要的部分。”*Lerna Yank,Constructing Turkish “Exceptionalism”:Discourses of Liminality and Hybridity in Post-Cold War Turkish Foreign Policy,Political Geography,Vol.30,No.2,2011,p. 85.在对外关系层面,厄扎尔强调奥斯曼遗产和伊斯兰文化作为土耳其软实力的来源,以此增强土耳其的国际地位。在他看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给中东、巴尔干等动荡地区带来了史上时间最长的和平。*Hakan Ovunc Ongur,Identifying Ottomanisms:The Discursive Evolution of Ottoman Pasts in the Turkish Presents,p.423.他还提到奥斯曼帝国宗教和文化的多元性,他认为奥斯曼的政治文化系统可以成为20世纪土耳其完美的模式。他说“在波斯尼亚、科索沃、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我们看到与阿拉伯国家完全不同的伊斯兰——突厥化的伊斯兰、更加温和的伊斯兰,一种适合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伊斯兰”,以此强调奥斯曼和土耳其模式的特殊性和优越性。
3.改变对西方和西方文明的看法
有人认为凯末尔代表了土耳其的共和主义,而厄扎尔则是土耳其自由主义的代表。1950年,厄扎尔从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电力工程专业毕业,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有在美国生活的经历,对美国的自由主义非常推崇,认为美国的成功源于自由主义,而奥斯曼帝国与美国都是多元文化的“熔炉”, 具有相似的政治结构——民族、经济、文化、宗教方面的多样化。*Yilmaz Çolak, Ottomanism vs. Kemalism: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Pluralism in 1990s Turkey,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42,No.4,2006,p.592.厄扎尔对西方的看法与凯末尔主义者不同。凯末尔将欧洲视为文明和现代化的唯一标杆,推行激进的西方化改革,认为这是保证土耳其国家生存的唯一选择;厄扎尔则认为土耳其的落后在于缺乏自由主义和科学思维,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在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进行选择,土耳其不是必须经历欧洲的启蒙运动,可以直接采用西方文明的成果。*Laçiner Sedat,Özalism (Neo-Ottomanism):An Alternative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Journal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vol.1,No.1,2003,p.170、162、169、169.凯末尔推行西方化改革,但并不代表他在内心信任和亲近西方国家;相反,凯末尔主义者对欧洲大国一直怀有强烈的警惕和不信任感,总是怀疑西方冠冕堂皇的话语背后真实的意图,警惕西方支持土耳其国内的分离势力、干涉土耳其内政,最终达到分裂土耳其的目的。而厄扎尔的个人经历和他执政期间土耳其的经济成就和国家实力的增强使其对西方更为信任,他认为只有与西方整合,才能保证土耳其的安全。1987年,厄扎尔政府提交了加入欧共体的申请,他认为世俗的、多元的文化已经在土耳其扎根,加入欧共体会进一步促进土耳其的民主化,他强调欧洲的多元化,努力使欧洲人接受土耳其是欧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即欧洲的穆斯林的观念。
4.积极的干涉主义与大国雄心
凯末尔主义者恪守凯末尔“国内和平,世界和平”的信条,一直避免介入周边国家的内部事务。厄扎尔公开批评这种政策,认为面对前所未有的国际机遇,凯末尔主义显得太过保守,他说“事情已经发生变化……土耳其应该抛弃之前消极、迟疑的政策,采取积极的政策”*Laçiner Sedat,Özalism (Neo-Ottomanism):An Alternative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Journal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vol.1,No.1,2003,p.170、162、169、169.。海湾战争结束以后,厄扎尔以伊拉克库尔德人的保护者自居,针对萨达姆政府在伊拉克北部对库尔德人的镇压活动,他说“东南部(土耳其)的人是我们的兄弟,伊拉克北部地区的人是他们的兄弟,那也应该是我们的兄弟……土耳其在过去忽略了伊拉克北部发生的事情,我们说那是我们国界以外的事情,与我们无关。这种政策必须改变。土耳其的新政策应该是如果巴格达在那儿进行另外一场暴行,我们将反对”*Laçiner Sedat,Özalism (Neo-Ottomanism):An Alternative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Journal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vol.1,No.1,2003,p.170、162、169、169.。他暗示唯一能在中东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方案是组成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之间的联邦。对于保加利亚对境内土耳其人的同化和迫害政策,*1986~1989年,保加利亚日夫科夫政府对国内的土耳其人实行民族同化和排挤政策,导致30万土耳其裔保加利亚人迁往土耳其。厄扎尔威胁要进行军事干涉。他在波黑危机中的态度最能反映厄扎尔时期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转向。土耳其努力说服北约介入南斯拉夫内战,以保护波黑的穆斯林。1993年2月13日,厄扎尔在伊斯坦布尔参加了针对波斯尼亚危机的示威游行,以抗议塞族对穆斯林的“暴行”。厄扎尔的政策改变了土耳其建国以来不介入周边国家国内政治的传统。
大国雄心和追求大国地位是厄扎尔时期“新奥斯曼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厄扎尔提出了“再造一个伟大的土耳其”的口号。他将新出现的突厥语族国家视为土耳其的战略依托,试图通过经济和文化手段确立在突厥语系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厄扎尔宣称土耳其的发展模式和政治体制比俄罗斯、伊朗、沙特更适用于中亚国家。厄扎尔频繁出访突厥语系国家,与这些国家签署了一系列涉及经济、贸易、教育、卫生、文化等各领域的合作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了4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70亿美元的贷款。*Laçiner Sedat,Özalism (Neo-Ottomanism):An Alternative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Journal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vol.1,No.1,2003,p.170、162、169、169.土耳其外交部设立了专门处理与中亚和高加索国家关系的新机构。除了官方活动外,厄扎尔积极鼓励土耳其企业、社会组织、宗教团体进入中亚,土耳其在中亚的公共外交空前活跃。
四、正发党执政以来“新奥斯曼主义”的演进与异变
2002年,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对外政策呈现出“范式”转换,很多学者将其外交政策称为“新奥斯曼主义”。正发党的“新奥斯曼主义”与厄扎尔时期的“新奥斯曼主义”一脉相承,可以说是厄扎尔“新奥斯曼主义”在新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下的发展和演化。两个阶段的“新奥斯曼主义”都主张重新看待和评价奥斯曼遗产,都试图从奥斯曼历史、制度、文化和经验中寻求适用的工具,以解决当代土耳其在国内和国际上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厄扎尔时期“新奥斯曼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外交和对外关系层面,正发党的“新奥斯曼主义”不但体现在对外政策领域,而且具有了政治和社会维度,在土耳其政治和社会中同样影响巨大。
一般认为,达武特奥卢*达武特奥卢毕业于博斯普普斯大学,能讲流利的阿拉伯语,早年在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大学讲学,回国后在马尔马拉大学任教,后成为贝伊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研究领域涉及政治学、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哲学和历史学。2001年出版了《战略纵深:土耳其的国际地位》一书,2002年他成为正发党领导人埃尔多安的主要外交顾问,2009年被任命为土耳其外交部长,2014年担任政府总理,2016年5月5日宣布辞去土耳其总理和正发党主席职务。是正发党外交路线的主要设计师。在其著作《战略纵深:土耳其的国际地位》(Strategik Derinlik, Turkiye’nin Uluslararasi Konumu)(以下简称《战略纵深》)*由于达武特奥卢不愿意其《战略纵深》被翻译为英文,该书迄今为止没有英文版。一书中,集中阐述了他对土耳其国际地位和外交战略的思考。其核心观点:一国在国际上的价值是以其地缘位置和历史纵深为基础的,基于土耳其独特的地缘位置和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这一历史遗产,土耳其可以成为国际体系中有分量的大国;土耳其与巴尔干、中东乃至中亚存在文化联系和共同的历史,土耳其传统的政策忽视了这些对于土耳其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应该重点发展与这些地区的关系,以增进土耳其的影响力。
随着达武特奥卢从学者向政策顾问、外交家、政治家的角色转变,他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和言论不可避免地出现前后不一致乃至相互矛盾的情况,因而必须综合考察其外交理念和正发党的对外政策。达武特奥卢的“战略纵深主义”是对厄扎尔时期“新奥斯曼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正发党的“新奥斯曼主义”有了新的表现和特征。
1.利用奥斯曼遗产,积极介入地区事务

达武特奥卢认为土耳其应该放弃保守、怯懦的外交政策,积极介入地区乃至全球事务。他认为冷战以后土耳其面临着与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类似的形势:国际体系中国家间权力的重新配置;寻求新的政治认同以应对上升中的民族主义;新思想与传统价值之间的平衡;整合进入欧洲体系(维也纳协调与欧盟);与超级大国(英国和美国)的协调。*Mustafa Gokhan Sahin,Turkey and Neo-Ottomanism:Domestic Sources,Dynamics and Foreign Policy,p.182.他强调在国际和国内新形势下,土耳其处在东西方之间这一地缘位置,就是可以兼顾东西,因而要改变冷战期间完全倒向西方的战略,实行更为平衡的政策。
2.不甘于“桥梁”国家的定位,力图做中心国家
凯末尔建国以来,土耳其将自身定位为欧洲的一部分,强调自己欧洲国家的身份认同。达武特奥卢认为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在文化上多元化、地缘上涵盖多个地区的帝国,土耳其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不应该做欧亚之间的桥梁国家,而应该做亚洲、欧洲和非洲之间的中心国家,成为原奥斯曼统治区域的领导国家。在《战略纵深》一书中,他将“桥梁”国家划分为两类,有强烈的认同和自信的国家和没有自信、遵循实用主义的国家,*Lerna Yank,Constructing Turkish “Exceptionalism”:Discourses of Liminality and Hybridity in Post-Cold War Turkish Foreign Policy,p.87.并暗指土耳其应该属于前一种。在2008年接受采访时,他说处于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土耳其既不应该做“桥梁”国家,也不应该做“前沿”国家,更不应该做普通国家,而应该做中心国家。*lu,Turkey’s Foreign Policy Vision:an Assessment of 2007,Insight Turkey,2008,Vol.10,No.1,p.78.
达武特奥卢将土耳其视为地区乃至世界政治的中心,认为土耳其的地缘位置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他说如果世界有一个中心点,那就是伊斯坦布尔。他批评凯末尔主义者没有意识到土耳其深厚的历史和独特的地理空间优势。按照他的观点,地理纵深是历史纵深的一部分,土耳其既是黑海国家又是地中海国家、既是亚洲国家也是欧洲国家、既是中东国家也是高加索国家,这种地理纵深使土耳其处于多个地缘政治影响的中心。在中东、黑海、高加索,土耳其应该利用其历史和地缘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相比厄扎尔的以融入西方为目标,达武特奥卢和正发党追求更为宏大的目标,试图成为中心国家和全球性角色。
3.开展积极、多维外交和调解外交
厄扎尔虽然主张积极发展土耳其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但仍然坚持以西方作为土耳其主要的战略方向,认为欧盟在很多方面需要土耳其,所以迟早要接纳土耳其。达武特奥卢则认为欧盟不会真心接纳土耳其,欧盟希望与土耳其维持一种特殊伙伴关系,因而土耳其不能消极地在欧盟的大门之外等待,而应该利用地缘优势,采取一种真正的多维外交。*Murinson Alexander,The Strategic Depth Doctrin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 42,No.6,2006,p.952.土耳其应该采取积极的、建设性的政策,为周边地区提供秩序、稳定和安全。达武特奥卢批评之前的政府对“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消极态度,在正发党的积极活动下,2004年首次由土耳其人担任“伊斯兰会议组织”的秘书长。土耳其全面加强与俄罗斯在政治、经济、能源和军事领域的合作,更不顾西方的强烈反对承认哈马斯,加强与苏丹、叙利亚、伊朗等西方眼中的“无赖国家”的接触与合作。

4.正发党“新奥斯曼主义”的异变
在正发党的前两个任期内,正发党在推进国内民主化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达武特奥卢提出的“邻国零问题”外交也取得了实质性成果,土耳其有效改善了与所有邻国的关系,与中东、巴尔干、高加索等周边地区国家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水平。然而,从正发党的第三个任期开始,特别是“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土耳其的内政和外交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达武特奥卢说“民主社会是土耳其主要的软实力……可以成为中东国家的榜样”*Türke,Decomposing Neo-Ottoman Hegemony,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Vol.18,No.3,2016,p.200.,但是埃尔多安的威权主义倾向和专断作风破坏了正发党党内民主、团结的气氛,包括阿卜杜拉·居尔在内的一批元老被清洗,正发党日益成为埃尔多安的一言堂。*达武特奥卢担任总理以后,与总统埃尔多安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的分歧和矛盾持续加大,达武特奥卢逐渐被架空,在埃尔多安的压力下,2016年5月达武特奥卢宣布辞去土耳其总理职务。另外,正发党利用国家权力在国内政治中压制反对党,加强对媒体的管制,借未遂政变排除异己,土耳其的民主遭到严重破坏。正发党执政前两个任期曾采取了一些安抚库尔德人的政策,试图通过文化多元主义和伊斯兰纽带解决库尔德问题,承认库尔德人文化、语言方面的权利,库尔德问题有所缓和。随着地区局势和国内形势的变化,正发党对国内库尔德人的政策重新走向强硬,土耳其东南部自2015年7月以来再燃战火。*李秉忠、菲利普·罗宾斯:《土耳其埃尔多安政权的强势治理及其脆弱性》,《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1期。
“新奥斯曼主义”在对外政策层面也出现异变,谨慎、理性的“新奥斯曼主义”逐渐演变为狂热、冒进的“新奥斯曼主义”,埃尔多安的政策目标超出了土耳其的国家实力,“新奥斯曼主义”中意识形态的成分凸显,逐渐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而外交服务于国内政治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有学者批评埃尔多安在国内搞独裁、反民主,但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中东却推行所谓的“民主化”外交,支持叙利亚、埃及反政府势力。正发党曾经将土叙关系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和免签协议,然而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出于对国际形势的误判,土耳其冒险介入叙利亚内战,两国关系跌入历史低谷。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等叙利亚问题的溢出效应最终危及土耳其自身的安全和稳定,2016年发生“7·15”军事政变以后,土耳其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陷入困境。如果说帝国视野和文化多元是“新奥斯曼主义”的两根支柱,随着正发党执政地位的日益稳固,无论是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对外政策中,“新奥斯曼主义”强调“文化多元和共存”的一面黯然褪色,而“帝国视野和大国野心”和强调“伊斯兰世界的团结”的一面则日益突出。
五、余论
“新奥斯曼主义”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厄扎尔执政时期,成型于21世纪正发党执政以后,与奥斯曼帝国晚期出现的“奥斯曼主义”存在一定的历史联系:二者都试图解决分裂性民族主义带来的国家认同危机,并构建一种新的共同体的合法性秩序;都宣扬奥斯曼(土耳其)的特殊性和优越性,试图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寻找一条新的道路;都强调奥斯曼时期不同种族、宗教和文化群体在同一种实体内和平共处的历史。“奥斯曼主义”着眼于解决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内部危机,以救亡图存为目标,是一种带有防御性的政治思想;“新奥斯曼主义”反对凯末尔主义者割裂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系,主张回溯到奥斯曼的历史传统和经验解决当代土耳其的认同危机,重建土耳其的大国地位和地区影响,虽然也有国内政治的含义,但更多的是一种外交理念。“新奥斯曼主义”在土耳其国内政治中的含义是明确的,也没有贬义,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重新理解凯末尔的世俗主义,给伊斯兰教提供更多的政治和社会空间;第二,修正凯末尔“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国家概念,主张文化多元化,给库尔德人更多的自治和表达的权利。但是,作为一种外交政策的“新奥斯曼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似乎是含混不清、变动伸缩的,往往被视为一个带有贬义的词汇。考察从厄扎尔到埃尔多安两个阶段“新奥斯曼主义”的演化和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很强的连续性和共性:都将中东、巴尔干、高加索和中亚视为土耳其外交的重点和国家崛起的战略依托,对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做浪漫化和理想化的处理,利用奥斯曼遗产追求土耳其的大国地位。其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伊斯兰国家,强调同为穆斯林的伊斯兰认同和历史文化上的联系;第二,对非穆斯林国家,宣扬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宗教宽容和文化共存;第三,对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念念不忘,试图成为地区的领导国家进而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角色;*历史上中亚从来没有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但厄扎尔和正发党都积极扩大在中亚的影响力,试图成为突厥语系国家中的领袖,就是受到这一动机的驱动,土耳其的帝国视野也是奥斯曼遗产的一部分。第四,强调对海外土耳其人乃至穆斯林有保护的责任,甚至介入他国内部事务。如前文所述,土耳其在对外关系方面拒绝“新奥斯曼主义”的标签,但在国内政治中并非如此,正发党多次称自己是“新奥斯曼人”,连埃尔多安也称自己为“奥斯曼人的子孙”。
厄扎尔在推行“新奥斯曼主义”的理念和政策方面有些势单力薄,在政府内部和土耳其社会中不乏反对者,他的政治和外交思想带有不少折中色彩。而埃尔多安背后则有不少与他理念相近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在土耳其的政治和社会中更是拥有一大批忠实的拥趸。厄扎尔的“新奥斯曼主义”的影响主要局限在外交领域,在社会和公众当中影响较小;而正发党时期的“新奥斯曼主义”开始深入土耳其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活当中,甚至引发了近年来土耳其社会在建筑、艺术、音乐、餐饮等各领域兴起一股崇尚奥斯曼的风潮。与厄扎尔时期相比,“新奥斯曼主义”在当今的土耳其有着更为坚实的社会基础。
伊斯兰回潮是“新奥斯曼主义”的重要特征。“新奥斯曼主义”强调要超越世俗和宗教的二分法,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对凯末尔主义的反叛。如果说厄扎尔承认伊斯兰教是土耳其社会和国家认同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达武特奥卢则在伊斯兰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将伊斯兰教视为土耳其文明的支柱。正发党执政以来,“新奥斯曼主义”不仅仅是土耳其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也是土耳其国家认同的核心部分。
厄扎尔不反对西方并以融入西方作为土耳其主要的战略目标。在他看来,土耳其外交的转向不能以损害与西方的关系为代价,加强与突厥语系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发挥土耳其在这些地区独特的影响力,反而会提高土耳其在西方联盟中的战略价值和地位。总的来说,厄扎尔时期土耳其在地区事务中努力争取西方的支持,避免单边行动,*Didem Özdemir Albayrak,Neo-Ottomanism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hrough the Lenses of the Principal-Agent Theory,Rearch Gate,Vol.1,No.1, 2016,p.145.也不违背美国的战略和利益。正发党借入欧进程,肃清了军方在土耳其政治中的影响力,实现了对军队的管控,此后便日益暴露出越来越明显的反西方倾向。在政府和媒体的影响下,土耳其社会很多人将对奥斯曼的怀念和对西方大国的怨憎混合在一起,认为西方大国毁灭了奥斯曼帝国。*Igor Torbakov,Neo-Ottomanism Versus Neo-Eurasianism?Nationalism and Symbolic Geography in Postimperial Turkey and Russia,Mediterranean Quarterly,Vol.28,No.2,2017,p.137.正发党不甘于再做桥梁国家,试图成为中心国家乃至世界大国,它认为美国和欧盟固然重要,但更需要发展与疏远的邻国俄罗斯和伊朗的关系,发展与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关系,以平衡对西方的过度依赖。
与厄扎尔时期相比,埃尔多安政府对地区事务的介入和干涉更深,力度更大、范围更广。厄扎尔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波黑问题的介入是以服从美国的整体战略为前提的,埃尔多安则以损害与以色列甚至是西方的关系为代价来增强土耳其在伊斯兰国家中的影响力。可以说,正发党政府在“阿拉伯之春”后军事介入叙利亚内战,这在厄扎尔时期是不可想象的,是土耳其建国以来对外政策的重大转折。在正发党的大国雄心推动下,土耳其对重要利益区的划分已经超出奥斯曼原有领地范畴,强调土耳其在穆斯林世界的地位以及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历史联系,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土耳其的触角还伸向非洲和拉美。与厄扎尔时期相比,正发党时期的“新奥斯曼主义”并不限于原奥斯曼统治区域,它凸显的是土耳其的全球思维和大国抱负。塔纳斯科维奇认为可以把“新奥斯曼主义”界定为“一种将伊斯兰主义、突厥主义和奥斯曼帝国主义相混合的意识形态”。这一观点是极有见地的,“新奥斯曼主义”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土耳其的领导人往往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国家利益的需要从奥斯曼帝国历史的武器库中选择适用的工具,如在中东强调同为穆斯林的伊斯兰认同,在中亚强调突厥人相同的种族和语言,在巴尔干则强调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宽容和身为欧洲国家的历史和认同。
厄扎尔时期以及正发党执政前期,西方学者大多将“新奥斯曼主义”视为温和伊斯兰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结合,甚至有人认为“新奥斯曼主义”是美国“大中东战略”的补充。近几年,西方学者对土耳其的看法变得越来越悲观,美欧对土耳其亲近中东、偏离西方的政策非常担忧,对“新奥斯曼主义”基本持负面的看法,认为土耳其试图在原奥斯曼帝国统治区域恢复历史上的影响,在地区事务中争夺主导权。这种看法折射了欧美国家的利益考量和立场。如果从土耳其的历史和国情出发,奥斯曼被肢解的历史使得土耳其人心灵深处对西方的疑虑也从未消失。土耳其人曾经建立起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对其辉煌的历史和文明念念不忘,一直有追求大国地位的雄心,一旦土耳其在经济和现代化上取得成就、国家实力增强、对西方的安全依赖减弱,其追求大国地位的冲动便会不可遏制地萌发。“新奥斯曼主义”在土耳其存在深厚的政治和社会土壤,虽然达武特奥卢在2016年已经去职、埃尔多安的专制倾向也越来越明显,但无论今后土耳其政治走向如何,“新奥斯曼主义”在土耳其政治、社会和外交中的影响绝不会轻易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