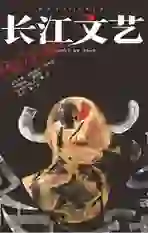厌倦与创造(创作谈)
2018-05-18徐则臣
徐则臣
这两个短篇,《古斯特城堡》和《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都与厌倦有关:前者为了克服厌倦,后者写的就是厌倦。
读了三十多年的书,看多了老三篇,能不看尽量不看;写作也二十年,老三篇写了肯定也不少,连自己都烦了,所以能不写也尽量不写。我想克服一下这个厌倦,来点别的,但机杼别出谈何容易。老三篇在某种意义上是所有人的极限。你想在别人已经到达的终点上再往前走半步都很难,你想在自己的极限处再往前走半步更难——这个终点和极限既是题材意义上的,也是艺术和思想意义上的。
艺术和思想上的终点和极限不难理解,高度到不了就是到不了,跟你是不是年轻力壮没关系。题材上的局限好像有些费解,不就换个领域写写吗,原来写打铁的现在改写木匠活儿。要真是这样就好了。如果就是把人物手里铁匠锤子换成木工刨子这么简单,我早就去写心仪已久的科幻小说了。锤子你看得懂,刨子你也看得懂,但锤子和刨子的内心你未必就全看得懂;隔行如隔山。
但是要克服那个厌倦,再难也得干。你要努力去看,深入他们的内心。这几年碰巧在国外隔三差五地待过一些时候,看了一些西洋景,也看了一些西洋里的东洋景,有一天我突然想,能不能写点“外面的事”呢?如果你对当下的文学比较熟悉,你會发现,“外面的事”基本上都是“外面的人”在写,即使他们是“我们的人”,那也多半是过去的事了。在“我们这里”,极少有人僭越妄为把手伸到外面去,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其实缺少一个写“外面的事”的传统。传统很重要,传统意味着相对成熟的审美规则、表达路径和比较完善的意义阐释系统。也就是说,你能够在“传统”里轻而易举地找到进得去又出得来的方法。可我现在找不到。找不到让我心怀忐忑,也让我高度兴奋。忐忑和兴奋同时来临时,通常表明你开始“创造”了。
对文学和艺术,最美妙的词大概就是“创造”。黑暗里你给出了光,荒野里你走出了路,大水中你驶过来船。这么说貌似宏大的创世纪,其实没那么严重,点燃一根火柴也是光,两脚宽的小径也是路,简易的舢板也是船——但它们是新鲜的,起码于我是这样。在原有的写作疆土上,你开辟了新的海岸线,你就多了一个观察和思考世界的向度。和过去的写作相比,“域外故事”给了我全新的体验。当然,一切才刚刚开始,关于“外面的事”,我才写了两个短篇小说,一是这个《古斯特城堡》,另一个是《去波恩》。
要克服对老三篇的厌倦,有了《古斯特城堡》;在《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中,我看见的是深深的厌倦。小说里主人公对“动荡”的厌倦,主人公老婆对“静止”的厌倦;途中偶遇的女人对爱情的珍重,完全可以表述为对“离别”的厌倦,而她老公出狱后对财色报复般的贪婪,其实也是对“正直”的厌倦。所有人都生活在某种“厌倦”中,而此一种“厌倦”也许意味着彼一种“想往”与“信守”。
在写这个小说的两三年前,我从朋友那里听来火车上女人的故事。朋友正是在火车上与她偶遇,如小说里所写,她也给了我朋友救急的药。她坐长途夜车去探监。很长时间里她都夕发朝至去另一座城市,她丈夫被关在那座城市的监狱里。但监狱拒不让见,她就在门外守上一天,然后乘长途火车回家。过一阵子她又来,再在门外守一天。如此反复,还是一个要见,一个不让见。我想象这个爱情的西绪弗斯有一脸决绝的表情,她的坚毅几同于绝望,她的信守是另一种厌倦。
那段时间我正患着“城市病”,看见车水马龙就烦,一到乌泱泱的人群里就怕,下了班就缩在家里,遥想退休后的生活。一天晚上出门散步,专找没人的地方走,突然就想到朋友给我讲的这故事。然后有了这个小说。
小说发表后,朋友在杂志上读到,给我打电话,说前段时间跟火车上的那个女人联系上了。我说她现在如何?朋友叹口气,说来话长,下次见面再慢慢与我道来。挂电话时补了一句:看来小说真有预言功能。我就明白了。此后我跟朋友见了好几次,但一直都没再聊起火车上的女人。朋友可能不想聊,我觉得不必聊。世事无常,什么结果都可能有。
从第一次听朋友讲她与那女人在火车上的偶遇,十几年过去了,每年我都会想起那女人几次。关于她的长相我一无所知,却莫名地认定,她生就一张决绝的脸;而“决绝”在她的脸上,最恰切的同义词就是“厌倦”。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不明就里,我常倍感惆怅。
2018年3月25日,安和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