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20年 沈从文和他的“无量快乐”
2018-05-18欧阳诗蕾
欧阳诗蕾
2018年5月10日,沈从文去世30周年。我们采访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他在《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九讲》《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及新书《沈从文的前半生》等作品中,细述沈从文的独特及丰富,并思考一个知识分子乃至一个人可能和时代、社会构成的关系。对以往一些对沈从文的公认解读,他认为“太不够了,它把沈从文的丰富性挡在了外面”。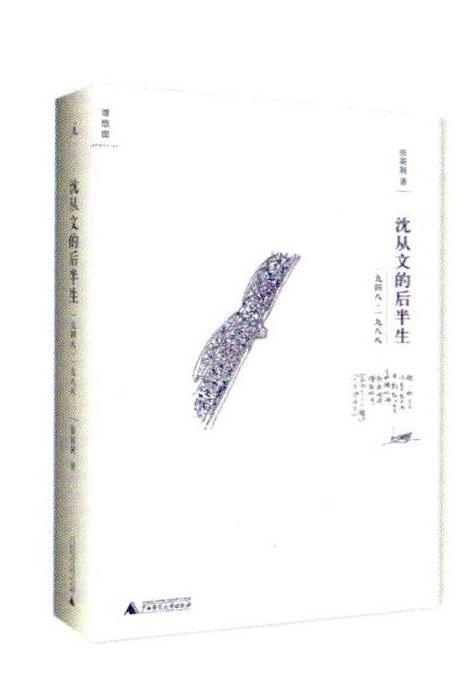
江从禾库山岭劈下,一道支流循山势流淌,辟入湘西深山中,泼洒出两岸人事兴衰的因缘。
这一条河清冽,来势汹汹,经繁郁丛林滋养兽物,涌入青山环抱的村镇时,柔和了些。如中国古代山水画中一景,河是几线墨,湍流里清洗的衣布、菜叶、人、牛羊、家犬,皆为宣纸上一点。万象气韵汇通。
“我的想象是在这条河水上扩大的。我把过去生活加以温习,或对未来生活有何安排时,必依赖这一条河水。”1933年,作家在31岁时写下这些话,正值意气风发。
大师常被历史简化。隐忍、被动承接时代苦难的文学家,是公众熟悉的沈从文的基调。再细致些,人们热衷于“深山里只受过小学教育”的天才传奇,或将他定义为“刻画桃花源”、展现“人性之美”的作家。
“三姐,我对不起你。”1988年5月10日,心脏病突发的的沈从文,在生命的尽头,将最后一句留给了妻子。这副陈旧身体已在生死之间徘徊几遭。少时两场持久高热,家里棺材曾备下。1949年,他的精神矛盾升到顶点,刚烈至以剃刀割破脖子,喝煤油,自杀。
1974年冬,在张兆和居住的小羊宜宾胡同的宿舍院中
与现代化进程相契的20世纪中国,从不缺传奇和悲剧。沈从文的一生也交织进社会、时代的复杂纹路。出生在濒临灭亡的清朝,战乱中“运动”、“革命”纷涌,崭新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建立后,又接着新一轮“运动”,他的一生见证了古老大地的极速巨变。
“现代以来的中国,也许是时代和社会的力量太强大了,个人与它相比简直太不相称,悬殊之别……这样一种长久的困难压抑了建立关系的自觉意识,进而把这个问题掩盖了起来。不过总会有那么一些个人,以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坚持提醒我们这个问题的存在。”研究沈从文二十余年的学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认为,沈从文太独特了,要真正了解沈从文,需要回溯他的来路。
斯人已逝30年。生命另一端,是大众所陌生的沈岳焕。这个“沈从文之所以为沈从文”的内核,读者侯孝贤熟悉,读者贾樟柯也熟悉。他发源在1902年的湘西,是一个崭新明亮的山林小兽。
天地之大德日生
“要打吗?你来,我同你来。”
逃课跑出凤凰城外,七岁的沈岳焕时刻备着这句话。同齡孩子一旦遇上,说不上为什么,总得打一架。一群孩子里挑出个同体魄气力的,打完架,俩人扫扫身上的土,和和气气告别。
一个好事人,若从200年前的地图上找寻,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这个名为“镇簟”的小点。300年前,清政府在此处驻扎,镇抚和虐杀当地残余苗族。在暴政与反抗中,血一度染赤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
沈岳焕出生时,镇簟已名“凤凰厅”。小山城热闹又和气,苗族、土家族、汉族杂居,还有江西、福建、广东来的商人。平民、兵卒、土匪,少数读书人和多数军官结合的上层阶级,生活皆各守其道。本地军人互相砍杀虽不出奇,但行刺暗算却不作兴。
凤凰城石板巷子里,1909年那些清晨,沈岳焕挎着书篮一出门,两只鞋就扯手上了。“我自己总以为读书太容易了点。”他识字早,记忆力好,背诵前临时读几遍,也背得一字不差。什么也拴不住这颗小小的心,待过的几个学堂里,没人比他逃课点数更高了。
上学路总得多绕一段,路上铺子邻比,染坊里石碾晃荡;剃头铺任何时节,总有人手托一个小木盘呆呆让师傅刮头;屠户肉案桌上鲜猪肉砍碎时跳动不止。如果从西城走出,可以见到牢狱,常有尸体被野狗咋碎或拖到小溪中,他就走过去,用木棍戳一下脑袋,看会不会动。
“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他写下,“逃出学塾,尽我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万汇百物的动静。”
去嗅,死蛇、腐草、屠户的气味,烧碗的土窑被雨放出的气味,推风箱从火炉口喷冒的气味。自然中,时节流转清晰,人的感知亦更敏锐,他分得清:蟋蟀、各种昆虫的声音,藏在田塍土穴中的大黄喉蛇的呜叫,还有更细微的,一只黄牛当屠户把刀剸进它喉中时的叹息,黑暗中鱼在水面泼刺的微声。
逃学走去了城外庙,就看一个一个的人,织竹簟的,做香的。有人相骂,沈岳焕也认真站着望,看大人们如何骂来骂去。到了夏天,就得去偷李子枇杷。主^追着挥竿子骂,小孩一下就窜远了,还非常得意,“—面吃那个赃物,一面还唱歌气那主人。”
“我的爸爸因这件事十分陵怒,有一次竟说若再逃学说谎,便当实行砍去我一个手指。”七岁孩子显然是凉到了。每次逃学被发现,家里学塾两方得各挨一处打,“我还是想逃学时就逃学,绝不为经验所恐吓。”
善泅水,也会爬树,识得30种树木、十来种草药,知道怎么把鱼用黄泥包好塞到热灰里煨熟了吃,会抽稻草心编制小篓小篮。而年幼的他也隐隐感觉到了,“在我面前的世界已够宽广了,但我似乎就还得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看杀头
道尹衙门口地上,辕门、云梯木棍上,全堆挂着血污人头。爸爸陪同下,九岁的沈岳焕望着眼前一切,实在稀奇,云梯上竟飘着长长一串人耳朵,“一生真再也不容易见到过的古怪东西!……我并不怕,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就让兵士砍他们。”
这一年,隔壁省辛亥革命枪响,震动湘西。沈岳焕的父亲曾与天津总兵罗荣光驻守大沽口炮台(沈岳焕的祖父做过贵州提督)。革命一来,做了一生将军梦的父亲再度杀仗去了,革命军—夜覆没,接着是衙门一个月剿杀。
城外河滩上,尸首常躺下四五百。剿杀也有些稀里糊涂。“有被杀的站得稍远一点,兵士以为是看热闹的人就忘掉走去”。衙门每天捉来的人有一百两百,多是无辜农民,杀人那一方也寒了心。
沈从文家人合影。左起:沈从文、沈荃(三弟)、母亲、沈岳萌(九妹)、沈云麓(大哥),1929年摄于上海
1948年夏,沈从文夫妇与友人在颐和园。前排左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张奚若夫人、杨振声
既无法全开释,也不忍全杀头。一条命,活不活,最终想出的办法是掷筊看天意,未免有些荒唐。而既是天王庙大殿前掷的,又有四分之三的开释机会,被杀头的也信服。“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份颓丧那份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
“我刚好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对这场浩浩荡荡的革命,沈岳焕的印象是“杀戮那几千无辜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革命让家中也有变化,爸爸和+姓吴的竞选长沙的会议代表失败,心里不平,赌气出门往北京。
1917年,沈岳焕高小毕业,家境衰败,背上包袱离乡去当兵。战乱年代里当兵的苦暂且念不上,15岁的他欢喜一切新奇,且那么渴慕自由,对外面世界充满了憧憬,“深觉得无量陕乐”。
仍然是离不开辰河。沈岳焕所在的游击第一支队,属于张学济管辖的靖国联军第二军。入队后第一个任务是清乡,即剿匪。沿路到达的每个寨堡,地主皆蒸鹅肥腊肉作食。而部队一走入山中小路,便遭到无数冷枪袭击,队里死去几人。清乡四个月,部队杀去近两千人。
接着,部队移防怀化镇之后,填造枪械表需要写字人,沈岳焕就升为了上士司书,到总秘书处做事。白天街市尽头,经常有几个兵士前面走着,中间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挑了两个人头,这个人头便常常是这小孩子的父亲和叔伯。
“我在那地方约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我皆瞳透了。”他写下,“这一分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一致了。”
而这一切经历作用于他,使他“对于城中人在狭窄庸儒的生活里产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得忧郁强悍不像一个‘人的感情了”。
渐增的寂寞,更高的光辉
见天地、知人事的同时,塑造生命的另一种东西在沈岳焕生命中暗涌,日益显示出重要性和沉潜的影响力。
留守怀化做司书时,沈岳焕遇到司令部一位姓文的秘书官。《辞源》、《申报》……都是文秘书引入这个湘西小兵生命的崭新世界,蕴含外界广阔天地的信息。而后,再因为身上军衣为年轻女孩子惧怕时,沈岳焕心里就有点委屈了,“我以为我是读书人,不应该被别人厌恶。”
部队在鄂西来凤遭袭,全军覆灭,沈岳焕在内的二十来位留守怀化的散兵也各自回家了。1921年初,去芷江投亲时,舅父黄巨川和姨父熊捷三每天作诗,沈岳焕就替他们抄诗,自己也开始写五律七律,这时又恰好爱上了一个女孩,便开始整天整夜作情诗,结果被骗去很多钱。而姨父家的两大箱商务印书馆印行的《说部丛书》,成了他接触到外国文学的契机。
“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约半年里,沈岳焕在箪军统领陈渠珍身边做书记,日常事务包括保管整理大量的古书、字画、碑帖、文物。没事时,他就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取出鉴赏,或翻看《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一类书。
表面生活的动荡,远不如内部精神世界变动得剧烈。书一本本读下来,他感到了巨大的寂寞,听姨父聂仁德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进化论。这么一来,脑子里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我总觉得有一个目的,一件事业,让我去做……但我不明白这是什么事业,又不知用什么方法即可得来。”
1922年,一场热病袭到了沈岳焕身上。头痛得像斧劈,鼻血一碗、一摊地流,亦无法进食。20年生活造就的顽强体魄,撑下了这40天。危险期刚过,他收到了一位猛虎般结实的老同学的死讯,只源于一个泅水的“争口气”。
望见那具在水里泡了四天的臃肿尸体,沈岳焕帮忙收拾尸骸掩埋后,一个人闷闷沉沉痴呆想了整四天,“我病死或淹死到外边去饿死,有什么不同?”“我知道见到的实在太少,应知道应见到的可太多,怎么办?”
8月,从保靖起身,过辰州时与家人短暂相聚。接着出湖南,经汉口,到郑州,转徐州,又转天津。“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压上去,赌一注看看。”19天之后,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他在旅店簿上登记——
“沈從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对话张新颖
贯穿一生的不安分
人物周刊:以往谈到沈从文,总聚焦在《边城》这一段。你之前说的沈从文的三个阶段,想请你谈一下。
张新颖:第一个就是我们通常描述的文学阶段,从他开始文学创作到1936、1937年左右,大致到抗战为止。一个人通过写作,慢慢变成一个有成就的文学家,创造出《边城》《湘行散记》一批有特色的作品。
第二个阶段开始,大家就很少理解他了,因为他文学创作少了。但这个阶段很重要,从抗战开始到1940年代结束,沈从文面对的也是一代人、知识分子面对的问题。但是他和同代人、前后几代人不一样,他面对这些问题时有独特的反应方式。
我把它称为“思想者的阶段”,这个名字有点冒险,但是我特意把“思想”当成动词来强调,不是说沈从文有一个完整固定、可以描述清晰的思想。而是说当他面对乱七八糟的社会现实的时候,他一直从自己出发在思在想,他想得很痛苦,他和各种力量要去争论、辩难。
第三阶段是从建国到生命最后,我在《沈从文的后半生》里处理了最后这一阶段,相对来说比较清楚。就是一个人以前的事业毁掉了,怎么重新寻找建立新的事业,在一个新领域安身立命,从一个文学家变成了研究历史、研究文物的人。
1949年夏,出席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的朋友到沈从文家中拜访。左起:沈从文、巴金、张兆和、章靳以、李健吾
我现存慢慢觉得我说的三个阶段不完整,因为在我说的三个阶段前面还有一个作为前提的阶段。沈从文从小长大成为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人的阶段,是他20岁以前在湘西的阶段。
人物周刊:我第一次读《从文自传》很受冲击,因为我们熟悉的沈从文比较柔和隐忍。但自传中他非常清亮明快,甚至顽劣,生机勃勃的。整个人最初的这股气象,你觉得是贯通一生的吗?
张新颖:一般对沈从文的印象,可能跟我们聚焦他上世纪30年代的作品《边城》等有关,但(沈从文)可能确实不是(一般人印象中那样)。李辉有一篇文章《平和或者不安分》,说大家都认为沈从文是一个特别平和的人,但是他看到的是特别不安分的一面。“不安分”其实从少年阶段一直贯穿到老年。前面讲的沈从文第二个阶段,很痛苦的思想阶段,他就老和人去吵架,其实就是从少年阶段贯通下来的。
再回过头说你刚才说的《从文自传》,要注意写作的时间。写作的1932年,那时他在青岛过得比较好,从前期的伤感走出来,变得刚健。你说的清亮、刚健、明快在自传里表露得特别充分。同样一段经历在不同时期的表述里而是不一样的=1949年前后,他又重新写了自传,这个时候重新呈现出来的少年形象会写到敏感、脆弱、害羞、内向等等。
在不同阶段,他会挖掘自己生命里不同的成分。不仅仅是写成作品,也是在行为情绪里表露出来。比如1930年代的时候,他那么愉快。到了1940年代,他那么痛苦。但不管怎么说,《从文自传》描述了一个生命力特别丰富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他以后的生命里都会用得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贯通一生的。
人物周刊:你最早研究沈从文是在1997年,到现在20年有余了。这些年来研究沈从文,跟当初的预想有什么反差吗?
张新颖:这个人总是比我想的丰富,所以我会特别觉得,以往我们对沈从文的一些大家公认的解读太不够了,它把沈从文的丰富性挡在了外面。我是一个非常没有耐心的人,但我读沈从文是一个挺愉快的过程,因为不断在他作品经历里有新的发现。如果一个人的作品,你能一下就全部把握到,那么你就不会再继续读下去了。
人物周刊:我看到之前你还原他的经历时,是以周作为时间单位。
张新颖:我觉得我们的研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要研究的那个问题本身还没有说清楚,就开始发表见解了。我们关于五四有无限多论述,但你找有些谈五四听上去很有道理的人,去问他最基本的,五四这天,五四前前后后,从早晨到晚上发生了哪些事?恐怕有不少说不清楚的。
当然日期只是举个例子,就是你要小心翼翼地对待那一个生命,他身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小事情,大事情,这样才有可能把生命的历程还原出来吧。生命身上的丰富性,把它小心翼翼地保护下来,而不是很粗地将它忽略掉
张新颖 图/受访者提供
由排斥构成的生命经验,是狭隘的
人物周刊:很多时候讲到沈从文,会强调他只有小学的学历。当他20岁出头走出湘西的时候,他已经拥有了哪些作为写作者的品质?
张新颖:还是讲到湘西的特殊,小小的地方聚集了这么多不同因素,使得密度质量大大超出一般地方。我在《沈从文的前半生》里写凤凰一定要强调各因素间的不同,比如暴力和自然风光的秀美,地理偏僻和思想意识走在时代前面,不同才会拉开空间。就像摆秋千,秋千荡的力很大,幅度才开。沈从文从一个小地方出来,但这个小地方里不同力量拉开的幅度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些因素的张力会过渡到他的身上。
《从文自传》强调了他的顽劣,其实这个也只是他在1930年代强调的。我们同到我们通常以为的文化教育概念来说,他小书也读得很好。我们从《从文自传》也可以看出他对中同古典文学的阅读与了解,还有超出文学的范围对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文物的了解,还有当时的新文化,还有西方文学,比如商务印书馆林纾翻译的小说。
你想在20世纪初的时候,一个人接触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文化和历史、西方文学,有了一个基本的视野。其实我们有时候强调他光读大书,不读小书这一方面,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人物周刊:自傳里写到的湘西,是个莽莽苍苍、生机活泼的大世界,这里人的情感、善恶观,都是一个相对原始的状态;沈从文说过他是以艺术家的情感在看待世界,这二者有没有必然联系?
张新颖:当然是有很深刻的联系。这样一个湘西世界存在的形态,孩子成长确实不像我们现在小孩子从小受的教育,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区别、选择,其实就意味着要排斥一种东西,你的心会对世界的某一部分关闭掉。
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是一直用眼睛用心灵敞开去看的。后来的经历中,他不一定像我们对事物一开始就有一个对错的明确判断。最初他看到的这样一个丰富的世界,影响了他对整个人生、整个世界的理解。
人物周刊:而且沈从文在很多地方讲过他不给人下道德的论断。
张新颖:所有的论断都意味着排斥,就意味着说有的是对的,有的是错的。如果你认为它是错的,那么就意味着要将它从你的生命中排斥出去。这个由不断的排斥构成的生命经验,恐怕是狭隘的。
独特,划不到任何一个派别
人物周刊:比如说到20世纪初的作家,经常会讲到左翼、新月派等等,大多是把沈从文划到新月派里面,我觉得其实挺突兀的。张新颖:我为什么说沈从文特殊,他有丰富性呢?因为沈从文其实是不能划分到任何流派里面的。像刚才你说的,哪怕和他比较亲密的新月派,他和徐志摩他们关系很好,但他个人的气质、经历以及他的文学,和新月派的差异还是很大的,这也是沈从文很有意思的地方。
根源在于他有一个跟大家不一样的我,他坚持从这个非常独特的我出发来看待来描述世界,描述他对这个世界的感触。
文学会有潮流,会有派别,那是有一个共同差不多的东西来看待、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而这个可以公约的东西才能形成一个派别,但沈从文一直坚持自己非常独特的东西,任何派别和沈从文是没办法公约的。
人物周刊:说到这个独特的我,我想到你说过《从文自传》对自我的确立,而五四中也经常说“自我发现”。
张新颖:现代文学大的叙述模式里,五四前后有一个普遍的觉醒。文学青年、新青年接受了新的思想和觀念,然后受到启蒙觉醒了。觉醒是断裂时刻,否定之前的人生阶段“旧我”,产生了一个新的生命阶段“新我”。这个模式影响特别大,是一代人面对现代思想观念的改变经历。新我的诞生,其实就是我接受了一个现代的思想观念再产生的,所以新我其实是从体外产生的。
但是沈从文的我不是断裂的,他是从过去一点一点累积来的,有历史有来路有根源。所以他和那些否定了旧我的人,差异就一下子出来了。这样的人面对世界时自然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沈从文的文学,不是启蒙的文学,也不是后来革命的文学。他是一个带着他生命从过去到现在的丰富信息的文学。
也不是说沈从文一开始就有这样明确的想法,他的确是到了城市,经历了很多事情,才一点一点意识到了这样一个我,这样一个过去生命来历和它的重要性,到1930年代初写出了这样的《从文自传》,把这个我描述和重新确立出来。《从文自传》的意义更在于他说了一个自己和很多人不一样的我,以及这个我对于他的现在、将来的影响。
“天地不仁”与古典文学中的“天地”
人物周刊:你之前说沈从文笔下的人是中国古代山水画中的一个点,特别小,我觉得很有天地的概念。
张新颖:其实现代文学就是人的文学,沈从文的文学比人的文学要大。稍微往前看一看的话,古典文学是比人的世界要大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说不清楚,我们姑且把它叫作天地吧。
沈从文是一个现代人,但他在作品里还保留了天地的信息。他的文学当然也是人的文学,不过人的位置是在天地之间,而不只在人间的位置。所以你看《边城》,被翻译成了《翠翠》,其实不对。因为他写的是有天有地的边城,翠翠是里面一个角色。你把名字换成了《翠翠》,其实是现代文学的观念。
这个东西蛮难讲的。现代文学人的文学里,人觉得自己是天地的主人,看起来人很大了,但是他的力量只是人自身的力量。但你说的那个天地,浩浩荡荡莽莽苍苍,人在天地里,人的行为、人的生息是和天地互相沟通呼应的,所以反倒是人会更有力量。
人物周刊:说是文学,更像是思维本源。之前你说《边城》讲的是天地不仁。
张新颖:是天地不仁,但天地还有另一面,天地之大德日生,生生不息。
人物周刊:所以翠翠的故事读完,也不至于人伤而不返。
张新颖:按照现代小说的说法,小说到高潮就结束,但是他故事发展完了之后,又写当地的人出钱把塔修起来了。看起来是多余的,但是一定要把这个塔修起来,一定要写那个人也许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就是一定要说,有这样一个生生不息的一面。人类就是这样活下来的。
时代的力量太大了,悬殊之别,极难构成关系
人物周刊:20世纪中国是和现代化相契合的,轰轰烈烈的现代化来了,文学,商业,政治……大家都纷纷涌上去。在当时沈从文还是提出了很多自己的反思。
张新颖:沈从文不是一个反现代的人,我特别不喜欢有人把沈从文描述成一个反现代的人,我觉得这个观念太简单了。比如说《长河》中,湘西的现代化炼油厂替代了农村手工业作坊,这个事隋会被简单概括为现代工业方式代替了落后的手工业小生产方式。但是沈从文看到了这个现代名目背后是权力在运作,比如具体的买卖途径和定价,政治和商业勾结对农民实行多层剥削。
他反对的是现代面目下,政治和商业勾结借着“现代”来做各种各样的事。其实在当时的现代建制中,他能够深刻地看到背后,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不能把他描述成一个很落后的、留恋农业的生产方式的人。
人物周刊:上世纪30年代,民族国家概念的浪潮下,作家的笔成了枪杆子。那个时期沈从文很喜欢争论,也很困郁,现在反商业化反政治化的纯文学口号也挺多的,但是他的立足点有什么不同呢?
张新颖:这个问题就很难说了,因为很容易把他跟现在的“纯文学”观念等同起来。“纯文学”的概念是1980年代之后出来的,“文革”以后,我们觉得文学应该从政治经济里解放出来。这个概念往后再慢慢发展,就有了一种“文学什么都不要管了”的倾向。这个就很麻烦了,如果文学什么都不管了,那么文学是什么?
回到沈从文来说,他其实并不是文学就只写很美的东西就好了。沈从文的观念和五四的观念还是相通的,文学是一个重新塑造民族国家精神的东西。但在19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救亡是时代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会迁就形势把文学用作更短期的使用。你说不对吗?好像也不能说不对。
湖南湘西凤凰古城
沈从文不是说这不对,是在这一同时,他要强调文学要更长远地为民族国家的根本来努力。而当文学成了两个党争夺的工具时,他更要强调文学是政党工具之外的存在。他强调的文学要从商场从官场解放出来,文学应该恢复到五四时候他讲的那一个“勇敢”和“天真”。
而且沈从文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对于五四的理解,我觉得别人不一定像他讲得那么清楚。他说五四的新文学最早是和学术、和教育结合起来的,这个出发点很好,一可以更正文学,二可以改善教育。所以他在1940年代总是在讲五四,想把文学和学术、教育联系在一起。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東西,但它并不是可以短时期见效的工具性的东西。这种争论表明,他并不是一个纯文学的作者。你讲到这个本源就更难讲了,因为要回到他个人的自我、他和世界的关系来理解他所说的文学。
人物周刊:争论中他抗争的是什么呢?他一生的反抗,本源是反对对生命的束缚和规训吗?
张新颖:束缚是肯定的,甚至是把生命工具化。不同时期他所抗争的东西,我们没办法把它描述成同一个东西。但束缚生命自发的丰富和生机,引导、强迫生命以唯一的方式来发展,这种力量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名目,来自不同方面,沈从文反对的是这一个。
人物周刊:作家写“看杀头”,鲁迅和沈从文风格很不一样。鲁迅写杀头是象征性的,沈从文是实感的,看起来会少很多立场。你也讲过沈从文和鲁迅在文学深处、思想深处是相通的,这一点我也很好奇。
张新颖:沈从文写杀头时故意表述得好像没有立场,但是我们后来接触到他的生命的时候,会发现这种特别残酷的经历极深地影响到了他对生命的感触。一个人经历了这样恐怖的事情,所以他才对美好的东西更敏感、更珍惜。所以他会讲哪怕一个平常的农妇的微笑,他也会觉得很感动。
说到他和鲁迅的思想共通,其实他们都是从根本的立场来着眼于文学作用和自己对世界的评判。鲁迅所讲的国家民族精神根本的东西丧失了,要寻找这样一个东西。沈从文的文学其实也可以看成寻找民族丧失掉的本根。他的文学并不是很小很美的山水,而是有一个着眼寻回本根的精神,要寻找健康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从更大的影响来讲,我觉得它们是相通的。
人物周刊:沈从文后来的研究对象,是—些被历史研究抛弃的寻常生活中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和你说的这个民族本根有关吗?
张新颖:这跟他对历史对世界的理解有关。他的文学着眼于普通人,所以他理解的历史也是由普通人的劳动力量和智慧创造的。梁启超在20世纪初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有历史,记载的是一个朝代换成另一个朝代杀来杀去。是朝代更替的历史,没有老百姓是如何生活。沈从文和这样的历史观念是相通的。
我们这个民族历史延续到今天,不仅是上层政治的更替,也不仅是文人知识分子所创造的东西,更是有一代一代的沈从文文学里面所写的人创造的东西,所以他后来的历史研究,研究的就是传统历史不去研究的东西,不是“文物”的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