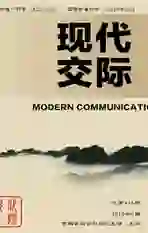《镜花缘》原著与韩译本比较研究
2018-05-17王潇
王潇
摘要:《镜花缘》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流传到了韩国并被翻译成谚文在民间流传,近两个世纪后又用现代韩语被再次翻译成书出版。韩译本的翻译中凸显出两国文化交流的阻滞与碰撞、误解与扭曲等创造性叛逆。文章通过对韩译本翻译中归化、异化及人称和地名的翻译与原著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两者的异同及其背后的文化原因和译者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镜花缘》 韩译本 翻译 创造性叛逆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6-0113-03
《镜花缘》①是清代文人李汝珍在1795—1815年间创作的著名长篇小说。该书不仅在国内大受欢迎,更是流传到海外诸国,尤其在1835—1848年间被韩国贵族洪羲福(1794—1859)全译百回本并更名为《第一奇谚——镜花新泽》,开启了其在韩国的民间传播。洪羲福的译本,翻译者和翻译年度明确,无疑是朝鲜后期翻译文学史上弥足珍贵的资料,但是现在20卷当中第9卷和第12卷已经遗失,加之所用的古朝鲜语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镜花缘》在现代韩国社会的传播。韩国全南大学中国语专业的郑荣豪教授多年专研《镜花缘》,也对于韩国现在还没有用现代(韩)语翻译的《镜花缘》全译本而深感遗憾。[1]
正当韩国学者和读者处于没有《镜花缘》现代韩文译本可读的窘境下时,2011年12月29日,一部用现代韩文翻译的《镜花缘》全译本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这部全新的译本分为《■1》(镜花缘1)、《■2》(镜花缘2)②两本,由■(文学─知性社)出版发行,■(文炫善)③翻译。综观中国和韩国对于《镜花缘》的研究,涉及文本的语言、结构、儒家文化、女性主义、与《红楼梦》中女性形象比较、与《格列佛游记》比较以及从翻译研究视角分析《第一奇谚》等诸多方面,但原著与最新现代韩语译本的比较研究尚未涉及。《镜花缘》原著虽是白话小说,但其中大量运用方言土语及俗谚俚语,又以“才学小说”著称,距今也有近两个世纪的时间,这些因素无疑给翻译工作带来挑战,因此也产生了无数文化意象的遗失、增添和迁移,凸显了文化交流过程中所受到的阻滞、碰撞、误解和扭曲等。译者采取“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在充分顾及韩国读者接受心理的同时也尽可能再现中国社会的异域风情。本文对韩译本“归化”翻译、“异化”翻译及人称和地名翻译与原著进行比较,并探讨其背后的文化原因和译者的翻译策略。
一、韩译本翻译中的“归化”
译介学中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尤为突出,我们看到该书原著的目录有54回是8个字的两个句子,46回是7个字的两个句子,类似于诗句,工整简短的句子里包含了较多的意象和信息,译者若要完全保留原著的形美的一致必将丧失原文全部的含义。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忽略了原著目录诗句的韵律、对仗、平仄、典故等,主要从字面意义和文本内容来进行翻译,“归化”的翻译策略在目录翻译中得到了十分集中和突出的体现。例如译者将“第29回服妙药幼子回春传奇方老翁济世”[2]P2译成“■29■■(第29回起死回生的世子和传授处方的多九公)”[3]P6,通过对比我们很明显地看到译本目录与原著一样概括出本章的大致内容,译者为保持译本与原著目录的形美一致作出了很大努力,以至译本与原著目录句子长短大概一致,然而更多的是差异和不同。
在第20回中,译者将“丹桂岩山鸡舞镜碧梧岭孔雀开屏”译成“■(丹桂岩山鸡和碧梧岭孔雀的较量)”(P6),其中创造性地添加了“■(较量)”(P6);第23回中,将“说酸话酒保咬文讲迂谈腐儒嚼字”译成“■(炫耀学识的酒店服务员和咬文嚼字的虚假儒生)”(P6),创造性地添加了“■(炫学的——自认为学识渊博并以此为傲去炫耀)”(P6)和“■(虚伪、虚假)”(P6);第56回中,将“游瀚海主仆重逢”译成“■(海上宿命的相逢)”[4]P7,创造性地添加了“■(宿命的)”(P7)。这些具有创造性的文化意象的添加,使得译文比原著目录更加感情饱满、形象贴切地反映出文本的内容,也使得译文目录更加意味深长且具备了比原著目录更为突出的读者导向性。
又如第72回中,译者将“瑶琴”译成“■(玄鹤琴)”(P8)。“瑶琴”是我国古琴的别名,我国的古琴是用桐木和杉木制成,7根弦,演奏方法不需要道具仅用双手完成。而韩国的弦鹤琴用桐木制成,6根弦,演奏方法是右手用一根木棍挑,左右拨按琴弦。两者的外观、演奏方法等都不一样,这样的翻译显然不妥当。韩国另外有伽■琴(■),是桐木和栗木制成,12根弦,演奏方法跟我国古琴更接近,但是演奏者多是艺坊妓女,而玄鹤琴有很多演奏者是贵族,译者综合考虑后选择将其译为“■(玄鹤琴)”(P7),这种翻译方法采用了维奈和达贝尔内所提出的两种普遍的翻译策略中的“曲径翻译(Oblique translation)”中的“适应(Adaption)”方法,由于中国的“古琴”在韩国并没有与之对等的文化符号,译者便用本国与古琴相似的一种文化符号来表示,虽然中国古琴和韩国的玄鹤琴并不一样,这也体现了雅客布逊提出的“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中的“差异对等(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的翻译理念。以上例证是译者通过在翻译中创造性地遗失、添加了一些意象,寻找不同语言文化中的对应与等值,最终用极其流畅、自然的韩语来表达原著目录的内容,却程度不等地“吞并”了原著的文化意向。[5]
此外,韩译本对于部分文言文的翻译是经过“语内翻译”再到“語际翻译”,即译者先将文言文理解后,再用现代韩语翻译出文言文的意思。例如在41回武太后为璇玑图所做的序文是一篇文言文,节选译者翻译如下:
“■(■)■■ ■ ■ ■■.(窦涛将擅长歌舞的赵阳台安置在别的住所,之后知道此事的苏蕙鞭打和侮辱小妾,而赵阳台也拿着苏蕙的短处诽谤她,窦涛听了之后十分生气。)”(P434)
不难看出,译者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虽然遗失或省略了原文中诸多的意象,但是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用通俗易懂的本国语言将原著的文言文翻译出来,大致传达了原文内容。
二、韩译本翻译中的“异化”
《镜花缘》原著中由璇玑图生出盈千累万首诗歌、众多药物名称和古籍、典故等。在这部分的翻译上,大多采用了直接翻译(Direct translation),集中体现了“异化”的翻译策略。例如韩译本对第41回璇玑图的翻译,两幅璇玑图原封不动地搬到了韩译本中,将璇玑图中诗歌的诗句直接标记成“■(仁智■德■虞唐),■■(■),■(■英皇),■(■漂浮湘江)。”(P437)对于这样的译文,译语国读者很难理解,然而文化翻译学家苏珊·巴斯奈特认为读者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文化翻译观要求译文的读者能够适应文化差别,通过对译文的阅读了解异国风情和文化。[6]译者在这部分的翻译策略上“异化”的使用比例也大大提升,给译语国读者留下较大的想象和解读空间。
还有药物名称和药方的翻译,例如:将“葱白”(P173)译成“■(■白)”(P318),“七厘散”(P174)译成“■(七厘散)”(P320),将药方“麝香伍分 冰片伍分 朱砂伍钱 红花陆钱”(P174)译成“■■(麝香伍分,冰片伍分,朱砂伍钱,红花陆钱)”(P320)等。纷纷体现了译者“异化”的翻译策略。但是药名和药方的翻译虽然和上面两部分一样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然而译语国读者对药名和药方译文的理解上却比诗歌和文言文的理解要容易得多,因为中医学早就传到韩国,今日中医学还在韩国大受欢迎,韩国人对中医的熟悉程度和理解接受能力自然比日常生活中不常接触和使用的诗歌或文言文要强太多。因此,虽然都是字对字或词对词的直译,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译文对译语国读者产生的效果却相差甚远。
译者对于原著中旁征博引的古籍和典故也都采用直接标记或加脚注说明的“异化”翻译策略,将中国的古籍和典故积极地介绍给译语国读者。例如,译者在翻译第16回中的“荣列胶庠”(P91)时虽然意译为“■■(名列光彩荣耀的学校)”(P176),但在脚注里解释道“■(■庠)■(周代)■(■),■(庠)■■.(原文是胶庠。周代时大学称胶,小学称庠。后代便以此统称学校。)”(P176)详细的介绍词意的来源、词语背后的典故和文化背景,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上具有充分的自觉性。另外对于古籍名称的翻译亦是如此,将“‘《毛诗》‘《左传》‘《尔雅》”(P92)直接标译为“‘■(毛诗)‘■(左■)‘■(■雅)”(P178),加脚注介绍《毛诗》和《尔雅》的名称变迁和大致内容。译者在译著中有意隐身,主动介绍中国典籍和文化的同时也顺应着中韩两国友好邦交的时代主旋律,迎合了韩国当下兴起的“学习中国经典”的社会风气。然而这些理由在当今商业为王的韩国资本主义社会都不足以让韩国译者重译《镜花缘》这部作品,因为对于汉学功底薄弱的大多数韩国读者来说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这部文学经典,即使听说过对他们来说也太难懂,这也决定了这部译著很难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更何况译者还选择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在介绍异域文化的同时也增加了译语国读者对该著作的理解。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译者再度翻译这部著作并采取这种翻译策略呢?我想从美学和哲学的角度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毋庸置疑,《镜花缘》是一部文学经典,它透露出的文学和文化之美是显而易见的,而审美活动是人性和人的精神需求,它超越了实用功利的活动,亦超越了个体的有限生命[7],所谓“人诗意地栖居着”[8],正是这种审美需求使得韩国社会能够再译这部作品。译者在不少地方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不仅是想要向译语国读者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学之美,更是想传达原著中表现出的中国人进退自如的文化心态、顺其自然的处世准则[9]、既出世又入世的哲学观和人生智慧。[10]
三、人称和地名翻译
《镜花缘》韩译本中,对人名和地名的翻译基本上都采用字对字的翻译,即每个汉字都有根据其发音所对应的韩文文字表示,本书中对人名、地名的处理也大都如此,但却有两处的翻译处理值得说道。
首先,是译者对“嫦娥”的翻译。韩语中“嫦娥”的表达方式有两种,分别是“■(嫦娥)”“■(嫦娥)”,两个单词虽然都是嫦娥的意思,但是韩国人在表达“嫦娥”时用“■(嫦娥)”的频率远远高于“■(嫦娥)”,但是译者在这里却选择了使用频率极低的“■(嫦娥)”(P24)来表达,乍一看让人费解,但是当我们深入了解一下两个单词的含义之后可以窥见译者在翻译选词上的用心。“■(嫦娥)”除了有嫦娥的意思之外,还表示“孀居寡妇”等。而“■(嫦娥)”还可表示“成为尚宫之前的小宫女”等。在《镜花缘》原著中的嫦娥形象并不是寡妇,而是一个地位不高的小仙女却能挑事儿、爱记仇,因此很明显将其翻译为“■(嫦娥)”更能再现原著所要表达的人物性格及形象。
其次,在第16~18回中译者将紫衣女子对唐敖和多九公的称呼“大贤(P95)”,译成“■(老先生/老者)”(P188)。“■(老先生/老者)”在韩语中是对别人的父亲或年老者的敬称,在实际运用当中多称呼有一定金钱和地位的贵族老爷。而原著中的“大贤”很明显也有对年长者表示尊敬之意,同时主要是指唐敖和多九公来自万邦之首的天朝,天朝儒士在外邦小国心目中的形象是饱览诗书、博学多才的,在学问上首屈一指,外邦小国无法企及,因此在原著中“大贤(P95)”不仅仅表示对长辈的尊重,更是指天朝儒士在邻国人心目中有道德、有才能的形象,也与后面故事情节的发展形成反差和对比,从而暗含了原著作者的讽刺寓意。而“■(老先生/老者)”(P188)并不能传达这样深层的文化内涵,只能传达对年长者的敬称这一层含义。但是如果译者将其直译为“■(大贤)”,译文就会变得十分蹩脚,这样翻譯既不符合韩语的表达习惯也同样无法传达原著的涵义,因为韩国历史上早在1948年就施行了谚文专属用途法(简称谚文专用法),是汉字被依法废除的法律依据。尤其在朴正熙(■,1962—1979年任韩国总统)执政时,极力主张废止汉字并严厉禁止在小学有任何汉字教育活动,对违反规定的老师会以“不配合国家教育政策”处以惩戒、免职等处分。因此用这种“字对字”的直接翻译方法,译语国读者反而更难理解原著涵义,不如用“■(老先生/老者)”(P188)能够使译语国读者理解接受。然而这小小的人称翻译背后隐藏的社会历史文化渊源却令人感叹。
最后,是译者对“天朝”(P86)的翻译。根据原著写作的历史背景,故事发生在唐朝,唐朝时期我国国立鼎盛,声名远播,国人都以国家为骄傲,以“天朝上国”自居,尤其是到了李汝珍生活的清朝,这种“天朝上国”的民族自豪感更浓厚,表达了国人的爱国和骄傲心里。“天朝”对应的韩语单词是“■(天朝)”,将“天朝”翻译成“■(天朝)”本是无可厚非,但是译者却做了不同的处理,译者将唐敖、林之洋、多九公之间对话时候说到的“天朝”(P86)都翻译成“■(中原)”(P167),却将男主人公一行游历所到的那些小国家的人和男主人公说话对象是外国人的时候说到的“天朝”(P86)都翻译成“■(天朝)”(P167)。这样翻译符合了韩国人的语言表达习惯和语言文化心理,正如韩国人对内很亲切地称韩国为“■(我们国家)”或“■(韩国)”,然而韩国自古就是弱小的朝贡国,十分渴望树立国力强大的对外形象,对外就称自己的国家为“■(大韩民国)”,却忽略了当时原语国的民族文化心理,而未能传递给译语国读者原语国人民的国民风貌。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镜花缘》的韩语翻译是极具挑战性的,译者顺应时代呼唤翻译出该书的百回全译本,整体来说韩译本既忠实又灵活地反映出原著的内容,赋予了作品在异域新的生命力。[11]引人深思的是《镜花缘》在韩国的传播是韩国人自觉接受的结果,根据洪羲福自述他翻译这本作品是因为其娱乐性和百科全书似的知识性[12],到了现代韩国社会,《镜花缘》中的航海经商流露出的冒险精神也被韩国资本主义社会所崇尚和提倡,海外游历的奇闻异事更是被韩国译者单独抽出来翻译成儿童文学得以流传。美学和哲学的需要自然也是韩国社会自觉接受这部著作的精神层面的深层次原因,审美的社会性及审美的主客观统一性[13],也解释了为何遭到中国读者诟病的炫学部分内容反而被韩国社会理解为“百科全书似的知识性”受到重视。中国传统学术中未能孕育出以跨越异文化为根本特征的比较文学,一是汉文学自成体系,自我衍生和更新能力强大;二是儒家传统的谦虚为怀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学者不会像法国学者那样通过研究比较文学来弘扬自身的文学自豪感。因此,一直以来都是汉文学单边性的“独语”或汉文学对周边小国文学的“发话”[14],我们的谦虚同样也是我们的骄傲,直到国门被西洋的枪炮打破,我们才开始产生向西方学习的意识,翻译西方著作,比较文学的概念也慢慢萌芽。而对于中国文学在韩国等亚洲地区的流传与接受,我们公认中国是他们文学和文化的母体,中国与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周边国家的比较文学研究相对匮乏,这方面的研究价值并未真正引起中国学者的正视和重视,自主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学的意识严重不足,相比之下我们更着重于中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比起汉文化圈国家对中国文学的自觉接受,我们基于平等对话上的主动传播与宣扬同样意义非凡,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必不可少的一步。
注释:
①本文所引《镜花缘》中文原文皆出自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版《镜花缘》,以下仅标注页码,不另注。
②本文所引的韩文原文皆出自最新且唯一的2011年版《■1、2》(《镜花缘》)现代韩语译本,文学知行社出版,为比较起见,所引中文译文皆由笔者从韩文版回忆,仅标注页码,不另注。
③■(文炫善)本科毕业于梨花女子大学中语中文专业,硕士毕业于梨花女子大学口笔译研究生院韩中专业。后任教于梨花女子大学口笔译研究生院,同时在梨花中国翻译空间编辑、翻译中文图书。现在■■(华音口笔译机构)翻译事务部担任组长,兼任韩国网络大学中文系任兼职教授及产业研究院海外产业研究助教等职。主要译著有《无目的美好生活》洪晃著(《■■》)、《用人大师》宫惠民著(《■》)、《黎东讲方史:细说三国》黎东方著(《■ 》)、《变》莫言著(《■》)等。
参考文献:
[1]郑荣豪等.■下(读东洋经典4文学下)[M].首尔:人本出版社(■),2006.
[2](清)李汝珍.镜花缘[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
[3]文炫善.■1(镜花缘1)[M].首尔:文学—知性社,2011.
[4]文炫善.■2(镜花缘2)[M].首尔:文学—知性社,2011.
[5]谢天振.译介学(增订本)[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6]赵莉,何大顺.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J].文学教育(下),2009(6):38-39.
[7]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8]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9]吴家荣.比较文学新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10]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涂又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1]謝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12]朱淑霞.几点翻译研究方法论的省思——以朝鲜时代中国小说翻译《第一奇彦》为例[J].中国语文论译总刊,2011(7):131-151.
[13]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三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14]王向远.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孙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