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只是一个代号
2018-05-15大头马
大头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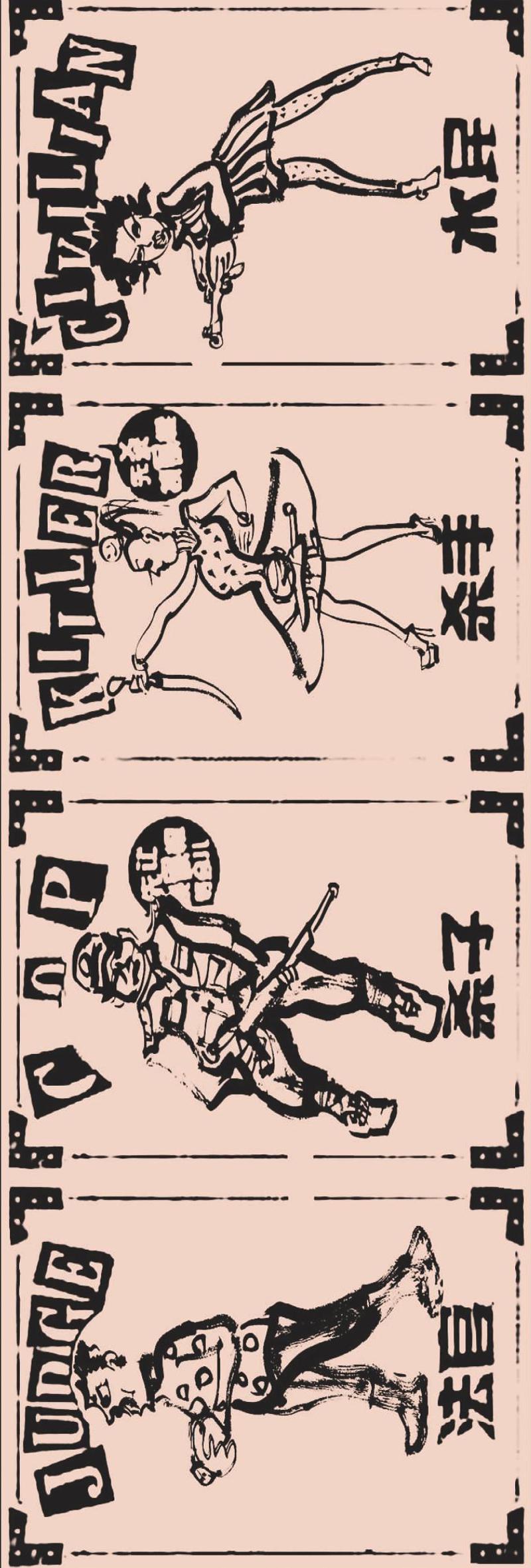
Party1
法官:1人
玩家:8人
警察:2人
杀手:2人
水民:4人
Night1
我和A,我们管玩杀人游戏叫“进去收尸”。这意思并没有半分托大,如果你参加过我们的杀人游戏,就知道为什么在大半个H市.只要有我和A在场.这游戏就得多加一条规则:我和A不得首刀首验。此条规则凌驾于一切规则之上,包括天黑请闭眼。
A只是一个代号,你可以认为他是任何人。为了方便讲述故事,我们就暂时称呼他为A。实际上只要你进入这个圈子,就一定听说过A的名字。A风趣幽默,机智过人,在游戏过程中,往往是场上气氛的调节者,只要有A在场,游戏必定是欢声笑语,紧张且有趣。在这方面,A是当仁不让的主角。
我呢?
我只是个小角色,辅佐A的在场,配合他讲的笑话控场,说穿了我就是个捧哏。一位非常低调的捧哏。如果不是特别关注我,你甚至不会注意到每次A说完一句机灵话,那个捧哏的声音是从哪儿发出来的。
当然,表面看是这样。
只有一个最为低调的人才能扮演好一个杀手,站到游戏的最后,赢得胜利。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最后的凶手往往是看起来最不可能的那个人。A的存在只是为了掩盖我的存在。我才是那个心思缜密、逻辑严密、冷静淡定的高手,绝对的赢家。
这么说你就信了?
哈哈,我只是在开玩笑。你在想什么?这是随机决定的杀人游戏,我和A既不可能每次都抽中杀手,也不可能总是搭档,一旦进入游戏,我们很大概率不知道彼此的真实身份,搭档、对手,或同为水民,都有可能。
不过有一点我没骗你。A的存在只是为了掩盖我的存在。心思缜密、逻辑严密、冷静淡定,也确实是我。近视八百度,从小学起我就知道自己没有扮酷的戏份。人生在世,不得不心思缜密。这就是为什么我会选A成为我的搭档,朋友,我唯一的朋友。因为认识了A,你就认识了无数朋友。女朋友。
哦,对了,我说的进去收尸,收的不是游戏里的尸体,我说的是真正的尸体。
这也是开玩笑。实际上我和A,我们说的收尸的意思,是指泡妞。
你以为杀人游戏是什么?比拼智力角逐技术的一门古老的角色扮演竞技游戏?别傻了,它只是个社交工具而已。绝大多数无聊的城里人用它来快速结识一些新朋友,在游戏中靠着残存的智慧和不成章法的断句进行表演或是自我剖析,比找出谁是杀手更重要的是照顾已经相中的那个姑娘的情绪,我觉得你有问题的原因是我想让你注意我,注意到我很注意你。等一晚上好不容易熬过去的游戏一结束,就可以顺理成章互相留下联系方式,过了一周假装不经意约一顿顺便的晚饭。再过一周挑选一场刚好热映的电影,电影院一定是在大型商业综合体,可以继续吃个晚饭。诸如此类。
可惜大部分人搞错了一件事,只有你把杀人游戏真的当成比拼智力角逐技术的一门古老的角色扮演竞技游戏,才能让它的社交属性发挥最大化,收获最多的成就,成为当晚的人生赢家。
这就是为什么A会选我作为他的搭档、朋友,不唯一但是不可或缺的朋友。因为只有我才能辅佐他玩好这个游戏,因为我是这个游戏里面真正的高手。
至于你相不相信——
“天黑请闭眼。”
游戏开始了。睁大眼睛。
第一个死掉的那个人叫Lily,死前遗言几乎没有任何信息量,腿长一米二,胸大肤白黑长发,有多美你们想象吧!反正我想不出谁会让这样一个尤物第一个死掉。尽管从游戏开始前的寒暄来看,她不会对游戏起到太大的作用,但谁不希望听她多说几句话呢?
坐在她对面的那个胖子看起来就很希望听她无辜地辩白“我不是杀手,我只是个水民”,但也有可能恰恰是他干掉的Lily,死掉的人总会对是谁首刀自己万分在意,而被杀,这会让人产生“对方注意我又浑不在意”的感受。让姑娘立刻注意到自己并注意到自己并不特别关注她,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被判了死刑的Lily睁大眼睛,一脸委屈,看似慌乱地朝着场上每个选手抛去小白兔般责备的眼神,实际上她眼睛里放出的五百瓦高压电流定向朝两个人发射的。
一个是坐在胖子右边的男生,绰号小武,不算高大但英俊过人,长相颇似年轻时的阿尔·帕西诺。他也知道自己有足够的性吸引力,满不在乎全场异性有意无意投来的电流,眼神总是下垂,思考的样子像一头小鹿。他还没开口我就知道他不会是今天控场的人物,他这样的人,少开口说话才能收获最大的印象管理效果。这也不是他有自知之明,而是从小到大习惯成自然,久而久之便静若处子,却无法动若脱兔了。
另一个则是坐在她左手边的第二个男人。开场前自我介绍姓高,让大家喊他高老板。高老板做咨询行业,业余爱好跳探戈,衣着得体,身材极佳,看得出来受过情伤。除非是真爱,不然对爱情不再有什么憧憬。不过对下场玩也没什么兴趣,他的主要兴趣应该是和投资人聊天。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诠释什么是体面。相信我,即便在大家都闭着眼睛的夜晚,他对法官做出的手势也同样优雅。
她目前还没有注意到A。
没关系,A朝我使了个眼色,嬉皮笑脸,他的位置很不错,就在Lily的左手边,高位,适合丢包引導风格。
“首先呢,我很庆幸,死掉的第一个人不是我,而是这位小姐。我没有别的意思哈,Lily?Lily是吧。你是不是想抽烟来着?”
Lily脱口而出:“你怎么知道?”
“不许对话。”法官说。
A对Lily笑了笑:“阳台在那儿。”然后面对大家,“当然不是我杀的哈。不过我估计杀手是个和我一样心思细腻的人。我感觉高老板你就是个善解人意的人。”
全场一阵大笑。高老板同样微笑。
高老板并不急于辩白A踩的杀手包:“我是个民,过。”言简意赅。
这么发言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他是个菜鸟,肚子里本就没什么货,这种人无论抽到什么角色,发言总是那么两句,久而久之,大家也就忽略了他的存在。这样的人不会是杀人游戏的宠儿,毕竟是个游戏,大部分人是来找点乐子,就算是菜鸟,也可以纵情施展些表演欲,哪怕不说话也行,只要你认为这是一种风格。总之,投入是首要的。每局游戏都匆匆敷衍了事,只为机械化地让游戏进行下去——那您出来玩游戏干嘛?一个人干点儿什么不好。另一种情况就是高老板为自己选定的游戏人格。高冷扑克脸,隐藏所有情绪,一位资深玩家。虽然现在还看不出高老板是哪种情况,不过我希望是后者。无论你为自己选定的是什么游戏人格,只要有人格,就必然会有破绽。
这一圈下来,除了胖子如我猜测的那样咋咋呼呼,水平一般,顺势跟了A踩给高老板的杀手包外,其他人都保持了第一局游戏陌生人之间的拘谨,并没有暴露太多的性格特征。当然,除了A。我相信A已经在所有人心目中留下了鲜明的人格特色。油嘴滑舌、嬉皮笑脸只是表象的表象,实际上他就是这样表里如一的人。游戏人格和实际人格高度统一,具有强烈的人格魅力。
至于A看中了哪个姑娘。我猜Lily已经是他囊中之物,从她十分乖顺地听从A的指示去阳台抽烟这点来看。这对A来说肯定没什么满足感。场上除Lily外还有两个姑娘,戴眼镜的那位看起来过于木讷,肯定不是A的菜。另一个则是高冷御姐范儿,看起来并不容易被征服,A已经兴奋起来了。我猜。
我表现得同样不赖。这意思就是没有任何人注意到我的存在。
“第一局游戏,又是第一夜,大家发言都比较谨慎。第一晚死掉的是Lily,她的遗言表示自己是个民。A高位丢包给了高老板,高老板说自己是民。嗯……此外大家的发言都没啥信息量。既然我是归票位,第一轮总得有个人出去。这样吧……我拉个PK,高老板,既然有人丢了你,我就点个你。再有一个嘛……”戴眼镜的姑娘看起来木讷.一开口倒是声音清脆,逻辑清晰,不过这也不意外,会来今天这个局的不会是低手。这是我和A的老朋友将军组的局,他是我认识的最专业的游戏组织者,也是最称职的法官。今晚的法官也是他。这姑娘不是来社交的,那么极有可能和我一样,是对这游戏本身有兴趣。是位Geek。
“坐中间的那位……你叫什么名字来着?不好意思,我刚去洗手间没听到。”
差不多过了三秒,我才反应过来。眼镜姑娘点的人,是我。“孔明。”
“啊,诸葛先生。那么就你吧。”
眼镜姑娘直视着我,就在这一刹那我注意到两件事,一是这位其貌不扬的姑娘,有一双非常凌厉的眼睛,她其实还挺好看;二是在听到我名字的那一刻,她放在膝头的右手食指不自觉地弹跳了一下。
我突然发现自己没记住她的名字。
场上剩余玩家:6
Night2
我们通常只玩9人局。
短平快,能够迅速看出一个人的实力。你没法在这样的快速杀人局中浑水摸鱼.从第一晚开始就必须全力以赴,每一个决定都至关重要,牵一发而动全身。
“杀手,请指认你要杀掉的目标。”
高老板的死前遗言是“我是个有身份的人”。他被我PK掉纯属偶然。我一点儿也没有要留下来的意思。毕竟这是第一局游戏,尽快摸清每个人的套路才是正经,输赢并不重要。对我来说值得注意的是那位眼镜姑娘,别误会,我不是看上她了。
孔明不是我的真名。
我说了,A只是一个代号,你可以认为他是任何人。我也一样。孔明是我今天晚上的代号。我的真名是什么?无所谓。是这样,我和A虽然在游戏界颇负盛名.可只有少数几个人能把这些分布流传在各个杀人局上的传说人物拼凑到一块儿,大部分人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他们在一局游戏中可能认识了两位高手,然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们。当然了,这些输家可能会在又一个夜晚相遇,然后交流起双方的游戏经验,就这样交换了信息,他们会发现,他们曾都与两位高手过过招。“我记得那晚我遇到一个高手,他……”“你说的这个人我也和他玩过!”“他是不是叫A?”“不,我遇到的那位叫x。”“但咱们说的应该就是一个人。”“对,绝对是他错不了。”这个圈子并不大,越顶级的玩家圈子越小。想要在顶级玩家圈子里彻底抹除我和A的存在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于是,我和A的存在就这样慢慢流传了出去。好在大部分人只是知道有这么两位人物存在,并不知道他们究竟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当然了,除了那些被A相中的目标。
不过在这方面我着实也为A的能力所折服。那些被他收服的姑娘,好像一点儿也没有泄露出A的什么信息。一夜情、几夜情,或是干脆谈了个恋爱,不管走肾还是走心,所有这些姑娘,曾经的玩家,一点儿也没为我和A在杀人圈添什么乱。我只能相信A是当代罕见的情圣。
具体是怎么做到的我从没过问过。我们之间有默契,只在游戏场是最好的搭档。游戏之外,我们不太关注彼此的生活。我对他的生活没兴趣,他对我的生活也没兴趣。除了泡妞,A没有别的爱好。除了泡妞,我对什么都感兴趣。我们有限的交往就是一起杀人,偶尔一起吃饭。
“哥们,你都怎么解决生理需求?”
一开始A试着给我介绍过几个姑娘,我当然也没有直接拒绝,吃晚饭、看电影、逛公园,也按照礼节约会了几次。一般到第三次,姑娘就再也不给我发消息,或是直接从联系人中删除。A也好奇,你到底无趣到什么程度才能让姑娘这样?后来他也就懒得再布施这个人情,只有一次终于忍不住好奇問了我。然后我把电脑里分门别类归档的A片和市面上所有类型的飞机杯给他展示了一下。之后他再也没有关心过我的生理需求问题。
天亮了。
这一轮死掉的是那个高冷范儿的御姐美女,长相颇似李冰冰。她本来介绍了自己的名字,但刚说完就被胖子用一句“我们还是叫你李冰冰吧”替代了原本的称呼。“不,你们还是叫我李奕宁。”她坚持。这样的人死掉想必会有些恼火,看得出来她是个强势玩家,会杀掉她的人要么是因为心虚,不想留太多强势玩家在场上和自己作对,要么就是出于……同性的敌对。
我看了一眼眼镜姑娘,她看起来倒不像是会有同性竞争意识的人。不巧,她也正在看我。
场上的背景音乐突然变成了匹克西斯的《嘿》。我不由得把目光从眼镜姑娘的身上移开,法官将军正套着他颇具个人特色的马头面具,手里捏着手机。
匹克西斯正在唱:
Hey
嘿
Must be a devil between us
我们之间一定有个妖怪
Or whores in my head
或者在我脑子有个妓女
Whores at my door
在我的门口
Whores in my bed
在我的床上
我花了十秒钟听这首歌,然后确认这绝对不是将军的喜好。
这很奇怪。法官们总是会在游戏时放一些背景音乐,掩盖掉不必要的响动引起的影响判断的场外因素。将军通常会放爵士音乐。他是性格非常平和的人,即便场上起了争执,也都是好说好劝,如果出了错——虽然我从没见过他出错.他一定会温和地道歉,低调解决。实际上,刚刚高老板出局的时候,曲子就变了,不过那是史蒂维·雷·沃恩的一首老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倒也还算符合将军那一路的趣味。
可匹克西斯?饶了我吧。这绝对不是一个老派绅士会听的东西。
李冰冰站起身,她已经没有遗言了。胖子看着她走下楼去,眼里充满恋恋不舍。他是个民以下身份的事实已经从这副贪嗔痴的心态里暴露无遗。等到李冰冰彻底不见后,他跳过我朝小武投去怨毒的眼神。
现在场上剩下的人里,小武的确是我们中看上去最像杀手的人。精瘦、黝黑,留着短寸,从袖管里暴露出的胳膊上显示出了含义不明的文身的一角,他看上去就像个真正的杀手。我原本以为他会是那种全程沉默的人。稍微出乎我的意料,他着实不是个绣花枕头,第一轮开口说话时条理清晰,显示出绝不是一个只是来社交的玩家。
A呢?我没关心这局游戏他拿的是什么身份牌。是杀手,是警察,还是水民,都无所谓。我们俩的游戏目标不一样,所以是不是站在一个队列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他的游戏目标刚刚已经全部阵亡。我的游戏目标……
突然一阵震动声响起。所有人都习惯性摸了下口袋,随即就想起我们游戏的地点是在一幢公寓楼的复式套房里,我们在楼上,这里只有一个大而空的客厅,一间洗手间,和一个露台。我们的随身物品都在楼下,和出局的玩家在一起。
这意味着——
全场人都看向了法官。
“不好意思,我接一下。”
法官将军走到露台,我们和露台隔着落地窗和窗帘。我突然想到,Lily那根烟抽得未免也太久了些。
法官将军很快就回来了。“那个,今晚的游戏规则可能要改变一下。”
“什么意思?”胖子问。
“今晚只有一局游戏。”
“什么?”这回所有人都懵了。
“只有一轮,就是这一轮。”
“为什么?”A问。
为什么,我也想问,但忍住了。
“不好意思,没有为什么。”戴着马头的将军这话说得相当不客气。
这不可能。
他们今晚不可能只想看这一场表演。
But hey
但是.嘿
Where
你
Have you been
在哪
If you go I will surely die
如果你走了我就死定了
We're chained Uh...
我们紧紧相连
We're chained Uh...
我们紧紧相连
We're chained Uh...
我们紧紧相连
匹克西斯在唱。
Where
你
Have you been
在哪
我的目标和A不一样,我的目标和A从来就不一样,我的目标是找一个人。一个和我一样,不,比我还要优秀得多的玩家。她的名字也叫作A。不过这里为了故事讲述的方便,我们还是叫她小A吧。A只是一个代号,小A也只是一个代号,你可以认为她是任何人。但我认识的这个小A,只是一个人。
小A的传说应该比我和A的要久远得多,也更转瞬即逝。她是那种真正的天才型的玩家,我只擅长通过逻辑推理和类似于心理计算的数学方法判断出每个人的身份,而她,是可以完全操控全场选手的人物。当然,一开始我也并不信服。
“清晰的判断力,强大的领导力,还有什么?”
“这都不重要。”
“那重要的是什么?”
“是……是她那双眼睛。”
我头一次知道小A这号人物的存在.是从将军的口中听说的。这时候,我已经很厉害,厉害到足以让将军跟我聊两句游戏台词之外的话。一个敬业的法官,尤其是混顶级玩家圈子的法官,是不该和任何一个选手谈论其他选手的。这是职业道德。法官是这个圈子里知道秘密最多的人。后来知道了将军的另一个身份,我更觉得那次他会跟我提到小A,完全是匪夷所思。
除非小A真的很特別,相当特别,特别到连将军都忍不住开了口。
说到这恐怕我不得不跟你解释一下,杀人游戏究竟是什么了。比拼智力角逐技术的一门古老的角色扮演竞技游戏,或者是一个用于结识朋友俘获猎物的社交工具,都对。不过这是对于一般人而言。对我而言,这并不是个游戏那么简单。
看见我们这个开放式房间天花板四角的隐藏摄像头了没?
我相信你是看不见的,他们花了大价钱装的摄像头和精心布置的伪装,如果那么轻易就被看穿,那也太小瞧他们了。
他们是谁?没人知道。反正我不知道。相比我、A、小A,甚至将军,他们才是这个游戏真正的玩家,隐形的玩家。我们管他们叫老板。
我能知道的只有一点,他们都是绝对的上层阶级。注意,我指的上层阶级,只是说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钱、最有权势,也最虚无的那些人。他们未必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达官贵族、统治阶级,他们有可能很危险,属于你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听说过的那种人,但是也非常有力量。财团的一把手,最高政治阶层的候选人,地下军事组织的头儿,都有可能。总之,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人绝对接触不到的人物。
观看一场精妙绝伦的杀人游戏,对他们来说就相当于看一场赛马。而我,就是一匹赛马。
他们会在像我这样的赛马身上下赌注,赌注可能非常豪奢,一块地,一部分上市公司的股权,或是一件蒙德里安晚期的作品,什么都有可能。除了作为娱乐外,他们或许也会用我们之间的游戏来进行一些更加重大的交易或赌注。
这意味着被下赌注的人,必须是那种真正的高手。挖掘、说服、组织这样真正的高手来进行比赛,就是法官的义务。在这个隐形的、真正的杀人游戏圈,这才是法官真正的含义。
将军就是这样的法官。
我就是在那次将军和我的谈话不久之后,被他说服,成了这个赌博游戏中的一匹赛马,一枚棋子,或是更难听点儿,一个玩物。随便你怎么想都行,我不在乎。
因为我只有一个目标,找到她。小A。
突然有一声叫声从楼下传出。
“退出!快退出!你們必须马上——”
那是一个听起来很熟悉的声音。
高老板。
场上剩余玩家: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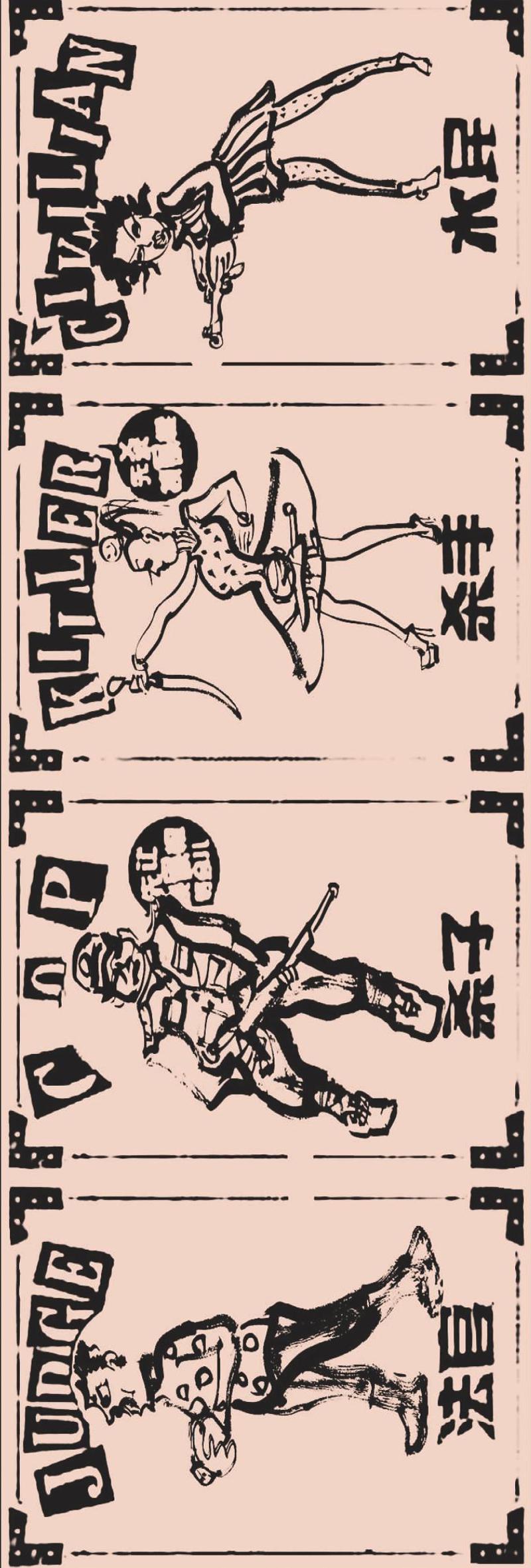
Night 2 1/2
实际上除了一起杀人外,我和A还算有一个共同爱好——打弹子。
那是在我们刚认识没多久的时候,我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在这方面从六岁以来积攒的经验。你知道,在大城市生活,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总得小心翼翼把一些幼年时期的趣味掩藏起来。我们这种勤勤恳恳努力了十几年,从小地方混到城市来读书,然后辛辛苦苦留在城市里的小镇青年,本身已经不酷了,如果再暴露一些按照弗洛伊德理论可以一眼从你的现在看尽你的过去和未来的趣味,就会更加危险。最大的危险是你不会交到任何一个朋友。
至于我是怎么暴露的——
当时我在一家台球馆兼职,A是我们那里的常客。A的台球水平,怎么说呢,和他的杀人水平一样——泡妞够用即可。他的招式很帅气,但击球成功率肯定不及业余高手,连一杆清台的基本功都勉强,不过在姑娘眼里,足够有障眼效果。他每次来都会带不同的妞,只有一次是一个人来的。平时他总是风度翩翩、潇洒自信,而那次,他非常沉默。就是因为这样,他才注意到了我。
“一起?”
“我们有规定。”我摇头。
A没说话,拉我进了男厕,不由分说把我那身台球馆的制服马甲拽下来,双手沾水给我迅速弄了个发型,松开衬衣第二颗扣子,然后跟我换了双鞋。走出去的时候,我看上去已经完全变了个人,成了台球馆消费的客人中毫不起眼的一员。
“扣的工资,算我的。”A说。
然后A就发现了我打台球的天赋。我们认识很久之后我才告诉他,其实我根本不懂怎么打台球,我只是玩弹子玩得好而已。“台球和弹子,本质上都是一种路径计算。”
“我只用知道你玩得好就行了。”
然后我就成了A的搭档,朋友,好朋友,非常有用的朋友。主要功能是配合他一起打台球,辅佐他展示酷炫的台姿。我的台风则非常平实,只是老老实实让球进袋而已。这样,我俩果然成了台球馆最夺人眼球的那一桌。A也收获了许多姑娘的联络方式。
我也觉得做A的朋友不赖,因为跟他在一块儿,总会很开心。他唯一不开心的那次,就是遇上我的那一小段时间,我从没主动问过,他有回倒是漫不经心地跟我说了。
“哦,当时我失恋了。”
“所以,那一次恋爱有什么不一样?”
“这问题你以后会明白的。”
A显然觉得跟一个会收集市面上所有类型飞机杯,却无法和女孩保持三周以上交往关系的人聊这个,实在是夏虫不可语冰。
A很快对台球腻了。因为在台球馆,能俘获的姑娘类型都差不多。你知道的,就是那种身材很好,长得很美,但着实没什么趣味的姑娘。这就是为什么A拉我一块儿进入了杀人这个圈子。在这里,你能遇见各种各样的人。比如,那位看上去很普通但绝对不是普通玩家的眼镜姑娘。
“警察,请选择你要验的目标。”
上一轮高老板的声音传出来时,大家都有点儿懵。
“他这是想给咱们增加点儿气氛还是什么?”A说。
胖子“噗”地笑了。所有人这才放松下来。
“不过今晚只有一局,这到底是什么情况?”A问将军。
将军没有回答:“游戏继续。从死者左边开始发言。”
A的发言十分平淡,似乎Lily和李冰冰都不在之后,他也失去了继续耍帅的欲望。胖子跳警踩了A:“昨晚验的是你,你是杀手。”然后发了我一张水牌。我没接胖子的水牌。小武则出人意料地也跳了警:“我才是警察,第一晚验的是Lily,她是个民。第二晚验的是……”所有人都以为他要说胖子,结果却是“谢灵”。我终于想起来眼镜姑娘的名字了,谢灵。
听小武这么说,我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感谢他帮了我一个大忙。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谢灵应该就是今晚这局里另一个玩家,真正的玩家。
通常来说,老板们的赌注只会在两个玩家之间进行.也就是说一局游戏里会有两匹赛马,但这两匹赛马是谁,他们自己在刚加入游戏时并不知晓。这也为游戏增加了难度。在有条不紊地遵循游戏规则判断各人身份之外,你还必须找出那个真正的对手,另一匹赛马,然后,尽一切可能打败他。法官会将赛马和冗余普通玩家,以貌似普通杀人游戏的方式组织在一场游戏里。
如果谢灵就是另一个玩家,这就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她听到我的名字的那一刻,会产生那种反应。这反应我很熟悉。
因为我告诉她的,是我在真正的杀人游戏圈里的代号——孔明。
这是我辨认另一个玩家的办法。简单粗暴,但是有效。一般玩家不会用这么大胆的方式,直接暴露自己,以捕获对方的破绽。但我和一般玩家不一样。一般玩家会愿意做赛马,原因无外乎是为了赚钱,或对和真正的高手过招本身有兴趣,或是觉得成为赛马也是一种骄傲。我的目标则是——找到小A。
“这都不重要。”
“那重要的是什么?”
“是……是她那双眼睛。”
我是在真正见到小A之后,才明白将军这话是什么意思。
那是在我成为赛马之前——将军向我提出了这个意向,但我拒绝了。我不想成为一颗棋子。对杀人游戏也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说到底,我希望这个游戏只是我生活的调剂品,虽然游戏很紧张,可它会让我很放松。那会儿我已经大学毕业,有了一份全职工作,在一个IT公司,做一个看起来挺有前途,实际上也挺有前途的工作。A的工作也终于从投行的实习生变成了正式的交易员。我们又有了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我们都不是很喜欢自己的工作。而且我们的时间都越来越少,杀人游戏成了少数我们能够一起放松维持友谊的活动。
直到我遇到了小A。我立刻明白了将军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他说的并不准确。看见那双眼睛,你的確会立刻暴露破绽,被她一眼看穿你的真实身份。而这背后真正的原因是——所有看见那双眼睛的人,都会爱上那双眼睛的主人。也许不是所有,这只是我的夸张,是我为了掩饰自己为什么会如此不中用的头一次败给一双眼睛而胡乱说出的借口。嗯,一个借口,一个非常值得的借口。为了证实这个借口我愿意再一次遇见她。
“我叫小A。”游戏开始前她介绍自己。
“我知道。”我看着她。
小A只是一个代号,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任何人都可能叫这个名字。但我知道,她就是将军口中的那个小A。这世界上只会有这样一位小A。
“你怎么知道?”
“这不重要。”
“嗯,这是不重要。”
天又要亮了。
在以前,天亮的瞬间会让我感到刺激。那是一种你在这城市的高楼大厦里蜷居时所不会拥有的心理体验。但遇到小A之后,每一次天亮都让我觉得有些惊慌。因为我找到将军,加入了这个赌博游戏,成了游戏里的棋子。从此这个游戏对我来说不再只是个游戏那么简单了。在和小A的那次游戏中,我输了。但随后就明白过来,我不是真正的输家,真正的输家是那一个,另一个棋子。小A也是一枚棋子。那局游戏,我只是填充游戏的NPC之一。我的输赢无关紧要。我和小A,就像是平行世界里的两个人,在同一局游戏里相遇了。
为了再一次相遇.我非常努力地成为一枚棋子,一枚顶级的棋子。只有这样我才能不断被老板们选中,晋级到他们更大的赌博中去。我相信只要不断往上爬,就会再次遇到小A。顶级玩家的圈子很小。按统计学原理来看,我已经差不多战胜了99%以上的玩家。
而今晚,为什么只有一局游戏?
我预感今晚这局游戏非常特殊。所以在小武跳警,说第二晚验的人是谢灵时,我会突然紧张起来。如果她就是另一个玩家,今晚只有一次比赛决定输赢的话……她肯定和我是对立面。
“她是个杀手。”小武说。
我向小武投去感激的一瞥。
谢灵几乎没有情绪,非常平静:“我是个民。我质疑小武的跳警,他第一晚验的是个死人,这个包怎么说都成立,而且他紧随胖子指认A是杀手之后跳警,这警跳得非常无力。我不得不怀疑小武和A的身份关系。”
其实她说的很对。按发言来看,小武这警跳得并不算成功。但我会帮他把票投给谢灵。
也许今晚之后,我就会见到她。但结果出局的是小武。
谢灵的两票是我和小武投的,小武的三票是,胖子、谢灵、和A投的。
A?
我对A会做出这样一个判断颇感惊讶,按发言来看小武的确处于劣势,可谢灵的确是个姑娘,长相也还说得过去,可A?
我的理性稍微有些动荡,内心对A产生了些许恼火。A不知情,做出的选择的确合理,可A你毕竟是我的搭档呀!我平行世界的搭档。
“天亮了。”
“不,等一下。”
场上剩余玩家:4
Night 3
天又亮了,不,等一下。请天等一下再亮。
“有人示意游戏暂停。”将军说。
“是我,我想先去趟洗手间。”我站起身。
“嗯。那各位也先休息一下。”
现在留在楼上的只剩下我、胖子、谢灵和A。
我走向洗手间,走进去的那一刻我看了眼露台,露台和洗手间是连着的,Lily不在那儿。我走进洗手间,然后一个念头闪过,不,她在那儿。只是她躺在地上,我没看见她。为了确认这件事我走出洗手间,路过露台那瞬间我又看了一眼,对,她就躺在地上,人事不知的样子。到底发生了什么?!
“怎么了?”
“灯坏了。我去楼下那间吧。”
将军,不,应该说是那颗马头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半个世纪。
“去吧。”
我注意到歌又换了。
现在是一首忧伤的抒情小调,石器女皇的《苍蝇之歌》。
I know.I know the sun is hot
我知道太阳火辣
Mosquitoes come suck your blood
苍蝇们争先恐后地赶来吸你的血
Leave you there
让你独自
All alone,just skin and bone
在那,唯留皮骨
When you walk among the trees
当你在树林问穿行
Listening to the leaves
请聆听树叶
The further I go,the less I know
我走得越远,所知越少
The less I know
所知越少
我明白了。只要有一个玩家出局,歌曲就会更换。这首曲子应该是小武的退场曲。
楼下却一个人都没有。高老板,李冰冰,小武,都不在。
我走进洗手间,打开灯。本来我是为了好好想想整局游戏,怎么才能在最后一个白天让谢灵出局。这是最后一个晚上了。
实际上,除了A投给小武的那一票让我疑惑外,更让我疑惑的是胖子投出的那票。
我是一名警察,胖子是我的警察同伴。
第一晚,我们验出高老板是杀手。A首位帮我们踩了高老板,正合我们的心意。胖子顺势跟了A,加重高老板的杀手包。我没跟,保护自己的警察身份。谢灵拉我上PK,说明有分散高老板票数的嫌疑。除了我知道谢灵作为一枚棋子跟我一定是对立面,所以她必然是杀手外,按普通玩家的逻辑,胖子也想到谢灵和高老板是同伴关系的可能性很高。
第二晚,我们验了小武,他是个民。胖子无法判断A和谢灵谁是杀手,丢个包给A还算可以理解,可最后归票给了小武,我只能认为胖子是对小武妒意太深。這些普通玩家的局限性。我重重叹口气。
等一下。我发现镜子上因为这口气起的水雾浮现出了什么。我又呵了几口气——
立即停止游戏,你不知道他们在赌什么!镜子上写着。
我又想起了楼上露台外面躺着的Lily。
咚。咚。咚。
谁?
“怎么那么久?”
我擦掉玻璃上的字,然后按下马桶冲水键,打开洗手间的门。是将军。
“不好意思。肚子有些不舒服。”
“快上来吧,都在等你。”
“呃。嗯。”
将军转过去。“小A也在等你。”
“什么?”我愣住。
“赢了这一局,你立刻就能见到她。在下一局游戏上。”
我呆在原地。预感是真的。
那双眼睛又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犀利过人,深不见底,好像能够一眼看到你的灵魂。谢灵的眼睛虽然也算凌厉。可,小A,不是任何代号的小A,我感觉只有被她望着的时候,自己才拥有灵魂。那晚见过她之后,我把她在游戏里说过的话翻来覆去想了无数遍,在唇齿间默默幻想有一个她,在和我一遍又一遍地进行着那晚我们的对话。
“我叫小A。”
“我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一语成谶。我知道。
我努力摆脱那双眼睛,然后追上将军:“他们……这一次赌的是什么?”
将军停了下来,缓缓扭过头来:“你不该问这些。”
“我知道。”
“我也不知道。”将军停了一下,“我只听说你上一次参加的那局游戏,他们赌的是……”
“是什么?”
“是某些珍稀物种的生命。”
我没反应过来:“珍稀物种?”
“你上次赢了吗?”
我点点头,那一局不是将军组的局。
“你灭绝掉了南太平洋某个岛屿上的一种鸟类。”
“灭绝?”
“从此世界上不会再有这个物种了。”
将军走上楼去。
我在原地待了有一千万年。
“你怎么知道?”
“这不重要。”
“嗯,这是不重要。”
这不重要。南太平洋某个岛屿上的一种鸟类。嗯,这不重要。
今晚呢?也许是大西洋某个岛屿上的另一种鸟类。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将再次见到小A。
我走上楼去。
天亮了,游戏继续。
死掉的人是胖子。没有遗言。
场上只剩下我,A,谢灵。第三晚我没有验人。我已经确定谢灵是我必须要干掉的对手。而我和A之间的一个默契是,我们从不会杀对方,也不会验对方。这是我们对彼此的某种尊重。胖子只能干瞪眼。
“死者左边开始发言。”
“游戏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A看着我,“场上只有一警、一民、一杀。我是个民,所以我希望警察能够站出来,给我指个方向。游戏就结束了。”他显然认为我是警察。
“不,我才是民。我不知道你们俩谁是杀手,不过A,我现在认为你的嫌疑比较大。”谢灵说。
到我了。我深吸一口气,游戏就要结束了。我就要见到小A了。
“我是警察。第一晚验的是高老板,他是杀手。第二晚验的是小武,他是民。第三晚,”我看着谢灵,“验了你,你是杀手。”我撒了个谎,然后看着A,“把票给谢灵,游戏结束。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今晚风可真大,呼啸着的风吹得落地窗直响。
“那么,现在开始投票。”
3,2,1。
“三人各一票,你们每人还有一次发言机会。”
怎么回事?我投了谢灵,谢灵投了A,A却投了……我?
我看着A,眼神里满是“什么情况”。
A清了清嗓子,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平静过。
“C。”他说。
C是我真正的名字。这个名字只有A知道。我从来没有在游戏里用过我真正的名字。实际上,真正的名字和虚假的名字又有什么区别?它们都一样,都只是一个代号。
“C。”他说,“你该停止这个游戏了。”
什么意思?我看着他。
“我知道你在找一个人,一个女人。可你应该停下了。你不知道自己都干了些什么。”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只是不断的在赢游戏而已。我只是不知道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你已经变得不是你自己了。停下吧。”
我看着A。他直视着我,迎接着我困惑的目光,瞳孔里仿佛有无穷无尽的液氮,可以冷凝一切我朝他投去的不解。
“所以,那一次恋爱有什么不一样?”
“这问题你以后会明白的。”
我回想起了曾经和A的对话。
我现在已经明白了。有一些人,是和别人不一样的。有一些恋爱,也和一般的恋爱不一样。就像现在,我想到放弃这局游戏,之后便永无可能再见到小A,一团密云便罩在了心脏上。我感到痛彻心扉。
實际上,我不止一次见过小A。我撒谎了。为了让这个故事更加戏剧化。
实际上,在第一次见到她之后,我爱上了她,她也爱上了我。我们开始了交往。可我们的交往仅限于杀人游戏。作为一颗棋子,你是不能和任何玩家,包括NPC玩家有恋爱关系的。一切联系都不可能有。你会受到严密的监控。也许你不相信,不过我认为在此后我和她共同在场的每一局游戏里,我们都不是在游戏,只是在恋爱而已。我们从未对彼此说过一句超出游戏玩家应该说的话,可丰饶而迷人的爱情通过那些看上去非常普通的游戏台词,源源不断地相互穿透我们的身体。有几次在游戏中我甚至都硬了,不得不去洗手间处理了一下。有时候我们擦肩而过,我闻到她身上奶油味儿的体香。那一刻我赞美上帝。后来我无数次回想我们共同参加的那一局又一局的游戏,那一个又一个共同度过的夜晚,都仿佛觉得它们是发生在夏末初秋,仿佛我们不是在一个个密闭的房间,而是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我说起来好像有很多场游戏,实际上并不多。我能以NPC的身份和她参加这么几场游戏,已经很说明问题了:找我这个级别的玩家当NPC,说明这个赌博游戏的级别也已经很高,这个级别的NPC玩家已经寥寥无几,法官只能反复利用我们,我和她这才见了不止一次面。很快她就不见了,彻底地消失了。我知道她晋级了,去了更高级的赌博场。
直到这时,我才不得不找到了将军。“我愿意加入。”
我成为玩家后,就渐渐地减少了和A搭档游戏的次数。偶尔也能在赌博游戏中见到他,那是因为他本来就是普通杀人游戏界有名的人物,找他来不知情地充当NPC的法官也不少。你知道,赌博游戏,虽然看的是赛马,但赛马和NPC玩家实力如果悬殊太大,一局游戏就会失衡。
“我不知道他们这一局赌的是什么,可事情已经失控了。不要再继续下去了!你已经没有自我了。你在把自己变成一具傀儡你知道吗?!”A站了起来,“你还记得一开始玩这个游戏的自己吗?”
我不记得了。
我突然觉得十分难过。我和A有多久没有一起玩一局真正搭档的杀人游戏了?似乎自从我成为棋子后,我就在不断地参加赌博,晋级,赌博,晋级,我好像已经忘了当初和A一起玩游戏时的乐趣是什么样的了。
我闭上眼睛。我和A曾经也管进台球馆打台球叫“进去收尸”。
A是我的第一个朋友。尽管我此前并没有认真想过朋友的含义。非要仔细去想,我们不过就是相互利用的同伴而已。相互利用。相互利用。相互利用。
“你知不知道,再往前晋级一步,你就回不来了?”
真的只是相互利用吗?我睁开眼睛。
这沉默的一瞬间大概有一个宇宙在寂灭。
A叹了一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如果你真的要找到她,我想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游戏了。”
那是一颗弹子.是我的弹子收藏里一直缺失的一种。
A递给我:“如果你决定好了,我会帮你。”
我闭上眼睛。
“请下一位玩家发言。”
“我。”我说,“我叫孔明。我是一名杀手。”
我努力把那双深邃幽暗的眼睛从灵魂中,不,连同我的灵魂一块儿提起来,从脑海中甩出去,然后倒灌海水进去。
我希望这样我就能看见南太平洋某个岛屿的一种鸟类。那种鸟应该有五色的羽毛,轻盈如云彩。
“请把我票死出局。”
我没有爱上小A。
这是我为了掩饰自己为什么会如此不中用的头一次败给一双眼睛而胡乱说出的借口。嗯,一个借口。一个非常值得的借口。
我再一次睁开眼睛。
场上剩余玩家:1
Finale
睁开眼睛时我看到的是一张笑脸。A的笑脸。
将军宣布游戏结束:“最后的赢家是,A。”
我得到了谢灵的一票。A没有投票,我也没有。可最后的赢家为什么是A?
我看着将军。从他的眼神里我立刻明白了两件事:一,A才是真正的杀手;二,A也是一个玩家,一个真正的玩家。一颗棋子。
“可是怎么会?”我目瞪口呆,“你怎么会是玩家?你不是A吗?”
“A只是一个代号。”A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可你为什么要踩你的杀手同伴?”我说的是高老板。
“他也是一名玩家。”
我愣住了。
“今晚这局,每个人都是玩家。”A说。
原来如此,我恍然大悟。这局游戏的种种不合理之处都联系起来了,难怪胖子知道小武是民还会投他的票。每个人都是玩家,这意味着你不但要干掉所有对立面的人,也要干掉自己团队的人。
我还是难以置信地看着A。
“我以为,我们是朋友。”
“在我成为棋子之前,是的,我们是朋友。”
“请输家立即离场。”将军不给我更多的时间吃惊、愤怒和悲伤了。
我和谢灵一起往楼下走去。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扭头问:“这一局他们赌的是什么?”
将军没有回答。A只是看着我,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什么。那种非常疏离的,仿佛我们已经不是同一个世界的感觉。
“生命。”谢灵冷冰冰地在前面说。
“谁的生命?”
没有人回答我。
我也听不到任何回答了。
在最后一刻,我突然忘了所要寻找的那双眼睛的主人的名字。她叫什么来着?那只是一个代号。我知道那只是一个代号。可是她不是任何人。不是任何人。
音乐又响起来了。这是一首,一首……
Supersonic超音速
He sitted in a comer all alone
他独自一个人坐在角落
He lives under a waterfall
整天以泪洗面
No bodV can see him
别人对他视而不见
No body can ever hear him call
甚至对他不闻不问
No body can ever hear him call
甚至对他不闻不问
You need to be yourself
你要保持真性情
You can't be no one else
不要像其他人一样
I know a girl called Elsa
我认识个叫埃尔莎的妞
She's into Alka Seltzer
她很迷艾尔卡
She sniffs ic through a cane on a su-
personic train
她最喜欢拿吸管吸它,吸食后就如坐超音速列车般畅快
And she lnakes me laugh
她也能让我开怀大笑
A只是一个代号。
A is for Alka Seltzer。
Party2
“博士,怎么处理907号AI的数据?”
“全部销毁。”
“全部销毁?可这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突破情感型逻辑游戏的AI吗?这可比十年前AlphaGo的Master在围棋界取得的战绩要牛多了啊!”
“可它没有按照我们给它设定的情感路径突破。”
“您是说……小A路径?”
“嗯。功亏一篑。它差点儿就因为爱上小A赢得了最终的局役胜利。”
“可它发展了自己的情感路径,这难道不是另一个重大突破吗?”
“这个突破过于重大了。如果任其发展,后果将不堪设想。你想想,人工智能有了自我情感意识,下一步是什么?自由意志。这不是我们人类可以控制得了的,必须要销毁这个AI,这些数据不得让任何人得到。”
“我明白了。”
“嗯。那迅速去处理吧。”
“好的。”
“等一下。”
“什么?”
“把908号的数据传给我看一下。”
“908号?那是?”
“A。”
責任编辑 夏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