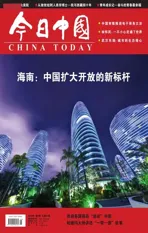从放牧娃到人类学博士—我与西藏四十年
2018-05-14文|格勒
文 |格 勒
我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时代。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藏族硕士研究生、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和藏族博士,家乡的父老乡亲甚至以此认为我是“整个民族的骄傲”。但是说实话,我长期为此忐忑不安,因为我个人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和能力,要说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就是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时代。
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
我出生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一位记者曾这样描述我:“格勒从一个‘约布约姆’之子成长为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学者,他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藏区的一草一木都和他息息相关,那是他生命的源泉和意义所在,在那里所经历的一切欢乐和痛苦,都能直达他心中最隐蔽的角落”。
这里的藏语“约布约姆”是男仆女仆之意,那是1956年民主改革前我们一家人的真实身份。那时我们家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只好终生为奴。我从很小时就开始跟着姐姐上山为领主放牧,拾牛粪当柴火,早出晚归。那时,妈妈希望我当喇嘛,因为那时只有当喇嘛才能有出息。

2009年格勒(左二)访问英国剑桥大学
1956年,我的家乡开始民主改革,领主的财产被没收后分给穷人。我们家分到了一套有玻璃窗的新房子、几亩地和几头牛。人民政府在家乡办起了西藏解放后的第一所小学,尽管当时寺庙仍以很强的感召力与之对垒,尽管当时叛匪的谣言在蛊惑人心,可只求儿子将来要出息的母亲还是拉着我的手走上三四公里路,第一个到政府办的小学给我报了名,妈妈希望我当教师。在以后的求学生涯中,每次遇到挫折和困难时,我都会想起幼年时解放军给自己的影响和对我家的帮助,想起民主改革后母亲第一次在自家土地上耕耘时喜溢眉梢的表情。
真正改变我命运的是改革开放之后。记得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我立即报名,第二年春天考上了西南民族学院,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入校的中文系本科生。第一个学期刚结束,又得知全国重启招收研究生的消息,在老师和朋友的鼓励下,我报考了中国社科院民族所民族史专业。1978年,我又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藏族硕士研究生,离开蓝天白云下的“世界屋脊”,来到首都北京,在“科学春天”的自由氛围中,步入梦寐以求的学术殿堂。
1983年到1986年,我在中山大学完成了人类学博士学位的学习。这段学习经历对我后来的事业发展影响深远。3年严格的科学训练,为我奠定了扎实的学术素养。
除了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我也有幸进入了两个好的学府,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山大学,并遇到了两个好的汉族导师,这就是李有义和梁钊韬教授。
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正是攻读学位期间的系统学习,使我从一个来自“世界屋脊”的懵懵懂懂、愣头愣脑的放牛娃,变成了一个“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年1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当江泽民总书记亲自把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的“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和荣誉证书颁发给我,在接过我敬献上的哈达时,他对我说:“你是藏族,是学人类学的”。是的,我是藏族,而且是一个出生于农奴家庭的藏族后代,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改革,我最多是一个会念经的小喇嘛,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更不可能有什么第一个藏族博士的荣誉和光环,更不可能成为一个“为发展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而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表彰证书和政府特殊津贴的学者。
见证西藏的变化

1962年格勒与二姐和姐夫在甘孜照相馆的合影

1980年格勒与硕士导师李友义教授在拉萨考察
四十年来,我西行西藏阿里,北上藏北草原,南下被称为“藏族起源的摇篮”的山南地区,东行昌都及云南、青海、甘肃诸省的藏族自治州,几乎走遍了整个藏区的城镇乡村。我曾为破解象雄之谜、古格之谜、神山神湖之谜而兴奋过;也为透过青藏高原神秘讯息,力图触及人类心灵、触摸文明轨迹、透析生命意义、关注人类终极问题而苦苦思索过;也为传统与现代边缘的藏族文化夙夜兴叹过。
不过,最令我感到畅快淋漓搞研究的还是我先后主持和承担多项涉及藏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国家级重点项目,如“中国藏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西藏百户家庭调查”,以及《挑战与机遇:加快西藏及其他藏区现代化建设步伐研究》、《西藏和四省藏区文化保护与现代化战略研究》等。
四十年来,我调查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西藏解放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承载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西藏农牧民的变化。根据我们对西藏城区、农区和牧区三种不同类型地区1000多户家庭的实地调查,结果显示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农村牧区和城市社会发生的变迁,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牧区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和牲畜的使用权、所有权由集体转到了个体农牧民手中,使他们有了与各自利益直接挂钩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主动权,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农牧民的收入,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改革开放以后,西藏农牧区由封闭单一型的自给自足经济逐渐向开放多样型商品经济形式转变。在市场经济调动下,农牧民不再仅仅从事农牧业,而开始利用开放的市场和便利的交通,从事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等多种经营。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牧民,他们的生活正在由温饱型向消费型转变,而且消费结构也在向技术性、教育性、旅游性和娱乐性倾斜。问卷统计结果显示,各种高档耐用消费品,如电视机、洗衣机、录像机、汽车、摩托车、手机、照相机、电冰箱、微波炉等都是改革开放后逐步进入藏区家庭,并逐渐由城镇传播到农村牧区。
改革开放后,宗教信仰政策得到落实,群众朝佛、转经、敬神等正常的宗教活动受到国家政策和法律的保护及社会的尊重,西藏人民恢复了享有最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调查结果显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西藏人民知晓程度最高政策之一,并且普遍认为这项政策“很好”。在传统西藏社会,年轻男人入寺为僧是最好的出路之一。改革开放后,60%以上父母希望子女成为干部和医生。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信仰佛教,只是他们就业观念发生了明显改变。
在居住方面,农牧民和城市居民的基本居住需求已得到满足,人均住房面积比民主改革前多了2.6倍。现在人们普遍追求的是旧房改造为新房,平房改为楼房,而且许多新房装饰华丽程度超过了解放前贵族的庄园。
在饮食方面,无论在牧区,还是城市,都由吃饱向吃好转变,并且饮食结构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主食(如糌粑)、原粮、粗粮等的需求虽仍很大,但已呈下降趋势,这都是饮食水平逐步提高的印证。
在穿着方面,西藏农牧民和城市居民对穿着的要求不再仅满足于保暖,而是追求式样新颖,色调协调,对中高档服饰的需求也在逐步上升。如在江孜班村,獐皮镶边羊裘属于中档消费品,拉萨城中穿汉装和西装的人越来越多。
在政治生活方面,改革开放后,西藏基层实行民主选举,成为普通基层藏族群众参与政治管理的重要途径。新的行政管理组织成员的选拔以其才能和社会成就为主要依据,取代了过去部落式,或家族式选举方式。
向世界介绍真实的西藏

2016年格勒在母校大门前
作为一名人类学学者,我经常会收到一些国外高校学术交流的邀请,对我而言,这就是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西藏的绝好机会。
1989年,我在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面对80多美国学者的学术演讲的题目就是“西藏是‘香格里拉’,还是农奴制?”。在美国加州大学,我对着台下60多名美国学生,给他们讲中国是56个民族的大家庭、讲什么是马克思的民族理论、讲什么是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团结……通过这样一种非官方的、民间的文化交流形式,美国年轻人了解到了中国少数民族的现实,当然其中也包括西藏的现实。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走遍了半个世界,发现西方国家学者有一个明显的矛盾心理:他们理所当然地生活在现代的社会里,而一旦讨论西藏的现代化就会引起不断争议和指责。对于许多西方人而言,西藏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神话,尤其是1933年《消失的地平线》出版后“寻找香格里拉”的热潮风靡世界,他们把西藏虚构成人类梦寐以求的精神家园和灵魂皈依之地。
作为一名中国藏族学者,我的物质梦想是西藏实现经济现代化,精神梦想是藏族同中华民族各族同胞一起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如今,我已进入古稀之年,但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还继续从事着教学和科研,为培养藏学和人类学人才而贡献余热,为西藏发展,为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团结做点事情—这是印在我骨子里的人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