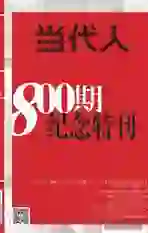从江的青春
2018-05-10蒋殊
蒋殊
11月下旬,正是北方的冬日。落地贵阳,迎面的风里便觉出暖。再行至从江,衣服便又脱去一层,让北方的人觉得又回了春。
坐大巴,若抛开路途的颠簸与漫长,一路是有好景致的。贵州处在群山环抱之中,除了山还是山。然而贵州的山是有韵味的。这里有老话“天无三日晴”,便让贵州的山多了几许朦胧与神秘。缭绕在山间的雾缥缥缈缈,营造出仙境般的美妙,恍若梦境。北方的人们,便要透过车窗呼出一声声惊叹,疑似上面住了神仙。那些花花草草,更摇曳着身姿一路挥手,倾诉着青春的风情。
从江的历史从元代就开始了,从江的名字却是1941年由永从、下江两县合并来的。处于黔东南部的从江,由于偏僻,成了贵州通车最晚的县。县内第一条公路是1964年才修通的。之后经40多年的不懈努力,到2011年321国道由北向南贯通全境,从江也融进外面的世界。2014年底,贵广高铁通车,让从江与外面的连接更有了新速度。
人们说,到了从江,就等于到了黔东南,因为苗、侗两个民族占了总人口的95%,是地道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然而这些年走过许多地方,觉得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都汉化了,不仅没了纯正的风情,而且必然与国内许多村庄一样,成了老弱病残聚居地,没了青春,没了生气,没了活力,落满一地乡愁。
没想到,从江,果断对我说了“不”。
占里村,是踏着那条长长的禾晾通道进入的。禾晾真是从江一道看不够的风景。一排排稻穗真是美啊,迤逦地倒映在水里,蜿蜒到村中。走过那位低头专注制麻纸的女人,以及一位叼着烟斗专心打制芦笙的男子,一个女孩笑盈盈站在鼓楼下。这样偏僻古老的村寨,这样青春的面孔,我的心不由轻轻动了一下。随后,忍不住与同行者围上去抚摸她的衣饰。她的服装是典型的紫色侗布,身上银饰环绕。现在回想,那时她的脸是桃红色,以至于我总记得她身着桃红色的服装。最吸引眼球的,是脖子上由小到大四条银项钏,还有两条长到腹部的银珠链。珠链是空心的,倒不太重。那四重银项钏可是实心,我试图两手托起,很吃力。
姑娘也笑,说重,戴一整天会累。但是要戴,因为好美。确实美。或许唯有这层层叠叠的银器,才能显示侗家女儿的妖娆与华丽。
姑娘的身后,鼓楼中的长凳上,一排女孩,一排男孩,相对而歌。他们唱歌不努劲儿,是唱给对面异性听的随意,间或带着羞涩。散落在周围一群一伙或闲适地做活儿,或独坐的老者,漫不经心地聆听着他们曾经的青春。一些小小童儿玩弄着手中的芦苼,跃跃欲试着此后要抵达的青春。
男性唱歌的队伍中,最边上一张面孔格外引人注意,他手上弹一支侗族琵琶,怀里倚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儿。小孩儿忽闪着一双童稚的眼睛,时而仰头盯了他的脸看,时而认真盯了他手中的乐器出神。那似懂非懂的神情中,是不是营造着一个辽阔的未来?
那张青春的面孔,难道是爸爸?鼓楼外这个女孩子回我,是的。
那么年轻的爸爸。“那么你呢?结婚了吗?”结了,有一个小孩。再问她年龄,說23岁。23岁的妈妈在城市很难遇到。上完什么学呢?她说初中毕业就回来了。没有继续上学的原因,一是因为家贫,二来也是喜欢回来唱歌。
回村唱歌。这个答案为何那么动人?
那一刻,竟没有为她惋惜。这样的环境,这样的青春,这样的歌声,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
又一轮侗歌响起,飘荡在这世外桃源。女孩快乐地加入队伍,亮开歌喉。远远回头一笑,暖了整个视野。
吊角楼上蓝色的侗布,在歌声里跳跃着,诱惑着女士们的视线。
记得前一天无意走进岜沙附近一个寨子,一位老人坐在一卷侗布前,专注着她的工艺。侗布已经由蓝变紫,长长地从晾衣绳上拖下。一条板凳,一把刷子,一个脸盆,她细致地在面料上一层层刷着。几经努力后终于听明白,刷的是蛋清,是制侗布的一个环节。从江县的门前屋后,随处晾晒着这样的侗布,再加上路遇的捶布者,以及几位制纱女子,一笔笔勾勒出他们身上成衣的全流程。老人把刷子递给我们,示意可以体验一下。认真刷过一层,心生愉悦,从此一件衣服上注入我的印痕。
另一边,两位中年妇女正在查看晾晒的侗布。问布有名字吗?她们只是摇头,后来才知是听不懂汉语。一位年轻的女子坐在门前,背上一个小儿,怀中一个。她正精心给怀里的女孩梳头。她的普通话很好,告诉我们布是侗家的布,是侗家女人的智慧与心血,颜色由板兰根等诸多植物染制而成。之前也听说,侗布从制纱、晾晒、纺织、染色、捶打、晾干?、裁剪、绣花到成衣,要三年时间。
两个孩童安静地盯了我们看,三只鹅咕咕叫着从对面走过来。回头细看,背上是一个男孩。不远的将来,他们也会身着侗衣,一个织布,一个制笙,一起唱歌。
离开村子时,一位农者赶了五头牛从身后跟上。长相不似北方的牛,其中一头在我们回头时竟不眨眼盯了过来,含着敌意。与它长久对视,是因为不敢轻易跑开,怕它像小时候追过我的那头一样举着牛角追来。好长一阵后,它或许看清我们是善良的远方来客,黑毛终于松懈了,带着失礼的尴尬把眼神移向别处。被赦免一般,我们一半惊一半喜飞速跑开。上到远处,回望仍在原地的它,终于敢哈哈大笑。
多少次梦里想象这样的村庄。当身处其间,总是莫名感动。
随后来的,是小黄的惊艳。小黄,多么动人的名字,像唤我少年时期的邻家伙伴。
小黄是从江高增乡一个村子,号称“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去时,是第十四届侗族大歌节前一天,也是小黄的节日。村中的人们大都聚集到广场上的鼓楼下,还不断有三三两两的人群向着鼓楼而去。我却总会对沿路那些孩子心潮澎湃。我的村庄是没了孩子的村庄,许多许多村庄是没了青春的村庄。那么多人一次一次书写故乡,挥发乡愁,不就是想唤回这种鸡飞狗跳孩子哭大人闹的图景吗?
对面又一个男孩过来了,一件紫色侗布上衣,头上包一块黑白小格布围巾。而他身边的两个小女孩,无一例外银头饰,银耳环,银项圈,银手镯,银围兜。带着小黄的表情,迈着从江的步伐。
鼓楼的人,越聚越多。抬眼数过,这里的鼓楼共15层,较占里高两层,彰显着民间艺术之乡的华美。然而令我震撼的不是鼓楼本身的壮观,依旧是鼓楼下那数不过来的青年、少年与儿童。目测过去,整体近千人。
一遍遍在心里问自己:哪里来的这么多孩子?实实在在,都是小黄的孩子。小黄包含小黄、高黄、新黔三个寨子,人口三千多。
这是一个正常的小黄,正常的村庄啊!
小黄的孩子,一代代传承着“小黄的歌”。小黄的歌不仅几度走上春晚,而且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便有9位姑娘受邀走上巴黎金秋艺术节,一出声便倾倒整个巴黎城。
歌声还未开始,孩子们却有条不紊,保持着他们的姿势,站立成小黄的风景。间或有一些耐不住无聊,与左右打闹几个来回。
终于,终于,小黄的声音响起,掠过观众,飘过鼓楼,渗进群山。小黄与贵州许多地方一样,都是在大山的某一处平一块地,住进人类。这里的人类,因而与群山融为一体。他们能看懂群山的表情,群山可听懂他们的歌声。
这个即将进入12月的季节,太阳将这里调成温和的春天。春天里,阳光下,年轻人在鼓楼中唱得动情,唱得磅礴,唱得婉转,唱得震天动地。观看的队伍中,一位很英俊的本地年轻男子,热情地跟我们打着招呼,回答着远方客人一个又一个神秘的问题。并一再邀请,如果不走,就到他家做客。
被他的诚挚感动。说话间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跑过来,缠他。问,知是他的儿子。刚刚得知是1990年出生的年轻男子,一弯腰把儿子抱起,任他在怀里扭捏淘气。那一刻,他的眼里突然就没了孩子气。
与占里那位女孩一样,由不得问他留在村里的原因。他一边安抚怀中的孩子,一边告诉我,虽然到城市打工挣的钱可以多一些,但会失去在村里唱歌的欢喜。
还是舍不下这种生活,习惯了。他最后这样说。
又是欢喜回村唱歌。确实,这里人人会唱歌,小孩子从会说话那一天就开始学唱歌,会走路就歪歪扭扭摆弄乐器。在这里,歌声是他们的信念,是希望,是生活,更是日子。
说话间,一个女子走来,在身边站定,朝怀里的男孩笑。女子挺着大肚。男孩说:我媳妇。
女子瘦瘦的,黑黑的,矮矮的,没有男子好看。又突然想到占里鼓楼下那位23岁的女孩,与眼前这个男孩,倒是很般配的一對。可见天下男女,有多少终老也走不到一起。又可见,天下男女,缘分根本不在外貌的般配上。
他们对视的眼神里,溢着幸福。问女子:老二几个月了?她腼腆一笑:春天生。
春天生的胎儿,被母亲的手柔柔地抚摸着,被小黄的歌悠扬地滋养着。
一位看上去六十岁左右的妇人,远远望着女子的肚子走过来。在身边站定后,又抬眼慈祥地看着男子怀里的孩子。一问,果然是女子的母亲。无须开口,一家人的交流全在眼神里。温暖散遍周遭。一家四代,可以日日相聚在这鼓楼下,这动人的歌声里,这奇妙的山水间。所谓幸福,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诱惑?
歌声还在继续,空灵中透出暖。一些不唱歌的年轻女子,边听边一针针忙活着手中的绣片。男子怀里的孩子,也终于从爸爸的衣兜里掏得10元钱,咯咯笑着下地跑了。
当晚,便是从江第十四届原生态侗族大歌节。
广场很大,舞台很大。四面八方涌来的人群川流不息,一不小心就会被挤散。前面的苗家侗家各种节目,都给最后的大歌留了足够的期待空间。
侗族大歌,要登场了。震撼,是从演员上台开始的。确切地说我之前没有见过这样的上场方式,身着民族服装的侗家歌手手牵手,起初是四五岁的孩子,后来是十来岁的,之后是二十多岁的。男男女女,大大小小,整整齐齐,川流不息,一行又一排。那一瞬,观众忍不住望向台下,好奇这支庞大的队伍突然从哪里冒出来的。那么大的舞台,他们一层一层排开,高高低低,错错落落,布满整个舞台。好长一阵了,后面依然有人在登台,走也走不完。终于,大舞台再也容纳不下,台下的演员只好止步。
这是贵州大健康产业示范区内的中国传统村落峰会会址广场。一个峰会会址,一个广场大舞台,居然容纳不下一个节目的演员。
这便是侗族大歌气势的开篇。这是从各个村落汇聚而来的几千人大队伍,没有乐队,没有指挥。他们光芒四射地站在舞台上。
全场呼吸瞬间静止。
大歌响起,向观众发出侗家的嘹亮。广场立时被这原始的音色笼罩,有些落在观众席,有些飘向远方。声音忽柔,忽强;忽抑,忽扬;或高亢,或低沉;或万马奔腾,或小桥流水。观众的心也跟着或喜,或悲;或收,或放;或一马平川,或荆棘丛生。广场上空成了声音的天堂。有贵州的朋友扭身告诉我:有8个音哦,仔细听。我当然听不出来,但是我的泪出来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感动了我,打动了我,触动了我。
总之,我的泪出来了。
夜空中有多半个月亮,也静止在我们头顶,发射着温柔的光,告白着内心弯弯的流淌。
我在有限的镜头中,将舞台上那些面孔拉近,又推远。推远,他们却挤占了我的心。
大歌,波澜壮阔地结束。舞台上艳光四射的演员下得台来,很快消失在朦胧的月色中,三三两两行走在回家的路上。大山深处,有等待他们的一盏盏灯。不用回头,只听身后那叮叮作响的清脆,便知有一群曼妙的侗家女儿随后。她们身上的银器太诱人,独一个围兜,就嵌着四十多片圆形银饰。许多女孩,背后还背着一个S形银饰,拦下问过她们,只是谁都不知道换作普通话如何读。
大门外,一名女子与同伴挥手,走近路边一辆车子。她细致地一件件褪下身上的银饰,整齐地码进车的副驾驶座位。几分钟内,她从一个光彩照人的演员变成一位普通的侗家女子。一弯腰钻进车内,抱起在奶奶怀里耐心等她的孩子。看得清,孩子在她怀里咯咯笑着。
看她坐定,爱人扭身,发动了车子。
一家人远去,离开这个依旧沸腾的大广场。一群群演员还在鱼贯出场,如同车中的女子,走下盛大的舞台,回归脚下的土地。
如此从容的转身,华美也笑,耕田也笑。
舞台上最小的那群孩子也牵手出来了,飞向迎候他们的爸爸妈妈。
突然想起第一天走进岜沙时,一群五六岁的孩子冲着我们叽叽喳喳。看他们又蹦又跳的情形,想是开心看到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可是一次次细听下来,却懂了。原来,他们重复喊的是两个字:给钱!给钱!
心内一惊。幸亏,之后再没有遇到类似的事。我知道,孩子们无错。起初,一定是哪一个远方来的游人,向这些贫穷伸出了手。此后,又一些人,以同样的方式“怜悯”着眼前人 。日久了,孩子们便觉得这该是远方来客一份见面礼。
有些风气,是游人无意推动养成。
愿,许多游客没有像我一样,执着地要听懂他们嘴里的话语。事实也是,大多数游客并未在意。他们眼里,这些跳着笑着的孩子,只是在跳着,笑着。
这所有的所有,都是从江的青春。
编辑:耿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