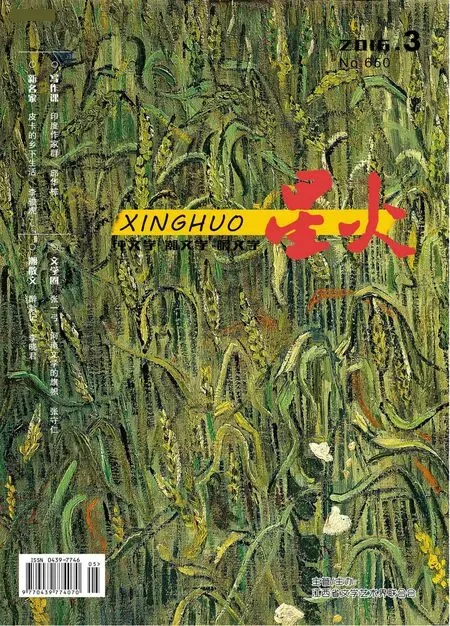换肾记
2018-05-02○李琼
○李 琼

李琼,七零后。医务工作者。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西省作协会员。有作品散见《散文选刊》《散文百家》《中国文化报》《中国妇女报》《中国水利报》《创作评谭》《东莞文艺》等。入围第一届“浩然文学奖”。
世间要换肾的人很多,已经换肾的人也很多,没有换成肾的人更多。我从没想到,我的妹妹,她居然也会成为中国数百万亟待肾源的病患之一。
此刻,我与姨妈一起乘坐在开往省城的列车上,高铁还没有开通,走得急,没买到票,托熟人送上车的,然后在过道照顾性地给了两张塑料凳坐着。两个人都心急火燎的,没有过多的对话。姨妈只是问了一句,是真的配上了么?嗯,我半信半疑地回答。这样接一个电话就急匆匆往省城赶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早有些麻木了,亦有些厌烦。妹妹执意要换肾,父亲因着高昂费用的缘故犹犹豫豫的。父亲在省城的同学江伯伯知道后,一拍桌子,这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呀,你不能不管,你放心,我来安排。江伯伯动用他多年的人脉终于联系到了省城一家医院,开始帮妹妹排队等肾源。
一进移植科,走道两边站满了来排队的病人,加上陪同的家属,乌泱泱一大片。病人的脸因长期透析的缘故,一般都偏黑,这让你很容易就分清谁是病患、谁是家属。大部分人沉默不语,或席地而坐,或好几个人挤在有限的长凳上,家属一般都不去占位的。偶有几个心态好的在一起叽叽呱呱,说谁谁上次配型配到了,羡慕的语气嫉妒的语气都有。有位病友从上海过来排队,这边的费用和上海比要便宜好多,肾源也没有上海紧张,结果好不容易配上了,飞机因为天气原因不能起飞,错失肾源。有位病友回回来都无功而返,有回电话又通知他来,他想我每次都没配上,这次肯定是又跑空;结果偏偏有指标,气得他只能怪命该如此。他们私下小声说打电话通知的护士要打点到,有一个病人排队排了三年都没接到过电话,一问别人来过好多趟了。有个病人的老公是某系统的领导,她老公帮她搞了两个肾源过来,像单位选举,其实早已内定,为了走过场,形式上还是要搞一搞的,于是妹妹就当了一回“陪选”。通知了四个人候场,化验费花了好几千,满心欢喜,以为这次非自己莫属,最后四选二,还是出局。病友们纷纷恭喜妹妹,说下次就是你了,果不其然。
A型、B型的肾源相对更多些,AB型、O型的肾源就比较紧张。一般早上九点以前配型初筛结果会出来,有时候也会较晚,有回等到上午十一点才出来。护士长来宣判时,病人和家属大气都不敢出。念到了名字的赶紧欢天喜地去办理住院手续,有如买彩票中了头奖,没被点到名字的就麻木地失望而归。一群人作鸟兽散。
这次妹妹是四点起床,赶早上五点多的火车,要在八点前赶到医院。我们都有事脱不开身,没人陪她去,她一个病人,独自早起赶车,差点误车。冥冥之中,或许是菩萨保佑,火车居然晚点了,妹妹有惊无险地上车了,而且就是这次居然给配上了,差点步了上海那位病友的后尘。
没配上型的病患们又马不停蹄地赶紧回去透析,权当来了回演练,只是演练的次数多了,人就渐渐麻木了。回家的火车要赶去售票点买票,病人为防感染得戴着口罩,因透析严重变形的手腕每每引来异样的眼光。血液透析疗法,简称血透,就是将患者的血液和透析液同时引进透析器(两者的流动方向相反),利用透析器(人工肾)的半透膜,将血中蓄积的过多毒素和过多的水分清出体外,并补充碱基以纠正酸中毒,调整电解质紊乱,替代肾脏的排泄功能。血透是不能中断的,否则可能导致原来的疗效功亏一篑,甚至威胁生命。因此血透室不像别的科室,你可以打招呼随便插队,病人都是掐着时间来透析的,每次透析的时间是四至五小时。当下血透室的情况是透析的病人越来越多,血透机增长的数量往往赶不上病人增长的数量。像这样临时去省城就要和别的病人调机。血透室一般分两班,有时晚上也会开机,但不会天天晚上开机,你没赶回来就意味着你不能按时上机,后果很严重。新来的病人一般都是晚上上机,等做了几个月,医院才会慢慢调整到白天上机。
在后来与妹妹交谈时,妹妹说从开始知道有机会换肾起她就时刻做好了准备,控水,控血压,每次省城打来电话都是充满希望赶过去,路上还要和透析室讲好调时间,哪怕每次都以为会有肾源但是次次都没有。坚持了一年多,这一次终于可以换,心情既激动又忐忑。上午化验的时候以为还是像以前一样“演习”一遍,谁知中午就有电话通知真的可以换。可是检查还没做完,钱也没有到位,身边一个家属也没有,心里慌得不得了,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父亲的同学中恰好有一位在这家医院退休又被返聘,他暂时代替父亲充当了家属的角色。这次是三台手术一起进行,一位男患者换肝,妹妹和另一位男的各换一个肾。别人家的家属一大帮人,妹妹孤身一人,立马想到的是赶快和单位领导打电话请求马上打款,然后通知我这个当姐姐的赶快过来签字。妹妹先是一个人跑来跑去把没做完的检查做完,接下来又跑银行查询钱到位否。钱不到位肾源可能会通知给其他人,一旦错过这次机会也许很难再等到O型肾。幸好钱顺利转入了医院给的账号,我们也在最后一刻赶过来签字,妹妹才上了手术台。在手术室妹妹的心脏怦怦直跳紧张得不行,血压好高。麻醉师居然是老乡,他过来用家乡话安抚妹妹不要紧张。要打麻药了,妹妹偷偷瞄了一下,只见玻璃针管里一支牛奶一样的液体被推入点滴管,妹妹马上睡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事后妹妹回忆当时手术室里好吵,就好像有几十个人在大声说话,但没有一句是听得懂的。应该是听到了另一个空间的声音。醒来后妹妹就发现自己在监护室了,身上七八根管子,一动也不能动,比透析还难受。血压一直超高,接近二百,尿有但是量不算太多,隔一小时就要量一次血压,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输液洗肾。刚开始不可以吃东西,后来可以吃流质了,可也不怎么敢吃,吃了东西要排泄,全是些十几岁卫校的实习小护士帮你弄,妹妹这辈子从没有上过这样的“厕所”,怎么排得出来?手术后的头几天晚上,换肝的病人不停地讲胡话,吵得妹妹根本睡不着。旁边一同换肾的病人因为咳嗽影响了新肾,尿血,痛得哇哇叫。吓得妹妹呼吸都不敢变大。好不容易熬过了七天终于可以出来了,妹妹以为可以慢慢走到病房,没想到一下床就瘫在了地上,浑身没有一点力气,最终还是坐着轮椅出去的。一出来就迎来了姨妈热烈的欢呼,心里暖暖的。在病房的日子就舒服多了,基本上可以自理。不需要劳烦别人伺候上厕所,只要打完点滴,这一天就没有事情了,医生除了查房再也看不到人影,住满了七天就拆线出院了。为了方便复查,妹妹在省城租了间短租房暂住。在省城住的那一个月,身上一直没有力气,走不了多远,每天只能坐在租来的短租房里看电视,幸运的是有姨妈的陪伴及细心照顾。期间我回去上班了,爸爸和继母带着妹妹的宝贝女儿过来看她,继母一直板着个脸,不高兴的样子,但见到久未见面的女儿,妹妹还是很欣慰。
没妈的孩子像棵草,母亲过世多年,好在我们有姨妈。胖胖的姨妈身材高大,圆脸,说话嗓门大,她比母亲更能干更精于人情世故。姨妈身上有母亲的影子,有我们遗失的母爱,她代替自己的姐姐把母爱给了我们。妹妹换肾的前一个月我都在生病,刚可以下地挪步,就接到妹妹换肾的电话,父亲年高不能陪同(以我对父亲的了解,他去了也是帮倒忙),我只有咬着牙和姨妈一同赶赴省城。
一进病房,医生就叫我签了一大堆的告知,根本没时间看,看了也不可能有异议。送妹妹进了手术室门口,然后是漫长的等待。换肝的患者自己也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另一名换肾的是一生意人。都是生的女儿,都好孝顺的,七姑六婆的亲戚来了好多,只有我们这边人丁单薄。家属看到病人推出来就在一旁抹眼泪,明明手术很顺利,应该高兴才是。我很平静,或许是在医院工作的缘故。更多的时候我都在操心费用的事,万一超过预算了怎么办?家里已是弹尽粮绝!妹妹是最后出来的,麻药没醒,没法交流,护工直接把她送移植监护室了。一连几天都见不到妹妹,也不让你探视,偶尔在门口的监视器里让你望一眼,外面的家属热情地和病房里面的亲人打招呼,里面的人其实是听不到的,但外面的人相信里面的人会感应得到。从视频中看到亲人的一霎那,个个都热泪盈眶。我的工作不能长期请假,是姨妈一直守在妹妹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她。妹夫自妹妹尿毒症后不久就离家而去,不闻不问,听说他在外面早有女人。后来他屡次来哀求,妹妹还是放他一马,办了离婚手续。
术后医院通知交费,十万。前面入院时已交十万,这十万一交,身上就没有一分钱了,万一再有个什么情况,还不知要交多少钱。我担心钱不够,打电话向妹夫开口,他立马答应出几千元。不像自己的姐姐,人影都没有,打电话不理,更别说经济上的帮助了。我还打了电话给父亲,让他也打点款过来,不可能妹妹做一个这么大的手术,不出一分钱吧。父亲告诉我,继母说没有存款拿不出钱。一个县级干部的退休工资相对普通老百姓应该是不低的,我无语。父亲退休多年,工资卡在继母手里攥着,有心无力。后来得知父亲当天冒着倾盆大雨骑着电动车跑好远找同学借钱,万一路上有个闪失,我岂不成了罪人?妹夫当时答应送过来的几千元迟迟没有动静,我再次打电话过去,才得知妹夫当晚就把钱送到父亲手里了。气愤的我站在医院的楼道里打电话质问父亲,父亲停顿了一下,说是准备过几天再转钱过来的。后来,不出所料,父亲的同学给妹妹手术捐的款项全被继母截留,给抵了借款,不足的款项从父亲每月的零用钱里扣除。
当时我不能接受妹妹生病,更不能接受我一人独挑重担,甚至在卫生间里崩溃到泪流满面,压低着嗓子哽咽地在深夜里打电话向朋友宣泄:天底下有这样的父亲么,我有时候宁愿我没有这个爸爸。共处一室的姨妈体贴地装睡,至今未提起这件事。
在后来与妹妹渐渐多起来的交流中,我发现自己当时是多么的没心没肺,好像妹妹患病的早期我一直是缺席的。她的病起于一次普通的感冒,一星期都没有好转的迹象。母亲带妹妹到医院看病,医生说怎么脸好像有些肿,去化验个小便吧。化验小便时发现有两个蛋白,马上办了住院手续。住了一段时间蛋白一直没有消失,母亲转而寄希望于本市一位医术高超的老中医。中药都是一大碗一大碗地喝下去,蛋白才降为微量蛋白。药不能停,一停蛋白就上升,也不能感冒,一感冒蛋白也会上升。父亲后来又联系了外地多家肾病医院,把检查结果发过去,由那边寄中成药过来,可治疗效果都不是很明显。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有父母操劳,我从没把妹妹这事特别放在心上。老公常年出差,我边上班边带小孩,一大摊子事呢。
母亲出事那天我正在医院上班,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说母亲突然倒在地上,人事不知,送医院后喷射性地呕吐,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溢血。母亲手术后成了植物人,我在医院没日没夜地照顾了一个月,落下了双侧脑血管痉挛的毛病,好长一段时间一看书就头疼。妹妹身体不好,没让她来守夜,母亲出院后护理的重担就落在了父亲和有病的妹妹身上,更主要的还是有病的妹妹身上。虽说请了保姆,但外人哪有自己人照顾得尽心尽力呢。父亲晚上起不来,妹妹要起来两次给母亲换尿不湿,保姆走人的空档还有休假的日子都是妹妹在服侍,她本来稳定的病情也因着照顾病人血压猛增,再没降下来过。随后一系列的副作用也紧跟而上,妹妹由慢性肾炎慢慢地转成了尿毒症。
直到有一天,我遇到妹妹的领导,这位心地善良的人叫住我,告诉我妹妹走路都走不动了,就是不肯去住院,要我做做工作。那个时候妹妹购买了一套小产权房,简单装修一下刚搬的家,债都没还清。知道妹妹身体不好,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打电话给她,询问病情,她一直在电话里骗我说各项指标都不错。那时我刚从婚姻的围城里出来,它带给我的心理阴影持续了好多年,使我动不动就歇斯底里,在亲人面前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至于女儿好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和我亲近。坏情绪的我靠沉溺于书本慢慢调整自己,自顾不及,就这样第二次忽视了妹妹的病情。等我赶到妹妹家,看到父亲陪在一旁,妹妹只是掉眼泪,家里的锅盖上都是一层厚厚的油污。我又气又恨,气她这样放弃自己,气父亲不把她送去医院,恨自己没有关心她。第二天,我押着妹妹到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病人目前的情况随时会猝死,那个医院只能做普通血透,妹妹要做急诊血透。我找熟人联系了床位,立即把妹妹转了院。
妹妹开始了将近三年的透析,在透析的日子里,她结识了好多病友。
Y是一位四十左右的女人,短发,脾气温和,一周三次血透,非常注意保暖。别人穿毛衣的时候她就穿棉袄,别人穿一件棉袄她穿两件棉袄。她血压不高,每次都能平和地坚持四小时。Y是下岗女工,娘家条件还可以,姐姐母亲都拿钱给她用,拿的虽然是低保,两次免费透析加上低保可以二次报销,基本可以维持开销。Y的老公没有正式工作,平时打打零工。Y做透析的时候,Y的老公每次都不放心,从透析开始一直守到透析结束。平时,Y在家附近和邻居打打小牌,家中大小事务一概老公全包,而且老公毫无怨言。妹妹一说到他两口子就酸酸的,是想起她自己的境况了。
还有一位女病友叫P。P的姐姐是一位五十左右的退休女工,高高瘦瘦的个子,脾气温和;P的哥哥家是做生意的,不知有上百万还是上千万,但是不管在人力还是金钱上都是P的姐姐一个人在付出。P的姐姐每月退休金只有两千左右,用于P身上的占了大头。P的老公和儿子一次也没有见过。P是一周五次透析,每次都是她姐姐把P从家中接到医院。P中过风,脾气暴躁,经常骂人。她姐姐不能离开病床一步,一离开P就骂她。而且每次透析时P总要扭来扭去,有很多次针头差点出来。有一次针头出来流了好多血,气得她姐姐骂护士不负责任。P血管不好,透析过程中容易掉血压,有时候会引起呕吐或者大小便失禁,她姐姐不怕脏不怕累每次都给她收拾干净。每次P的姐姐见到我妹妹换了肾后很好的样子,总是叹气,说自己的妹妹也能换肾就好了,可惜没有钱,她说自己捐个肾给她都行。妹妹总是拿P的姐姐来和我对比,怪我做得不好,经常吼她。
G是一位男生,当时才28岁,是我见过的最独立的病人。他个子高高瘦瘦,永远很乐观,从来没有抱怨。G透析的时候他小孩才一个月,每次我见到他都是一个人来一个人回。当时妹妹有几个玩得比较好的病友都是刚开始透析,只能轮夜班,晚上透析,经常和他聊天,都说他讲话很有意思非常幽默。从下午四点多开始透析到五六点订餐食堂送饭过来,我就想看看他怎么用一个手吃饭。只见G要护士把床头的小桌子移到胸前,把饭放在上面,左手在透析不能动,他就用右手拿着一次性筷子,用嘴撕开包装,歪着身子一口一口地吃起来,一次能吃两盒饭。后来听说G转到另一家医院去透析了,并且G一直在工作,他也要生存的。现在G的工作是做房产中介,不知道跑来跑去他怎么吃得消。妹妹一直牵挂着他,可菩萨难救世间苦,我们有心而无力……
L个子中等,性子慢悠悠的,比妹妹大几岁,结婚未育。因为是老幺又生病的缘故,家中一切事务不管,由母亲打理,每次血透都是母亲或者老公陪她。透析的时间久了L的脾气也会烦躁,母亲年事已高还要买菜做饭照顾她,时间久了L的姐姐难免会有怨言。有一次碰到L的姐姐,说L在家什么也不做,又总发脾气,一说她就摔筷子摔碗。妹妹的境遇截然相反。妹妹刚发现尿毒症时,我求父亲搬回家居住,方便照顾妹妹,父亲以继母不愿意为由拒绝了。姐姐早几年前就与家里人没有来往了,思前想后,我做出决定,搬过去照顾妹妹。搬至妹妹家照顾她的第一天,父亲对我说,以后妹妹就交给你了。我的抵触情绪马上上来:凭什么交给我,你不还健在么,不还有姐姐么。这种怨恨的情绪一直气结于心。后遗症是很长一段时间,我只要和父亲通电话就会吵架。
认识Z的时候他三十不到,听说在单位本来是马上要提拔的,因为这个病上不了班,女朋友也分手了。Z不太爱说话,碰到偶尔打个招呼,每次都是Z的母亲守护着他。Z是透析室最爱干净的人,每次来透析所有的床单被套全部换掉或者换上自己家里带的,然后要洗很多次手。Z基本上不和病友聊天,只看到Z总是在抠自己的身上——Z身上有很多的烂疤,而且洞很深,毒素引起的痒让他无法控制地抠,甚至抠到疤里面去。Z的母亲总是唉声叹气,家里一儿一女,女儿耳聋已结婚,儿子又是这样,让自己不能省心。Z非常地颓废,不能吃的东西他控制不住,异食癖导致Z总偷吃干茶叶,茶叶里有成分会引起贫血,并且磷高会加重瘙痒。可是谁说也没有用,他就是要吃,而且是论斤吃。在透析的四个小时里,Z的母亲一直都用手轻轻地给他抚摸身体,减轻瘙痒。
刚透析那会,妹妹什么也不懂,时间久了心里才有谱,自己最多能脱多少水,什么时候要吃降压药,什么时候快要掉血压了。医生只是机械性地重复,不可能一一关照。在透析的两年半里,妹妹每次去透析都很害怕,害怕打那铁钉一样粗的针,害怕透析四小时不能动的过程,害怕透析室压抑的气氛。而我常常把这归于她矫情,别人能做你怎么不能做。隔两天重复一次的痛苦通常让妹妹感觉生不如死,每次做完四小时都好累,浑身酸痛,总是在那默默地流泪感叹自己命苦。为了生存忙于上班的我,只能给她打气。打气的次数多了,就变成高压的管制,你不靠自己靠谁呢?我们家这样的情况,我不可能陪你一辈子的。妹妹告诉我,透析完以后虽然累但是身体比较轻松,因为去除了一部分的水分和毒素。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就会非常纠结,嘴里总是很干,总是渴望多喝点水,喝完又担心脱不出水。临近透析的日子,人是最难受的——经过两天的积累手指会变粗会胀、僵,全是水,毒素还会引起瘙痒——这个时候又期待把水透出去,又害怕透析。妹妹那时候经常想这种日子不知何时是个头,有时甚至有一了百了的念头。
长期透析的人都会变黑,甚至脸部骨骼都会变形,身体和心理上都会产生变化。有的人会迟钝,有的人会暴躁,会自卑,感觉没有脸见人,甚至有的人毒素入脑会诱发精神病。妹妹说她就经常不想说话,觉得活着没意思,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没有食欲,甚至有自杀的念头。
换肾以后,妹妹和以前透析的病友很少有交集了。妹妹要上班要打理家务,而病友们总是在透析,不透析的日子也是不舒服,慢慢的联系就少了。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妹妹又有了一批换肾的病友。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广东的病友M。M是农村的,在深圳打工,有一次感觉不舒服,坐公交车的时候吐了,去医院检查是尿毒症,后来他父亲捐了一个肾给他。M在网上开了一个网店,做客服经常不能休息,晚上好晚才能睡。去年听说M找了一个工作,卖手机,晚上上班要到十一点才能回来,而且始终要站着。M很想有个伴,可惜这是奢望。他和父母在家没有话讲,一家人性格都比较沉闷,有时候一开口说话就会吵架。我在家里和妹妹也是没有交流的,一开口就吵,每天各进各房,房门紧闭,她念她的经,我看我的书,偶尔她熟睡后我会进去看看,听听她还有无呼吸,时时担心某一天她会在某个深夜突然离我而去。
父亲曾经是本城春晚的总导演,他为了请到一位好编剧,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事,他亲自上门去请。这是父亲的朋友,我的一位长辈告诉我的,他就是那名编剧。一心扑在事业上的父亲一向疏于对我们的管教,勤快却不能干的母亲在爷爷那里受气了就把怨恨撒在我们身上,管教我们时出手很重,少不更事的我不能理解母亲心中的委屈,心中更添怨言。人到中年,才发现,我们自以为明察秋毫,但往往只能看见我们想看见的东西,听见我们想听见的声音。其实,各人都有各人生活的难。经历了妹妹的这场病以后,我渐渐懂得了当年母亲的心境,也慢慢明白正是因为父亲一生正直、为官清廉,才有我与父亲目前的矛盾,这都是缺钱惹的祸呀!
这一页终于翻篇了,我们挣扎着过来了。我们这样的家庭平时吃饭穿衣是没有问题的,遇到大病就束手无策了,我可以想象那些下岗工人家庭,那些农村没有医保的家庭一旦摊上这种事时的焦虑与无奈。我做志愿者时就遇到很多家庭是因病致贫的。好在目前国家加大了医保的救助力度,越来越多的病人将会有病可医。愿那些亟待肾源的病患都有妹妹般的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