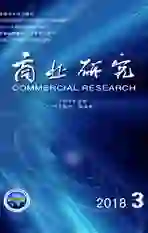城市集聚经济与劳动力流动
2018-04-29周光霞林乐芬
周光霞 林乐芬



内容提要:集聚经济在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通过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两个互补性机制带动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推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金融外部性通过产业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利用价格机制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技术外部性则利用劳动力共享、交流、学习获得的知识溢出效应影响着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基于城市层级数据的经验检验表明:金融外部性和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之间存在“U”型关系,技术外部性和劳动力流动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型”非线性关系,在“集聚-户籍”两种力量博弈中,城市集聚经济主导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因此,进一步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发挥集聚经济机制作用依然是中国城市化目标实现的基础。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集聚经济;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户籍制度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18)03-0152-10
收稿日期:2017-11-20
作者简介:周光霞(1978-),女,山东平原人,安徽科技学院财经学院副教授,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经济学;林乐芬(1959-),女,山东烟台人,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城市化在二元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项目编号:AHSKQ2014D49;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项目编号:gxyqZD2016209。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6年城市化率达到57.35%①,这是集聚经济力量和户籍制度改革形成的城市化动力积极推动的成果。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对优质资源的争夺和追逐,是集聚经济力量配置资源的表现,而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影响颇深的户籍制度,阻碍或者延缓了这种资源配置。虽然近年来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一直在推进,然而有证据表明户籍制度对于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短期内不会消除。根据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2016年10月刚刚出台的推动1亿非农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中国到2020年要实现60%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和45%户籍人口城市化率的目标,依然有15%的城市常住人口缺乏城市戶籍,成为“城市过客”。中国城市化模式和城市形态一直是“集聚-户籍”两种力量博弈的结果。大规模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伴随着经济集聚增强和户籍改革推进,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范围逐年扩大,1990年、2000年、2010年的跨省流动规模分别为11065万人、42419万人和85876万人,并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典型的空间集聚特征(余吉祥和沈坤荣,2013)。根据2010年“六普”数据统计,东部地区②吸引全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7973%;约61%的农村劳动力以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带作为迁入地;常住人口规模在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吸引了3562%的农村劳动力,其中约1993%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常住人口规模在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特大城市作为迁入地。可见,在“集聚-户籍”这两种中国经济发展格局中不可忽视力量的作用下,中国城市化实质为农村劳动力及其经济活动不断在城市空间集聚的进程,是东部地区、区域经济带、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自我加强”的过程,呈现出“强者恒强、强者更强”的特征。那么,在集聚力量和户籍改革博弈过程中,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空间流动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呈现出显著的集聚累积效应?如何更好地处理“集聚-户籍”两种力量才能形成强有力的城市化动力?该问题的回答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相关研究总体上呈现两个特征,一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要研究视角,近期逐步向集聚经济视角转变,二是以省级/地区为研究对象。新古典经济学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前提下,将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机会作为外生变量,发现经济因素在流动决策中占据中心地位,城乡绝对收入差距构成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动因,并且与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相关(李实,1999;蔡昉等,2002)。然而伴随着集聚经济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注意到就业机会增长内生于城市集聚经济中,在要素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前提下,生产要素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会激励企业选址在集聚经济较大的地区,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要素价格水平,在地理空间上形成吸引农村劳动力及其经济活动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集中的力量(余吉祥等,2013;王永培等,2013;陆铭等,2012)。
集聚经济的系统论述最早来自于1890年马歇尔的外部经济,1931年美国经济学家Viner按照外部性是否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将外部性分为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集聚经济是金融外部性和技术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在解释集聚经济机制方面具有互补性。马歇尔指出集聚经济来自于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投入品共享和知识溢出,实质上强调的是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对于集聚的共同影响(梁琦和钱学锋,2007)。然而,从集聚经济视角研究劳动力流动的文献,或者笼统研究集聚经济和劳动力流动的关系,不区分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余吉祥等,2013;Puga,1998;Moretti,2010,2011;Topel,1986;Bound et al,2000);或者侧重于集聚经济的单一机制,没有将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同时纳入方程(王永培等,2013;陆铭等,2012;Crozet,2004)。虽然杜旻和刘长全(2014)在集聚效应框架下,构建包括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模型,研究城市人口增长率和集聚经济的相关性,但是并没有考虑户籍因素。因此在中国户籍制度造成的二元经济社会中,集聚经济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相关性还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同时缺乏同时考虑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的经验研究。而且研究对象大多以省级/地区为主,没有在城市层面上实现突破。
鉴于此,本文拟将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分析集聚经济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的影响。从文献的角度看,尽管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一个被长期关注的问题,然而基于集聚经济视角、在同一框架内考虑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效应并无专论。从研究对象来看,由于长期以来缺乏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数据,大部分研究以省份/地区为研究空间单元,缺乏城市层面的研究,而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真正建立起与城市“实体区域”一致的城市人口统计标准,为我们提供了省级、副省级和地级城市的劳动力迁移数据。本文结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快速城市化模式下农村劳动力空间分布不均衡的成因,为“新型城市化”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市民化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证参考。
二、集聚经济与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框架
(一)基本假设
假设1:假设一个经济体中有M个地区,每个地区用下标i表示。每个地区存在农村和城市两个部门,生产农产品A和工业制品I两类产品。其中农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产品无差异的市场,不存在贸易运输成本,即各地区的农产品价格是一致的。工业制成品市场类型是垄断竞争市场,产品是多样化的,可以满足消费者特定需求,并且工业制成品是可以贸易的,工业制成品在地区i和地区j之间的运输存在“冰山”贸易运输成本τij,假定运输成本是两地区距离dij的增函数(B>0;δ>0)。
τij=Bdδij(1)
假设2:消费者具有相同的消费偏好,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Cobb-Douglas)表示i地区消费者的间接效用函数:
Vi=P-αIiP-(1-α)Aiyi(2)
其中α,1-α分别表示工业制成品、农产品的支付份额。yi表示消费者的收入水平。PIi、PAi分别表示地区i的工业制成品价格指数、农产品价格指数。根据假设1可知,农产品市场为完全竞争的、产品无差异的市场,因此,各地区的农产品价格是相同的,因此可以假设农产品价格指数等于1,即PAi=1。工业制成品价格指数为:
PIi=[∑h∈NIip(1-σ)Ih,i+∑j≠i∑h∈NIj(τij,pIh,j)(1-σ)]11-σ
=[∑h∈NIip(1-σ)Ih,i+∑j≠i∑h∈NIj(BdδijpIh,j)(1-σ)]11-σ
=[∑Mi=1NIi(BdδijPli,j)(1-σ)]11-σ(3)
其中σ表示用CES函数表示的工业制成品间的替代弹性,NIi表示i地区多样化的工业制成品的类别,M表示经济体中地区的数量。
假设3:借鉴Puga(1998)的研究,假定劳动力在迁入地i获得工作机会的概率服从期望值为ρLi的泊松分布,Li是迁入地i的人口数量,即迁入地人口数量越多,越容易吸引劳动力的流入。流动成本c在区间[1, eδ]服从密度函数dF(c)=1/δc的分布。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决策取决于流动带来的效用增加能否抵消流动成本,只有当迁入地带来的效用和迁出地效用之间的差距至少超过流动成本c,流动才会发生。劳动力流动的动态过程取决于以下因素③:
L·si=λ∑j=1,2∑r=U,Rln(Vs,iVr,j)Ls,iLr,j (4)
其中L·si指i地区s部门(R农村,U城市)在时间t劳动力的变化,Vs,i、Vr,j表示迁入地和迁出地消费者的效用,Ls,i、Lr,j分別表示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劳动力数量,λ=ρδ。
(二)基本理论模型
1.单个地区的城乡流动模型
首先假设M=1,存在一个地区,该地区存在农村和城市两个部门,那么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的动态过程为:
Mur=L·ur=λln(VUVR)LuLr=λln(P-αIuyuP-αIryr)LuLr=λln(yu(Bdδur)-αyr)LuLr (5)
(5)式描述了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以及带来的城市人口规模的动态变化过程。从中可以看出,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因素主要有:城乡人口规模Lu,Lr,流动成本参数λ,城乡间的收入差异yu、yr。
2.多地区的城乡流动模型
在(5)基础上,将地区数量扩大到全部地区(地区数量为M,每个地区存在农业部门R和城市部门U),研究劳动力在地区间动态流动问题。那么i地区的城市部门U的劳动力可能的来源:i地区的农村部门R以及其他地区。
MUi=L·Ui=λ∑Mj=1∑r=U,Rln(VUiVrj)LUiLrj=λLUi[ln([∑Mr=1NIr(BdδrUiPIr)(1-σ)]-α1-σyUi)A-B](6)
其中,A=∑Mj=1∑r=U,RLrjB=∑Mj=1∑r=U,Rln(Vrj)Lrj。
根据Crozet(2004)的研究,工业制成品价格指数可以看成市场潜力的逆函数。
pIi=f(mpi)(7)
因此将工业制成品价格指数用市场潜力代替,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到:
MUi=L·Ui
=λLUi[ln([∑Mr=1NIr(BdδrUiPIr)(1-σ)]-α1-σyUi)A-B]
=λLUi[ln(f(mpUi)-α1-σyUi)A-B] (8)
从(8)式中可以得到以下两点结论:
第一,一个地区的市场潜能(工业制成品价格指数)与劳动力流动规模相关,其背后的机制是城市集聚的市场机制(金融外部性),它通过价格机制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根据相关研究可知,金融外部性首先被定义为“后向关联”(Scitovsky, 1954),即生产者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Krugman(1991)及其后的新经济地理学将金融外部性扩大到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联,即“前向关联”,“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均与当时的市场价格指数呈负相关关系。由于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成本节约等,激励大量企业进驻经济集聚地,这为潜在的流动人口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因此,劳动力会在金融外部性的引导下流动,市场潜能大的地方可能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流入,期望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和较高的非农工资收入。
第二,一个地区人口集聚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流入。技术外部性是指基于技术外溢和扩散的关联,强调的是劳动力共享、交流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农村劳动力流动则被认为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城市把大量的人口集中在一起,地理上的临近可以增加劳动力之间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产生面对面的知识外溢。而对于农村劳动力而言,与具有较高技能或者知识的人接触有助于技能的获得、知识扩散和传播。并且大城市存在激励效应,城市中存在的优秀高收入阶层激励着普通劳动力努力工作。因此,大城市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会在地理空间上形成吸引农村劳动力及其经济活动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集中的力量,城市化会呈现“强者恒强”的特征。
(三)城市集聚经济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非线性关系
Krugman et al(1996)认为经济地理模型必须考虑“向心力”和“离散力”的紧张对立关系。“向心力”主要来自于本地市场效应、劳动力市场共享、知识溢出等,是促进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向城市集中的驱动力,是城市集聚带来的外部经济。“离散力”主要来自于城市集聚带来的外部不经济,包括运输成本增加、拥挤效应、竞争加剧、环境污染以及企业从竞争激烈地区搬离的倾向(Tabuchi, 1998)。1991年Krugman建立的“中心-外围”模型以及Puga(1998)等人的后续研究,完美地阐述了城市集聚经济的“向心力”和“离散力”。因此,根据新经济地理理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空间分布,是两种对立力量作用的最终结果。城市集聚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空间关系可能呈现非线性。
首先,城市集聚效应的发挥需要一定的市场规模和城市规模、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否则城市集聚外部性难以发挥集聚作用。那是因为当城市规模较小、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厂商竞争力较低,可能只能服务于当地,因此难以发挥集聚能力,甚至有可能导致经济要素及其经济活动向更大的城市转移。李国璋(2011)证实了市场潜能所代表的金融外部性需要较低的贸易成本、较大的市场规模、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可以推断,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发挥作用需要达到一定的城市规模,未达到该门槛值之前,可能发生城市集聚不经济。
其次,当城市达到一定规模后,城市集聚效应开始发挥作用。城市集聚经济是个积累过程。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表现为正的外部性,就形成了吸引农村劳动力及其经济活动向城市流动的“向心力”:生产中的规模报酬递增,专业化或者多样化产业集聚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共享、学习效应,会激励企业选择在市场潜能和人口规模相对较大的地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从而创造出较多就业机会和较高的要素价格水平,在地理空间上形成吸引农村劳动力及其经济活动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集中的力量,城市化呈现“强者恒强”的特征。此时,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与城市集聚经济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第三,伴随着城市生产要素及其经济活动的集聚,集聚经济的外部成本逐步凸显。从金融外部性而言,这表现为在城市经济集聚地,租金和工资成本通常更高,因此随着城市经济活动的过度集聚,以及中小城市生产的专业化,企业将有向外流动到更为专业化的中小城市的激励(Tabuchi, 1998)。另外对于劳动力而言,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产生了竞争激烈、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负向外部成本。一般来说,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競争变得更加激烈,交通变得更加拥堵,环境质量趋于下降,城市生活的外部成本显著上升,迫使经济要素及其经济活动趋于离散,即产生城市集聚经济负外部性的“离散力”。因此当城市集聚的“离散力”占据主导地位时,农村劳动力规模与城市集聚之间会呈现负相关关系。
因此,城市集聚经济将就业机会内生于经济增长中,引导着农村劳动力流动,农村劳动力流动是集聚经济“向心力”和“离散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集聚经济产生“向心力”和“离散力”之间的紧张对立过程中,随着城市规模增长,“向心力”占主导地位,农村劳动力有向大城市流动的趋势。但随着城市规模的进一步增长,由拥挤效应带来的“离心力”会促使其向小城市迁移。集聚经济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非线性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一)实证模型
为了估计出模型(8)参数,对(8)式两边取对数,同时借鉴杜旻、刘长全(2014)分析城市集聚效应和城市增长的处理办法,我们引入市场潜能(金融外部性代理指标)、城市人口规模(技术外部性代理指标)的二次项和三次项,来捕捉城市集聚经济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空间非线性关系。因此构建对数线性计量经济学模型:
lnrurali=β0+β1·lnpopi+β2·[lnpopi]2+β3·[lnpopi]3+β4·lnmpi+β5·[lnmpi]2+β6·[lnmpi]3+α·Xi+μi (9)
回归模型(9)是本文的基础模型。其中下标i表示城市i。ln(rural)是城市市辖区农村劳动力的规模,ln(mp)和ln(pop)分别是城市市场潜能(金融外部性的代理变量)和人口规模(技术外部性的代理变量)的对数,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μi表示误差项。
(二)变量与数据来源
rural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本文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标准界定农村劳动力流动。在时间上,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空间上,现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现住地为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而户口登记地为外省或者本省其他地区的乡或者镇的村委会,这种不一致包括跨地级市(地区)的变动,以及跨省的变动。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候鸟式流动”模式。由于未获得城镇户籍,该部分流动人口在生产、消费等方面显著不同于城镇居民。数据来自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库中7-5(全省按现住地、户口登记地类型、受教育程度分的户口登记地在本省其他乡镇街道人口)和7-6(全省按现住地、户口登记地类型、受教育程度分的户口登记地在外省人口)。为了进一步验证结论的可靠性,我们使用农村劳动力相对规模pro_ruralpop(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常住人口规模中所占的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
pop城市人口规模:文章选择市辖区本地人口规模作为技术外部性的代理变量,用市辖区常住人口规模减去农村劳动力规模而获得。原因在于城市人口规模和农村劳动力流动之间较强的内生性问题,城市人口规模越高的城市越容易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增加又会进一步扩大城市人口规模。市辖区常住人口规模数据来自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库中1-1(各地区户数、人口数和性别比)。
mp市场潜能:市场潜能用来度量城市所拥有的市场规模,是金融外部性的代理变量,我们采用Harris(1954)市场潜能计算公式,具体为:mpi=∑Yj/dji。式中,Yj为第j个城市的GDP,dji为第j个城市和第i个城市之间的距离,该变量为地理距离,由于市政府所在地很少发生变化,所以以两城市的市政府所在地的最近球面距离表示两城间的距离。当j=i时,城市内部距离定义为:dii=(2/3)Si/π,Si为城市行政辖区的面积。为了更加接近市场潜能的本质含义,这里市场规模使用的是城市行政辖区的GDP。数据来自于《201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控制变量:根据相关文献,经济因素依然是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决定因素,较高的收入预期可以促进劳动力流动。城市级别收入数据在中國不可得,本研究采用《201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平均工资(salary)替代。不过该项数据来自于单位就业人员的工资统计,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遵循传统的人口流动研究文献,我们在控制变量中加入失业率(rate_unemployment)、城市建成区面积(area)、对外开放程度(pro_fdigdp)、产业结构(pro_industry)、政府财政支出(per_fiscal)、城市基础设施建设(per_road)、城市宜居程度(per_green)、资源型城市虚拟变量(zycity)、城市级别虚拟变量(citylevel)、省份虚拟变量(province)等因素。
表1中总结了模型中变量的基本信息。
(三)结果分析
表2汇报了实证模型分析结果。回归结果(1)、(3)是以农村劳动力绝对规模(rural)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2)和(4)报告的是以农村劳动力流动相对规模(pro_ruralpop)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的结果。
回归结果(1)、(2)中市场潜能一、二、三次项均不显著,这很有可能是由于三次项效应的发挥需要更大的市场潜能,而现实中市场潜能还不够大。在回归结果(3)、(4)中去掉市场潜能的三次项。结果发现市场潜能对于农村劳动力影响的一次项为负、二次项为正,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主要对表2中回归结果(3)进行分析。
1.城市规模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型”非线性关系
根据表2的模型(3)的回归结果,城市人口规模与农村劳动力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型”曲线关系,并且一次项、二次项、三次项都在5%水平上显著,一次项小于零,二次项大于零、三次项小于零。这意味着伴随城市人口规模的逐步增加,由于人口集聚而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对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有一个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作用。通过求导计算可知,在其他因素被控制的情况下,门槛值分别为12547248和15644056,对应的城市规模分别为28131997和62248257。图1反映了技术外部性和农村劳动力规模的非线性关系。仅有8个样本城市位于曲线的第一阶段(丽江、鹰潭、金昌、嘉峪关、普洱、吕梁、云浮、三明,其中6个位于西部地区(云浮、三明除外)、6个为资源型城市(鹰潭、嘉峪关除外)。上海、北京、重庆、天津、武汉、广州、南京等7个城市位于曲线的第三个阶段,其余157个城市位于规模经济区间,城市规模越大,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越大,人口城市化速度越快。
图1 城市人口规模与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的
“∽型”曲线关系
之所以存在第一阶段的下降趋势,可能的原因在于,城市人口集聚产生的技术外部性的发挥需要一定的城市规模,当城市规模小于一定的门槛值,“向心力”不足以吸引各种经济要素及其经济活动集中,并且还可能在周围大城市集聚力的影响下,劳动力、资金、技术、信息等向其他大城市流动。因此当城市规模过小的情况下,可能发生的集聚不经济会使得各种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向其他地区流失。当城市人口规模超过第一个门槛值后,由于人口集聚而产生的劳动力共享、匹配、知识溢出效应等技术外部性越强,城市经济集聚效应以“向心力”为主,或者由于劳动力共享、知识溢出效应等产生的“向心力”可以抵消由于人口集聚而产生的拥挤效应、竞争效应等“离散力”,进而促进城市规模的增长,加速人口城市化进程。然而当城市规模达到第二个门槛值后,经济集聚的“离散力”将会居于主导地位,经济要素及其活动会向其他地区扩散,最后实现“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2.市场潜能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U”形非线性关系
回归结果(3)和图2显示,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与市场潜能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市场潜能(对数)的一次项和二次项都在1%水平上显著,一次项小于零,二次项大于零。“U”型非线性关系的存在,意味着根据行政辖区GDP和空间距离计算的市场潜能超过一定的规模后,劳动力流动规模将随着市场潜能的增加而增长。根据一次项和二次项的-3384和1101的回归系数计算,市场潜能(对数)的门槛值为1537483,对应的市场潜能为47555837万元,超过这一规模,市场潜能增加带来新的市场机会,吸引更多的产业和企业进驻,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必然会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规模和市场潜能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图2 市场潜能与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
“U”曲线关系
在2010年“六普”的172个样本城市中,只有30个城市(4个城市位于东北地区,26个城市位于西部地区,15个为资源型城市)位于U型曲线的左边,约占样本城市的17%。可能的原因在于市场潜能所代表的金融外部性需要较低的贸易成本、较大的市场规模、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当这些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金融外部性难以发挥集聚作用。这30个城市的人均GDP平均为328万元,低于172个城市的平均水平431万元。因此,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市场潜能作为城市集聚经济金融外部性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驱动城市规模增长、影响农村劳动力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当市场潜能低于门槛值,金融外部性所需要的条件不满足,金融外部性难以发挥,会限制城市增长。对于超过门槛值的城市而言,市场潜能和农村劳动力规模呈正相关关系,进而会促进人口城市化进程。
3.其他控制变量分析
根据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同传统的人口流动理论和实证结果一致,经济因素始终是农村劳动力流动决策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迁入地的工资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则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增加1071个百分点,该结果在1%水平上显著。
其次,城市的市辖区面积增长1%,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则会上升0377%,该结果在1%统计水平显著。城市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带来的土地城市化会促进人口城市化,原因在于地方政府通过经营土地,获得地区发展需要“土地财政”,加大对城市的硬件和软件投资,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生活便利,另一方面,通过市辖区扩张,城市容纳更多的外来流动人口,增加城市的承载力。
第三,城市的非农产业越发达,创造的就业机会越多,会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相较于其他城市,资源型城市则不利于人口城市化的推进。其他控制变量则对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推进人口城市化并没有显著影响。
4.稳健性检验
为了证明文章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选择以下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方式一:用人口密度(density)替代常住人口规模,作为技术外部性的代理变量。原因在于,一些文献使用人口密度来衡量城市集聚的相对规模效应(Ciccone and Hall,1996;吴晓怡和邵军,2016;Fingleton,2006;Fingleton and Longhi,2013等),规模和密度要结合使用才能客观反映集聚特征(汪曼琦和席强敏,2015)。
方式二:分别利用常住人口规模小于1000万、人口密度大于100人、非直辖市城市等三个子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原因在于,本文的结论有可能对样本城市的类型和城市规模具有较高的敏感性。与其他城市相互比较,直辖市在经济区位、产业基础、对外开放程度、政策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极大可能出现异常值。城市人口规模和农村劳动力流动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循环累计因果关系,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增加了城市的规模;而当城市规模增加,又进一步增加了就业机会,吸引着人员进一步增加。
表3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证实,农村劳动力规模与城市人口规模“∽型”曲线关系显著存在,农村劳动力规模与市场潜能的“U”型关系也显著存在。因此,本文的结论是可靠的,城市集聚经济引导了劳动力流动方向。
5.内生性问题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规模与城市市场潜能、人口规模等存在互为因果关系。城市集聚的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可能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决策,进而影响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规模,这是本文关注的因果关系。然而,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也会进一步影响城市的经济集聚水平,比如,市场潜能大的城市可能会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越容易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这会导致上述模型设定存在内生性问题,并且其他可能影响流动人口的不可观测的因素也会造成估计的遗漏变量偏误。
借鉴Crozet(2004)、Paluzie(2009)、王永培等(2013)将解释变量滞后的办法,本文利用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分别采用2009年、2008年、2007年、2006年和2005年的市场潜能和年末市辖区人口规模替代2010年的城市集聚能力。表4汇报了内生性检验的结果:农村劳动力规模与城市人口规模“∽型”曲线关系显著存在,农村劳动力规模与市场潜能的“U”型关系也显著存在,和表2的结论一致。
四、结论和建议
集聚经济内生的劳动力需求和户籍制度的逐步改革主导了城市化动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集聚在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了东部沿海地区、大城市等“强者更强”的人口分布格局。本文从理论层面分析城市集聚经济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机制,将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实证检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和劳动力流动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以城市人口规模衡量的技术外部性和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型”关系,只有达到一定的人口规模后,城市集聚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对农村劳动力规模的增长有一个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样本中约91%城市处于上升阶段;以市场潜能衡量的金融外部性和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非线性关系,只有当市场潜能超过一定的门槛值后,城市集聚产生的金融外部性和农村劳动力规模存在正相关关系,约83%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处于“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等集聚经济互补性的两个机制确实有助于农村劳动力的向上流动。为了实现国家制定的城市化目标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充分发挥城市集聚经济的“向心力”作用,提高城市经济集聚规模,让市场机制引导资源合理配置。从金融外部性而言,目前绝大部分城市的集聚程度低于适度强度,进一步引导企业选址集聚和靠近消费市场,利用生产者之间的“后向关联”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前向关联”,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工资收入,使得勞动力不仅仅从农村走出来,还要在城市待下去。从技术外部性而言,除少数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外,应该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共享机制,增加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效益,让农村劳动力通过“干中学”提升人力资本,增加自身的竞争力,最终实现“人的城市化”。“∽型”曲线关系意味着城市人口规模会在经济集聚中走向均衡,即使对于那些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政府而言,更加开放性和发展性的公共政策框架也是必要的。
其次,提高城市资源承载能力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缓解城市集聚带来的“离散力”,为集聚经济效应的发挥提供硬件支持。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将财政资金更多地配置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上,同时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2016年《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制订了实施配套政策的指导原则,为今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要明确责任主体,增加监管力度,同时要增加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融资能力,为集聚经济机制的发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三,要進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降低落户门槛。《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规定的重点落户群体为农村学生升学、参军进入城镇人、在城市就业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口以及新生代农民工。从中可以看出,农民工取得城市户籍的前提条件是有能力在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举家进城落户,而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落户,要具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参加城镇社保年限和连续居住年限等条件。因此由于就业能力差、工作稳定性差、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大部分农民工很难成为全面开放政策的重点群体,该方案最终可能覆盖了高校毕业生、留学回国人员、城市间流动人口、各类技术人员等,绝大部分有留城意愿的农村劳动力依然会被拒之门外。因此要彻底改变“候鸟式迁移”,户籍制度改革应该广泛覆盖农村劳动力,进一步降低门槛。一个可行的措施就是实施差异化管理,城市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引导农民工向集聚经济部门集中,将户籍和就业挂钩,在政府规划的部门和行业中,农村劳动力只要在城市取得合法的工作岗位,就应该给予城市户籍,这样既可以发挥集聚经济机制,又可以实现户籍城市化目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户籍制度改革是个系统工程,要逐步将落户农民逐步纳入到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住房保障体系等保障范围内,扩大城市福利覆盖面,实现真正的“人的城市化”。
注释:
① 城市化水平的最新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相关内容见http://financesinacomcn/roll /2017-01-20/ doc-ifxzutkf2122186shtml
② 遵循文献中的惯例,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等9省属于东部地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省属于中部地区,内蒙古、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2省位于西部地区,黑龙江、辽宁、吉林等3省属于东北地区。
③ 具体推演过程见Puga论文的234-235页。
参考文献:
[1] ABUCHI T.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 A Synthesis of Alonso and Krugman[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98,44: 333-351.
[2] BOUND J, HARRY H. Demand Shifts, Population Adjustments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during the 1980s[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0,18(1): 20-54.
[3] CICCONE A, HALL R.E. Productivity and the Density of Economic Activit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6,86(1): 54-70.
[4] DIEGO PUGA.Urbanization Patterns: European Versus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1998,38(2):2331-251.
[5] FINGLETON B.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versus Urban Economics: An Evaluation Using Local Wage Rates in Great Britain[J].Oxford Economic Papers,2006,58(3): 501-530.
[6] FINGLETON B, LONGHI S. The Effects of Agglomeration on Wages: Evidence from the Micro-Level [J].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2013,53(3): 443-463.
[7] HARRIS C. The Market as a Factor in the Localization of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54,44(4):315-348.
[8] KRUGMAN P 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3):483-499.
[9] KRUGMAN P R, ELIZONDO R. Trade Policy and the Third World Metropoli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6,49(1):137-150.
[10]MARSHALL 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M].London: Macmillan, 1890.
[11]MATTHIEU C. Do migrants follow market potentials? An Estimation of a new economic geography model[J].Journal of economics geography,2004,4(4): 439-458.
[12]MORETTI E. Local Multiplier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100(2):373-377.
[13]MORETTI E. Local Labor Markets. In O. Ashenfelter and D. E. Card, eds.,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Amsterdam: North Holland,2011.
[14]PALUZIE E, PONE E J, TIRADO D A. Test of the Market Potential Equation in Spain[J]. Applied Economics,2009,41: 1487-1493.
[15]SCITOVSKY T. Two Concepts of External Economies[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4,62(2):143-151.
[16]TOPEL R H.Local Labor Markets[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4)
[17]VINCER J. Cost curves and supply curves[J].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konomie, 1931(3):23-46.
[18]蔡昉,都陽. 迁移的双重动因及其政策含义[J].中国人口科学,2002(4):1-7.
[19]杜旻,刘长全. 集聚效应、人口流动与城市增长[J].人口与经济,2014(6):44-56.
[20]李实.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增长和分配[J].中国社会科学,1999(2): 16-33.
[21]陆铭,高虹,佐滕宏. 城市规模与包容性就业[J].中国社会科学,2012(10):47-67.
[22]梁琦,钱学锋. 外部性与集聚:一个文献综述[J].世界经济,2007(2):84-96.
[23]李国璋,戚磊. 市场潜力、经济集聚与地区间工资差异[J].财经科学,2011(5):71-78.
[24]吴晓怡,邵军. 经济集聚与制造业工资不平等:基于历史工具变量的研究[J].世界经济,2016(4): 120-142.
[25]汪曼琦,席强敏.中国主要城市化地区测度——基于人口集聚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15(8):26-46.
[26]王永培,晏维龙. 中国劳动力跨省流动的实证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3(2):53-59.
[27]余吉祥,沈坤荣. 跨省流动、经济集聚与地区差距扩大[J].经济科学,2013(2):33-44.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Rural Labor Mobility: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Empirial Study
ZHOU Guang-xia1,2,LIN Le-fen3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2.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Fengyang 233100, China;
3. College of Finance,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ation, agglomeration economy has led to the flow of large scale rural labor to the city by pecuniary externalities and technological externalities, which are complementary in explaining agglomeration effects,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rough forward and backward linkages in the industry, pecuniary externalities affect rural labor mobility by means of the function of price; technological externalities influenc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through the knowledge spillover gotten by labor sharing, communication and learning.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measurement test show there is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ecuniary externalities measured by market potential and the rural labor mobility scale, there exists “∽” 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ical externalities measured by city population and rural labor mobility scale, and in the two kinds of power game of “agglomeration - Household Registration”, urban agglomeration dominates China′s urbanization. Thus it is still the foundation of realizing the goal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o explore the reform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make good use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rural labor mobility;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pecuniary externalities; technological externalitie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