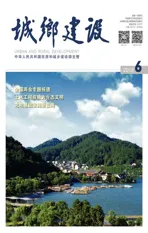医治“乡村焦虑”
2018-04-20许圣义许昌浩
■ 特约记者 许圣义 许昌浩
近些年来,我们为粮食连增的势头欣喜,为城乡一体的蓝图振奋,为扶贫攻坚,为全面小康的目标奋斗。然而,从乡村传来的另一类信息却令人倍感困惑和震惊—“乡村焦虑”成为构建“美丽乡村”的羁绊与掣肘。
那么,有没有破解“乡村焦虑”、构建“美丽乡村”的良策呢?

“乡村焦虑”决非空穴来风
单身汉和极度贫困人群丧失进取之心,坐等政府救济而终日无所事事,甚至破罐子破摔,赌博盗窃嫖娼……空巢老人不堪抑郁,留守学童服毒自杀……或许这一起起悲剧性事件只是一些极端的事例,但是它们牵连出的乡村农民心理健康和精神疾患,其间显露出的孤独、冷漠、自卑、抑郁、焦虑和暴戾等不良情绪,却是必须引起人们警醒、呼唤社会疗救的紧迫问题。
中国有近3亿徘徊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阶层,这是中国真正的工业产业大军。在中国制造业总体下滑的今天,农民工就业机遇日益萎缩,收入落差日益凸现,进城还是回乡?也是令人深深焦虑的事情。按照城乡人口比例来讲,农村大学生数量庞大,而农村大学生囿于社会资源有限导致就业特别困难,“毕业即失业”无疑成为农村大学生的标配,极度的资源匮乏和极度的生存危机形成的就业焦虑、发展焦虑常常在广大乡村迁延弥漫,挥之不去,因上大学导致债台高筑的大学生家庭由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由此造成的乡村焦虑,摧毁着农民脆弱的心灵,“乡村焦虑”成为构建“美丽乡村”的羁绊与掣肘。
“乡村焦虑”成因复杂
为什么一向平和宁静的乡村日益凸显“乡村焦虑”?
贫富分化的鸿沟深了。告别了当年吃“大锅饭”时共同守穷的日子,今天的农民心气高了,门路广了,出去打工经商办厂的,在村里开农家乐当农场主做新网农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家家都有不一样的光景。一些政府补贴的项目、社会资源的分配和福利政策的实惠,往往被各种各样的“强人”“能人”抢占攫取,收入的急剧分化就发生在村民的眼前,村庄的天平倾倒了,邻里的和谐打破了。那些困难户,在贫困化的同时承受着边缘化带来的生活和心理的双重冲击。
家庭结构的框架散了。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拍打着乡村封闭的堤坝,年轻力壮的农民带着新生的憧憬背井离乡涌向外面的世界,去寻找致富的机会,把乡村的阴影留给了孤老的父母和孱弱的孩儿,千百年来看似坚固的家庭开始松了铁箍散了框架。
乡土社会的纽带断了。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交换关系和来自城市文明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浸润到农民日常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生活之中。人情关系逐渐利益化,社会关系逐渐陌生化,代际关系逐渐疏离化,血缘地缘的传统纽带日见脆弱,村落社区的文化认同已经淡漠,熟人社会的价值根基也在松动,“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传统互助合作精神加速消解。
公共服务的重心浮了。这几年大力推进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本是破解城乡发展二元化的良方,可是不少乡村遭遇的,却是再一次的边缘化困局。在掌握了集约化城镇化的发展话语权之后,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都纷纷向县城流动、集聚,既有的城市与乡村的二元转变成县城与乡村的分化。本来,留一所学校就能给一个村庄留下一缕书香、一种气韵;可是,一刀切的撤并,加速了许多乡村公共生活的凋敝和精神文明的衰败。
乡村治理的取向偏了。伴随着村庄的空心化老龄化趋势,乡村治理出现了松散化悬浮化现象,导致违法犯罪增多,乡村治安恶化。一些基层干部作风腐败,许多时候不是矛盾的解决者和秩序的创建者,反而成了矛盾的制造者和秩序的破坏者。农民的精神需求心理健康,农村的文化复兴社会建设,在不少地方官员的视野中还是一片盲区。
当下的乡村,在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双重推力中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广阔的原野上升腾起崭新的希望和无限的生机,也衍生出种种原子化、陌生化甚至丛林化现象。农民从中体验到的,既有欣喜和期盼,也有迷惘和苦闷。跨过温饱生活的门槛,他们向往全面的小康;摆脱计划体制的束缚,他们追求自主的权益;怀念熟人社会的交往,他们渴望温暖的人情;抗争贫富分化的歧视,他们诉求生命的尊严;应对变动不定的世界,他们努力把握命运的支点。他们是市场竞争和社会分化中的弱势者、受挫者,更多地感受着彷徨无主和焦虑不安。
多管齐下破解“乡村焦虑”
社会已经开始警醒,发出声声呼吁:建立心理咨询,开展社会关爱,拓展志愿服务,改善乡村治理……
笔者以为,更为重要的是在自主发展的起点上,在契约社会的治理中,在多元利益的协调中,将农民组织起来,重建乡村社会,重建公共生活,重建精神家园。笔者日前去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余关镇黄楝村进行“美丽乡村”专题调研,深受启迪:农村是有价值的,农民是有尊严的,农业是有前途的,“美丽乡村”不只是梦!核心在于建设一个健康、健全的乡村社会,黄楝村就是一个鲜活的样本。拓展乡村教育,修复乡村社区,焕发乡村文明,拓宽农民特别是农村大学生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创建宜居社区,增加农民对未来生活的预期,让小山村也有大风景,让农民找回心理归属,提升发展自信,共创幸福生活。
略加分析,黄楝村“美丽乡村”建设,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解放思想,多种经营增加收入
2008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内乡县全面推开。村党支部不失时机地和浩林果业达成了薄壳核桃种植意向,“现在人养树,将来树养人。”并和周边村联合,流转荒坡林地近万亩,规模治理荒山成田,栽上摇钱树,结出“金疙瘩”。
这几年来,内乡县委、县政府把水利局、林业局、农业局等9个单位的项目进行整合,使涉农项目和资金跟着产业走,确保项目服务产业、产业致富群众、群众维护项目,实现倍增效应。
在支村两委的大力争取下,投资超亿元的牧原十七分厂项目落户黄楝村,依托这个项目,衍生出占地千亩的生态农业示范园项目,拉长了产业链条,改变了农民的养殖观念和种植模式。
(二)产业支撑,门口就业有“钱”途
牧原和浩林“两大巨头”的引进,产生了人口聚集效应。2011年,牧原公司邀请湖南城市规划学院在黄楝村高起点规划牧原兴盛社区,该社区以岱军河为主轴、以牧原路为中心、南北延伸1000米,划分6大区块5大功能区,可容纳4000人。
牧原落户黄楝村用工量达到200多人,浩林果业的固定用工量达到600多人,季节性用工量则达到1000人以上,他们农闲时在浩林公司上班,农忙时种地两不误。还有多人从事物流、商贸、服务等行业,这得益于群聚带来的溢出效应。社区内开设的农贸市场、商品超市、农资超市、饭店、浴室等吸纳了大批劳动力。近两年来,不但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因为产业结构调整和环保升级改造而从外地下岗返乡后在村子里的企业上岗再就业,而且村子里的大学生除了14.43%在城市就业外,其余85.57%全部在村子里的企业就业。
(三)宜居家园,现代生活不是梦
一缕阳光清新沐浴,新居竹柳若隐若现,拱桥亭榭错落有致,绿荫芳草生机盎然,岱军河水静静流淌……好一幅韵墨山水画。
五米多宽的水泥路两旁绿树成荫,几对喜鹊在树丛间盘旋,叽叽喳喳地鸣叫,统一粉刷成淡黄色、红屋顶鳞次栉比的居民小院。笔者情不自禁地赞叹:小山村也有大风景!
曾一度贫困的黄楝村如今焕发新活力,世代生活于此的农民过上了富足生活,依托“清洁家园”行动,从环境整治入手,基本实现了“村庄洁化、民居美化、河渠净化、四旁绿化”,面貌焕然一新。
(四)发展文教卫生事业,重建精神秩序
落户黄楝村,投资超亿元的牧原十七分厂,是亚洲最大规模单体养猪场。随着落户黄楝村的外地大学生和职工人数增多,村子里只有1~3年级的小学校已经满足不了需要了,牧原公司和内乡县教体局共同投资,2014年在黄楝村投资1500万元新建1~6年级的高标准现代化小学,村民上学不再难。
如今,黄楝村民过上了幸福生活:水泥路硬化了,道路林种上了,“保障电”通上了,路灯亮堂了,放心水吃上了,太阳能用上了,1000多平方米的村文化广场也热闹起来了,超市、药店、健身器材、农家书屋、远程教育一应俱全,村民们安居乐业,其乐融融,昔日的焦虑与落寞荡然无存。
(五)重塑乡村治理结构,保持“美丽乡村”建设可持续
笔者在黄楝村看到,新的乡村治理结构呼之欲出。
黄楝村对于未来乡村治理已经有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与实践。诸如监委会、理事会、议事会、政经分离,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新家训家风,公共服务站、政府购买服务,新乡贤、大学生村官、第一书记……乡村治理方面的新元素不断出现。黄楝村重塑乡村治理结构,保持“美丽乡村”建设可持续。当然,如何构建新乡土中国是未来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新命题。我们需要更多地释放乡村社会自治空间,为构建新乡村治理体系提供土壤;依托中华传统文化,挖掘传统道德资源,按照现代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重建由正确价值观支撑的乡村道德体系;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重塑新乡村社会治理主体,培育新型乡村道德共同体。沿着这条路,我们一定可以找回那个温暖的乡村道德世界,重温那一份乡愁,真正消除“乡村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