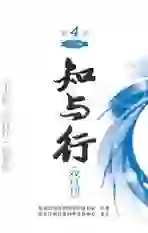顾炎武社会治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2018-04-17王义李园园
王义 李园园
[摘 要]顾炎武作为清初实学的三大家之一,在明末清初的时代大背景下,针对 “王学”末流的弊端,提出经世致用的理念。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亟须社会的大治理、大调整。儒学的经世致用集中体现在如何实现明末清初社会秩序的规范和社会力量的整合,也就是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历史上的儒学传统一直有“内圣”“外王”两个维度。“外王”就是要倡导追求社会事业的进步,追求良好的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一般而言,传统儒学以“民本思想”为核心,以“礼法兼用”为手段,以“王道政治”为终极目标。在社会治理方面,顾炎武一方面继承了儒学的传统,提倡民本思想、王道政治、礼法兼用的社会治理方式 。另一方面顾炎武对时代的问题也有所回应,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产生了以“机户”为代表的新型社会阶层,手工业与农业逐步分离,原本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儒家思想,已无法完全适应当时的社会状况。因此,顾炎武对传统的社会治理提出了自己的创新之处,如“分权众治”的社会治理理念、“才足而化行”的社会治理过程以及最终达到“天下治”的社会治理目标。这些继承和创新,对今天的改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比如党中央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在为人民谋福祉的问题上,可以借鉴顾炎武的“民本”思想;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顾炎武所开出的模式也具有参考价值;在加强社会领导方面,顾炎武也做出了合理化建议,等等。
[关键词]顾炎武;礼法并用;分权众治
[中图分类号]B24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8)04-0005-0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简而言之,社会治理就是,通过社会中各个多元的利益主体,以互相协调、互相连动来共同管理一些社会事务,从而达到社会的正常运行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基本需要。最理想的状态是,社会治理从政府全面深入管理转向各种利益主体的自我管理,从而实现因时、因地、因人、因物的治理。顾炎武处在明末清初的时代大转型之下,社会治理出现严重的问题,内心的秩序与外在的秩序严重脱节,尤其是“袖手谈心性”的王学末流对时代造成的伤害,迫使他重新思考时代的治乱问题。顾炎武处于儒学主导的社会大背景是无法改变的,因此,他必须在继承儒家传统的基础上有所作为。同时,面对时代的课题,他提出许多有价值的社会治理思想。
一、顾炎武对传统儒学社会治理思想的继承
关于儒学的传统,很多学者将其鉴定为有关社会治乱的学说。就一般而言,儒学自孔子创建以来,就内含着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而从偏重来看,历史上自儒学上升为“王官学”之后,其主题一般都是关于国家的兴衰治乱,也就是政治儒学占据更主导的地位。两汉时,为了社会的治理寻找到“天道”的依据,而在两宋时期找到了“心性”的依据。著名的社会学家郑杭生曾说:“由于中国学术的经世致用传统,中国社会思想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社会管理思想史。也就是说,社会学和社会管理学一样,都是一门求治去乱的学问。”[1]而儒学作为中国思想史的主干,其主旨在社会治乱是没有异议的。顾炎武秉承了儒学的传统,关于社会治理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民为国家之主”的民本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王道政治观和“礼法兼用”的社会治理方式。
(一)“民为国家之主”的民本思想
传统儒家认为,“民”作为一个群体处于整个政治生活的核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也就是说,治理一个大国,要谨慎而有信用,节约用度而爱惜百姓。爱惜民力成为“民本”思想的基础。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在他这里,民与君的地位是完全不对等的,民是国家的基础,是第一位的,国家和君主分别等而次之。在儒家思想成为意识形态之后,董仲舒虽然提到了“屈民以伸君”,但又提出“屈君而伸天”,把“天”与“民”等同起来,同样是为了凸显“民本”,只不过渗入了“天”的神圣维度。“天”“民”“君”三者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循环,民是由君来管辖,听从君主意愿;而君要服从天的旨意和意志,不得做出有损天意之事;而天的真实表达来自百姓的诉求。由此保证“民意”得到传达。宋明理学时期,“民本”又有了新的发展。理学派认为,天下万物就是一个理,符合理,自然通常,万物和谐,百姓安康;不符合理,则政治黑暗,百姓民不聊生,统治者尤其要注重“存天理,灭人欲”,通过遏制统治者的欲望来伸张“民众”的需求。而就心学派而言,强调每个人跟从自己的内心,对自我生命做主,已形成一种从“群”中解放出“个体之民”的趋势,尊崇内心的秩序也就是符合社会的管理。
顾炎武继承了儒家的民本传统。他提出“民为国家之主”的思想,民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居主导地位,“君”只是一种为民而立的职位,与公、侯、伯、子、男等爵位是一样的。“为民而立之君,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貴。代耕而赋之禄,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2]面对君权的日益加强,顾炎武觉察到由此带来的社会隐患,他提出君的主要功能和效用是因民而设,只是一个爵位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高贵的。所以,在面对人民的尊严和财富的问题上,不能有自专的行为。如此看来,顾炎武为社会治理树立了一个终极目标:一切的爵位、国家制度都是为民而设。政府是为民服务的机构,君与臣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在这个机构中的不同功能和职务。君与臣共同完成自己分内之事,最终达到人民幸福安康的“善治”。虽然,顾炎武着重于现代国家的思考,但在根源上他与儒家的“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王道政治
儒家自创始以来,就以“天下”这个无限的地理范围作为治理对象,其最终落脚点是“文化”治理。所谓的“天下”就是由修身、齐家到治国,不断向外扩展,形成一个可以伸缩的伦理圈。《大学》中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是在“国”实现良好治理之后的又一层境界,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可以无限延展的。在无线延展的时间和空间里,文化或理念才是治理的终极模式。因此,在治理的过程中文化的意义就超越了一般的王朝和家族。
顾炎武提出“亡天下”与“亡国”的不同含义。“国”更多意义上是指某个王朝,而“天下”更多地是指良心、道德、风俗、文化。他目睹了明亡的整个过程,重新思考国家的治理,认定“亡天下”是“亡国”的前兆,是更为可怕的毁灭。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 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2]297国与天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区别是:国是指在某个时间有一姓家族统治的王朝,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天下”更多指代道德、伦理、风俗、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趋近于无限。就其联系而言,“国”是体,“天下”是魂,“国”依靠“天下”的情怀和道德文化来凝聚,“天下”需要“国”来具体实践其理念。“天下”在顾炎武看来,是更为根本的理念,在王朝危在旦夕的关键时期,更要重视培育。从某种意义上说,顾炎武认为儒家创建的文化是属于人类的,具有普世价值,只要是人类存在就不能“亡天下”。而“天下”理念的孕育和培养需要千百年,需要几十代人的共同努力,得之不易。
(三)礼法并用的社会治理思想
《论语》中首开“礼”与“法”关系的论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用现代术语来说,在社会治理方面,如果以政令、刑法作为主要的手段,导致的后果就是,百姓所关心的是如何不被惩罚,而不会有羞耻之心,不会去关注一些“善”的事物;如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采用礼制和道德,则百姓一方面不会违反社会规范,而且对于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感到羞耻。两者相较,当然礼制与道德更是一种良好的社会治理方式,更多地体现了人作为人的尊严。董仲舒的“德主刑辅”配以“三纲五常”成为之后两千年的指导思想。从社会学角度讲,礼与法分别是指内在心理和外在行为的控制。儒家始终坚持内在控制的效果远远高于外在控制,要“礼”为主,“法”为辅。但在现实的王朝政治下,礼法并用显得更常见。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两千年关于社会治理的法则一般形成如下格局:一是良知,就是不被人发现却可以约束自己的行为;二是舆论和社会风俗,通过倡导某种风气对试图违规者造成压力;三是国家颁布的法律,对违法者予以制裁,从而防止继续作恶。良知和舆论属于“礼”的内容,国家颁布的法律属于“法”的内容。法安天下,礼润人心,是两者最佳的分工。
顾炎武基本继承了儒家关于礼法的思想。“礼法”兼用既体现在廉政建设,也体现为社会治理的方面。而这两方面是分不开的,在传统社会中,一般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法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规范,一经制定就具有无上的威严,而在执行的过程中,官吏起到表率的作用。因此,官员的清廉决定了法令的执行程度。而就官吏的品行,是要通过“以礼治心”的方式,培育他们的廉耻之心。而对于极端自私的人,则只能依靠“法”来治理,顾炎武认为:“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2]311只有明确的法律和严格的执行,才是官员清廉的制度保障。同时,顾炎武重视儒家所提倡的“礼”,在国民中普及做人的标准和行为的规范,使人人都养成守规矩、不妄为的品行。用现代术语来说,顾炎武强调的是法律的客观性和有效性。所谓法的客观性是指在维持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平正义的时候体现出的客观准则。而法的有效性是指在立法者和实施法律者都能爱护法律、尊重法律,使其有效。因此顾炎武“礼法并用”的思想就有了具体的意义,法侧重于客观性和威严,礼则侧重于有效性。
二、顾炎武对传统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创新
顾炎武总结明王朝灭亡的教训,认为原因有三:一是宗族势力衰弱,二是君主权力极度强化,三是伦理道德沦丧。其实,这三条原因都有内在的逻辑联系:首先由于“王学”末流的弊端,导致社会的规范被破坏,没有共同遵守的社会标准,致使伦理道德沦丧;而伦理道德的沦丧引发统治者通过外在的组织和权力来加强统治,从而使君主权力极度强化;而君主权力的强化自然会削弱各个宗族势力,而宗族势力衰弱,也就没有“豪家大姓之力”来护国。同样,由于宗族势力的衰落,没有具体的家族组织维护社会道德秩序,从而使个体的道德在“王学”的旗帜下,不断走向衰落,又由于家族的衰落和个体道德的沦丧致使君主通过集权来稳定社会的统治。针对明朝灭亡的三个原因,顾炎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也是对传统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创新。
(一)“分权众治”的治理结构
顾炎武批评了君主专制集权,认为这是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而后,他提出“分权众治”的治理主张。面对幅员辽阔的国家,人口、地理、风俗等的不同,如果仅凭君主一人之力无法完成有效的治理,需要将君主的权力分割,为下级赢得更多的自主权,这样就可以做到因时、因地、因人、因物的恰如其分地治理。他说:“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自公卿大夫至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2]212君主的权力来源于天下,也将分于天下,从公、卿到百里宰相都可以分天子之权,通过每个爵位和官职遵从自己的位份,最终实现天下的“善治”。将君主的权力下放,在顾炎武看来有两个措施:一是“寓封建于郡县之中”,二是“寓封建于士大夫之中”。
就“寓封建于郡縣之中”而言,封建与郡县两种体制反映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简单来说,郡县制类似于科层级别的上下一体管理体制,从中央到地方一共分为若干级,级与级之间有隶属关系,下级只需要对上级负责、执行上级命令即可。郡县制最大的优点是效率高、执行力强,但弱点就是容易一刀切,不顾地方具体的实际情况,最终导致政策的流产。而封建制原意是“封土建国”,在中央统一的权力之下,地方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封建制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实现因地制宜,根据实际的情况做出相应的政策,实现恰当的治理,但它的弊端就是对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有影响。顾炎武设计的理想郡县应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郡县采用自治的方式,县令是由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地理山川的贤能之士来担任。二是中央对郡县的管理主要集中在对县令的考察、任免、奖赏与惩罚方面。三是县令对全县的情况负责,包括人事、财政和诉讼等。这样安排之后,一方面吸收了郡县之优点而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保证了中央的理念、方针能够通过合适的人选贯彻到地方;另一方面吸收了封建制的特点,由熟悉当地情况和特点的、具有地方背景的人来担任当地长官,可以更好地处理该地的发展和治理。另一个措施是“寓封建于士大夫之中”。所谓“寓封建于士大夫之中”,意在通过恢复家族势力来使百姓获得更多的权利。在顾炎武看来,士大夫就是指一些豪家大姓,在兵兴之时,可以作为保一方平安的势力,在太平之时,可以作为抵制君权泛滥的堡垒。用现代的学术语言来说,顾炎武重在培育社会势力。在不改变现有体制的情况下,通过培育家族势力来改变“君主集权”的现状,最终形成政府与社会二元互动的结构,政府的刚性力量与社会的柔性需求相得益彰。
(二)“财足而化行”的“天下治”
经过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几百年的洗礼,明朝末期整个社会充斥着心性、气节、精神、顿悟,而一些实际的关乎百姓生活的富足、财货等被视为境界不高、庸俗的表现。如果公开谈论“私欲”,更被加以“洪水猛兽”来对待。在清初,针对以上的靡靡之风,掀起了经世致用的实学风潮。他们强调实用、实行、实效,认为学术须利国利民,为百姓和国家的现实生活着想。他们针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之辨,首先承认人有私欲,在此前提下再谈社会治理。顾炎武即是实学三大家之一。
首先,顾炎武承认人有“私”。他说:“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为之禁。”[2]59这已与传统儒家有很大的不同。在儒家传统中,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是源于一种天然的情感,孔子认为这种情感是人之为人以及社会治理的基石。孟子在见到梁惠王之后,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但在顾炎武看来,“私利”是可以存在的,这是人性的表现,也是一种天然的状态。顾炎武公开承认人的“私情”,反映了近代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以“机户”为代表的新型社会阶层,手工业与农业逐步分离,原本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儒家思想,开始注入一种新鲜的血液。他认为无论个人、家庭、家族都完成自己的“私”,则对整个社会而言,就实现了“公”。在顾炎武出生100多年后,西方经济学始祖亚当·斯密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在《国富论》中指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会使他将资本投于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
其次,在承认人有“私”的前提下,顾炎武提出社会治理的过程就是“财足而化行”的天下治。《论语》中孔子认为社会治理的次第是“庶之、富之、教之”。只有在富足的生活之上,教化才是有效的、合理的。管仲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基本权利的保障,促使人去寻找更高的理想。“天下治”,简单来说,就是社会中大多数个体的利益都能得到保障,每个人的潜能得到发挥,社会呈现一种生机勃勃,动态而又不失和谐的状态。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欲使民兴孝弟,莫急于生财。以好仁之君,用不聚敛之臣,则财足而化行,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矣。” [2]149在顾炎武看来,若实现“天下治”的目标,财富,并且是掌握在民眾手中的财富,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藏富于民,藏德于民,最终形成政府和社会互动的均衡状态。在传统儒家看来,孝悌是人之根本,是一切道德的根基,不需要外在的力量来助长。而在顾炎武看来,“兴孝悌”需要“生财”,君与臣都负有管理财富的责任,财富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实现“亲其亲,长其长”的和谐局面。
三、顾炎武社会治理思想对现代的启示
以上就是顾炎武关于社会治理的思想,我们之所以回顾,更多地要古为今用。在今天,我们的改革已经到了关键时期,改革开放初期释放的红利已尽,唯有向纵深领域推进,才能得到更大的收益。在这些具有新的历史特征的伟大工程面前,一切有利于改革的思想都应当拿来借鉴。顾炎武关于中国本土化的社会治理,更能结合中国的实际现状对我们的改革有深刻的启示。
首先,在“民本”的问题上。我们要牢牢记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众的利益是第一位的,是整个政治生活、组织结构的核心,并且民众利益是否得到保障也是政府是否合法的判断标准。因此,我们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权利。历代统治者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都以“民生”作为保障社会稳定的基石,但如何实施好还需要制度作保障。
其次,寓封建于郡县和寓封建于士大夫,是实现“民本”思想的制度保障。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是改革的重点。为了避免出现“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出现,顾炎武的建议值得我们思考。我们要更多地跳出“中央——地方”的二元对峙结构,重视培育社会组织,实现区域、行业、家族的自我管理。顾炎武对他的“寓封建于郡县”十分自信,他说:“后之君欲厚民生,强国势,则必用吾言。”[2]358这是实现民富国强的必由之路。的确,两千年来大一统的格局也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进入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对此有些反思,可以尝试着在统一的政权下,适当放松与放宽对企业、行业、家族的管理,让他们自己管理,形成一个既可以作为整个国家有机体的一部分,也可以形成独立的运作单元。
再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当前社会资本的培育有很大的启示。所谓社会资本,是指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资源。社会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资源,它源于人的品质和特定的位份。而顾炎武的“天下”类似于这样的社会资本,需要长久的积淀和历史的演绎,“亡天下”就是指社会资本不足,致使道德沦丧、风俗日下,完全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人与人缺乏基本的信任和理解。而“兴天下”就是人与人建立互联互通的信任,在一种互惠互利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中,社会资本的培植需要文化的涵养。文化既塑造社会资本,也被社会资本所影响。此处的文化,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指引下,吸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借鉴西方世界的优秀文化,树立革命时期的艰苦奋斗文化,探索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文化,而这一切的判断标准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
四、结语
四百年前,顾炎武以其一身的丰富经历来思考社会治理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完整的思想体系,今天之所以研究,是因为他的思考更能触及异样的时代气息,更能深植于中华5 000年的沃土。党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也必然是以遵循时代和历史的条件。
[参 考 文 献]
[1] 郑杭生.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与中国社会学使命[J].社会学研究,2011,(4):39.
[2] [清]顾炎武.日知录[M].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70.
〔责任编辑:崔家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