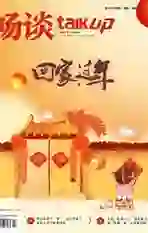年的乡愁
2018-04-16张嫒嫒王立群等
张嫒嫒 王立群等
在西方人看来,春运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存在,而这种阶段性“大迁徙”产生的唯一理由即中国人对春节的信仰。
回家,结束这一轮四季。不畏风雪,不畏严寒,愿化作一缕春风抚乡土。因为过年,一大批人像候鸟迁徙—样,从城市回到乡村。
年是一种节日,更是一种团聚。每到年关,乡愁分外浓,无论远近都怀念那片成长的热土。对故土的依恋,让人跨越万水千山也想回家看看。
回家过年是一种信仰,而这种信仰本身就是一种仪式:回家、过年。在漫长的中华文明演变过程中,过年这个貌似简单的概念被赋予了无数种仪式,因时间及地域的不同,内容迥异。它们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春节生态系统,千百年来,其中所包含的约定俗成的文化元素,形成了中国年里稳定的分子结构,正是它们的存在,让我们的年,过得隆重而充实,充满“味道”。
年,说到底过的还是亲情,是年迈母亲守在门口迎着风雪的翘首企盼,是游子跋山涉水万里还乡时急切的脚步,是一家人围坐桌前其乐融融的团圆,是回不了家的人无以名状的彻骨思恋。
如果游子是飘荡天空的一只风筝,那年就是拉紧风筝的绳,家便是缠满绳子的轴;如果游子是漂游海面的一叶舟,那年就是助它前行的一条桨,而家则是不断回望却渐行渐远的岸。
回家的路
小时候,回家的路就是从姥姥家到自家的山路,从学校到家的小路,从同学、亲戚家到家的不同路。回家的路不管怎么变化,家门口的那一小段永远不变。每次看到路口的那棵老树,我就知道离家近了。
那时总觉得从学校到家的路好远好远,最烦的就是下雨天,路变得泥泞不堪;最爱的也是下雨天,洼地里总是积攒了雨水可以玩耍;顽皮的我硬是把半个多小时的回家路走成了一个多小时。那时总觉得日子很长很长,回家的路可以慢慢走。
时间挡不住我的脚步,我向往书本里说的大世界,拼命地学习只为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终于,我如愿以偿地去了千里之外的大城市读大学,回家变成了一年两次的期待。
那时候回家路漫漫,是一张火车票到不了的距离,是绿皮火车上彻夜不眠的煎熬。坐完火车,再转汽车,还要再走一遍当年上学的路,只是路早已不是那条土路了。
现如今,我早已告别绿皮车了,跨越万水千山的回家路变得不那么漫长了,但家却在忙碌中变成了驿站,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家乡,就又要启程去外面的世界打拼。即使是春节,我在家乡的停留都是那么仓促,以前可以从腊月过到正月十五的年,现在似乎只剩下一顿年夜饭的时间了。
儿时的“年”
年还是小时候的好,从除夕到十五,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期待。小时候除夕前夜会兴奋地睡不着,因为起床就会有新衣服穿,就能吃到平日里很难吃到的零食。
家乡的习俗,除夕早上放鞭炮,吃包子,换新衣,上山请祖先回家过年。
请完祖先之后,回到家里供奉好祖先,开始贴春联。因为村庄靠海,家乡的人们多以打鱼为生。那时父亲是打鱼的,贴完家里的春联,还要赶去贴船上的春联,去船上放鞭炮,祈求来年风调雨顺。靠海吃海的家乡人,大都有几分信天信命,会尽力把这些在城里人看来迷信的仪式做到最好,因为他们相信“心诚则灵”。
除夕那天,每一顿饭前,每家每户都会放鞭炮,一听到传来鞭炮声,就知道誰家要吃饭了。吃饭的那个时间段,村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那时还没有雾霾,不仅家家户户放鞭炮,从村头到村尾到处都是玩鞭炮的孩子们,就连我这样胆小的人,也忍不住加入他们的队伍。
吃完除夕夜的饺子,就可以开始拜年拿压岁钱了。那时候的压岁钱,数额很小,我很怀念那时,怀念不用很多钱就会高兴很久的日子。
在城市里为生计奔波,再也找不回当年的欢乐。年后上班的第一天,晚上刚结束忙碌,母亲打来电话:“吃饺子了么,今天‘收人呢?”我一愣才想起,正月初七是收人日,我们那儿的习俗是要吃饺子的。想起童年时过年,一场又一场的仪式,在孩子的眼中既神秘又神圣。还记得从饺子里吃出硬币的兴奋,磕头祭祖时候的虔诚,现在想想,那才叫“年”。
梁实秋曾经在《北平年景》中写道:“过年须要在家乡才有味道”。确实如此,过得最好的“年”,还是童年的“年”。现在老家的年味也淡了,村里的人都往城里走,村里几乎没有年轻人了,只剩父母那一辈人守着家乡的山,家乡的海,以及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习俗。但父母为了顾及我们这些奔波在外的游子,村里的年也变得匆匆忙忙。
故乡的井
月是故乡明,年也是家乡好。繁忙的生活,让我没有时间仔细看看家乡的景,只能在朋友圈里为家乡点赞,为家乡的蓝天点赞,为家乡的花花草草点赞。无法言说的思念,似乎只有通过点赞来传达,思念家乡的土屋土路、老街老巷,还有村头的那一口老井。
漂泊好多年,早己忘记家乡老井的样子,只记得小时候一次又_次地被父母从井边拉走。那时候总觉得这井里有着无数的故事,里面或许住着坐井观天的青蛙,总是忍不住把脑袋伸进去看看。
说起故乡,我总会想起这口老井。一老井、—石碾、一石臼,在技术还没有主宰生活的年代,它们是人们美好生活的依赖。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每到傍晚父亲会从铺着青石台的老井打上两桶水,挑着水哼着小曲,快乐地回家。我偶尔会蹦蹦哒哒地跟着父亲去老井,只因为对老井充满了好奇。现在想起来满是愧疚,因为无知和好奇,年幼的我向老井里扔过活的小螃蟹。我不记得为什么要把螃蟹扔进去,我只记得在没有七彩斑斓玩具的童年里,我养过蝌蚪抓过螃蟹,上过山下过海,村子的角角落落都探索过,现在想起来甚是美好。
不知承载了多少故事的老井,已经掩埋在新农村的建设中了。它曾是生活的源头,灌溉了庄稼,养育了村民。离家多年才深刻理解背“井”离乡,离开的是源头,是根,枝繁叶茂也不能忘了的根。
奶奶的面
奶奶在世时总喜欢说:“咱们庄稼人,不能忘了本,忘了根呀。”奶奶看不惯村里不务正业的年轻人,不好好读书也不好好种地。奶奶总觉得有本事就该好好读书,当大官;没本事就老老实实地种地打鱼,过日子。奶奶把小儿子供成了大学生,虽然没当大官,但是住的是楼房,干得是拿笔杆子的活儿。
每到节假日,尤其是春节,叔叔一家都会赶回来,和大家一起过节。到了那天,爷爷总会在村头等着叔叔回来,奶奶会准备好面条迎接叔叔一家。
在老家,有这样的说法:“上车饺子,下车面。”下车回到家,吃碗面条,面条如绳,可以“拴”住来人,多留一留。“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躺着”,在老人们眼中饺子是最好吃的东西,把最好吃的东西送给即将踏上旅程的人吃,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我刚来到城里上大学的时候,每次回家奶奶也会给我准备面条,现在妈妈接过了奶奶的“衣钵”,用最好的料做最暖心的面,迎接我们的归来。面不仅是一根拴住游子的绳,也是妈妈的一缕思念,一丝牵挂。
小时候总以为最好吃的东西是买来的烧鸡烤鸭,长大后才知道最好吃的东西是妈妈做的饭,在外漂泊得越久,越怀念那味道。
妈妈做的年夜饭里总有几样是永久不变的,那几样是我的最爱。妈妈喜欢说:“有妈的孩子是个宝,不管多大都是。”可是都说“养儿为防老,可儿山高水远他乡留”,每次看着变老的父母,心里的愧疚就越發地深,多么希望父亲还是那个挑着水还能哼小曲的男人,母亲还是那个分分钟搞定家务的利索女人。
时间狠心地在父母身上留下岁月的痕迹,拉开了我与故乡的距离,我变成了故乡的陌生人,故乡也变得我不认识了。年关将近,既期盼快点再次回家过年,又害怕时间走得太快,留不住故乡,留不住记忆。
网络时代的新鲜味
时代在变,人们过年的心态在变,“过年”所蕴含的各种仪式也在发生变化。
如果说传统意义上过年的关键词是“回家”和“团聚”,那么,网络时代,“分享”与“交流”成为家族关系之外新的情感沟通形式,这是当下人们生活与交际空间拓展带来的新的年味。
网络时代的“过年”,有一种疯狂叫抢红包,红包的意义不在于数字的多少,只在于你争我抢的趣味,你少我多的快感。
网络时代的“过年”,有一种虐心叫“你××了吗”,那是七大姑八大姨的关切,是一种亲情裹挟之下的“心理虐待”,由此产生的恐归成为当下春节独特的印记。而其背后更多的是时代变迁带来的代际间思维与生活方式的差异。
网络时代的“过年”,有一种幸福叫“每逢过节胖十斤”,身体里多出来的未必是肉,而是“在父母眼里,你最喜欢的永远是排骨”带来的幸福感。不胖几斤,你怎么好意思说你回家过了年?
回家,过年。从腊八开始,从祭灶神开始,从微信圈里晒出的回家的路开始,从每一个与春节有关的仪式开始。
就如《小王子》中的狐狸所说:“比如说,你下午四点钟来,那么从三点钟起,我就开始感到幸福。时间越临近,我就越感到幸福。到了四点钟的时候,我就会坐立不安;我就会发现幸福的代价……”
我们对过年的期待,不正如此吗?(资料来源:《山东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