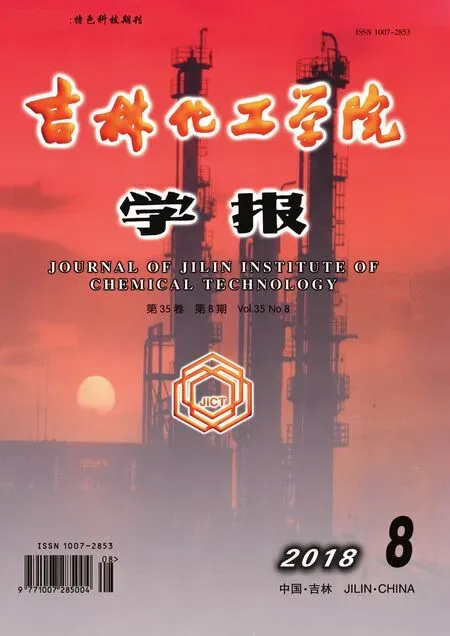明清易代与士人生计
2018-04-14李岸
李 岸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士人阶层是中国的创造,是传统封建社会一个颇为特殊的存在群体,其组成人员大部分是通过科举考试的文人学者。这种文人兼官僚的独特角色所构成的官僚群体发展至明代已经壮大且完善。在强盛富足的大明王朝的统治下,经历了明代君主颠覆性的统治,加之严酷吝啬的官僚制度的剥削,士人的政治热情逐渐被消磨。在大明王朝突如其来的灭亡后,他们最后一丝生存的希望被吞噬。习惯了大明衣冠的他们,在“乌托邦”式的太平盛世的幻想破灭后,身为士大夫的儒家伦理道德并不具有往日的十足效力,在现世感和现实性的压迫下,治生成为他们的首要任务。
一、易代背景下的士人处境
明清易代,士人的人生被截断,文人所谓的“学而优则仕”的政治理想分崩离析。整个士大夫阶层乃至预备的准士大夫阶层,此刻都统一的成为一个群体——遗民。士阶层所组成的遗民群体不同于农民白丁的混沌的生活,亦不同于商人巨贾的投机求生,他们的文化水平决定了他们的道德水平,而既有的道德认知又决定了他们的人生态度。这样的人生态度包括政治上的忠君爱国、生存上的舍生取义、经济上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等等。可以说这一时期遗民式的准士人阶层,他们应该坚定不移的站在既定的儒家传统道德价值立场上,自我主观意识上选择孤孑。
现实生活琐碎繁复,非伦理道德书本知识可囊括得了的。对于士大夫而言“遗民”身份是社会强迫他们的符号化认同。这一时期的士大夫是没有自己作为个体生命的身份认同的,同样更没有所谓的选择权利。遗民作为一个群体,被界定归类,成为一套概念,形成一种观念。士大夫阶层无论怎样选择怎样突破,他们的处境使他们作为遗民的身份被定了下来,清晰而鲜明。这种片面化凝固化的被迫的自我界说和诠释,是士大夫在易代之际对自身生存及历史处境的感知基础上的实现自我保存要求的一种表达方式。同时士大夫阶层并没有多少时间去伤春悲秋,失去既成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地位,士人的人生比普通人的人生更颠覆同时也更艰难。
二、流亡士人的治生选择
易代波折中的沉痛悲哀,使一些士人以自杀的方式抗拒,如陈子龙、夏完淳、夏允彝、张煌言等等;也不乏吴三桂、洪承畴、范文程等未等国破就入仕新朝之人。但大部分的士人面对易代不能入仕,为了生存,其选择自然不同。
(一) 教书与躬耕南亩
张履祥、朱舜水、陈确等人都曾先后论述过“学者以治生为本”的合理性。但在他们面对治生选择的时候都不约而同的先后选择了耕读这一途径。张履祥种菜养鸡鸭,章慥灌园养家。可耕读是明清易代之际士人反己求生的最通俗的途径。衣食无仰的士人只有自己和自然可以拥有进而得以生存。虽是无奈下的最优选择,但不免有为人所不齿的地方。《金华府志》中记载,易代之际的私塾讲师为生计所迫,收徒弟不看资质只看金钱。在明清交替的商品经济发展、重视经济的思想开化的时期,整个士人群体的选择变得更接近平民,不复之前的高贵典雅。必须承认的是长久以来乞讨般赌徒式生活是可悲可叹的现实,重财尚利,虽不可取,却也是无奈之举。
(二) 游幕与入仕为官
士人都不想放弃已经拥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转向另一个未知领域去求得生存。换句话说,如果条件允许,如果士人的情感洁癖没有那么严重,他们还是会选择士这个阶层去生活。明代大儒钱谦益、老一代遗民顾炎武,还有不算有名的阎尔梅等一批士人选择游幕与入仕为官。在当时这样的选择为很多人所不耻。士人在世俗生活中竟然放弃了身为士的品行,为了身份地位钱财富贵,以至于道德沦丧思想腐化。但这样的选择也使得圣道得以保存,士人关怀得以发扬。之中是非,不能一概而论。
(三) 润笔与弃儒从商
余英时在《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变》一文中指出:“到16世纪士人阶层与商人阶层的传统界限已变得非常模糊”,“此时期士人阶层与商人阶层彼此之间都已意识到自身的两个社会阶层已经出现了新的关系与联系”[1],这一时期的士人与商人关系可谓“士商互动”与“士商合流”。在这一阶段很多士人以为商人写墓表为兼职,还有士人将自己的字画拿出贩卖,有士人变卖收藏的书记古玩,更士人为了生计直接弃儒就贾。传统的四民思想、等级观念在此生死存亡之刻不再重要。士人观念的转变直接作用于文学,前代一直不受重视的、未被真实描写的商人形象变得多元丰满起来。主要因为此刻落魄的人生经历使得士人与人民群众离得更近,从而距离商人群体更近。
纵观中西,中国士人的不吝金钱大公无私的态度实属罕见,其直接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获取生存资本的途径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阶层、不同于其他体制下的同阶层群体。长久以来士人从来没有直接获得经济来源的方式,他们用他们的智慧才学“被养”。易代将他们变成遗民,没有了既定的生存基础只能提高生存能力。这样的乞讨般的赌徒式生活,在明清交替的商品经济发展、重视经济的思想开化的时期,整个士人群体的选择变得更接近平民。标志着晚明士人开始从传统的儒家道德传统观念中解脱出来,实现经济独立的他们为士人塑造了一个新的形象标准。
三、士人死与生的内心纠葛
(一) 义利之辩
士人是知识阶层变成政治共同体的新的角色身份。正是因为这样的文人特质,才使得士人的行为作事总是不免被其他社会阶层乃至后代的我们冠以迂腐的名称。易代之际士人的个人生活无法维系,士人的家族生活更是举步维艰。这一时期生存相较于士人气节似乎更为重要。陈确强调自立,身为士大夫的他甚至说道:“确尝以读书、治生为对,谓二者真学人之本事,而治生尤切于读书。”[2]穷困而无立锥之地的士人除了满腹四书五经之外根本谈不上所谓的尊严。如此看来此时的士人在生活现实的压迫下“不择手段”的治生是阶层限制的无可奈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明末清初众多思想家提出诸多关注个性、追求个人解放的思想,但身为文人士大夫的固有教诲仍是士人认识世界、判断世界的基础。无法改变的儒家伦理道德观首当其冲,舍生取义的教诲犹在,故士人在此阶段进退维谷。他们也要生,他们也要守住这个阶层的尊严。但不同于孟子的舍生取义之说,因为此刻的生死不是一瞬间的事情,而是一种颇具残酷意义的日常化状态。遂选择生的不能被批评成苟且,选择死的又有多少原因是士人的附会,其中意味几经曲折,无从辩解。
(二) 理欲互博
对于理欲这一概念的理解从明代就开始有所变化。在宋元之交,许衡率先提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进及作官谋利者,殆亦窘于生理所致。士君子当以务农为生,商贾虽逐末,果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3]明代泰州学派王艮提出了“身为天地万物之本”的尊身论,强调人赖以生存的物质需要的重要性。李贽更是离经叛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圣人不欲富贵未之有也。”[4]明代士人虽然俸禄极低待遇不好,但是明代士人对“物”的追求几近痴迷,奢华程度令人咂舌。《长物志》《遵生八笺》《随园菜单》等等一系列恋物成癖的总结性书目形成了这时期特有的文学作品——小品文。复杂繁多的物用庞大的数量不断重复质的品阶,体现着士大夫细腻的生活风格和骄傲的生活态度。他们在病态的物化中找寻万事万物本来的样子。
很多巨儒高官流连声色,把玩器物。他们不愿面对既成现实中的百孔千疮,从而逃避逐物,用自己的与传统礼制不相宜的行为,试图为这个乱世创造规则;看破虚妄,藐视一切束缚,体验人生,超脱世俗,追求自由自在。更多的人没有了牢靠的物质基础,生活变得艰难,甚至变卖家当以求自保以求生存。他们被迫换了一种逃避生活的方式,然而对于物仍旧是执着的。理欲的纠葛甚重,这样的欲的追逐是在理不可得的情况下产生的。相对应的基础理论是士人的心理安慰,是士人给自己的行为寻找的合理化借口。虽然对物的欲望是人性中的基本欲望,但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的大部分人还是有理的信念的,而后的种种,不过是生活带给他们的不得不去面对的现实而已。在这样复杂的纠葛中,士人向着未来更进了一步。
(三) 公私气节
士一词发展至这一时期有了新的社会意义。吴伟业认为治生才能行道,将私仁利益作为公共利益得以保障的基础。“学者以治生为急”取代了当时的“公私”“气节”之辩是当时易代士人的相对普遍的共同认识。“被养”的士人失去了经济维护,不可能再无忧无虑地将自己视为卫道士。从这一角度看,传统的“公私”“气节”同样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只不过这样的经济手段不可维系,政治手段更无从开展,无公家之明确概念,便只能先让私人个体生活下去了[5-7]。
易代波折对政治态度的考验,政治态度与价值立场的博弈,生活方式和理想信念的冲突,情感状态同生活方式的纠葛。不能否认的是传统儒家道德精神是士人自由生活的障碍。它控制着士人的躯体与意识,使士人呈现出被束缚的优雅。易代的士人精神的转变使之后的儒家道德精神开始具有新的看到人生的自由意义。在这一阶段儒家传统道德精神伴随着理论与实际生活的新的衍生具有近代性和现代精神。士人走下政治与道德的神坛,泯然如众人。他们经济观念逐步形成,与社会接触更多,文人小说戏剧等市民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更是丰富了中国文学,于他们悲喜参半,于我们利大于弊。
四、结 语
被贴上“遗民”标签的士人群体,其治生手段是被逼出来的个体选择,看似自由其实只是一种错觉。生是必然选择,治生手段的变化亦是无可奈何[8-10]。但士人的信仰让他们的心灵不得解脱。作为社会阶层划分中最上位的他们,有不同于农民商人的政治权利,就不能避免的需要承担与国同生同死、为君分担忧虑、为民出谋划策的相应义务。所以在那些看似光鲜亮丽的背后、在那些得以保全的生活中,他们暗自痛苦着、纠结着。纵然有那么多的“求生无错”的理论依据存在,那份士大夫的骄傲与荣光还是让他们无法彻底抛弃道统中所说的安贫乐道、重义轻利、君子固穷的传统。这样的士人在那个改朝换代的动荡混沌时空里,用尽了自己全部的力量,发出微微的光。他们是那个没落时代的最后的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