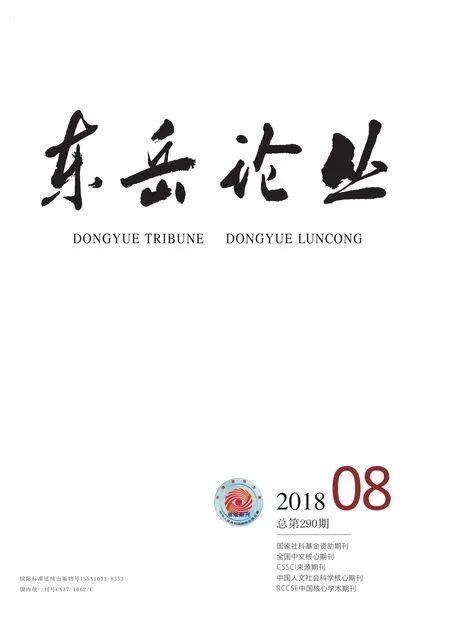中国古代书院的礼容之学与成人之道
2018-04-11肖永明
肖永明,李 江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要素,大至国家邦交,小至日用伦常,无不贯穿着礼的规制详节与精神追求。在先秦儒家典籍中保存着众多论礼、述礼之语,涵盖了礼容、礼器、礼制、礼意等方面。相较于外在形制与精神价值的研究,礼容之学尚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书院是中国古代文教的重要载体,对礼容之学的讲求尤为措意。中国古代书院将礼容之学在书院的开展视为变化诸生气质、涵养德性的关键环节,藉由礼容之学的落实来培养书院诸生的君子人格。本文试从儒家“成人之道”的角度讨论中国古代书院的礼容之学。
一、儒家礼容之学的历史渊源
礼容作为“礼”的重要内涵之一,源起甚早。《史记·殷本纪》记载周王伐纣胜利后“表商容之闾”,《史记索引》引郑玄云:“商家乐官知礼容,所以礼署称容台”①(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9页。。据此,裘锡圭先生指出在“商代便已经有掌容之官”②裘锡圭:《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7页。。又《中庸》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记正义》解释“三千”之数说:“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礼之别,其事委曲,条数繁广,故有三千也。非谓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别有三千条耳。”③(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裘锡圭先生认为“古代所谓威仪也就是礼容”④裘锡圭:《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7页。,据此可见古代礼容之学的繁琐。就礼容的节目而言,《周礼·地官》中已有详细的分别:“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正是因为礼容之学极其繁琐,所以针对不同的礼仪场合,设置有专门的人员对行礼者的礼容进行规范。如《周礼·秋官》载:“司仪掌九仪之宾客摈相之礼,以诏仪容、辞令、揖让之节”。司仪负责掌管接待邦国宾客的摈相之礼,其责任就是告诉周王接待宾客之时应有的仪容、辞令和揖让的节度。
孔子自幼好礼,深于礼学,对礼容也是十分熟悉。《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906页。。《论语·乡党》篇于夫子之容貌、举止、言语、服食皆有记述*朱熹认为《论语·乡党》篇“于圣人之容色声动,无不谨书而备录”。,就其中的相关记述可见孔子本人为了达到内在性情与外在容态的一致,在不同场合下的仪容仪态就不尽相同。孔子之视听言动、穿着饮食等无不随时间、场域以及交接对象的变化而不同,极其注重自己的仪容仪态,足证孔子对礼容的重视。孔子对礼容的态度,奠定了儒家学者注重礼容的传统,因此在儒家经典中对礼容有十分丰富的记载。如《礼记·玉藻》篇载“(君子)既服,习容,观玉声,乃出”。孔颖达疏解云:“既服,著朝服已竟也。服竟而私习仪容,又观容听己佩鸣,使玉声与行步相中适”*(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1页。,即是对行礼者的容貌与礼乐形制高度契合的强调。此外,诸如行步之法、动止之容、瞻视之仪等,在《礼记·玉藻》中都有详细的规定,足见儒家对礼容之学的关切。
到了汉代,礼容更是成为专门之学,一批学者因善容而为礼官,而且从中央到地方还设有一套专门的礼官系统。《汉书·儒林传》中记载:
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颂。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襄。襄,其资性善为颂,不能通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亦以颂为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恒生、单次皆为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诸言《礼》为颂者由徐氏。*(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4页,3615页。
颜师古注此段称:“颂,读与容同。”又引苏林曰:“《汉旧仪》有二郎为此颂貌威仪事有徐氏。徐氏后有张氏,不知经,但能盘辟为礼容。天下郡国有容史,皆诣鲁学之。”⑤(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4页,3615页。可知,徐生、徐襄及徐氏弟子等人虽不通经,却皆以“善颂”,即善为礼容而为礼官。据苏林所述亦可知当时地方郡国有“容史”,需到鲁地学习礼容,专司“颂貌威仪”之事。洪业曾将汉初礼学划分为三种形态:
礼学盖有三途。一曰,有汉朝廷之仪节;此叔孙通参杂古礼与秦仪论著也。一曰,鲁人颂貌威仪之礼容;此徐氏父子门徒之所以为礼官大夫者也。一曰,在孔子时已不具,迨秦火而益残之《礼经》;此高堂生之所能言,徐襄之所不能通,徐延之所颇能而未善之《士礼》也。*洪业:《仪礼引得序》,载《洪业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页。
换言之,汉初之礼学,有由叔孙通参酌古礼与秦仪而形成的“汉朝廷之仪节”、“鲁人颂貌威仪之礼容”以及高堂生所传授之《士礼》之学。而专门负责“颂貌威仪”的礼容之学已成为礼学重要内容,而且还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彭林教授就认为汉代重视礼容之学是因为“作为礼经的《仪礼》中,几乎没有关于颂的记述,传经时若无人示范,则学者无从知晓,仪节再全,而无容貌声气与之配合,则礼义顿失”*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0页。。礼容之学发展到汉代,内容更趋细化,汉初贾谊《新书》中有《容经》一篇,就礼容所涉及的具体节目而言,即有立容、坐容、行容、跘旋之容、跪容、拜容、伏容、坐车之容、立车之容、兵车之容等*参见(汉)贾谊著,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27-229页。,涵括个人生活的各方面。
两汉以降,儒者对礼容之学的探索亦不绝如缕,礼容之学融入儒者日常的修身、齐家等行为之中。阮籍曾著《咏怀诗》,其中一首为:“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魏)阮籍:《咏怀诗》,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08页。阮籍是“竹林七贤”之一,重“自然”而轻“名教”,据诗可见他对儒者在日常生活中遵守严格的礼容较为反感,但从反面亦能印证礼容之学在魏晋时期士人中的流传。此外,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中第六篇讲的是士大夫的“风操”,其开篇即言“吾观《礼经》,圣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皆有节文,亦为至矣”*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9页。,也谈到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都应该有相应的规范。值得注意的是,礼容之学在不断的发展中,已经不仅限于行礼时所需要的表情、举止、服饰,发展成为对儒者日常生活中言谈、举止、服饰、容貌的普遍性规范。同时,礼容也不再是为了达到行礼的目的而需要的辅助性手段,在宋明儒者的思想中,礼容之学具有涵养德性、培养君子人格、变化社会风气的作用。吕希哲就将辞令、容貌、举止视为初学之要,他说:“后生初学,且须理会气象,气象好时,百事是当;气象者,辞令容止、轻重疾徐,足以见之矣。”*(清)黄宗羲著,(清)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04页。朱子亦将举止、表情、言辞等的规范提到了“修身之要,为政之本”*(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4页。的高度。此外,宋代的诸多学者都将礼容之学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如程瑞蒙和董铢所作的《程董二先生学则》、真德秀的《西山真先生教子斋规》、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等无不涵括言语、容貌、举止等礼容之学的内容。
二、礼容之学在书院的具体展开
受到理学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的书院在其教育实践中十分重视礼容之学的开展。张栻在论述岳麓书院育人宗旨时曾说:“岂将使子群居族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宋)张栻:《张栻集》(三),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900页。书院的成人之道,不仅在于经典的研习、知识的传授,更在于书院诸生德性的养成,礼容之学便是涵养德性的关键环节。相应地,书院生徒若能不染俗流气习,动容周旋皆能中礼,即使才智有所不足,学业有所欠缺,亦远胜于人。如张思炯告诫玉潭书院生徒:“圣贤千言万语,均是教人做人的道理,非为博取功名计也……且书院为古庠序之地,一邑观望之所,入此者,非特伦纪宜修,即衣冠言动,亦必可象可仪,不染俗流气习,则虽文艺稍逊,已过人远矣。”*(清)张思炯:《玉潭书院切要四条》,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32页。基于这种理念,书院从言语、仪容服饰、举止等各方面制定了详细的规则。
(一)言语
“言”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概念,“言”不仅指话语本身,也指语言行为。孔子十分重视“言”,认为通过“言”可以“知人”,即通过对人言语内容以及说话时的动作、表情等的观察,能够探悉人内在品性的善恶*《论语·尧曰》篇将“言”与“命”、“礼”并举,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朱熹解释说通过“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而且,“言”还与人内在德性紧密相关,如孔子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渊》)。
书院教育实践秉承孔子的这种思想,注重生徒的“言语”教育。在说话的语气上,强调要和缓,切勿急躁。如诸多书院要求学生“忿词不出于口”*(明)方世敏:《瀛山书院学规》,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01页。,“致详审,重然诺,肃声气,勿轻,勿诞,勿戏谑喧哗”*(清)梁廷柟:《粤秀书院学规》,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3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在房读书,无事静坐,不得结队聚谈,高声肆叫”*(清)梁鼎芬:《端溪书院生徒住院章程》,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3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都是对书院生徒言谈语气的规范。要求书院诸生言语和缓,有助于处理书院诸生间的朋友关系。李来章认为“朋友居五伦之一,关系最重,必推诚以相与,致敬以相交,然后可收砥砺之益”*(清)李来章:《连山书院学规》,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3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页。。如果大家切磋讨论学术,不能平心静气,必定无法达到切磋学术的效果。李文炤对此深有所感,认为如果同辈交游之时“一言不合,怒气相加,岂复望其共相切磋”*(清)李文炤:《岳麓书院学规》,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第2册),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035页。。
在言谈的内容方面,书院的主事者痛陈滥言之失,如郑之侨认为:“口舌之祸,惨于刀锯”*(清)郑之侨:《辛酉劝诸生八则》,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1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页。。朱一深则告诫凝秀书院的学生:“易言之弊,起羞与戎,一言之玷,终身之辱,口舌之地,祸福之阶。”*(清)朱一深:《凝秀书院条约》,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2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页。当时书院存在“屠贩市侩、恶薄无赖之诙谐,公然出于学士大夫之口”*(清)边连宝:《桂岩书院学约八则》,《任邱县志》(卷11),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1541页。的现象也被书院主事者严加指责。相反,书院诸生应当做到言语朴实、谨慎,不得随意非议他人,更不得在闲谈中捕风捉影、无事生非。古代书院的学规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规定:“不得语及个人私事,不得语及闺门隐事,不得语及官员贤否及他人得失,不得语及朝廷公事及边报声闻”*(清)李颙:《关中书院学程》,《二曲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18页。,“痛戒讦短毁长”*(清)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36页。,“诐淫邪遁之辞勿出诸口”*(清)阎尧熙:《培英书院劝学十则》,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第1册),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6页。等。粤秀书院则将人的言语与地方风俗联系起来,告诫生徒:“若趾高气扬,筋骸放纵,或信口刻薄,喜造艳词,以及横议时事,既非载道之器,必为风俗之忧”,进而要求书院学生“勿及乡里人物长短及市井鄙俚无益之谈”*(清)梁廷柟:《粤秀书院学规》,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2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第17页。。
(二)容貌服饰
《论语·季氏》称:“君子有九思:……色思温,貌思恭。”邢昺疏解曰:“色思温者,言颜色不可严猛,当思温也。”*(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书院生徒若要养成君子人格,表情当以“温”为宜。后世书院大多要求书院学生“容貌必庄”,即表情应该以和蔼、庄重为主,做到“厉气不行于色,惰慢之容不设于身体”*(明)方世敏:《瀛山书院学规》,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01页。。吕祖谦强调容貌表情应该随着情景的差异而变化,他为丽泽书院所定学规就说:“会讲之容,端而肃;群居之容,和而庄。”*(宋)吕祖谦:《吕东莱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47页。粤秀书院则规定容貌“必端严凝重,勿轻易放肆,勿粗豪狠肆,勿轻有喜怒。”*(清)梁廷柟:《粤秀书院学规》,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2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第17页。窦克勤从人身内外关系出发,认为“端容貌所以坚德性也”,所以主张“学贵端容貌”。
就《论语·乡党》篇即可见孔子对于衣服的颜色、配饰以及在什么时节、场合穿什么衣服都有讲究。虽然,儒家并不讲究衣着华丽,却要求穿着要合时宜、得体。《大戴礼记·劝学》载:“孔子曰:‘鲤,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可见得体的服饰穿着的重要性。对此,古代的书院对生徒日常服饰也有诸多规定。如要求书院诸生服饰要朴素、不得衣着华丽。李颙在关中书院强调“立身以行俭为主,居家以勤俭为主”,“不可衣服华美”*(清)李颙:《关中书院学程》,《二曲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17页。。王文清要求岳麓书院诸生“服食宜从俭素”*(清)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36页,第436页。。此外,穿着还宜保持干净整洁,切勿衣着怪诞。粤秀书院在“衣冠必整”一条便指出“勿为诡异华靡,勿致垢敝简率,虽燕处不得裸袒,虽盛暑不去袜。”*(清)梁廷柟:《粤秀书院学规》,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2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梁鼎芬所作《端溪书院生徒住院章程》也要求“各生徒不得短衣赤足,群立房门。”*(清)梁鼎芬:《端溪书院生徒住院章程》,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3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陈寿祺《拟定鳌峰书院事宜》要求诸生“正衣冠”:“每逢课期,诸生务豫蚤齐集,各具衣冠,以俟点名领券,不得先后参差……点名时,不得科头短衣,拥挤至前。”*(清)陈寿祺:《拟定鳌峰书院事宜》,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第1册),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543页。黄舒昺在明道书院要求学生“衣冠带履,必检饬端庄”*(清)黄舒昺:《明道书院学规》,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6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页。。就众多书院学规来看,书院主事者大多要求学生衣着整洁,此类记述在书院学规中十分普遍。因为如果穿着不雅,和市井之徒就没什么区别了,而且还有损自身的德行修养。如李来章在《连山书院榜文》中告诫生徒说:“后进末学,习为轻佻,燕居袒裸,不着巾袜,彼此戏谑,以巧为胜,其于市井牙侩,不分毫厘,不但外观不雅,其于心术,放辟邪侈,荡无束检”*(清)李来章:《连山书院榜文》,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3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
(三)举止
除了上文所举的言语、容貌、服饰外,书院对诸生日常坐、立、行、视、听等举止动作亦有相应礼仪规矩。宋代程瑞蒙和董铢所作的《程董二先生学则》被朱熹称赞“有古人小学之遗意”*(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879页。,为后世书院所广泛采用。广东粤秀书院吸收其中的一些仪则来规范诸生行、坐、立等行为:“居有常处,序坐以齿。凡坐必直身正体,勿箕踞倾倚,交胫摇足。寝必后长者,既寝勿言,当昼勿寝。行必徐,立必拱,必后长者。勿背所尊,勿践门阈,勿跛倚。勿淫视,勿倾听。”*(元)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合肥: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3页,第9页。元人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教人如何坐、行、立、言、揖。此书被当时的国子监颁于郡邑学校,对书院、家塾等都有重要影响。江东书院等就吸收其中一些内容,作为教育书院诸生的学规。比如,坐应“定身端坐,齐脚敛手,毋得伏鞶靠背,偃仰倾侧。”行则应该“笼袖徐行,毋得掉背跳足。”立应该“拱手正身,毋得跛倚欹斜。”而作揖的时候应该“低头屈腰,出声收手,毋得轻率慢易”⑩(元)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合肥: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3页,第9页。。这些举手投足之间应有的仪节规范被书院主事者借鉴来教育书院学生。如李颙所定《关中书院学程》要求学生“行步须安详稳重,作揖须舒徐深圆。周中规,旋中距,坐如尸,立如钉。”*(清)李颙:《关中书院学程》,《二曲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17页。岳麓书院告诫诸生要“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清)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36页,第436页。。孙诒让在算学书院时,要求“学徒宜敛气凝神,端视静听,谨言审问,挺坐卓立,阔步徐行,切戒浮躁、疲恭二习”*(清)孙诒让:《算学书院学规》,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第1册),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440页。。明道书院的学规则要求书院诸生“拱手端坐,如泥塑然,凝神安寝,如龙蛰然;思毋或邪,防意如城;言毋或妄,守口如瓶。所以养于静。”*(清)黄舒昺:《明道书院学规》,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6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页。此外,对于书院祭祀、拜谒山长、师生相见、同学相见等也有详细的礼仪规范。书院对诸生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的要求,虽看似具体而琐细,却体现着儒家精神的核心理念。
三、书院讲求礼容之学的意义
在《周礼》《仪礼》《论语》等儒家经典中有许多关于礼容的记载。自孔子以来,礼容之学虽体现在儒者修身、齐家、治国的诸多细节方面,却俨然成为儒家成人之道、作圣之基。礼容之学更是受到了汉代以来儒者的高度关注,在后世落实到书院教育之中。中国古代书院的教育,以培养人才为目的,除了传授儒家经典外,更以涵养德性、变化气质为宗旨。书院对礼容之学的讲求与落实,不仅在于礼容之学对书院诸生德性的涵养、气质的变化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其学业也有实际的帮助。因此书院诸生的仪容仪态教育受到了书院主事者的高度关切,成为书院日常教育的重要部分。
儒家强调身心一体,主张内在德性与外在举止之间具有互为表里、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儒家主张一个人内在“质”的美恶决定了其外在表现的善恶;另一方面,又强调可以通过对外在身体的规范使自己符合具体的礼仪、道德规范,从而实现对德性的涵养。《大戴礼记·劝学》篇曰:“盖人有可知者焉:貌色声众有美焉,必有美质在其中者矣。貌色声众有恶焉,必有恶质在其中者矣。”即是说,外在“貌色声众”的善恶,是由人内在的“质”,即人的本性、本质所决定的;当人内有善良的德性,其外在的声色容貌必定也是善的。在原始儒家这里,不仅强调内在的“质”对外在容貌举止的规定性作用,同时也强调外在容貌、举止对内在德性所产生的能动作用。《礼记·乐记》称:“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553页,第2068页。既然内在德性的性质规定了一个人外在容貌、举止的善恶,同时外在举止、容貌又能对内在德性产生能动的作用,那么最完满的状态,即孔子时常所说的君子人格,就应该是一个人内在的德性与其外在的容貌、仪态相称,二者构成内外相符的关系。儒家这种身心一体、内外相交的思想,凸显了外在举止、仪容、言辞的重要性,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的举止符合德性,他才能算是德性圆满的人。同时,也肯定了通过对身体的外在规范以达到修养德性的可能性。孔颖达就认为:“德在于内,行接于外,内既有德,当须以德行之于外。”③(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553页,第2068页。因为德性内在于人,德行之于外就是人的各种表现。所以,通过对外在的身体仪容仪态的规范教育,能够起到涵养德性的作用。
原始儒家这种“内外相交”的思想在宋儒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尤其表现在“主敬”的修养工夫上。孟子曾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孟子认为,学问的根本宗旨在于将人放逸外驰的心收敛回来,主宰人身。朱子十分推崇孟子的为学之道,将孟子的“求放心”视为“为学第一义”*(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2页,第210页,第210页,第2851页,第2854页,第211页。。同时,朱子又在诸多场合将“敬”视为圣门第一义。他说:“敬字功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2页,第210页,第210页,第2851页,第2854页,第211页。实则,朱子的“主敬”功夫与孟子所谓“求放心”意义相通,二者具有紧密联系。朱子常将“敬”与“心”合起来说,认为:“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⑥(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2页,第210页,第210页,第2851页,第2854页,第211页。,“摄心只是敬”⑦(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2页,第210页,第210页,第2851页,第2854页,第211页。,“只是要收敛此心,莫要走作,走作便是不敬”⑧(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2页,第210页,第210页,第2851页,第2854页,第211页。。朱子的主敬功夫最终是要落归于心上,是如何让心能够安定的修养工夫。而主敬的功夫又必须落到具体的事上来说,是可以具体操作的,朱熹认为:“持敬之说,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齐严肃,严威严恪,动容貌,整思虑,正衣冠,尊瞻视,此等数语而实加工焉。”⑨(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2页,第210页,第210页,第2851页,第2854页,第211页。可见,在朱熹的思想中具有身体规范、主敬功夫、心性修养的由外到内的思想脉络。
历代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学者对礼容之学在涵养心性、变化气质过程中重要性的认识,对中国古代书院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书院非常强调外在仪容仪态对“求放心”“主敬”的作用。乾隆年间,李来章知广东连山县事,建书院,并亲自讲学。他在《连山书院榜文》中告诫诸生说:
正衣冠,尊瞻视,进退揖让,循循有礼,匪第饰为美观,正所以检束身心,使不外驰,且令父老子弟悚然起敬,环视叹美,有所则效,亦转移风化之一端……凡整齐于外者,皆是收敛此心,使不外驰,于学者最为切要。*(清)李来章:《连山书院榜文》,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3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
在李来章看来,人的服饰、表情、进退举止都符合礼的要求并非为了外在美观,其中所体现的是儒者由身及心的修养工夫,是通过礼的规范达到对身体的约束,藉由礼来改造人的自然性,促成儒者人格的成长。事实上,这种强调身心一体,通过外在仪容仪态的身体规范来达到对内在心性的修养是许多书院教育家共同的认识。如窦克勤在朱阳书院提倡:“端容貌所以坚德性也……此内外交符之道也。”*(清)窦克勤:《朱阳书院学规》,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6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39页。郑之侨亦认为:“衣冠者所以摄其心志也。衣冠不肃,心志之惰慢可知矣。”*(清)郑之侨:《壬戌示诸生十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1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页。
有的书院还直接把外在仪容仪态的“整齐严肃”与“敬”的修养功夫直接等同。如郑之侨《鹅湖书院学规》:“所谓敬者,亦止是整齐严肃,收其放心,使起居语默以及酬酢应事不失此主,一无适之本体。”*(清)郑之侨:《鹅湖书院学规》,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1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页。在这里,在整齐严肃、起居语默、酬酢应事的具体过程中收其放心,就是“主敬”的修养功夫。有的书院则将“敬”分为“内”与“外”两种,将整齐严肃视为“外敬”:“有内敬,凝定专一是也;有外敬,整齐严肃是也。”*(清)邵松元:《明道书院日程》,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6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69页。所谓的内敬是指心(内在精神)而言,而外敬则是针对日常的仪容仪态而言。在他们看来,仪容仪态的整齐严肃本身就是“主敬”的工夫。
书院强调儒生日常仪容仪态的教育,也直接针对当时学者存在的问题。当时的许多生徒“往往日读圣贤书,而立身行己不免流俗污下,与经书相背”*(清)沈起元:《娄东书院规条》,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第1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李来章在训诫连山书院生徒时说:“今之从事于学者,既患无出众之姿,然而稍有聪明才力者,便又不免失于轻佻,流于浮薄,狙诈而不实,傲忽而自满”*(清)李来章:《连山书院学规》,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3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页。。儒生一旦患上轻浮的弊病,自然影响学习效果,书院执教者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如余丽元所作《龙湖书院学规》首条就说:“轻佻者不足与任重,浮躁者必至于无成。倨傲之习,狂妄之情,稍有聪明,沾沾自喜,学问何由长进。故虽才美如周公,使骄且吝,亦不足观。”*(清)余丽元:《龙湖书院志》,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0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1页。古代书院对于学生流于轻浮甚为警觉,众多书院主事者都在所定学规中痛陈书院学生流于轻浮的弊病。边连宝在《桂岩书院学规》中就强调说:“学者气质病痛各殊,而轻浮二字则尤恶薄之甚者”*(清)边连宝:《桂岩书院学约八则》,《任邱县志》(卷11),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1531页。。因此,许多书院都试图通过日常的仪容仪态教育来矫正书院生徒流于轻浮的弊病。
在朱子看来,由外在仪容仪态到内在德性,再到为学,是一以贯之的。他认为“轻最害事,飞扬浮躁,所学安能坚固”*(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3页。。朱子的这种思想在书院主事者那里被反复申述,边连宝告诫桂岩书院学生:“盖轻则浮,浮则不入,纵聪明绝世,读尽五车书,终是门外汉,况心不到则眼不到,口亦不到,且欲成诵不能,况能入其阃而探其奥乎?”*(清)边连宝:《桂岩书院学约八则》,《任邱县志》(卷11),第1531页。祝廷芳在《兴贤书院条约》中也说:“士品以端重城悫为主,而轻浮放逸者勿取焉。每见读书之人恃才傲物,佻达成风,殊不知以涉虚华,必至逾闲荡检,纵令才高七步,亦有玷士林。”*(清)祝廷芳:《兴贤书院条约八则》,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第2册),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705页。而日常的仪容仪态教育则是矫正轻浮之弊的关键。黄式三就认为:“《经》戒不重,欲学者于言语、动作、衣冠、瞻视必以整齐严肃为要也。”*(清)黄式三:《论语后案》,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既然日常的言语、容貌、服饰、举止等关乎德性涵养与学业成就,以培养儒生的君子人格、传授知识,追求成人之道为目标的书院,自然应当将儒生的日常仪容仪态教育放在重要地位。
四、结 语
在先秦典籍中,关于礼容之学的记载非常丰富。自孔子开始,礼容之学就成为儒学的重要内容。此后,尽管礼容之学在历代的显隐程度不尽相同,但始终是儒者们修身、齐家、治国不可或缺的工夫。更多时候,礼容之学更是融入其日常生活之中,日用而不知,却起着涵养德性、化民成俗的作用。
杨儒宾先生指出“儒家所期待的教育,乃是培养一种内外交融、身心交摄、心气交流的机体性人格。”*杨儒宾:《儒家身体观》,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年版,第21页。这种人格得以可能的前提在于儒家强调“身心一体”,主张形(身)与心、外与内的统一。同时,这种人格的养成,还必须依赖于实践的修养工夫。而礼容之学强调通过对外在身体(言语、举止、仪容)的规范达到对内在心性的修养,就是这种工夫的最好体现。在此内外交涉的过程中,人的身体得到改造,不再是自然性的血肉的身体,而是道德性的、精神化的身体;其结果是人的自然属性得到克制,人格趋于圆满,道德流行其中。
传统书院教育强调“求道”与“求学”的统一,以“成人”为培养目标,而外在仪容仪态被视为“成人之道”的重要内容。基于这一认识,讲求礼容之学成为书院教育的必然选择。当代教育存在重视知识教育而忽视德性涵养的偏弊,关于仪容仪态的教育较少被纳入教育内容之中。这种状况,加剧了社会的粗鄙化,亟需加以矫治。在这方面,中国古代书院的礼容之学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与宝贵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