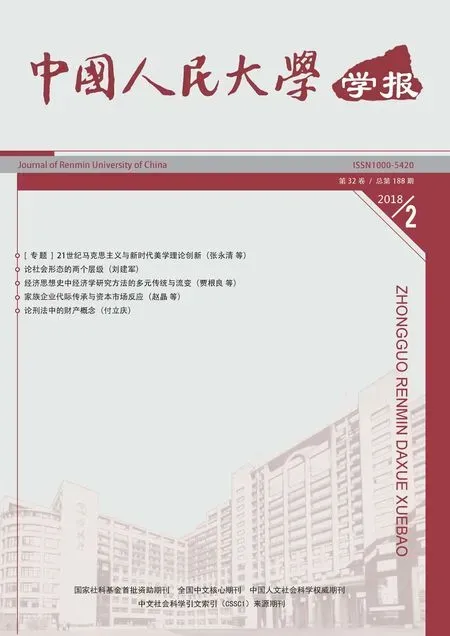经济思想史中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元传统与流变
——普利布拉姆《经济推理史》的创见和缺陷
2018-04-11贾根良何增平
贾根良 何增平
由于相对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熊彼特、米切尔等大家,普利布拉姆的名气要小得多,所以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他和这部作品作一个简要的介绍。卡尔·普利布拉姆1877年生于当时隶属于奥地利的布拉格。从学术渊源来看,普利布拉姆和奥地利学派关系密切。他在布拉格大学接受教育,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维塞尔是他的老师之一。后来,在维塞尔担任奥地利商务部长期间,普利布拉姆当了一段时间维塞尔的教务代理,负责给他代课。按照普利布拉姆的说法,他开始关注经济学方法论在经济理论当中的作用是受到了维塞尔、庞巴维克等人的影响。*普利布拉姆的研究范围涉及经济思想史、经济学方法论、社会政策、经济周期、卡特尔问题、经济统计等诸多领域。他不仅参加教学研究工作,而且还有在政府工作的经历。他参与建立了奥地利的社会保障体系。1933年,受到纳粹上台后欧洲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的影响,普利布拉姆决定接受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工作邀请,举家迁往美国。此后,他一直在美国生活并于1952年退休。退休之后,普利布拉姆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经济推理史》的写作当中。遗憾的是,在这部著作最终完成之前,普利布拉姆于1973年去世了。现在我们所见的这本书是由他的夫人编辑并最终于1983年出版的。

需要说明的是,普利布拉姆所说的推理模式这一概念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如归纳法、演绎法等具体的推理形式,但这一概念的外延要广泛得多,和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学方法论更加接近。由于这部著作篇幅非常大,所以它可能更适合作为经济思想史教学的参考书。对于想要了解这本书内容的普通研究者而言,普利布拉姆于1951年发表的论文《经济推理史的绪论》(Prolegomena to a History of Economic Reasoning)是很好的参考。这篇论文交代了这本书的基本观点,被收录到了这本书的附录当中。而对于想要充分理解普利布拉姆的经济思想史观的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参阅普利布拉姆于1949年发表的著作《对立中的思想模式》(ConflictingPatternsofThought)是很有必要的。尽管这部著作里的很多结论都有待商榷,但是对于全面理解普利布拉姆的思想,特别是理解《经济推理史》当中一些语焉不详的概念,这本书是必要的参考。
一、经济学推理模式与哲学社会思潮
将每一时期的经济学说的推理模式与该时该地出现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哲学思潮联系起来考察,是普利布拉姆《经济推理史》的第一个突出特点。这一点我们从他对不同类型的经济思想的命名中就可以看出来。普利布拉姆常常用与一种经济学说相关的哲学思想来为其命名,例如笛卡尔经济学(Cartesian economics)、培根经济学(Baconian economics)、效用主义经济学(utilitarian economics)。他认为各个历史时期所特有的哲学社会思潮决定了那个历史时期经济思想所采取的推理方法。“在经济分析的基本面上的纷争是由外在于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范围的因素引起的。这一纷争的最终原因可以从相互对立的思想潮流当中找到,这些思想潮流决定了西半球所有思想、社会、政治和道德活动的推理方法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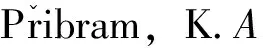
而对于重农学派来说,其哲学社会思潮背景则大有不同。普利布拉姆认为,当时在法国起码有六种不同的社会思潮在涌动,启蒙运动当中的百科全书派受到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而重农学派则更多地受到笛卡尔哲学的影响,所以,普利布拉姆将重农学派称为笛卡尔经济学。笛卡尔的哲学观点认为,唯有通过理性而非感性经验我们才能发现真理。与培根重视经验归纳不同,笛卡尔强调演绎推理特别是将数学作为获取真理的重要方法。按照普利布拉姆的解读,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观点就是这样一种通过理性反思得到的原理,而经济表则是采用演绎推理特别是数学方法的典型例子。
普利布拉姆的这种经济思想史观是他脑海中的一个更加宏大的历史观的一部分。按照这种历史观,不单是经济思想,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现象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的思想潮流以及思想潮流所决定的推理模式的影响。普利布拉姆的另一部著作《对立中的思想模式》就是这种观点的产物。在这本书中,普利布拉姆试图将美苏两大阵营以及纳粹极权主义在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差异都归结到推理模式的不同上。这部著作印证了保罗·西尔弗曼(Paul Silverman)对《经济推理史》的主题的评价:“这个主题是一个更加宏大的历史观的一部分,在其中思想是历史发展的基本的决定因素;当普利布拉姆将其应用到经济活动上时,这使得他认为思想模式的改变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要比制度变迁或者不同阶级的物质利益要大。事实上,他强调了思想上的转变使得制度结构转变成为可能。”*Silverman,P.“A History of Economic Reasoning Karl Pribram”.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989, 61(3): 557-558.显然,普利布拉姆这种将观念的转变作为社会形态变迁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值得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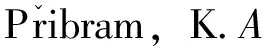
但是,如果回归到文本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尽管普利布拉姆确实试图去论证这样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经济思想史研究范围的命题,但是他的论证却不是那么一致的。一方面,他认为,尽管经济思想的内容会受到当时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但是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归根到底还是要追溯到推理模式的变化上。“于是,更广泛地说,社会经济组织和经济现象的基本观念都可以被看作是同样变量的函数,也就是推理方法的函数。”③并且,普利布拉姆坚持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我们认为这些推理模式的背后会再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就这样,人类主观思维模式的转变就被赋予了一个优先于其他客观经济社会因素的地位。如此一来,普利布拉姆就为他的历史观给出了一种逻辑上的论证。这一观点有着明显的奥地利学派主观主义的特点。但另一方面,这种逻辑在《经济推理史》中却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在更多的时候,普利布拉姆实际上是将经济思想中蕴含的推理模式作为一个单独的因素分离出来。他认为,经济学家们的推理模式是主要受当时流行的哲学社会思潮影响的产物,而这种推理模式的自身特点限制了经济学家们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按照这种思路的逻辑,哲学社会思潮并不能直接告诉经济学家研究的结论是什么,而是通过影响经济学家采取的推理模式来间接影响其经济思想的。但在方便的时候,他也不排斥用社会经济因素来解释经济思想当中出现的变化。
显然,这种经济思想史观是与很多流行的观点相对立的。比如,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当中关于哲学社会思潮对经济分析的影响评价不高。在论及亚当·缪勒和所谓的浪漫主义经济学的时候,熊彼特认为哲学和经济学“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它们在任何一处均无接触之点,没有一个世界能够告诉我们关于另一个世界的现象——或者不管应当使用什么字眼——的任何事情而不使它自己的论证归于无用”*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72页,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而在第三卷中,当他对讨论中涉及的社会思潮进行总结时,熊彼特断言:“究竟上述一切对于这个时期的主要经济学家具有什么意义呢?我可以非常有把握地回答说:意义是很小的——比在前两个时期的意义还要小(我们知道,在这两个时期中意义本来就不大)”*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对于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而言,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他花了大量的篇幅去论及每个时期出现过的种种社会思潮;另一方面,他则斩钉截铁地否认了这些社会思潮对经济分析的影响。对此熊彼特所做的辩解是有些模棱两可的。他区分了社会思潮对经济分析的影响和对经济学家本身“一般态度和眼界”的影响,认为后者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对前者来说,“没有哪一种哲学能够被证明在下述意义上影响了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家,即如果没有得到某一个哲学家的指导,他们就不能得出任何已经得出的某种分析上的结论,或者说他们之所以未能得出某种分析上的结论,是因为没有得到某一个哲学家的指导——除了在他们的方法论上的研究和争论以外”。参见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42-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如果我们愿意接受普利布拉姆的观点,那么我们可以说,熊彼特构造的“经济分析”这一概念远远不能涵盖经济思想史中出现的相互对立的多种推理模式。
这种忽视不同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存在的观点促成了辉格史观在经济思想史研究当中的大行其道。在忽视多元并存的相互对立的经济学推理模式的情况下,这种观点将某类经济理论及其方法作为评判过去经济思想的准绳,从而经济思想史就被处理成某一类理论获得胜利而其他种类的理论被淘汰的过程。这类被作为准绳的经济理论就自然成了历史的最终胜利者。这一历史观在历史学界早已受到了诸多批判,成了一个贬义词,然而在经济学界,萨缪尔森却将辉格史观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正确方法来倡导。*贾根良、贾子尧:《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辉格史方法及其争论》,载《学习与探索》,2016(1)。并且,按照辉格史观,经济思想史研究自然就只是一种出于历史的趣味性而存在的学科,因为既然最后的胜利者已经存在于教科书当中,那些陈旧的经济思想又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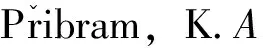
二、经济思想史中的两大推理模式:唯名论与本质主义
(一)两大推理模式的划分
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是普利布拉姆《经济推理史》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在一篇经济思想史的经典论文中,伊利亚斯·L·哈立勒(Elias L.Khalil)将普利布拉姆的《经济推理史》视为普遍主义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代表。这种普遍主义的方法论认为思想史上的“经济理论只是改变了其外观而保留了一个恒久的核心或者本质”*Khalil,E.L.“Has Economics Progressed? Rectilinear, Historicist, Universalist, and Evolutionary Historiographies”.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5, 27(1): 43-87.。这种核心或本质一般不是指某种具体的理论,而是指方法论层面的某种特征。对于普利布拉姆来说,这种方法论层面的核心问题就是唯名论(nominalism)和本质主义(essentialism,他有时也使用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一词)的对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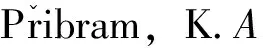
普利布拉姆的看法和波普尔的看法很相似(并且在我们后面将谈到的对历史决定论的诟病上,两者也有颇多相近之处)。波普尔是这样描述方法论上唯名论和本质主义(这里翻译为唯质论)的区别的:“方法论上的唯质主义者有意以‘什么是物质’、‘什么是力’或‘什么是正义’之类的词句概括科学问题;他们相信,对这类问题的深入的答案,就揭示出这些词句真正的或本质的意义,从而就揭示出它们所指的那些本质的真正的或真实的性质,——这至少是科学研究的必要前提,如果不是它的主要任务的话。与此相反,方法论上的唯名主义者则会以‘这个物质是怎样行动的’或‘它在其他物体的面前是怎样运动的’之类的词句提出他们的问题。因为方法论上的唯名主义者主张,科学的任务仅只是描述事物是怎样行动的;他们提出要完成这一点,只要需要,就可以随意引进新的术语,或者只要方便,就可以重新规定旧的术语的意义,而可以轻松愉快地忽略它们原来的意义。因为,他们把文字单纯看成是有用的描述工具。”*波珀:《历史主义的贫困》,6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7。
按照普利布拉姆的观点,如果将唯名论和本质主义视为经济学推理模式的两极,那么,经济思想史中的各种经济理论则处在这两极之间的不同位置上。极端的本质主义推理的代表是中世纪的经院式推理(Scholastic reasoning,由于托马斯·阿奎那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所以普利布拉姆称这种类型的经济学为托马斯经济学(Thomistic economics))。这种经济学试图按照上帝的意志来确定经济概念的本质,从而对各种经济现象做出符合教义的评判。例如,对于高利贷问题,这个时期的一种观点认为,由于钱的本质是人们用于交易的工具,钱作为工具本身是不能产生钱的,因而高利贷是不符合教义而要加以抨击的行为。而在经济学推理模式的两极的另一端,唯名论的代表则是经由边际主义和数学化的盛行在一战之后初步成型的假设经济学(hypothetical economics),它的推理方式被普利布拉姆称为假设推理。
普利布拉姆认为,长期以来经济思想史中就一直并存着多种经济学推理模式。它们依据和这两种对立观点的相近程度散落在这两极之间的区域中。在19世纪之后,则明显地出现了三种不同推理模式并存的局面:边际经济学为代表的假设推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书中称为辩证经济学,dialectic economics)为代表的辩证推理和德国历史学派(书中称为有机经济学,organismic economics)为代表的有机推理。普利布拉姆认为,在这三种推理模式当中,假设推理更接近于唯名论,而另外两种推理模式则更接近于本质主义。在历史上,这三种推理模式有着各自的发展脉络。
(二)唯名论推理模式的经济学
经济学向唯名论推理模式的转向在重商主义时期就开始了。普利布拉姆认为,早期重商主义时期是由经院式推理向唯名论式推理转向的时期。例如,这时期将财富的本质视为贵金属,以此作为指导国家政策的原则,这是典型的本质主义推理。但与此同时,一些重商主义者将一国贵金属的拥有量和贸易状况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唯名论式推理。
此后,两股思潮对唯名论推理模式的经济学影响重大。一是自然科学特别是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影响,它为唯名论者构建自己的经济系统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系。在这种系统当中,世界被划分为若干互不相关的独立系统,这些系统是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牛顿“将所有复杂的现象分解为一个共同点——原子——并假定这些原子(最终的不可分割的元素)之间的关系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这些规律是基于在绝对空间中这些惰性物体的相对位置的”*。同时,自然科学中的均衡观念和数学形式对唯名论推理模式的经济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按照普利布拉姆的观点,唯名论推理模式的经济学在李嘉图之后通过边际主义革命进一步去除了其中的本质主义成分。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经济学的进一步数学化,原本边际主义内部存在的分歧(特别是反对数学方法和均衡概念的“心理版本的边际主义”,也就是奥地利学派)被进一步消除。这时候成型的假设经济学是唯名论推理模式的代表。
(三)本质主义推理模式的经济学
普利布拉姆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采取的辩证推理和德国历史学派采取的有机推理是更加接近于本质主义推理模式的。但是,因为这些推理模式当中都有假设推理的因素在里面,所以不能把它们等同于中世纪的经院推理那样极端的本质主义推理模式。
与受到英国效用主义哲学影响的假设推理模式的经济学不同,早期德国历史学派较多地受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按照普利布拉姆的看法,这场哲学运动对德国历史学派的主要影响在于,“他们建议使用‘直觉’过程来分析社会现象,因为直觉过程使得观察者可以抓住统一的集体性的‘总体’的本质和机能。‘总体’虽然不能被直接感知到,但是可以被认为是外在于人类意识的实在之物”⑤。因此,普利布拉姆也称这种推理方法为直觉推理(intuitional reasoning)。而他之所以称这种推理方法为有机推理,是因为德国历史学派所考察的总体常常被类比为处在演化中的有机生命体。“按照这些准则,每个国家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它们的存在和发展是由自身的规律和目标决定的。这些规律的潜意识运作被认为会在一国的社会制度当中表现出来。”⑥这种对社会制度的关注同时也受到了当时法学思想的影响。施穆勒的研究纲领就是这种思想背景的产物。他力图在国家和社会具有特殊性的前提下,运用直觉推理的方式得到更高层次的抽象。这种推理方式很典型地体现在了历史学派的各种历史阶段论当中。国家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被认为能够通过直觉推理的方式把握到它的本质,虽然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一本质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德国历史学派最终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理论,很多时候这种做法停留在了对每一阶段的历史事实的陈述上,而没有深入下去。
后来,以维纳·桑巴特和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新新历史学派在继承历史学派传统的同时,还受到了当时新康德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普利布拉姆认为,这种哲学思想进一步强调了直觉推理的运用以及对制度和历史的关注。在美国,制度主义者受到了历史学派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实用主义哲学观念的影响。而随着纳粹的上台,这种推理模式的经济学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学派衰落了,而极权主义经济学产生了。有机推理在这时成了为极权主义统治辩护的工具。在纳粹意识形态当中,元首被认为是那个可以运用直觉获知国家和历史发展的本质的人,而国家中的一切要素就都需要按照这种意志各就其位。德意志民族被认为是有着高于其他民族的本质,于是这就为种族屠杀和所谓的扩张“生存空间”做了辩护。但是,德国历史学派与纳粹之间的联系是很复杂的。一方面,确实有一些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发挥想象力,用有机推理的方式为纳粹政权辩护。但另一方面,以施穆勒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却和极权主义保持着很大的距离。在纪念施穆勒百年诞辰的时候(1938年,也即纳粹上台五年后),一些历史学派的追随者站出来批驳当时存在的很多对历史学派方法的错误认识。其中哲学家埃里克·罗瑟克(Erich Rothaker)认为当时的很多说法都忽略了施穆勒方法当中的相对主义成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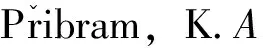
在《经济推理史》当中,马克思之后的辩证经济学占了很大篇幅。普利布拉姆认为,后来的辩证经济学很多都没有坚持马克思所采用的辩证推理的方法。他将此视为方法上的退化,马克思的辩证推理退化成类似于经院哲学式的推理方式,有些被用来服务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三、普利布拉姆对两大推理模式的评价与批判实在论的反思
(一)普利布拉姆对两大推理模式的评价

虽然在理论层面上普利布拉姆保持着中立,但是在实践层面或者说政治实践上,普利布拉姆的偏向是很明显的。在《对立中的思想模式》当中,他将唯名论的推理模式和西方“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而将本质主义的推理模式和纳粹极权主义以及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结合普利布拉姆的生平,他产生这种想法不足为奇。普利布拉姆在纳粹上台之后动乱的时局下生活过,他曾目睹受到极端思想蛊惑的青年学生焚毁书籍,曾经因学生暴动而受到死亡威胁,他因此举家逃往了美国。普利布拉姆做出这种论断的理由是:本质主义推理以及它常常采取的目的论式的论证意味着一种历史决定论,既然如此,所有人只需要按照元首的意志行动就可以了;唯名论的推理模式则从不试图寻求这种本质性的历史规律,并将概念视为人的主观创造,因而这些概念是可错的,这就使得没有人能对历史的结局轻易做出定论。
普利布拉姆的这个观点在逻辑上有颇多牵强之处。首先,可错性显然并不是唯名论的推理模式所独有的。历史学派的理论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样也是可错的。教条主义是任何推理模式的观点都可能犯的错误。其次,如果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有一个可行的判断真理的经验标准(例如波普尔提出的证伪)的话,那么,这已经偏离了这两种推理模式的内涵。换句话说,无论是本质主义还是唯名论,它们都不排斥经验观察的作用。最后,发现历史的本质规律不等于发现历史的结局。一种历史规律是否起作用取决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结局可能受到其他多种历史规律的影响;选择什么样的机制起作用还要受到人类主观意志的影响,这些都使得我们有理由认为本质主义推理试图发现历史规律的做法并不等同于历史决定论。更进一步的说明需要我们结合批判实在论,在接下来的内容中进行。
(二)批判实在论的反思:科学实践的本质与唯名论的误解
在1997年的一篇经典论文当中,安德鲁·谢尔(Andrew Sayer)对本质主义做出基于批判实在论的评价。*Sayer,A.“Essentialism, Social Constructionism, and Beyond”.The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 45(3): 453-487.他认为,本质这个概念是混杂的,本质既可以指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属性,又可以指事物当中蕴含的生成机制(generative property),这种生成机制与事物能够发生什么变化有关。例如,我们可以说水的本质是一氧化二氢(H2O)。这既是区别于其他物体的属性,也是其中蕴含的一种生成机制,比如水的本质意味着在某种情况下(比如通电)可能会分解为氢气和氧气。但是这两种本质是没有必要重合的。强的本质主义观点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一个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这是不必要的,这可能会引来种族主义等认识问题。而一种温和的本质主义则是可取的。这种观点认为不是任何的事物都有本质,而将本质视为事物当中蕴含的生成机制。这种温和的本质主义是和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相契合的。
如果我们回想普利布拉姆对本质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质疑,就会发现,人们之所以会将本质主义和历史决定论联系到一起,是因为人们错误地理解了因果规律。作为科学实践的研究对象,人们常常将因果规律当作经验层面的事件规则性,即“如果X,那么Y”的形式。然而,这种经验实在论的观点是无法理解科学实践的。在科学实践当中,科学家在实验室封闭系统下取得了某种事件规则性,也就是“在Z的条件下,如果X,那么Y”——这里Z指的是实验室控制隔断其他因素影响的条件。而到了实验室之外的开放系统当中,在条件Z无法保证的情况下,这种事件的规则性只有在少数极端条件下才能被观察到。但让经验实在论者感到奇怪的是,一般情况下人们会认为科学实践所发现的因果规律在开放系统中仍然发挥着作用。这说明,经验实在论将因果规律视为经验层面的事件规则性的观点是不能正确理解科学实践的。批判实在论认为,要理解科学实践活动,就必须将实在论引入到科学哲学的探讨当中。如果科学实践是可理解的,那么因果规律就不能是一种事件规则性,而应当是一种实在层面的机制、结构、趋势。实验室活动的目的在于以人为干预的方式控制其他趋势的影响,从而使得某些趋势的作用显现出来。而到了实验室之外的开放系统当中,不同的趋势在共同发挥作用,而具体哪些趋势在发挥作用则要取决于具体的条件。
按照这种对因果规律的重新认识,“通向决定论有四重障碍。首先,因果力量——比如生孩子的能力——是否存在依赖于具体情况下可能出现的特定结构或物体。第二,这些力量是否发挥作用是依情况而异的,而不是前定的。第三,是否以及什么时候它们发挥作用,这些结果依赖于和其他可能有关的现象之间的调和——或者说中和。第四种可能是,自然的或者社会的因果力量本身(并不只是说是否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发挥作用)是可以改变的”*Sayer, A.“Essentialism, Social Constructionism, and Beyond”.The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 45(3): 453-487.。
这时,如果回到前面关于本质主义的探讨中,我们会发现温和的本质主义观点与批判实在论是一致的,它们同样将因果规律视为实在层面的机制、结构、趋势。由于错误地理解了因果规律,普利布拉姆错误地将本质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画上了等号,这使得他在政治立场上更加偏向于唯名论的推理模式。但问题是,如果将唯名论视为本质主义的对立面,如果将唯名论视为否定一切本质的存在,就会产生由唯名论滑向相对主义的可能。这使得唯名论意味着科学实践当中产生的对规律的认识都是由人类主观生成的联系,而与客观实在没有关系。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就会难以理解人类社会所有的科学实践,难以理解这些科学实践所取得的成功。而且,按照这种观点,估计差不多所有这个名目下的经济学家都不会同意自己是唯名论者,都不会同意自己的实践没有在寻找因果规律。
然而,出于其他的理由,他们仍然可能成为唯名论的支持者。尽管唯名论名下的经济学家可能都不会同意自己的实践没有在寻找因果规律,但是他们可能会赞同要反对历史决定论;并且他们可能更会赞同没有什么本质主义者所说的社会关系、组织制度、主权国家、人类社会的本质,而只有孤立的个人和这些个人相互之间产生的联系,由此,这些经济学家们就有可能成为唯名论的拥护者。
但事实上,这种做法已经事先假定了人类社会在实在层面的结构、趋势、规律都是如同原子之间的机械关系,到头来只是用一种原子论形式的本质主义取代了一种本可以更加开放且更加现实的本质主义。因此,唯名论与其说是那些经济思想的推理模式的本质,不如说是一种它们共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于,它阻止了追随它的经济学家从实在层面来认识自身实践。这种意识形态使得这种情况成为可能: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这种推理模式的经济学在实在层面上被赋予了某种先天的假定,而这种先天的假定的存在就注定了这种推理模式的经济学被束缚在自设的狭隘范围内。
按照托尼·劳森(Tony Lawson)的观点,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当中类似的状况是由数学演绎主义带来的:“显然在回溯过程当中,可供选择的范围会受到假设前提和达成(数学上)可处理的目标的严格限制。”*Lawson, T.Reorienting Economics. London &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03, p.25.劳森认为,主流经济学在实在层面上的假定是原子论的和孤立的,而这种假定受到了数学演绎主义的鼓动。托尼·劳森考察的主要是现代背景下主流经济学的不现实的实在论假定。而在《经济推理史》当中,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的,普利布拉姆同样看到了这种推理模式具有原子论和孤立的特点,但他所展示出来的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当中,经济学的推理模式一方面受到了它所沿袭的理论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了当时哲学社会思潮的影响,在其中经典物理学和效用主义哲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如果说劳森是在进行横向的病理切片分析的话,那么普利布拉姆的工作则更像是在进行寻根溯源的历史学透析,尽管他所提出的唯名论的说法是有误导性的。
四、批评和总结

类似的问题还发生在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上。尽管普利布拉姆考察了诸如琼·罗宾逊、卡莱斯基等早期后凯恩斯主义者,但他还是将凯恩斯的思想视为假设推理模式的经济学的一次拓展,并且在他看来,凯恩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学发展的影响远不及数学方法以及动态化方法的影响。但事实上,经由保罗·戴维森、海曼·明斯基等后凯恩斯主义者的不断努力,后凯恩斯主义形成了与假设经济学反差强烈的方法论特点。他们强调人类社会的开放性和动态性,强调历史与根本的不确定性,这些与基于封闭系统的假设经济学是相对立的。*参见马国旺、贾根良:《后凯恩斯经济学70年——批判、重建与综合》,载《国外社会科学》,2005(2);贾根良、马国旺:《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新发展》,载《教学与研究》,2004, 38(9)。
《经济推理史》当中争议最大的问题是它对德国历史学派的认识。我们在前文已经说明:本质主义推理方式与历史决定论、法西斯极权主义统治没有必然联系。就具体史实来看,我们必须承认存在着一些继承了历史学派传统的经济学家和纳粹走得很近,甚至在当时出现了这样的声音:德国社会学家利奥波德·冯·维泽(Leopold von Wiese)在为施穆勒一百周年诞辰发表的纪念文章中,认为施穆勒会认可纳粹上台后德国的政治形势的变化。*Reheis, F.“The Just State: Observations on Gustav von Schmoller’s Political Theor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1989, 17(9/10/11):48-70.但事实上,尽管施穆勒强调国家干预,他的观点却与极权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按照近年来西方学者对施穆勒思想的重新挖掘,以施穆勒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赞成的是一种辅助原则(subsidiary principle),即国家干预只有在私人部门不能够有效运行的时候采用。*Prisching, M.“The Preserving and Reforming State: Schmoller’s and Wagner’s Model of the State”.In: Backhaus, J.G.(ed.).Essays on Social Security and Taxation: Gustav von Schmoller and Adolph Wagner Reconsidered. Marburg: Metropolis-Verlag, 1997,pp.173-201.他们对政府失灵有着清醒的认识。例如,施穆勒曾列举了三种政府失灵的问题:国家可能滥用自身权利做出违背公众利益的事情;官僚主义可能会盛行,从而政府机构臃肿,办事成本高昂;公权力可能会与经济利益挂钩,滋生垄断势力。*Powers, C.H., and K.H.Schmidt.“Justice, Social Welfare, and the State in the Eyes of Gustav von Schmoller”.In: Backhaus, J.G.(ed.).Essays on Social Security and Taxation: Gustav von Schmoller and Adolph Wagner Reconsidered. Marburg: Metropolis-Verlag, 1997,pp.239-258.施穆勒说:“我们不要求任何领导人,像一个人类的全能之神那样,应该控制、比较、检验和估测万民的品质和业绩,并以此来公平地分配收入。……国家总是可以通过改善社会制度的方式来主导实现一个更加公平的收入。……他们的智慧和正义感可以提升和改革制度,但是不能取代它们的位置。”*同时,历史学派内部的政治观点也是不统一的,例如施穆勒是偏向保守的中间派,布伦塔诺是怀疑国家干预,主张市场自由的激进派,瓦格纳则是偏向于国家干预的保守派。
同时,就具体的研究方法而言,施穆勒的方法也不是历史决定论的。我们需要结合施穆勒的伦理观念来探讨这一问题。一方面,施穆勒认为道德因素是决定人的行为的重要因素,它会受到现存的制度道德状况和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对它的研究需要结合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施穆勒认为,虽然现存的制度和道德规范为人的行为提供了可以预测的选择空间,但是人的道德意识不只是单纯地遵循现存的制度和道德,它还可以进一步去追求超出现实的道德目标,并且以此来改变现存的制度环境。这构成了施穆勒的演化观念的一大特色。他说:“把我们指引至此并且使得我们从其中产生正义感的观念绝不简单。一方面是法律规定的特殊性质,它是指导社会互动的确定的正式规则;另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的理想目标,它决定了法律的实质内容,这两者共同决定了这个概念。”*Schmoller, G.“The Idea of Justice in Political Economy”.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894, 4(5): 1-41.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盐野谷佑一(Yuichi Shionoya)指出的,目的论的论证方式不是对某种意识形态的辩护,而是基于整体论的视角进行的对社会变迁的前景的考察。*Shionoya, Y.The Soul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Boston: Springer Science+ Business Media, 2005,p.7.经济思想史学界普遍认为,施穆勒并没有完成他所设想的研究计划,他的《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只是他庞大的研究计划的阶段性成果,本身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体系,其所开创的研究传统还有待后人的进一步开拓和完善。
尽管《经济推理史》在史实和历史观上还有颇多值得商榷之处,但是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局限性带来的,我们不应过于苛求。例如,要等到20世纪90年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施穆勒复兴”潮流的出现,施穆勒的思想才被挖掘和重新认识。总体上说,普利布拉姆在其中展现出的渊博学识和独到见解使得这部著作无愧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典之作的美誉。这部著作将经济思想史上各种经济思想置于一个广阔的哲学社会思潮背景当中进行考察,这种研究方法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普利布拉姆不拘泥于只是陈述过去的经济思想,而是力图通过他独到的方法加深我们对不同经济思想所具有的独特思想背景的认识。在普利布拉姆描绘的经济思想史的整体图景中,辉格史观所构想的线性累积的发展道路是子虚乌有的;不同的哲学社会思潮塑造了截然不同的经济学方法论传统,以任何一种理论及其方法作为标尺的做法都可能会歪曲经济思想史的本来面貌。
《经济推理史》在梳理哲学社会思潮与经济学推理模式的关系的基础上,试图去探讨在经济学推理模式中的,也就是方法论中的某些核心因素。这种尝试正是哈立勒所强调的普遍主义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意义所在。普利布拉姆将方法论的核心问题视为唯名论和本质主义之间的矛盾,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唯名论的说法具有误导性。与其说它是一种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本质,不如说是一种令人迷信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使得经济学研究者在方法论层面放弃了对实在的探求,放弃了走向相对数学演绎主义而言更加开放、更加现实的实在论的可能性。但是,普利布拉姆的考察仍然有启发性。他的研究突显了经济思想史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重要作用。作为科学实践的一种,经济学研究有其独特的发展历史和实践的特殊性,因此对其方法论的研究不能脱离经济思想史,否则就可能成为空中楼阁。普利布拉姆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进一步认识现代经济学在方法论问题上的分歧,从而为经济学范式的变革提供历史经验和理论支持。因此,普利布拉姆的《经济推理史》是我们振兴经济思想史学科、推进经济思想史史学理论研究的有益参考。